《底特律不是某種抽象藝術項目》 - 彭博社
bloomberg
 路透社底特律現在是 美國最大的失去自治權的城市。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破產的市政府將無法控制自己的財政,這要歸功於密歇根州州長裏克·斯奈德上週決定將該市置於緊急管理之下。然而,與此同時,底特律卻很火——至少,如果你閲讀主要的美國報紙或關注文化博客,你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印象。在2011年,洛杉磯時報似乎與許多人產生共鳴,當它對汽車城的轉型進行了評估,稱其為 “藝術家的避風港。” NPR的一段節目問道,“底特律是下一個布魯克林嗎?” 就在城市的市中心似乎準備復甦之際,它卻失去了參與和控制其重生的能力。
路透社底特律現在是 美國最大的失去自治權的城市。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破產的市政府將無法控制自己的財政,這要歸功於密歇根州州長裏克·斯奈德上週決定將該市置於緊急管理之下。然而,與此同時,底特律卻很火——至少,如果你閲讀主要的美國報紙或關注文化博客,你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印象。在2011年,洛杉磯時報似乎與許多人產生共鳴,當它對汽車城的轉型進行了評估,稱其為 “藝術家的避風港。” NPR的一段節目問道,“底特律是下一個布魯克林嗎?” 就在城市的市中心似乎準備復甦之際,它卻失去了參與和控制其重生的能力。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貝爾法斯特的中央車站為北愛爾蘭的公共交通創造了新時代芝加哥應該考慮所有預算危機的解決方案,普利茲克説消除美國道路死亡的月球計劃AOC提議300億美元的社會住房管理局底特律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神話般的城市,某種程度上是美國的隱喻。到1950年代,它象徵着美國夢、工業的力量以及我們對汽車的痴迷文化。它催生了一個藍領中產階級,幫助誕生了一種新的政治秩序:所謂的“新政秩序”的城市自由主義。然後,在1960年代末,它象徵着種族衝突、騷亂和同樣城市主義的侷限性。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底特律已成為城市衰敗的典型城市。在短短50年的時間裏,它經歷了美國城市的整個生命週期,包括興起與衰落。在1990年代中期,有一段時間,許多人開始懷疑底特律所發生的事情是否會很快,或不可避免地,發生在大多數美國城市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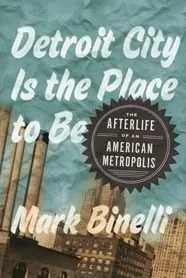 比內利深入城市,講述那些留下來並紮根的人們的故事。他的書是關於那些普通人,他們通過生活自己的生活,正在為拯救城市而努力工作。他發現,底特律的街道和社區確實發生着創造性和非凡的事情。與此同時,他強調,所有對這些新城市先鋒、那些不斷被描繪為城市救世主的潮人、藝術家和企業家的關注,忽視了什麼是真實的,以及什麼最有可能拯救城市——如果有什麼可以拯救的話。底特律很大,其問題同樣龐大。而沒有一小羣藝術家能夠單獨完成這一切。
比內利深入城市,講述那些留下來並紮根的人們的故事。他的書是關於那些普通人,他們通過生活自己的生活,正在為拯救城市而努力工作。他發現,底特律的街道和社區確實發生着創造性和非凡的事情。與此同時,他強調,所有對這些新城市先鋒、那些不斷被描繪為城市救世主的潮人、藝術家和企業家的關注,忽視了什麼是真實的,以及什麼最有可能拯救城市——如果有什麼可以拯救的話。底特律很大,其問題同樣龐大。而沒有一小羣藝術家能夠單獨完成這一切。
作為一個以黑人為主的城市,底特律如何復興,如果它真的復興的話,將會是一個黑人故事,Binelli 認為。因此,他跟隨一羣致力於當地黑人活動家和社區組織的核心成員,這些人很少成為國家新聞故事的主題。舉一個場景,Binelli 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擁擠的房間,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底特律是如何被外界定義的。在某個時刻,一位發言者懇求人羣:“我們不會讓紐約市的記者來這裏定義我們!”隨即,當地活動家 Marsha Cusic,她是黑人,也是 Binelli 的主要角色之一,站起來對幾乎全是白人的人羣説:“我不想冒犯任何人,但當你們談論‘我們’需要奪回這座城市時,我看着這個房間,不確定你們所説的‘我們’指的是誰。”後來,Cusic 告訴 Binelli:“底特律不是某種抽象的藝術項目……它是為真實的人而存在。”
最終,Binelli 發現,在金融破產和對白人新來者的憤世嫉俗中,底特律仍然有很多像 Cusic 這樣的人在努力尋找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Cusic 是傳奇底特律唱片店老闆 Joe Von Battle 的女兒,她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她沒有放棄這座城市,認識到它的過去,並致力於教育它的現在。Binelli 關注像底特律 Blight Busters 這樣的組織,以及那些無名的團體,他們救助流浪狗,種植花園,並在空蕩蕩的商店窗户裏放置杯子蛋糕。他與傳奇民權領袖和最近出版的 The Next American Revolution: Sustainable Activ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的作者 Grace Lee Boggs 共度時光。這位95歲的革命者和她在 Boggs 中心的追隨者們為下一代社區活動家創造了資源和榜樣。底特律的未來將依賴於 Boggs 和 Cusic 將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以實現未來所需的活力和創造力。而 Boggs 和 Cusic 所走的道路突然變得更加坎坷。
頂部圖像:一座24英尺長的鑄銅手臂和拳頭紀念碑,紀念拳擊手喬·路易斯,懸掛在底特律市中心的傑斐遜大道與伍德沃德交匯處的平衡懸掛裝置上。(瑞貝卡·庫克/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