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的摩,1968年,美國警察國家的發明 - 彭博社
bloomberg
 這是一張由巴爾的摩市警察局在1968年4月的民事騷亂期間拍攝的照片。詹姆斯·V·凱利/蘭斯代爾圖書館特別收藏許多人回顧巴爾的摩1968年聖周起義,以理解本週困擾該市的衝突。但今天的事件與那一年的民事動亂關係不大,更與建立在其廢墟上的全國性法治運動有關。
這是一張由巴爾的摩市警察局在1968年4月的民事騷亂期間拍攝的照片。詹姆斯·V·凱利/蘭斯代爾圖書館特別收藏許多人回顧巴爾的摩1968年聖周起義,以理解本週困擾該市的衝突。但今天的事件與那一年的民事動亂關係不大,更與建立在其廢墟上的全國性法治運動有關。
在20世紀偉大的黑人遷移北上過程中,巨大的經濟和政治變化改變了美國城市。結果既有民事動亂,也有對其的保守反彈。在巴爾的摩,起義及其主要批評者,馬里蘭州州長斯皮羅·阿格紐,永遠改變了美國政治。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一位藝術家重新構想童年的空間,結果卻充滿荊棘房地產開發商納夫塔利在邁阿密海灘尋找交易,推動佛羅里達發展美國的駕駛和擁堵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牙成為全球首個禁止石油和航空旅行廣告的城市黑人起義在1960年代中後期席捲美國北部城市。巴爾的摩的起義規模巨大:超過一萬名馬里蘭國民警衞隊和聯邦軍隊被派往該市,以平息1968年4月6日爆發的騷亂,這距離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槍殺僅兩天。令人震驚的是,超過5000人被逮捕(大多數因違反宵禁),並且在幾乎每個主要黑人社區都造成了1200萬美元的損失。詹姆斯·布朗的音樂會部分因市民中心成為拘留區而被取消。
在馬里蘭州,斯皮羅·阿格紐擔任州長的反應對全國保守派政治至關重要。破碎的窗户和防暴警察,當時和現在一樣,可以通過觀看電視報道推測出來。許多人當時看不見的,今天仍然模糊不清的是更深層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全國範圍內的暴動出現在一個背景下,即偉大社會改革和電視上展示的富裕所承諾的希望與日益加深的城市邊緣化相對抗。
“非裔美國人感受到了這一點,”凱斯西儲大學的歷史學家和社會正義研究所主任朗達·Y·威廉姆斯説。“他們也在抵抗。他們正在參與抗議。”
在20世紀中葉,美國城市經歷了一場重大的人口革命,黑人美國人從吉姆·克勞南部遷移,聯邦政府補貼了僅限白人的郊區發展,而曾經對黑人有希望的工業城市經濟(儘管將他們限制在最低工資的工作中)則遷移到了其他地方。
巴爾的摩的白人人口在20世紀後半葉急劇下降。與此同時,城市中黑人所佔的比例迅速上升。
與此同時,郊區的巴爾的摩縣見證了人口的爆炸性增長,從1950年的不到250,000人增加到1970年的600,000人,其中580,000人是白人,約克學院的歷史學家彼得·B·萊維説。在城市中,白人社區迅速變成了黑人社區,一個深度隔離的都市,分開且不平等,誕生了。
“在‘68年,巴爾的摩顯得極其種族隔離,”萊維説。“而郊區的‘縣幾乎全是白人。”今天,“它仍然是一個相當隔離的城市,”儘管巴爾的摩縣變得更加多樣化。根據萊維的説法,在1968年,黑人居民被迫住在破舊的房屋中,接受低標準的教育,某些市中心地區的失業率接近30%。政策制定者並沒有忽視,貧民區的條件助長了1967年席捲底特律和紐瓦克的巨大騷亂。
“種族隔離和貧困在種族貧民區創造了一個對大多數白人美國人來説完全陌生的破壞性環境,”國家民事騷亂諮詢委員會在其1968年關於城市動盪的關鍵研究中寫道,這項研究被稱為《凱爾納報告》。“白人美國人從未完全理解,但黑人永遠無法忘記的是——白人社會與貧民區有着深刻的關係。白人機構創造了它,白人機構維持着它,白人社會對此表示默許。”
與許多南方城市不同,巴爾的摩接受了正式的學校整合,並擁有眾多黑人公職人員。其警察部隊實際上因在追求對黑人居民的進步方法方面處於前沿而受到讚譽。但巴爾的摩,像北方大都市一樣,很快陷入了一種新的美國種族隔離形式,這種形式基於嚴格的市界限。這並不像站在學校門口那麼戲劇化。但其影響同樣是災難性的。
“通過法律、房地產、銀行實踐的技術或工具,以及聯邦和地方政策,種族隔離在巴爾的摩得以維持,並受到保護,”威廉姆斯説,她在關於巴爾的摩的書中探討了這些問題,公共住房的政治:黑人女性對城市不平等的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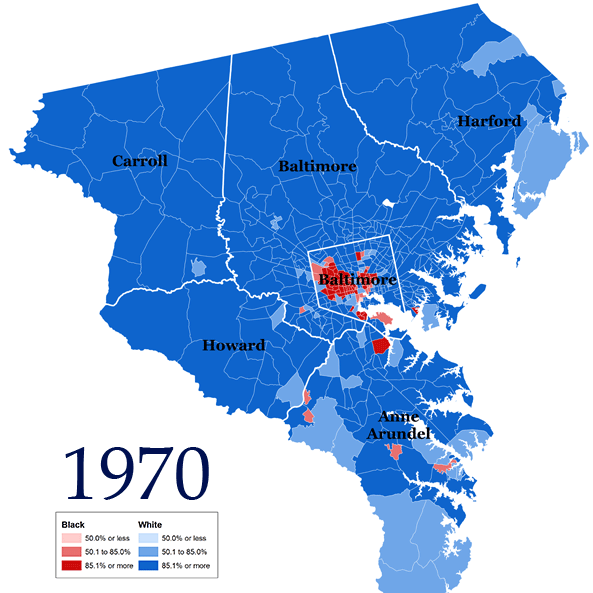 表面上是事實上的隔離,但在其真正基礎上是法律上的:政府住房和經濟政策。
表面上是事實上的隔離,但在其真正基礎上是法律上的:政府住房和經濟政策。
“吉姆·克勞在南方以其方式存在,吉姆·克勞在北方以其方式存在,”威廉姆斯説,她是西巴爾的摩的本地人。“我們是一個邊界城市。”
四十七年後,黑人總統、黑人市長的選舉以及繁忙的內港的經濟活力並沒有改變巴爾的摩貧困黑人社區許多人的基本生活事實。美國夢與貧民窟現實之間的尖鋭矛盾依然存在。
凱爾納報告在1968年巴爾的摩暴動前僅發佈了五週。
“1967年的夏天再次給美國城市帶來了種族騷亂,並給國家帶來了震驚、恐懼和困惑,”委員會寫道。“美國總統成立了這個委員會,並指示我們回答三個基本問題: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可以做些什麼來防止它再次發生?這是我們的基本結論:我們的國家正朝着兩個社會發展,一個是黑人,一個是白人——分開且不平等。”
凱爾納報告是自由主義建立的最後一次偉大努力,陷入日益增長的經濟矛盾和越南戰爭中,試圖在不斷上升的保守政治潮流淹沒之前解決日益嚴重的城市危機。但在金恩被刺殺後,巴爾的摩不僅爆發了更多的騷亂,華盛頓特區、芝加哥和匹茲堡也相繼發生。馬里蘭州的反應,斯皮羅·阿格紐擔任州長時,將對全國的保守政治產生關鍵影響。
最初,阿格紐州長對騷亂的反應相對温和。但他很快領導了一場保守的反擊,指責激進的煽動者(這應該聽起來很熟悉)和自由主義滋養了黑人不當行為。阿格紐向右轉的時機正值騷亂平息之際,4月11日,他會見了該州的主流黑人領導人,並指責他們懷有“扭曲的種族忠誠觀念”,這“激怒了”激進分子。他説,巴爾的摩的火焰並不是“出於壓倒性的挫敗感和絕望”,而是“在暴力倡導者的建議和指導下點燃的”,像斯托克利·卡邁克爾。
阿格紐在一份值得閲讀的聲明中全文,對黑人領導人進行了講解,稱“民權運動的目標在情感的過度簡化中被模糊”,認為“某種程度上,平等機會的目標已被瞬時經濟平等的目標所取代。”阿格紐,這位曾經的温和洛克菲勒共和黨人,將他對巴爾的摩騷亂的批評轉化為全國聲望,並在理查德·尼克松的領導下擔任副總統。
“阿格紐在'68年之前算是一個温和派,”萊維説,他已經進行了廣泛的寫作,涉及到起義和法律與秩序的政治反彈。實際上,“他最初是戰勝白人至上主義者當選州長的。”但他對騷亂的反應“將他推向了”全國舞台。“這引起了尼克松和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的注意。他得到了許多保守派的極為積極的反應。”
布坎南實際上最近寫道,“阿格紐對在大規模暴力面前沉默的民權領袖們宣讀騷亂法令……是尼克松選擇他作為副總統的一個主要因素。”
實際上,自由派建立了相對温和的對巴爾的摩起義的反應。在1967年騷亂之後,聯邦政府制定了新的“應對城市騷亂的詳細程序,”萊維寫道,包括“派遣部隊,命令他們不得裝填武器,並且要避免射擊搶劫者。”在巴爾的摩有六人死亡,而1965年在沃茨有34人遇難,1967年在底特律有43人遇難。根據萊維的説法,生命損失較少,主要是因為約翰遜政府的剋制反應。
但是阿格紐與保守派聯合抨擊《凱爾納報告》,稱其將“責任歸咎於除了實施者以外的每一個人”,並且“對白人種族主義的自虐式集體罪惡感滲透了報告推理的每一個方面。”他説,騷亂的一個更可能的“間接原因”是“違法行為已成為一種社會可接受且偶爾時尚的抗議形式。”(他還批評了“那些……從甘地那裏借鑑戰術、從課堂上獲取哲學、從父親那裏獲取資金的學生的虐待專制。”)
阿格紐在當選州長之前擔任巴爾的摩縣的執行官,成為了典型的新右派郊區人士。事實上,按照萊維的説法,他是全國首位高調的郊區政治家。阿格紐是尼克松的攻擊犬,捍衞尼克松沉默的大多數的理想,反對街頭的喧鬧少數派,並在他所認為的縱容黑人和學生抗議者的女性化自由主義面前,倡導一種保守的男子氣概。對於許多郊區選民來説,他提供了一個比狂熱的喬治·華萊士更為冷靜的選擇。
 馬里蘭國民警衞隊部隊回應巴爾的摩1968年的暴動。詹姆斯·V·凱利/蘭斯代爾圖書館特別收藏“阿格紐通過打破與公開捍衞吉姆·克勞的關聯,幫助合法化了白人反彈,並將其表述為強調秩序、個人責任以及辛勤工作、核心家庭和法律神聖性的語言,”萊維寫道。
馬里蘭國民警衞隊部隊回應巴爾的摩1968年的暴動。詹姆斯·V·凱利/蘭斯代爾圖書館特別收藏“阿格紐通過打破與公開捍衞吉姆·克勞的關聯,幫助合法化了白人反彈,並將其表述為強調秩序、個人責任以及辛勤工作、核心家庭和法律神聖性的語言,”萊維寫道。
阿格紐自辭職和失寵以來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正如萊維所見。但在理解新右派和20世紀末法律與秩序政治的過程中,阿格紐和巴爾的摩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騷亂或起義,常常在當下被誤解。但它們最具毒性的誤表述可能是在事後。1960年代的騷亂被普遍紀念為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使美國城市陷入衰退。但實際上,起義大多是結果而非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業和不平等隔離的結果。(即使是語言也不是中立的,正如你此時可能猜到的那樣:學者和活動家尋求強調城市混亂的政治和經濟維度長期以來使用“起義”這個詞而不是“騷亂”。
自1960年代以來,警務和監獄(當然還有軍隊)逐漸成為政府的定義特徵。今天也是如此,隨着全國各地的黑人抗議者反抗從1960年代末的廢墟中崛起的美國警察國家。這並不是在誇張的意義上,執法和司法在一個對法治漠不關心的永久例外狀態下運作(儘管它們確實常常如此)。相反,美國人生活在一個警察國家,因為自1960年代以來,警務和監獄(當然還有軍隊)逐漸成為政府的定義特徵。大規模監禁,使如此多的黑人男性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已成為美國居住隔離的一個字面延伸。
“這只是證明人們應該一開始就聽從凱爾納委員會的建議,而不是發起毒品戰爭和犯罪戰爭,”萊維説。
在尼克松和阿格紐將法治作為美國政治的核心,並將白人郊區居民和南方人視為其關鍵選民後,兩黨的建制派開始將城市危機和生活在其中的邊緣化黑人視為一個更好被忽視或鎖在監獄裏的問題。“這怎麼會發生?”一位年輕的國民警衞隊員在1968年警察執法巴爾的摩燃燒的街道時問道,萊維引用了他的話。某種程度上,沃爾夫·布利策這一週一直在問同樣的問題。種族隔離使一些問題在被忽視之前變得不可見,直到它們燃燒得太亮,無法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