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地區的朝聖者 - 彭博社》
bloomberg
 國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馬克·伯恩斯/城市實驗室我為在芝加哥的一週輕裝上陣,完全打算帶着同樣輕便的隨身行李回到拉瓜迪亞。但我卻不得不在兩個時區的兩個公共交通系統中掙扎,揹着一個鼓脹的揹包和一個明顯更重的行李箱,甚至得坐上去才能關上。我還得同時 juggle 一個笨重的紙板海報管和一個裝在拉鍊不太好使的軟袋裏的音樂會尺寸的共鳴烏克麗麗。
國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馬克·伯恩斯/城市實驗室我為在芝加哥的一週輕裝上陣,完全打算帶着同樣輕便的隨身行李回到拉瓜迪亞。但我卻不得不在兩個時區的兩個公共交通系統中掙扎,揹着一個鼓脹的揹包和一個明顯更重的行李箱,甚至得坐上去才能關上。我還得同時 juggle 一個笨重的紙板海報管和一個裝在拉鍊不太好使的軟袋裏的音樂會尺寸的共鳴烏克麗麗。
我在芝加哥生活了大約12年,從大學迎新到2014年秋季,當時我為了工作搬到了布魯克林。從我在阿巴拉契亞俄亥俄州的家鄉來到芝加哥,我擔心在這樣一個大城市裏再也聽不到安靜。我擔心我會討厭它的平坦。相反,我發現冬天讓我有了 bragging rights,而為了夏天的榮耀,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學會了如何找到我的人和我的去處。我學會了我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而其中一部分就是學會何時嘗試新事物。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對於租户來説,人工智能驅動的篩選可能成為住房的新障礙高盛測試傢俱銷售商Wayfair的債務需求新澤西-紐約市通勤者在最新的交通混亂中被困在公交車和火車上在創紀錄的炎熱夏季之後,空調強制令的壓力加大但我不打算讓東海岸改變我:我帶着一件“中西部最好”的T恤、來自最喜歡的地方的杯子和心愛的場館的演出海報來到了我的新公寓。
然後我遠離了芝加哥。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裏,我無法忍受回到我如此熱愛的地方的想法。當我終於裝飾我的公寓時,只有一幅小小的商品市場藝術印刷品掛在我的牆上。我想,如果我把太多芝加哥的視覺元素放在眼前,我會後悔離開。
 當然,你的舊家不會那麼容易消失。康尼島很不錯,但我想念密歇根湖。我找不到合適的漢堡、合適的啤酒、合適的比薩。在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大都會博物館,我為我失去的藝術學院會員資格感到悲傷。即使我心愛的即興莎士比亞公司在曼哈頓演出,他們的演出費用是兩倍,時長卻只有一半。
當然,你的舊家不會那麼容易消失。康尼島很不錯,但我想念密歇根湖。我找不到合適的漢堡、合適的啤酒、合適的比薩。在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大都會博物館,我為我失去的藝術學院會員資格感到悲傷。即使我心愛的即興莎士比亞公司在曼哈頓演出,他們的演出費用是兩倍,時長卻只有一半。
徹底戒掉芝加哥並沒有奏效。搬回去也不在計劃之中。但我終於在上個月讓自己去了一趟。即使是從奧黑爾機場跑道遠遠看到的西爾斯(是的,西爾斯)大廈也讓我淚水奪眶而出。身處我的城市——火車上的廣播聽起來是那麼熟悉,而我常去的中餐館老闆在我走進門時緊緊擁抱我——讓我感到無比恢復。然而,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依然存在:我現在在紐約付房租。我必須在我的一週結束後離開。
解決方案一半是聰明才智,一半是囤積本能。在 超市掃貨的偉大傳統中,我填滿了我的購物車。如果上面有芝加哥的旗幟、芝加哥的社區、市政符號或當地標誌,我就買下它。我買了帶有紅色六角星的激光切割木耳環。我買了帶有我舊區號(773!)和棕線站(達門!)的磁鐵。我買了一個旗幟補丁,準備縫在我肩包上的布魯克林工業標籤上。我買了宣稱“我寧願在芝加哥!”的徽章。我沮喪地抵制了超大復古地圖重印、手工製作的芝加哥旗幟切菜板、WPA風格的旅遊陷阱海報。我在我最喜歡的獨立書店和漫畫店買了太多書,並保留了購物袋、收據和書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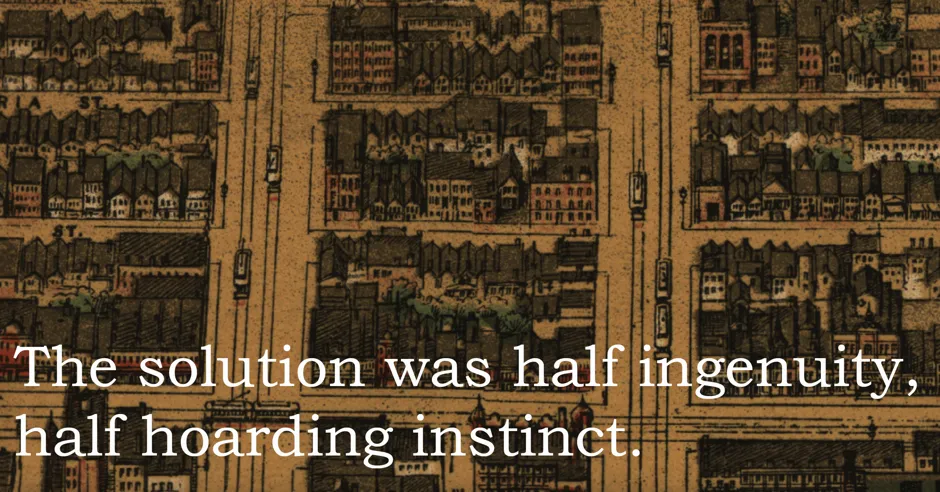 我的芝加哥是一個有限的、特權的和被改造的地方。我知道這是一個複雜的地方,就像它的地方自豪感一樣。儘管如此,這似乎是恆定的:芝加哥人喜歡來自芝加哥。他們喜歡在那兒生活,也喜歡離開時的感覺。當我在其他地方佩戴我的星星耳環、Half Acre T恤或精緻的黃銅旗幟項鍊時,我在等待另一個芝加哥人來完成一個秘密握手。你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得到一幅帝國大廈的批量印刷畫布。我不知道有哪個紐約人穿紐約的東西。芝加哥有一種廣泛採用的視覺語言,但芝加哥人是 解讀它的人。居民們認同這種圖標。它仍然是我們的。
我的芝加哥是一個有限的、特權的和被改造的地方。我知道這是一個複雜的地方,就像它的地方自豪感一樣。儘管如此,這似乎是恆定的:芝加哥人喜歡來自芝加哥。他們喜歡在那兒生活,也喜歡離開時的感覺。當我在其他地方佩戴我的星星耳環、Half Acre T恤或精緻的黃銅旗幟項鍊時,我在等待另一個芝加哥人來完成一個秘密握手。你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得到一幅帝國大廈的批量印刷畫布。我不知道有哪個紐約人穿紐約的東西。芝加哥有一種廣泛採用的視覺語言,但芝加哥人是 解讀它的人。居民們認同這種圖標。它仍然是我們的。
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我們更重視體驗而不是物品。這正是“我得到的只是這件糟糕的T恤”的全部意義。然而,在我訪問的中途,我站在老城民謠音樂學校的一面樂器牆前。我一直在告訴每個人,無論是陌生人還是朋友,關於我自從搬走後第一次回來的事,以及我想再次做所有事情。我想知道一切是否仍然存在。一位員工微笑着給了我一些乙烯基標誌貼紙。我無法將目光從這把尤克里裏上移開。
它是桃花心木的,比我那把小初學者的高音尤克里裏更重、更大。琴身底部有一個美麗的穿孔金屬板,帶有小提琴般的f孔,頸部鑲嵌着閃亮的鮑魚。它在我手中感覺很好。我買我的第一把尤克里裏是因為它能讓任何東西, 甚至 哈姆雷特,聽起來快樂。這把則講述了我不同的故事。在芝加哥,有一個我想成為的人,他創作音樂和藝術,跳林迪舞,參加即興表演團隊。等我作為客人回來時,很多這些都已經被拋在了一邊。難怪我對回去如此猶豫。
芝加哥開啓了我可以成為的樣子。你可以向前走,而不必拋棄你所愛的事物。那些東西並不是經歷,也不是自我認知。但尤克里裏如此便攜,這是一件好事。從這個意義上説,城市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