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弗羅裏達與新的城市危機 - 彭博社
Richard Flori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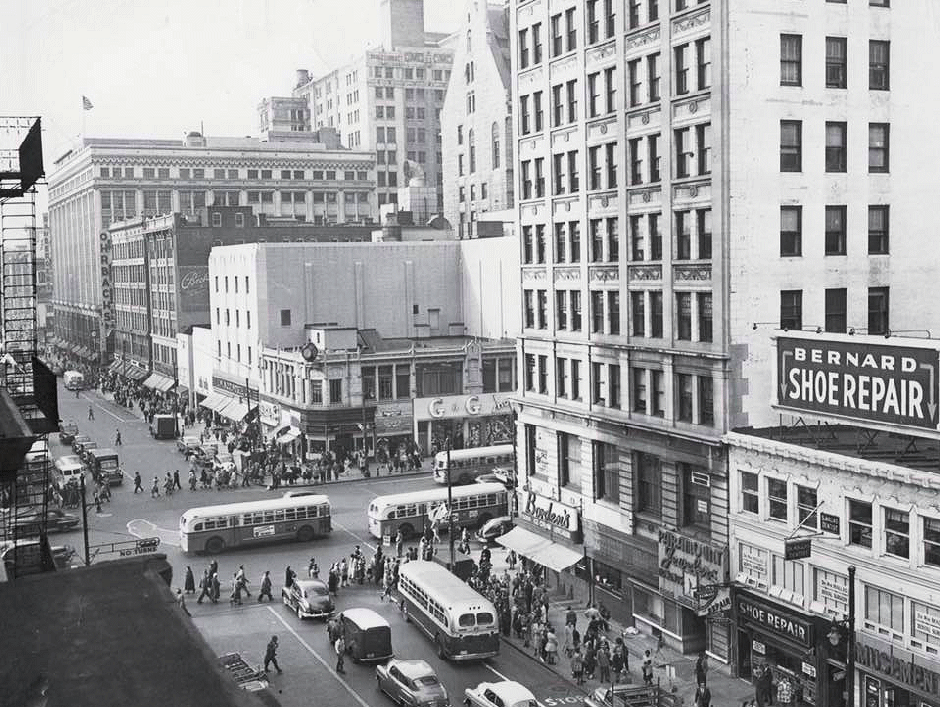 布羅德和市場街,紐瓦克,新澤西州,大約1960年代公共領域/OldNewark.com城市似乎深深印在我的DNA中。我於1957年出生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那時它是一個繁榮的城市,熙熙攘攘,有標誌性的百貨商店、早晚報紙、圖書館和博物館、繁忙的市中心以及龐大的中產階級。我的父母和其他數百萬美國人一樣,在我還是個幼兒時搬到了郊區。他們選擇了距離紐瓦克大約十五分鐘車程的小鎮北阿靈頓。他們這樣做,正如他們常常提醒我的那樣,是因為這個小鎮提供了良好的學校,特別是他們認為能為我和我兄弟準備大學的天主教學校——和平女王學校,這讓我們走上了更好的生活道路。儘管我們已經搬出了紐瓦克,但我們仍然在大多數星期天回到老鄰居,和我的祖母及仍然住在那裏的一家人一起享用豐盛的意大利晚餐。
布羅德和市場街,紐瓦克,新澤西州,大約1960年代公共領域/OldNewark.com城市似乎深深印在我的DNA中。我於1957年出生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那時它是一個繁榮的城市,熙熙攘攘,有標誌性的百貨商店、早晚報紙、圖書館和博物館、繁忙的市中心以及龐大的中產階級。我的父母和其他數百萬美國人一樣,在我還是個幼兒時搬到了郊區。他們選擇了距離紐瓦克大約十五分鐘車程的小鎮北阿靈頓。他們這樣做,正如他們常常提醒我的那樣,是因為這個小鎮提供了良好的學校,特別是他們認為能為我和我兄弟準備大學的天主教學校——和平女王學校,這讓我們走上了更好的生活道路。儘管我們已經搬出了紐瓦克,但我們仍然在大多數星期天回到老鄰居,和我的祖母及仍然住在那裏的一家人一起享用豐盛的意大利晚餐。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美國人如何投票導致住房危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轉學生提供專門建造的校園住所熊隊首席警告芝加哥沒有新NFL體育場的風險羅馬可能開始對特雷維噴泉收取入場費然後,在1967年一個炎熱的七月天,當我九歲時,我看到城市被動盪所吞沒。當我的父親開車帶我們進入城市時,空氣中瀰漫着濃煙:紐瓦克被其臭名昭著的騷亂所吞沒,警察、國民警衞隊和軍用車輛在街道上排成一列。最終,一名警察攔下我們,警告我們有“狙擊手”。當我的父親焦急地掉頭時,他指示我趴在地板上以確保安全。
 後果:1968年3月7日,新澤西州紐瓦克的斯普林菲爾德大道,騷亂爆發一年後。約翰·杜裏卡/AP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但我目睹了後來被稱為“城市危機”的展開。中產階級和工作崗位紛紛逃離像紐瓦克這樣的城市,轉向郊區,導致城市經濟空心化。到我在1970年代初進入高中時,紐瓦克的大部分地區已成為經濟衰退、犯罪和暴力上升以及種族集中貧困的受害者。我畢業的那一年,1975年,紐約市瀕臨破產。不久之後,我父親的工廠永遠關閉,使他和數百人失業。希望、繁榮和美國夢已轉移到郊區。
後果:1968年3月7日,新澤西州紐瓦克的斯普林菲爾德大道,騷亂爆發一年後。約翰·杜裏卡/AP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但我目睹了後來被稱為“城市危機”的展開。中產階級和工作崗位紛紛逃離像紐瓦克這樣的城市,轉向郊區,導致城市經濟空心化。到我在1970年代初進入高中時,紐瓦克的大部分地區已成為經濟衰退、犯罪和暴力上升以及種族集中貧困的受害者。我畢業的那一年,1975年,紐約市瀕臨破產。不久之後,我父親的工廠永遠關閉,使他和數百人失業。希望、繁榮和美國夢已轉移到郊區。
當我那個秋天去拉德格斯大學時,我發現自己被關於城市及其種族、貧困、城市衰退和工業衰退問題的課程所吸引。當我大二時,我的城市地理教授羅伯特·萊克給我們佈置了一個任務,讓我們遊覽下曼哈頓並記錄我們所見。我被正在進行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城市變化所吸引,尤其是在索霍、東村及周邊地區,被街道和生活在那裏的藝術家、音樂家、設計師和作家的活力所迷住。舊工業倉庫和工廠正在轉變為工作室和居住空間。朋克、新浪潮和説唱音樂正在為該地區的音樂場所和俱樂部注入活力——這正是後來成為全面城市復興的第一縷嫩芽。
但正是在匹茲堡,我在卡內基梅隆大學(CMU)教授了近二十年,我開始理清影響美國城市的主要因素。匹茲堡因去工業化而遭受重創,失去了數十萬人和大量高薪工廠工作。根據既定的經濟發展智慧,匹茲堡的領導者試圖通過提供税收減免和類似的激勵措施來吸引公司;他們投入資金建設補貼的工業和辦公園區;他們建造了一個現代化的會議中心和兩個閃亮的體育場。
 從杜肯山俯瞰匹茲堡Dllu/Wikimedia Commons由於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醫療中心和企業研發單位,以及主要的慈善機構,這座城市能夠抵禦最糟糕的情況。其領導者正在努力改變城市的發展軌跡。然而,儘管匹茲堡擁有前沿的研究和創新潛力,但該地區的大學人才並沒有留在這裏;我的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同事以及我自己的學生紛紛前往硅谷、西雅圖和奧斯汀等高科技中心。當互聯網先鋒Lycos突然宣佈將從匹茲堡遷往波士頓時,我腦海中似乎閃過一個念頭。
從杜肯山俯瞰匹茲堡Dllu/Wikimedia Commons由於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醫療中心和企業研發單位,以及主要的慈善機構,這座城市能夠抵禦最糟糕的情況。其領導者正在努力改變城市的發展軌跡。然而,儘管匹茲堡擁有前沿的研究和創新潛力,但該地區的大學人才並沒有留在這裏;我的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同事以及我自己的學生紛紛前往硅谷、西雅圖和奧斯汀等高科技中心。當互聯網先鋒Lycos突然宣佈將從匹茲堡遷往波士頓時,我腦海中似乎閃過一個念頭。
我在2002年的書中論證,創造階層的崛起*,*城市成功的關鍵在於吸引和留住人才,而不僅僅是吸引公司。構成創造階層的知識工作者、技術人員、藝術家和其他文化創意者正在選擇那些擁有大量高薪工作或厚實勞動市場的地方。他們還擁有我所稱的厚實交配市場——可以見面和約會的其他人——以及充滿活力的生活品質,擁有優秀的餐廳和咖啡館、音樂場景以及豐富的活動。
我發現自己面對曾經倡導的城市復興的黑暗面。隨着時間的推移,我的工作在市長、藝術和文化領袖、城市規劃者,甚至一些開明的房地產開發商中產生了相當大的追隨者,他們在尋找更好的方式來促進社區的城市發展。但我的信息也在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引發了反彈。一些保守派質疑我所描繪的多樣性與城市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繫,反駁説推動經濟發展的不是創意階層,而是公司和工作。其他人,主要是左派,指責創意階層和我個人,認為一切從租金上漲和城市更新到貧富差距擴大都是我們的錯。儘管一些更個人的攻擊讓我感到刺痛,但這種批評以我從未預料到的方式激發了我的思考,使我重新構建了關於城市及其所受影響力量的想法。
慢慢地,我對城市的理解開始演變。我意識到,我曾過於樂觀地認為城市和創意階層可以單靠自己帶來更好和更包容的城市主義。即使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經歷最大復興的城市中,貧富差距也在急劇擴大。隨着科技人員、專業人士和富人湧入城市核心,處於不利地位的工人和服務階層成員,以及一些藝術家和音樂家,正被迫退出。在紐約的蘇荷,我作為學生觀察到的藝術和創意的激盪正讓位於一種新的富人、高檔餐廳和奢侈商店的同質化。
 2015年,索霍歷史區的春街。模糊圖像/flickr我進入了一個重新思考和內省的時期,個人和智力的轉變。我開始看到迴歸城市運動是將其好處不成比例地賦予少數地方和人羣的事情。我發現自己面對着曾經倡導和慶祝的城市復興的黑暗面。
2015年,索霍歷史區的春街。模糊圖像/flickr我進入了一個重新思考和內省的時期,個人和智力的轉變。我開始看到迴歸城市運動是將其好處不成比例地賦予少數地方和人羣的事情。我發現自己面對着曾經倡導和慶祝的城市復興的黑暗面。
當我仔細研究數據時,我看到只有有限數量的城市和大都市地區,也許只有幾十個,真正能夠在知識經濟中取得成功;更多的城市未能跟上步伐或進一步落後。數千萬美國人仍然被困在持續的貧困中。幾乎所有城市都面臨着日益擴大的經濟差距。隨着中產階級及其社區的消退,我們的地理正在分裂成小塊富裕和集中優勢的地區,以及更大面積的貧困和集中劣勢的地區。
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人才和經濟資產的同樣聚集產生了一種不平衡、不平等的城市主義,其中相對少數的超級城市及其內部的少數精英社區受益,而許多其他地方則停滯不前或落後。最終,推動我們城市和經濟廣泛增長的同一力量也產生了將我們分開的差距和阻礙我們前進的矛盾。
如果像多倫多這樣進步、多元和繁榮的城市都可能遭受民粹主義的反彈,那麼這種情況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我對城市和城市主義的看法也深受我在收養的家鄉多倫多所看到的事情的影響。我在2007年搬到那裏,負責多倫多大學一個新的城市繁榮研究所。對我來説,這座城市是進步城市主義最好的堡壘。多倫多擁有北美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多樣化人口;一個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幾乎沒有受到影響的繁榮經濟;安全的街道、優秀的公立學校和緊密的社會結構。然而,不知為何,這座進步而多元的城市選擇了羅布·福特作為市長。
雖然他的個人缺陷和功能失調可能讓他贏得了福特國的支持者,但在我看來,他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反城市的市長。一旦當選,福特就開始拆除幾乎所有城市主義者認為構成偉大城市的東西。他拆除了自行車道,並制定計劃將城市市中心湖濱的一段黃金地帶改造成一個華麗的購物中心,配有一個巨大的摩天輪。
 2009年的多倫多湖濱:原本很好。Wladyslaw/flickr福特的崛起是城市日益擴大的階級分化的產物。隨着多倫多曾經龐大的中產階級的衰退和舊中產階級社區的消失,這座城市正在分裂為一小部分富裕、受過教育的地區,集中在城市核心及主要地鐵和交通線路周圍,以及一大片遠離市中心和交通的不利社區。福特的信息在他的工人階級和新移民選民中產生了強烈共鳴,他們感到城市復興的好處被市中心的精英所佔有,自己卻被拋在了後面。
2009年的多倫多湖濱:原本很好。Wladyslaw/flickr福特的崛起是城市日益擴大的階級分化的產物。隨着多倫多曾經龐大的中產階級的衰退和舊中產階級社區的消失,這座城市正在分裂為一小部分富裕、受過教育的地區,集中在城市核心及主要地鐵和交通線路周圍,以及一大片遠離市中心和交通的不利社區。福特的信息在他的工人階級和新移民選民中產生了強烈共鳴,他們感到城市復興的好處被市中心的精英所佔有,自己卻被拋在了後面。
我來這裏是為了看到這種日益加劇的階級分化如同一顆定時炸彈。如果像多倫多這樣進步、多元和繁榮的城市都可能成為這種民粹主義反彈的犧牲品,那麼這種情況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發生。
當時,我説福特只是這一醖釀中的反彈的第一個信號:更多更糟的事情將隨之而來。果然,緊接着英格蘭做出了令人震驚且完全意想不到的決定,選擇脱離歐盟(即“脱歐”)。這一決定遭到了富裕、國際化的倫敦的強烈反對,卻得到了被全球化和再城市化的雙重力量拋在身後的工人階級城市、郊區和農村地區掙扎居民的支持。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是出乎意料——甚至更加可怕: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為這個星球上最強大國家的總統。特朗普通過動員那些在美國被遺忘的地方的焦慮和憤怒的選民而崛起。希拉里·克林頓贏得了密集、富裕、以知識為基礎的城市和近郊,這些地方是新經濟的震中,以相當大的優勢贏得了普選票。但特朗普贏得了其他所有地方——更遠的郊區和農村地區——這為他在選舉人團中提供了決定性的勝利。特朗普、福特和脱歐這三者都反映了當今定義和分裂我們的階級和地理的深刻斷層線。
這些政治分裂最終源於新城市危機的更深層次的經濟和地理結構。它們是我們這一新時代贏家通吃城市主義的產物,在這種城市主義中,才華橫溢和有利條件的人聚集並佔據一小部分超級城市,拋棄了其他所有人和地方。新城市危機不僅僅是城市的危機,它是我們時代的核心危機。
局勢無法更為嚴峻。我們如何應對新的城市危機將決定我們是變得更加分裂,滑向經濟停滯,還是向前邁進,迎來一個更加可持續和包容的繁榮新時代。
本文改編自 新的城市危機:我們的城市如何加劇不平等、加深隔離,並未能滿足中產階級——以及我們能做些什麼。
***更正:***本文中的一段説明錯誤地將1967年紐瓦克騷亂歸因於1968年4月4日發生的馬丁·路德·金的暗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