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忠:想象的干預司法——重評司法地方保護主義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工作報告中説:“在經濟活動領域內,一些幹部……把法律當成保護本地區局部利益的工具。……如果法院判決本地應償還外地的債務,就不高興,就指責法院‘胳膊肘往外拐’;甚至阻撓法院對一些案件的受理、判決和執行。”這是第一次在國家最高議事議政儀式上提出地方保護主義話題。1988年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以上現象在最高法院的工作報告中被正式稱謂為“地方保護主義”。自1988年開始到2001年的歷年全國人大會上的最高法院工作報告,都批評“地方保護主義”對法院審判、執行的干預。
對當代中國民商事審判進行觀察的西方學者,在審判不公、法官濫用權力的歸因上,亦多認為系出於體制所導致的司法地方保護主義。對於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批評,逐漸演化為一種控制性話語形態,成為主導1990年代末啓動司法體制改革以來,直到晚近,對中國司法政治治理進行重構的基本敍事。

從地方保護主義敍事形成迄今三十年,已沉澱出一個可進行感知的較完整圖像,從而使得對地方保護主義話語形態進行評析,成為可經驗檢驗、測證的事件。
本文從地方保護主義發生的制度結構切入,試圖表達和論證以下事實:地方保護主義敍事來自於1990年代初期之前的印象。1992年後,劇烈的變革所產生的制度外部性,使得地方黨委、人大、政府,進行地方保護主義的激勵和所享有的支配力不斷衰退;從當事人的案件收益、尋租成本、搜尋成本以及各項風險量值來分析可清楚的判知,並非地方黨委、人大,而是上級法院,是當事人尋求對案件進行干預的優先選擇,持續三十年的司法地方保護主義敍事遮蔽了該事實。對於司法改革這一總前提的釐清、查勘,是司法改革政策設計再出發的起點。
一、司法地方保護的初始發生條件
“地方保護主義”的語義所指,在三個詞語關係項的背景下獲得界定:⑴“中央—地方”關係內,先地方,後中央;強地方、弱中央;⑵“地方—地方”關係間,一地阻隔、封鎖另一地,以鄰為壑;⑶“條條—塊塊”關係中,作為地方的塊塊利益優先,條條中的上級被抑制。
由於在中國,“中央”和“地方”,基本的指涉為黨委之間的關係,“條條—塊塊”關係中的“塊塊”,指涉為地方黨委、人大、政府,所以這三個詞語關係項,在以法院為討論主題時,具體表現為:⑴縣委/區委—市委/地委—省委—中央,在這一梯級內的地方下級黨委,對於利益獲取,優先於上級黨委,尤其是中央之上;⑵地方黨委、人大、政府將本區域的利益置於同級其他地方所轄區域之上;⑶地方黨委、人大、政府,強調本地政治經濟社會利益,將本地政治、經濟、社會後果的最優結果實現作為至上,排斥本級法院的上級法院、最高法院的規範性要求。
最高法院批評的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中的“地方”,顯然非虛空的地理所指,也不是普通百姓手持鐵鍬“暴力抗法”,而是指地方黨委、人大、政府。因此,司法地方保護主義敍事的基本外延,是在前述“地方保護主義”三個詞語關係項的第一、二種的部分形態和第三種形態內。在具體的發生因果上,地方黨委、人大、政府三個機構各自具有不同權力,對地方法院的事務介入,表現方式也不同。以學院內的視角來看,1980年代的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發生來主要自於兩個方面:
將以上促生地方保護主義的利益激勵和支配關係,置於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中,在具象的、真實發生的語境內,一一鋪陳開進行分析可見,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當時的“司法”和“地方”兩個方面的宏觀、微觀狀況,面對“保護主義”,或無力抗拒,或有其發生根由。
首先,在鄭天翔院長批評地方保護主義的1980年代中後期,經濟背景是所有制結構上,除東部極少量外資成分的企業外,經濟主體的基本形式是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查1986年4月最高法院工作報告擬定時所依據的經濟數據得知,1985年底,全國工業企業46.32萬個,全民所有制的9.37萬個,集體所有制企業36.78萬個,其他所有制佔0.17萬個。

最高人民法院第七任院長鄭天翔
地方黨委、政府,作為本地國營經濟的產權管理人、資產的具體代表人,對國有資產負有保值增值的制度義務。在計劃體制“一盤棋”的既定政策,和當時法院幹部的業務素養、審判水平下,如果地方黨委、政府對法院審判、執行,不進行實質性的審查關注,反而可能構成翫忽職守。其次,以1980年為界,至1993之前,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由“一灶吃飯”改為“分灶吃飯”,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乾”,實行多種形式的包乾體制,因此,地方黨委、政府儘可能留利地方,不讓肥水外流。
其次,因實行單一制經濟主體、管制經濟、票證經濟、單位制,加之人口較少流動等因素,糾紛極少,法院刑事之外的業務基本只以解決婚姻、家事和簡單民事糾紛為主,也並無現代西方將法院作為對行政機關等進行司法審查的制度,法院在政權內的分量極其輕微。以法院為專門的治理機制,而設計區別於政權內其他機關之外的單獨的審判人員任命和人財物體制,意義微小。
再次,除兩個激勵方向和兩個支配手段之外,另曾有兩個背景縱深因素曾對地方保護發揮作用:
1、在鄭天翔院長作報告的1986年,立法和司法解釋的總體規模極為微小,調整商事關係的規範網格極為稀薄,整個民商經濟方面的實體法,除簡陋的57個條款的《經濟合同法》之外,基本空白。
2、計劃經濟年代,物資調撥、資金劃轉等,都由地方政府通過各局、委、辦,依照上級計委下達的計劃統一調度。1985年開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基本經濟制度正從計劃經濟,向“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過渡,體制處於劇烈的調整時期。地方政府在管理經濟社會事務時,方式、手段上,進退失據。如對於銀行貸款無法收回,1987年前,多是銀行與主管局委,通過行政手段扣款解決。當異地法院以借款為案由介入收貸,尚未試點體制改革的地方政府會認為這是反制度行為。
二、初始條件的變化
以上制度狀況以1993年為轉捩點,發生根本性變化。隨着法院被賦予的處理經濟、社會事務的力量增強,對法院的治理也漸列入單獨序列而別於其他機關。
對於利益激勵第一個方向的外在激勵:首先,1994年開始實行分税制,中央和地方財政區分税種和比例分別徵管,不同企業的當家税種不同,對於地方的利益不同。2012年“營改增”後,地税更加萎縮,地方政府以留税留利在地方為目的進行地方保護的衝動衰減。其次,1997年中共十五大後進行大規模國有企業改制,各地政府“抓大放小”,剝離、重組後的國有獨資和國資控股的企業佔地方企業數量巨幅減少。目前各地,除中央企業在本地分、支公司之外,地方國有企業數量比例較此前已極小,少數保留的國企都是本地利潤表現優質,呆壞賬、拖欠等訴訟糾紛較少的企業。

對於利益激勵第二個方向的內在激勵,即個人私情、私利上,中共中央逐步建立了嚴格的地域迴避、避籍任職制度,以切斷黨政官員與地方的人情、利益聯繫。1995年,中共中央規定“地方黨委和政府領導成員在同一職位上任職滿十年的,必須交流;縣(市)委書記和縣(市)長不得在原籍任職。2002年之後,一方面將避籍任職範圍擴大,另外,由於人口流動,因父籍而發生的本人籍貫意義衰微,所以將幾類重要幹部的避籍任職改變為“本人成長地”迴避。因普遍異地做官,週末和節假日地方黨委、政府大院空巢,以及黨政官員聽不懂本地方言,成為政壇新現象。本地訴訟當事人與本地黨政領導層極少有深厚的、無法扯斷、無法躲開的親緣關係。
滋生地方保護主義的第二個方面,即地方黨委、人大、政府及於地方法院的“支配-順從”力量,尤其需細分出個項辨析。對於“人、財、物受制於地方”,這句成為成見的表述,細緻拆分後的形態如下:
(一)“人、財、物”中最重要的“人”,分為組織任免、編制、人事三項事權。
首先,組織任免。地方各級法院幹部的任免,是一種多重的條塊耦合結構。由於法院事實上是行政首長院長負責制,所以上級黨委對院長任免的決定權,在法院內部管理上是最高支配權力,本級地方黨委對副院長級幹部的決定權,嵌套在上級黨委對院長決定權這一前提內。激起地方保護的案件,通常較為重大,而重大、疑難、複雜案件,合議庭提交院長主持的審判委員會討論,基本上消解了承辦人、庭長、主管院長這些由地方黨委、組織部管理的幹部承受的壓力。
其次,編制。地方法院編制原由地方政府管理,法院增編、用編需向地方政府人事部門申請。1982年之後單列中央政法編制,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組織部等把政法機關編制“從國家機關總的行政編制中劃分出來,分別單獨列為國家公安編制、司法編制和檢察編制。實行統一領導,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分級管理。” 1988年設國家機構編制委員會,此後歷屆編委主任均由總理擔任。1991年升格為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中央編委),其常設辦事機構中央編辦單列為正部級,機構性質“既是黨委的工作部門,也是政府的工作部門”,權威度增強。
地方各級法院編制由中央編委統一領導。法院增編,層報中央編委、編辦批准,僅編制內用編,報地方編辦核准。地方政府人事部門的權力進一步弱化。
再次,人事。地方法院新進非領導職務的普通法官,原由同級地方政府人事局派遣,“法院想要的人進不來,法院不想要的人頂不住”。2004年後,主任科員以下非領導職務初任法官,一律實行省級統一招考,考試錄用由省級黨委組織部主管。基層法院、中院的進人計劃報高院,由高院統一審核彙總,報省級黨委組織部審批,統一向社會公佈。考試由省級黨委組織部會同高院組織實施,考務工作由省級人事廳考試中心統一組織考試,分數線由高院商省級黨委組織部確定,擬錄取名單經高院審核,報省級黨委組織部審批。市、縣、區各級地方政府人事局對於法院招考、錄用處於無權狀態。
(二)“人、財、物”中的“財、物”部分,其實際形態也已發生巨大流變,並非西方觀察者所想象的一籠統地估堆式由法院所在政府財政撥款,而是區分類別,區分財政級別,根據“財、物”內容的不同種類,分別由中央財政、省財政和法院所在的市、縣財政分級進行保障,保障原則也不同。中、基層法院所在的同級政府的制約力下降。
此外,立法供給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構成這兩個因素,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起點,也迅速變化。

首先,在加大法律供給,提高法院自組織能力上,1993年後,以民商事、經濟為立法中心的各級立法騰躍,到2010年底,“涵蓋社會關係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已經齊全;各個法律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經制定”。中國司法過程中,另有巨量的司法解釋和批覆、紀要等非正式規範發揮着規範作用。以政策、原則為遮蔽,實際注入地方個體利益的干涉,日益遭遇到成文立法的阻遏。
其次,1992年後,各級政府經歷了1993、1998、2003、2008四次大規模的機構裁減、合併、職能下放,直接管理經濟的紡織、商業、冶金、輕工、電子等部、委、局、辦,裁撤合併完畢。地方政府通過這些職能機構直接介入經濟流轉的具體手段衰弱。
綜上所言,地方黨委、人大、政府對於本地法院審理的案件利益“保護性”介入,經過二十年的制度改新,較之鄭天翔、任建新院長時代,驅動已極大衰微,支配力也巨幅衰落,來自地方政府的制約大部消散,地方黨委、人大有支配力的制約亦僅在在副院長以下的幹部任命上。當然,在權力的毛細血管層面,目前地方黨委、人大、政府各種潛在的激勵和具有的支配,也依然絲絲縷縷。
但是,如由此作為出發基點,對地方保護主義進行單線一維的制度主義獨斷,漠視了人是處於行動中,而非被教室黑板上板書、幻燈片標繪的模式圖所設定。當事人借重地方黨委、人大提供“保護”,的確是實踐中可能存在的一種情形,但只是情形之一,而現實中有多種可能作為備選,如果尋求其他手段,付出的成本,獲得的收益,以及行為風險量值,都小於前者,那麼地方保護主義就只是一種邏輯上的可能備選項,而非行動中的人的必然選擇。
在實踐的發生中,制度邏輯上的激勵因素和支配,落入現實的複雜的司法場域後,呈現出的外觀是:尋求案外干預的當事人優先選擇的是尋求上級法院,“地方保護主義”常處於被“存而不論”的境地。
三、司法地方保護髮生的可能方式
地方保護主義的斷言,是以非個體論的視域來看待法院和地方黨委、人大、政府,但是黯淡了任何組織都是由有着現實利益盤算的個人構成。訴訟中的行為由人實施,被納入地方保護主義這一主題進行分析的行動中的人有:訴訟當事人、地方黨政官員、受理案件的法院法官、上級法院的法官。成熟的、會算計的人,不會因為一個空的指號——大家都在本地工作生活,僅因為這種非理性的情感性因素,而幼稚地“保護”激烈對抗的各方當事人中的本地一方。以此視角,對地方黨委、人大、政府介入法院審判,進行仔細打量,可將“地方保護主義”分為三種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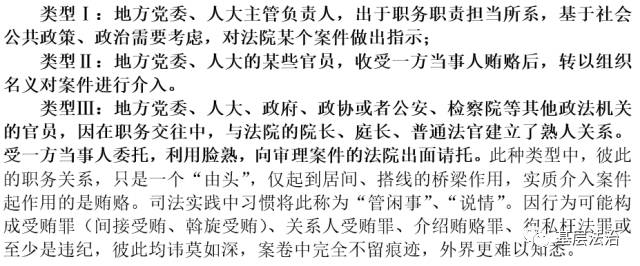
對以上三種介入,法院自身的各種報表、各項統計數據中,沒有列項,也難以統計,外來的觀察者更無從有實證的數據來證實或證偽立論。但是,作為一個精於計算的公務人,每個官員都會對自己行為的成本、收益和風險量值進行精算。具體情況包括:1.組織獲得收益、私人支付成本的行為,個人沒有激勵去實施;2.私人支付成本、私人也獲得超出邊際成本的收益時,個人才有激勵去實施;3.如果是組織支付成本,私人獲得收益,個人具有最大激勵。
以此作為分析工具,來看這三種類型。
類型Ⅰ,如果僅是當地企業獲得保護,而官員個人沒有超出的好處,但卻要擔負來自政治上的責難,導致政治前途黯淡,那麼,沒有官員會去行動。作為公務人,官員的目標是晉升。如果自己的公務行為並不有利於晉升,反而需要官員支付私人成本、職務風險,遭致政治上的降級和責難,那麼官員沒有任何動力去實施。
類型Ⅱ,與類型Ⅰ在外觀上相同,都是啓動組織程序,或利用職務,公開地打招呼,而不是私底下賄買法官。
但這兩種方式在訴訟中發生的可能性並不高,原因是這兩種方式在訴訟中有着極高的被發現概率。第一種以組織名義正式介入案件,方式是黨委、人大辦公機關啓動草擬-審核-簽署-傳遞公文流程,最後發送於法院,對應的法院辦公機關收文-呈送-會籤-下發審判庭,而不會是“一對一”兩人交易於密室。第二種沒有正式公文,只是黨委、人大負責人的批示或電話交代。對此,司法實踐中歷來的做法是,將批示附入案卷的副卷;如果沒有書面指示,僅是電話通知或會議協調,則由案件承辦人寫一個備忘紀要,由合議庭、審判庭相關知悉人共同簽名,附入副卷內,以資憑證。
但是,與黨政機關處理的行政事務不同,法院處理的事務是訴訟,而訴訟由對立、衝突的控辯雙方構成,法院只是一個裁斷者。因此,訴訟不是封閉的、信息密不透風的單方內部審核,而是由勢不兩立、劍拔弩張的衝突對抗中的當事人與法院三方構成的多重互動關係。
在持續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推動下,中國民商事訴訟的職權主義已弱化。出自法院職權、導致訴訟情勢中雙方當事人的任何細微顫動,都會被情勢不利的當事人所迅速感受到。如果承辦法官個人沒有在黨政領導“打招呼”的案件中獲得較大個人私利,那麼法官為避免追責和將矛頭對準自己,多會以確定的或晦明的,哪怕是點到為止的方式將領導批示這一信息,明示、暗示傳遞給另一方當事人,以為自己卸責。
由此可見,如果地方黨委、人大以組織方式介入爭議中的訴訟,偏袒一方當事人利益,將導致該事實被對立方當事人牢牢的抓住,訴諸於更高黨委、人大機關、媒體輿論的救濟。而實踐中,能夠牽動地方黨委、人大,以組織名義介入的案件,必定是重大標的案件,雙方當事人均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量。即使是地位極低下的當事人,也會以“弱者的武器”方式進行越級上訪、信訪、自媒體形式的網絡攻擊,從而導致地方黨委、人大官員個人政治上的不利。所以,類型Ⅱ和類型Ⅰ,尤其是類型Ⅰ,主要發生在近年流行的官場小説中,司法實踐中並不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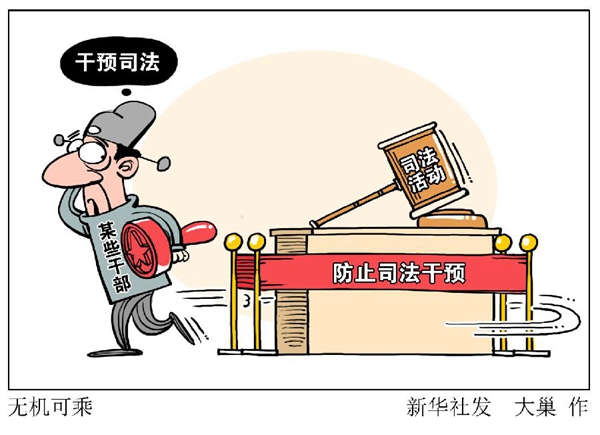
類型Ⅲ,並非出於公心,而基於個人利益,通過私密、隱蔽的利益勾兑、權力貼現方式,介入、干預訴訟,這兩種方式,不是鄭天翔院長所稱的地方保護主義。這種沒有職務制約關係,而是通過賄賂搭橋的情形,與地方黨委、人大的職權對於法院的支配關係無關,任何能夠與法院的承辦人、庭長、主管院長等人實現權力互惠、利益互換的人,包括地方黨政機關、人大、政協、公安、檢察院的官員、私營企業主、有支付能力的任何布衣鄉民,都可以以此方式涉入案件。
對司法冷靜的觀察,獲得清晰的認識:案件裁斷結果發生不正常的偏差,必然是貨幣或可兑現為貨幣的非現金收益方式在進行支配,而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臉熟”、人情面子在起作用。只要能夠支付購買審判權力對價的任何人,有能搭上線的渠道,即可能實現賄買目的。
訴訟實踐中表現出的情狀,確如馬克思所説:“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地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
因此,即使通過司法結構變動,法院徹底獨立於地方,不管是省級以下統管或最高法院垂直統一領導,還是法院原子式的獨立,都無法排除賄買行為。反而是,人財物獨立於地方,只能更加增大法院與這些官員、老闆、資本擁有者私底下進行權力貼現、勾兑、創租時,法院一方的籌碼和收益,對於改變法院、法官徇私枉法沒有任何撼動。
因此,進入本文討論主題的只有類型Ⅱ和類型Ⅰ。但由於類型Ⅱ和類型Ⅰ在外觀上無法區分,所以,必須從內容上再進行界定。類型Ⅱ雖然不是鄭天翔院長批評的那種地方保護主義,但是,因為其一方面利用對法院的職務制約關係,另一方面個人收受賄賂,非常具有隱蔽性,這被認為是地方保護主義的主要發生形態,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在訴訟實踐中,賄買的具體的基本形態是:1.當事人先搜尋到合適的官員,賄買該官員,該官員同意出面請託對法院有支配力的目標官員。2.目標官員向法院打招呼,要承擔政治名譽損失,另有被追責可能,因此當事人必然以支付賄金方式,彌合該官員的顯在和潛在損失。3.即使當事人賄買了高級別的目標官員,在由法院具體審判執行時,必須再向法官具體的相關人行賄。
當事人完成這一流程,有兩次大的跳躍:首先,搜尋到目標官員,支付了對價,目標官員同意向法院“打招呼”,官員“打招呼”的有效性如何,存在極大不確定性:繼而,因為賄買官員和法官行為是犯罪行為,一旦被查知、追訴,帶來人身自由喪失和案件收益喪失的雙重後果,必須評估自己行為敗露的風險,如果風險稍大,即使有收益,不足以啓動賄買司法行為。
這兩次跳躍,實際是雙重風險,其中任何一次風險發生,都將導致當事人的賄請支付行為失敗,沒有收益。所以,細化當事人的成本-收益表內的各項指標為:1.成本包括:搜尋官員需要支付的成本;賄買官員需要支付的成本;賄買法官需要支付的成本;2.訴訟收益是當事人從案件勝訴獲得的直接收益;3.風險量值為高度不確定值,數額可能為0~∞,0為無風險,∞為無窮大。

四、司法地方保護髮生的低可能性
拆解前述公式,對當事人的成本-收益表內的各項指標,進行分析如下。
(一)搜尋成本
批評地方保護主義主要劍指基層,即縣區和市。中國政制下,在一個市、縣、區中,能對法院進行批示,要求法院彙報工作,從而正當介入司法的制度角色有3-5位。因為中國法院80%的一審案件由縣區基層法院受理,因此,為節簡表述,以基層法院所在的縣為例,能合法介入司法的制度角色是:書記、分管政法工作的副書記、作為常委的政法委書記,人大主任、分管內務司法/法工委工作的人大副主任。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減少地方黨委副書記職數,實行常委會分工負責”的要求。副書記職數削減,不再有分管政法工作的副書記和同時擔任紀檢委書記的副書記以及分管組織、分管協調等工作的副書記,除作為副書記的縣長之外,僅有一位協助書記、負責統籌協調的副書記。在書記兼人大主任的縣,能通過組織方式介入地方法院,並對案件做批示的只有4位:書記(人大主任)、副書記、作為常委的政法委書記、分管內務司法/法工委工作的人大副主任。在區、市、省一級,雖然級別不同,但有支配力的官員數量大致保持不變。
對於司法政治的這種形態,部分作品的認識有偏差,認為地方政府序列內的官員經常干預司法。實際上,在中國的政治架構下,地方政府不可能對法院採取組織方式的干預。原因在於:
首先,中國政體架構是人大領導下的“一府兩院”,法院與政府平行,所以政府序列內的官員,無權以組織方式介入法院案件,即向法院發出批示或要求法院來彙報案件。這是政制基本規則。由於80%的案件由縣區基層法院受理,中院是最重要的上訴審法院,再以中級法院所在的市為表述對象析之:不僅作為市委副書記的市長、有常委身份的其他副市長無權以組織方式介入法院案件,分管政法的副市長也無此項組織權力。
市政府中雖然有一位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但其分管的是政府法制、公安、司法行政、信訪等部門,對於國家安全機關、法院、檢察院,職責僅是負責聯繫。依照中共黨內“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組織原則,如果其向法院發出指示,不僅有違基本政制、組織原則,而且僭越了黨委內分工政法工作負責人的職權,為政治紀律所不容。某些文學、影視作品,為誇大政府對於法院獨立的干預,多設計副省長、副市長等官員要求法院彙報案件的情節,背離基本政治常識。以法律與文學材料理解中國司法的部分學術作品,亦以此為據,顯與政制和實踐不符。這些幹部介入訴訟,方式是隱蔽的、私底的關説,起根本作用的是利益交換,而非組織制約。
其次,政府內計劃、財政、人事等部門的實權派官員,雖對法院有局部工作約束關係,但此種約束如前文所述,已日益萎縮。由於法院負責人在職級上高出同級政府部門負責人半級,依照中國的政治架構,這些官員更不可能通過組織體系對法院審判進行批示,或要求法院院長、主管院長前來彙報工作。如果其出面介入訴訟,是俗稱的“説情”,法院為之枉法,原因必然是貨幣賄買,或者這些部門負責人能夠和法院院長、主管院長、庭長等控制案件的行政負責人進行利益交換,如安排法院院長、副院長、庭長的親朋好友或關係人就業、為關係人進行職務提拔或其他利益照顧。性質屬於前述類型Ⅲ利用“臉熟”居間進行的賄請。

這即導致能提供給當事人,以組織方式向法院施壓的官員具有稀缺性。另外兩個原因導致該稀缺性進一步加劇:其一,前述中共中央嚴格實行幹部避籍任職、不得在本人主要成長地任職等規定後,異地交流、提拔到本地任職的主要官員,對本地當事人來説是“陌生的異鄉人”,短期內能建立超越組織關係的私密感情的人極少,搜索鏈過長。其二,任何現代社會都存在基於職業、職位、資本、出身、學歷等各種因素所存在的社會分層,在社會分層的層級內,跨層級建立私密關係極困難。
因此,一方面,能對法院辦理的案件有制約力,法院在人財物等方面有求於之,因而會聽命於其指令的人,數量有限;另一方面,有人脈關係網絡,能找到上述人物,並且能遊説動這些人出面給法院施加有效的壓力的訴訟當事人數量又極其屑微。
雖然從黨委、人大主要幹部的社會交往而言,社會上必然會有與本地、上級黨委、人大主要幹部有私密關係的人,但因為政治、社會、組工紀律等各種限制,這種關係基本是極小範圍獲悉,不必然公開地招搖、示形於江湖。找到目標官員,方式往往是層層打聽、託人,即使找到目標官員,該官員的品質德性,是否會接受該當事人賄買,又屬於極不確定要素。
因此,即使能找到目標,方式通常是:當事人→中間人1→中間人n-1→中間人n→地方黨委政府中的關係人→法院,搜尋成本過大。當然,訴訟中具有這種搜尋能力的當事人是存在的,無法否定確有當事人能直接搞定市、縣區委書記,但是,這種當事人還要考慮以下變量。
(二)賄買官員成本
當事人即使有能力可聯繫到這些官員,這些官員願意出面向法院發出指令,當事人需要支付的成本極高,賄金大小既與受請的官員級別高低正相關,也和請託的案件標的大小成正比例。
(三)風險量值1
首先,與知識壁壘和專業化限制相關。
地方黨委、人大的官員,對訴訟所涉及的高度複雜化的實體法、程序法通常極為陌生,對案件的構成、證據、法律適用精微之處也完全隔膜,面對民商事訴訟專業槽日益細密、精深的普通法律術語諸如締約過失責任、先合同義務、避風港原則、維斯比規則、INCOTERMS2010等都不明就裏。所以,來自黨委、人大負責人對正在辦理案件的批示,即使要求限期報結果,並由有關部門督辦的高級別領導人的函件,其所做的案件批示,都罕有技術性的直至案件中樞,而是內涵包容性大,並符合政治正確。多數只能是概括性、原則性的籠統提出要求“依法處理”,難以在極關節位置的證據、事實、法律適用要害處,直接點示。
其次,從社會心理上看,地方黨委、人大官員介入訴訟,非因公共利益,而是受個人私下所託,居間向法院遊説説情,這是一個分寸拿捏需極其細微的活動。
對官員心理而言,從推動力上,因個人情面以及金錢利益驅使,勢必要向法院打招呼。但是,一方面如前述,案件所涉證據、事實、實體法、程序法的法律適用高度專業化,官員的專業知識完全不匹配,因此,只能是籠統的提出請照顧,而不是具體的提出要求如何。另一方面,在官場上歷練多年、升遷至一定職位的黨政官員,都有一個基本的社會經驗:案件是雙方爭議,不能僅聽請託人一方之辭,請託人通常有隱藏的私密信息不會透露。所以,官員説情都有基本的限度,此限度的邊界就是足以自保,不能使這種説情成為“硬説情”,從而導致自己陷於可能的被動。這種心理決定了官員的説情通常只是籠統的轉告法院“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給予關照”。
再次,地方黨委中能卡住法院的幾位幹部,其職權治下有幹部職務提拔、房地產項目、工程發包或安排貸款居間等事項,此類事項既為他人辦“好事”,又不存在“零和博弈”下有確定的利益受損者可能引發持續信訪。

與在訴訟中因為受賄壓法院,導致對方當事人利益受傷相比,這些事項風險小的多。既然有可在“避風的”領域受賄這一“等功能替代品”,而且風險較小,所以,面對請託在民商事訴訟中打招呼,精明的黨政官員通常會謹慎對待。實踐中,黨政官員對無法磨開情面的請託,採用的方式往往是將自己出面打招呼的行動,能讓請託人明確知悉,即可交代得過去。
以上這些能被開放式地做各種理解,左右搖擺、搖曳多姿的批示、“打招呼”,與指向明確的附有“要結果批示”的轉辦函相比,差異明顯,力度一望即知,而且可以被法官用精細的技術性知識所化解,對於當事人往往用處不大。這導致當事人賄買官員所支付的成本,具有極大不確定性,極有可能沒有收益。
(四)賄買法官成本
這一環節,只有在第三個環節順暢運轉之後才能發生,如果在第三個環節,即“風險量值1”階段風險發作,第四個環節即不會發生,此前當事人的所有付出,在該案件中全部淪為沉澱成本。如果第三個環節順暢流轉至本階段,其繼續的邏輯如下:因為當事人所獲收益並不正當,因此打招呼通常不是一般的以勢壓人,而是在溝通、搭橋之後,另由請託的當事人以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進行實質性的權力賄買。所以,即使在官員做出的批示轉至法院後,當事人仍要不同程度地層層賄買法院的院長→主管院長→庭長→承辦人,費用極高。
(五)案件直接收益
按照最高法院1999—2008年的民事經濟案件管轄權劃分,基層法院的民商事案件級別管轄權極低,如在華東的安徽,合肥除外,包括沿長江經濟發達的安慶、蕪湖在內的各中院,受理以財產為內容的一審民事案件,爭議金額為20萬元以上不滿3000萬元;經濟糾紛案件爭議金額為40萬元以上,不滿3000萬元。全國多數縣區法院都執行20萬、40萬的標準。40萬、3000萬,都是規劃的最大值,在實踐中,縣區基層法院實際受理的經濟案件中,能接近40萬元標的上限之中線(即20萬元)的案件都極少。2007年,全國法院受理民商案件472萬件,案均標的金額15萬元。在爭議標的額中,當事人有效利潤又只佔百分之幾。為了區區幾千、幾萬元的利益,當事人層層託人,請動一個縣/區委書記、副書記,向法院施加壓力,或可能產生效果,但成本收益付出不對稱。

(六)風險量值2
首先,事情敗露風險。在持續經年的批判“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呼籲“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的口號下,民商事案件中的多數,由承辦人提出意見並簽發。如果是地方黨委、人大中的領導人打招呼,根據經驗中社會分層對等的規則,必然不是直接找沒有臉熟機會的低職級的承辦法官,而是直接找因長期共事、一起開會等原因而熟悉,並且級別職位相當的院長或副院長,再由院長、主管院長向庭長佈置,庭長向承辦法官佈置。因此,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徇私枉法的發生,通常是層層尋租進行權力貼現,步驟通常是:
這一代理鏈條過長,交易成本過大,而且因為環節多,信息發散可能性大,風險高。在每一個環節鏈條,好處費層層轉交,送給官員的好處費是赤裸裸的行賄。這種情形,如前述,在當事人對抗的條件下,發生明顯偏離的訴訟結果,信息又極為分散,收受這種案件上的賄賂,敗露的不確定性極大。
其次,二審改判風險。1990年代以來,各地為發展區域經濟大規模招商引資,地方政府以各種優惠搭台,實現經貿唱戲,尤其是給招入本地的利税企業大户各種袒護。因此,具有極強的遊説、交易賄買能力的地方企業是存在的。但是,即使一審中通過地方黨委、人大壓法院,造成請託當事人的有利結果,訴訟審級制度具有糾錯功能,如果對方上訴至二審法院後原審勝訴方敗訴,則一審中的鉅額付出皆歸於負數,整個風險量值2的閾值範圍(0~∞)即直接發作為無窮大。
綜上所言,通過賄賂地方黨委、人大有支配權的3-5位官員,向法院施加壓力獲得勝訴,這在邏輯是通暢的,但是成本付出和預期收益之間的不確定性過大。即使所有環節走通,最後贏得勝訴,最後極容易落入“贏者的詛咒”這一困境。
五、一審程序中的上級法院介入
理性的當事人從不必然按照書齋安樂椅上研究者鍵盤敲擊出的文字指示來行動。如果有兩種以上方式(EU(B)i,i≥2)都可以實現(訴訟收益-成本)-風險量值>0,那麼,當事人一定會選擇(訴訟收益-成本)-風險量值諸方式中,效用最大的一種(EU(B)i>EU(B)i-1)。實踐中,當事人更多選擇是(案件勝訴收益-搜尋上級法院法官成本-賄買上級法院法官成本-賄買法官成本)-風險量值1-風險量值2>0這一種方式,而不是尋求地方黨委、人大官員這一方式。
以前述的六個指標值,來測評賄買上級法院法官這一方式。
(一)搜尋成本
首先,與能對法院案件進行介入的數量有限的3-5位黨政幹部相比,在法院內部,因為審判關係,能介入一審法院案件的不僅是上級法院院長、主管院長,也包括對口的上級法院審判庭的內勤、助理審判員、審判員、審判長(常任)、副庭長、庭長。由於中國法院編制的分佈是倒置的金字塔型,級別越高的法院,人數越多,對口業務庭的上級法官數量層層遞增,上級法院的千根線,都系在下級法院一根針上。目標數量較大。

其次,《黨政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限制的地域任職迴避,僅限法院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審判長(常任)、普通審判員、助審員,均不在避籍、迴避主要成長地任職範圍,這些法官管理者和法官生於斯、長於斯,血親、擬製血親、同學、親朋、故舊在本地眾多,對於當事人來説,低搜尋成本地找到一個上級法院目標法官,較之找到能“打招呼”的黨政官員容易得多。
再次,搜尋到上級法院法官的概率極高的更重要原因在於律師的居間。與前述搜尋到能與黨委、人大主要幹部進行居間的關係人十分困難的狀態相比,能與法官居間的一個重要角色是律師。而長期在各個級別的法院所在地,以訴訟為主營業務的律師,有相當部分與本人主場所在地的法院各庭法官有各種人情關係。
這表現為以下形態:律師是合法、公開介入訴訟,提供法律服務的社會中介組織人員,以該身份為介質、橋樑,可以提供法律服務形式遮蔽之下的居間作用;某個律所和律師所提供的敞開式法律服務的內容和優勢,以及律師個人的出身、交往等特殊關係,以名片發送、網頁介紹、報紙廣告以及餐桌飯局、聚會時的言談誇口、博客、文章等各種方式廣而告之,昭告天下;律師服務遵守“出租車排隊法則”,只要客户能支付得起費用,服務對象無差別,為任何向他們尋求服務的客户提供服務。
最後,從可選擇性看,如前述,法官與黨政幹部相比,黨政幹部事權較寬,有意貪腐的官員可在職位提拔調動、房地產項目、工程發包、安排貸款等多個領域,有受賄空間且風險較小,而有意貪腐的法官,唯有“吃案件”一途,較之黨政幹部,貪腐的法官對尋價的律師具有更強的迫切性甚至主動性,創租者和尋租者能在一起案件中心領神會,此後即一拍即合。
從搜尋成本角度審視,在實踐中,法官和律師具有錯綜複雜的親密關係,使得以律師為渠道找到法官,極為便捷。兩者的親密關係有以下形態:
1.法官的配偶和子女從事律師工作,此現象極為普遍,以致需要連續發司法文件進行規範。
2.法官辭職、退休後擔任律師或律所顧問,雖不得再在原法院進行代理,但是無法根絕幫其他律師介紹案件、牽線、分成。
3.因強調法律職業共同體建設,排斥從其他途徑進入法院,律師和法官羣體逐漸均為法學院科班出身者,許多法官和律師是法學院的師生、校友、同學,甚至同門師兄弟。
4.法學院教師極高比例地擔任兼職律師,而許多法官在法學院擔任法律碩士兼職導師甚至博士生導師,法官在職讀學位、到法學院參加業務培訓,法學院教師到法院掛職,加深了彼此的業緣。5.部分刑辯律師和法官,雖然沒有親緣、血緣、業緣、同學等緊密關係,但部分貪腐的法官,刻意結識部分不良律師,雙方長期合作,彼此信任,結成介紹案件—利益均沾共享意義的“法律共同體”。
所以,在訴訟當事人遊走、搜尋於各家律所時,尋獲具有此種交易能力的律師極為容易。即使受託律師本人沒有直接關係,尋找到目標法官都並非難事,原因是律師圈所發揮的作用。
社會互動研究的一個基本範疇是“圈子”。圈子的一個特徵是內成員/局內人彼此共享一些成員之外的人不知悉的信息、規則。

從事訴訟業務較多的律師,對於圈內哪位律師與哪個法官或庭長、院長有特殊默契,大都心中有數心照不宣。只要當事人具有強支付能力,委託律師會直接與目標律師進行聯繫,以共同代理人的方式進行合作,收益分成。即使是案件訴至最高法院,尋找到與相關法官,甚至主管院長有私密關係的律師進行勾兑,都不斷有案例披露。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被認定的受賄罪共五起,金額為390萬元,其中四起為收受律師陳卓倫、陳文以及北京某高校教師趙某某的賄賂,向下級法院或本院承辦人打招呼、作出書面批示。
因此,從交易達成的可能性來説,通過地方黨委、人大介入案件,除極個別有強交易能力的當事人之外,對絕大多數當事人屬於不可能。而通過律師居間上級法院是普遍可以達致目標的行為。即使對於跨市、跨省訴訟,案件發生在本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之外、距離極遠的外地法院,找到避籍、交流任職的當地黨委、人大主要官員,幾乎不可能,但通過法院所在地律師居間,與主審法官建立暗線聯繫,並非難事。
在鄭天翔院長做報告的1986年及此後的幾年中,中國法律服務市場極不發達,從業人員的社會活動能力也不足。因缺乏替代性手段,尋求以案外方式介入訴訟的當事人,求諸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的官員,幾乎是唯一形式,所以極其突兀。在律師數量從1986年的2萬人上升到2014年的27萬人,尤其是律師的來源、構成,以1992年為起點,逐漸發生大變之後,如果在訴訟中當事人意欲以非正當方式切入案件,對居間角色的扮演,黨政官員基本被律師替代。
實踐中,通過上級法院干涉案件的步驟通常是:當事人→律師→上級法院法官。這與前述通過賄買官員的方式相比,環節少,交易成本極低。
(二)賄買上級法院法官成本
假定與賄買地方黨委、人大官員成本一致。
(三)風險量值1
上級法院對口業務庭的法官,對各種司法技能微妙之處瞭然於胸,進行的影響多直接、具體,且在法律上難以為旁人查知。
在方式上,上級法院的主管院長、對口業務庭室的庭長、副庭長或分片的審判長,可以要求承辦法院來彙報案件並簡單閲卷,或直接調閲案卷,從而會對案件的證據、事實、法律適用,有準確的認知。不用如黨政官員一樣擔心專業技術知識不具備,以及受到信息屏蔽,而被請託的當事人錯誤誘導下套。這些法官能直擊要害,從單個的證據證明力、證明能力和系統性的證據體系,以及細緻的訴訟程序和微妙的實體性構成事實、程序性構成事實等司法技術性知識切入,可以解構或重建整個案件的基本方向。從對訴訟當事人的收益來説,這種收益顯然更大。
所以,對於賄請的當事人而言,只要其賄賂到位,一般能得到預期收益。此前因知識格柵限制等導致地方黨委、人大官員的踟躕、猶豫,從而對案件具有的不確定性,在此降至極低。
(四)賄買承辦法官成本
假定與前述通過賄買官員的方式切入上,成本一致。

(五)案件直接收益
與尋求黨政官員的方式不變。
(六)風險量值2
首先,事情敗露風險。對於律師居間的情形而言,賄賂是以委託律師的收費名義出現,尤其是對所謂“風險代理”,即根據事後判決所得收益,支付了極高訴訟代理費的案件,彼此對這種超高律師收費背後的因素都心照不宣。
在風險防範上,從關係鏈條的第一環開始,違法性即被阻卻。在關係鏈條的最末一段,因為律師和法官具有前述的各種血緣、親緣和其他人身關係,不僅犯罪違法性再次被阻卻,而且相較於發生於陌生人之間的受賄,對這種親密關係人之間的受賄,在該當—違法—有責的各環節,出罪的裂隙多,尤其是圍堵、閉合證明標準對偵查的要求高,取證難度巨大。這對各角色的風險極小。
其次,二審改判風險。在前述訴訟當事人通過地方黨委、人大打招呼,案件判決後,被上訴或抗訴到上級法院,如果被改判,則一審中的付出悉歸於零。而通過上級法院對口業務庭向下級法院打招呼,事實上兩審合一審,一次勾兑,兩次受益。由於中國審判是兩審終審,實際是一次勾兑,終身受益。
在此種方式上,有一個環節上微妙之處,即之所以訴訟當事人已搜尋到願意進行權力貼現的上級法官,還要轉而向下級法院打招呼,而不是坐等上訴至二審法院再改判,原因在於:
1.除了法學課堂上研判的證據、程序、實體之外,法官優先考慮的是業績測評考核,由於改判將影響到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考核、評比,牽連到的不再是某個訴訟當事人的個體利益,而是下級法院與本院的整體機構利益,因此一般不會輕易做出改判。
2.一審判決後,二審如果僅維持原判,在二審法院內部,承辦人即可決定,而如果改判,則要報庭長或主管院長審批,內控機制複雜,這會導致尋租成本巨大。所以,訴訟中,對口的二審法院法官向尚在一審環節的案件承辦法官打招呼,對於兩級法院法官來説,結果都是最優:⑴一審法官不用擔心判決有偏而被改判;⑵二審法官作出維持原判的裁定,內控機制最簡單。因此,在許多案件中,即使當事人找到地方黨委、人大負責人出面勾兑,一審法院中被請託人會告知其最好找一個上級法院的法官、庭長來出面,因為這樣對一審法院也是風險最小。
所以,當事人訴諸於上級法院尋求“保護”,而不是訴諸於地方黨委、人大、政府,是實踐中最高頻次發生的現象。
六、上訴審程序中地方保護髮生的低可能性
前文分析以一審案件為對象。如果是二審案件,在目前兩審終審制下,二審法院裁定即終結,那麼二審法院所在的地方黨委、人大,是否會被當事人更優先選中?經驗測知,這種情形並沒有超出上述分析,即尋求二審法院的上級法院的方式。
(一)搜尋成本
一個縣區法院一審判決的案件,縣區的當事人要在市一級尋找到能對法院有支配力的3-5位官員;中院一審的案件,要到省一級尋找目標官員。從社會分層意義上以及前述幹部任職迴避、交流制度導致的後果上看,跨越層級和地域找人,搜尋難度進一步增大,概率進一步減少。
(二)賄買地方黨委、人大官員的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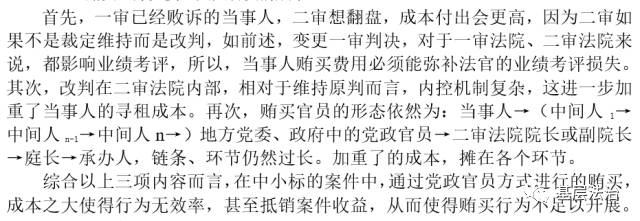
(三)風險量值1
一審已經敗訴,接受賄請的官員要干預二審改判,前文所述的知識格柵、社會心理等因素會更重,其干預會更遲疑、猶豫,從而導致啓動二審法院改判的有效性更低。
(四)賄買承辦法官成本
假定保持不變。
(五)收益
當事人從案件中獲得的直接收益,亦如一審時發生的情形。
(六)風險量值2
這在二審時變得更復雜。雖然在訴訟收益上,因為兩審終審,如能通過二審法院所在的省市黨政官員搞定二審,當事人不存在敗訴風險,但是,這變量受到以下因素影響,而變得不確定:
由此,在上訴審程序中,當事人請託地方黨委、人大官員依然是低概率發生的現象。
七、上訴審程序中的上級法院介入
如果當事人繼續選擇尋求二審法院的上級法院,相較而言,依然在成本收益上是有效率的方式,即一起縣區法院判決的案件,對方當事人上訴至中院,另一方當事人會繼續尋求、請託高院進行尋租,而不是在中院所在的市委、市人大尋找關係;如果是中院判決的案件,對方當事人上訴至高院,另一方當事人會繼續訴諸於最高法院進行尋租,而不是在高院所在的省委、省人大尋找關係。

這種行動,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反正式制度的,因為二審終審制下,二審法院對手上的二審案件説了算,不存在二審案件被三審上訴而被改判,但這是對中國法院上下級關係過於圖式化的理解,這也正提示了時下中國法院上下級關係的非制度化。這種行動邏輯的根由在於:
(一)搜尋成本
與搜尋級別越高的黨政官員越困難不同,當事人以律師為中介、居間,找到高級法院的法官,並不與審級增高而成正比例關係。
(二)賄買成本
一審敗訴的當事人二審翻盤,成本付出比一審要高,但是相比於尋求黨政官員,環節依然較小:當事人→律師→上級法院法官,比較成本同樣較低。
(三)風險量值1
相比於尋求黨政官員,通過二審法院的上級法院介入,在知識格柵限制和當事人從案件中獲得的直接收益兩個方面,都能給當事人帶來更大回報,因為出現二審法院的上級法院這種情形,在四級兩審制下,被選中的法院要麼是最高法院、要麼是高院。高院和最高法院的知識優勢表現在以下方面:
(四)賄買承辦法官成本
假定與尋求黨政官員相比,保持一致。
(五)收益
與尋求黨政官員相比,保持一致。
(六)風險量值2
在此方式下,一審法院已經查明的事實和法律適用對於二審同樣有制約,對方當事人信訪的壓力也始終存在。此外,二審法院的上級法院介入二審案件,翻轉了一審判決結果,與黨政官員介入的情形一樣,同樣會使得一審法院、二審法院、一審法官、二審法官業績測評不利。
但是,每一級地方法院的測評都是由上級法院作出的,中院的測評由高院做出,高院的測評由最高法院作出。如果一起案件的改判是由高院介入導致,那麼高院勢必會在考評時對此做出技術性處理,從而不使該中院利益惡化。最高法院介入的情形亦如此。這種內部測評上的變通關照,是法院體系之外的黨政官員所不具有的。這降低了一審法院、一審法官對於二審改判後抵制的風險。

這種尋求二審法院的上級法院相對於尋求黨政官員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在一些極端情形中表現得尤其明顯。當一方當事人的請託尋租方是上級法院,對方當事人的請託尋租方是地方黨委,兩種意見發生衝突,地方法院必須作出二擇一的選擇時,會選擇倒向上級法院。
制度性的原因在於長期交易互動的期待。在普遍實行黨政幹部交流、避籍任職制度之下,地方黨委的負責人在一地任職,時間很短,幾年時間即會升遷、轉任,或實現隱含的層級內提升。這一組織人事上的政治設計,對於中國地方政治產生的影響之一,即是作為紮根於本地的法院法官,要考慮短期收益和長期收益。地方黨委的官員在任職避籍迴避、任期制下,與上級法院相比,是“流水的地方黨委”。
雖然主管院長和庭長有輪崗的規定,但只是法院內部分工和有限庭室之間的輪崗,要求是任期滿十年之後,而不是如黨政官員異地交流,而且這種輪崗要求因出自法院內部自律,在多地是並未執行的柔軟的規範。即使跨庭室交流,由於上級法院內設庭室分工更細緻,從民一庭庭長交流到本院民二庭或民三、民四庭任庭長,對於下級法院民事口來説,依然是對自己審判業務進行領導的上級法院庭長。而且副庭長以下審判人員不屬交流範圍。所以,上級法院的主管副院長和庭長、副庭長、分管某片區的審判長,代表的是“鐵打的上級法院”。
因此,對於二審案件的當事人,繼續尋求二審法院的上級法院進行尋租,就是一種可期待的行為。在實現可能性上,這種期待同樣是在成本、收益、風險量值的比值上,在地方黨委人大和上級法院之間進行對比時,後者更有效率。當然,對於(訴訟收益-成本)-風險量值>0,這一公式中拆解出的六個指標值,單獨看某一項,都容易找到例外,但是各種因素以乘積的方式,結構性的發揮作用時,尋求上級法院總是比訴諸黨政官員有效率,因此成為作為理性人的當事人的優先選擇。
八、餘論
以上只是制度邏輯分析,經驗上的結論趨向與此基本一致。
前述分析的結論,即尋求案外干預的當事人,尋求上級法院優先於尋求地方黨委、人大負責人,獲得了統計數據的支持。
以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檢察年鑑》刊載的案件為檢索對象,對從1987年出版以來至2012年期間,任職地方市、縣區的黨委書記、副書記,人大主任、副主任,包括政府正副職負責人,對其判決認定的受賄案件進行檢索,沒有發現一起受賄干預或影響民商事審判執行的,包括密集收受賄賂的被告人,如瀋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受賄69起,累計970萬,山東濟寧副市長李信受賄40起,金額450萬,安徽阜陽市潁泉區委書記張治安受賄30起,金額359萬。

馬向東
僅有的兩個例外,都不是批評和對策所劍指的縣區、市,而是是省一級的官員,一起是貴州省委副書記黃瑤與其特定關係人李季秋共謀,對一起股權上訴案件打招呼,收受賄賂245萬。另一起是曾任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省人大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的王有傑,受賄干預河南高院對河南銀基房地產開放有限公司與拆遷户回遷糾紛一案。
對於人、財、物受制於地方的流行敍事,究其實,與經驗偏差也極大。時下中院、基層法院院長高比例的來自上級法院的庭長,或副庭長下派任黨組副書記幾年後提任,而不是地方縣區委、鄉鎮黨委書記或局委辦主任,這一現象本身就檢證了地方黨委“保護”能力的衰弱。就財、物而言,雖然對於法院“兩庭”(審判庭、法庭)建設,財政多有傾斜性的保障支持,但法院每每以超出地方財政、經濟、社會發展和其他本地局、委建設的水平,修建規模巨大的豪華辦公樓,一旦地方財力無力支持,即被學界批評為法院財、物受制於地方。
當然,中國司法的表現具有極為複雜的面向。
依目前的管轄制度,目前80%的案件由縣區基層法院審理。兩審終審制下,中院是絕大部分案件的終審法院。在時下政制語境下,對於有強大交易能力的當事人,勾兑縣區、市級重要黨政幹部,給法院施壓,目前的司法體制並不能抗制。對於有極強的能力建立權力貼現、貨幣輸送關係的大資本所有者,制度設計尤無法防止。如果擴大樣本收集範圍,細緻篩查,找到市、縣區地方黨委、人大負責人干預司法的例證,是不困難的。
但是,對於地方保護這一相比較而言低概率、小比例發生的現象,研究者給予了過度的傾注,上級法院也極力將高概率、大比例發生的上級法院干預現象虛化,置於地方保護主義的陰影之中。
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説:執行難的原因主要有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法律制度不夠完善。原湖南高院院長吳振漢也提出:“應儘快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以避免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有利於防止和克服地方保護主義。”但此後兩人均因重大受賄犯罪而案發,分別被判無期徒刑、死緩,犯罪事實中多有干預下級法院案件。

由此可見,原本是上級法院常態性的干涉下級法院案件,但培育多年的地方保護主義話語成功地將批評鋒芒轉致到外部的地方黨委、人大、政府,遮蔽了最高法院對全國法院、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在審判、執行上,以個體利益為目的進行不當干預這一經常現象。
在中國政制架構下,地方各級法院,在制衡關係上,出自於兩個方向:
⑴垂直方向,來自於上級法院的“上訴審——審判監督”關係;
⑵水平方向,來自於地方黨委和人大的領導,以及同級政府對經費、物質保障上的制約。最高法院和上級法院三十年來通過“法院—研究者”話語互動,不斷反對地方黨委、人大的領導和政府的制約,形成具有控制性的反地方保護主義話語形態,在後果意義上,水平方向上的制衡逐漸弱化、淡出。缺省的空間,被研究者自然而然地理解為轉而由上級法院擔當,促使決策層頒佈政策,或支持法院自己出台新政策,加強最高法院對全國法院、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統管,使得垂直方向上級法院的支配權膨大,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控制強化。這改變了中國地方司法政治的結構,為今後地方政治治理帶來新的趨向。
(本文刊於《法制與社會發展》2016年第6期,原文標題為“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話語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