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從《婚姻法》的歷史看“離婚條款”問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最近幾則看似毫無關聯的新聞在各大社交媒體上引起了不小的關注,首先是某影評人在微博上又炒了一把“八千湘女下天山”事件,借苦難的歷史革命敍事之酒,澆“現代女權”之塊壘,效果還是很可以的,讀者被激起了如同當年建設兵團在天山打井挖溝一般的評論熱情。
然後微信朋友圈裏不斷被一個朱姓渣男殺妻藏屍案刷屏,此案引發了全國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也驚動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明星級女犯罪分析師李老師,她的精彩點評甚至能壓過案件本身的戲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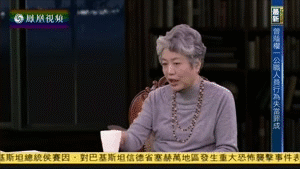
李老師在對朱姓渣男做犯罪心理分析
在春節後這個時間段,自然也少不了有關彩禮的話題,一張翻新版的“全國彩禮地圖”,外加各大高校的鄉村建設策劃師、鄉情觀察者們“述圖注經”,在這個很容易撕裂公眾意見的話題上,他們儘可能努力地找出了共識:農村女性的地位提高了,這總沒有錯吧。
有一個詞可以把上述新聞熱點串起來:婚姻。無論是八千湘女這樣帶有高度集體記憶的宏大歷史敍事,還是像彩禮這樣可以“禮失求諸野”的社會變遷的參照物,還是個人家庭悲劇透射的性別上的心理差異,都可以歸結於婚姻——這一最原始、最基本的人與人的“合作”模式。
《婚姻法》的誕生
從中國法制史的角度看,改革開放近40年來,“有法可依”這四個字,相比“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來講,走的路相對順暢和平坦,立法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截至2015年3月1日,我國現行有效法律243部,行政法規超過了700多件。在這些數量眾多的法律法規中,如果以歷史社會影響力、民眾反響度等指標加權分級,那麼新中國的《婚姻法》當之無愧的要排進第一等級,甚至在新中國歷史上的某些階段,《婚姻法》可以坐上“眾法之首”的交椅而毫無愧色。
因為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的特殊時期,《婚姻法》是和《土改法》、《工會法》等先於《憲法》而誕生的三大法之一。而且這三部法誕生的時間相差無幾(從1950年5月到1950年6月底),當時新中國“政體”未定,只是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職權,而且發佈的《臨時綱領》也只是臨時憲法的作用,所以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立法機關。在時間點上,婚姻法如此早的出台,是因為它太重要、太特殊了:它是向舊時代告別,建設新中國的宣言書。
細細研讀1950年《婚姻法》的各個條文,就很容易發現婚姻法包含了對人身權、財產權、兒童受教育權等多個方面的內容。當然,這也是婚姻本身的屬性所賦予的,因為人作為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以婚姻的形式締結“盟約”,絕不是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性與繁殖所能涵蓋的。那麼,倡導婚姻自由,保障婦女權益,必然要連帶解決財產權、教育權等諸多法律問題。
所以《婚姻法》乃是抽絲剝繭,對傳統舊有社會秩序進行大手術、大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從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入手,庖丁解牛,下學而上達,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題中之義,理解了這一點,才能從根本上理解為什麼我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同志曾經這樣説:“婚姻法是有關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僅次於憲法的國家的根本大法之一。”
某種意義上,1950年《婚姻法》的誕生是統一戰線下的全民共識,但共識之下未必沒有分歧,“和而不同”也是推動法制建設前進的動力之一。

1953年3月,天津人民電台召開了貫徹《婚姻法》廣播大會
1950年《婚姻法》誕生前夜,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是“離婚”問題。事實上這部法的精神軌跡承接了30年代中央蘇區的《蘇維埃婚姻法》,後者在該問題上是這樣表述的:“確定離婚自由,凡男女雙方同意離婚的,即行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亦即行離婚。”
黨內高層擔憂一旦確認了離婚自由原則,不利於家庭和諧和社會穩定,這對急需重建社會秩序的新中國來説很有可能是個隱患。但鄧穎超、何香凝等老一輩女革命家們還是力排眾議,堅持將離婚自由寫進了《婚姻法》,因為她們深知,當時中國女性被夫權和父權壓迫甚重,不以雷霆之勢重擊難以將包辦婚姻等沉痾剷除。
客觀上講,“反對派”的擔憂也不是沒有道理,1950年《婚姻法》實施的第一年我國各級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約為46萬件,之後,迎來了新中國第一個離婚高潮:到1952年,受理的離婚案子已經達到了106萬件,1953年更是暴漲到了117萬件。
自由離婚中的“自由”二字是法意理念的表達,或者是一種法的境界的言説,換言之,它只説明了“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程序要件,而沒有具體規定實體法律要件。而且對當時的離婚潮,各級黨委並非沒有心理準備,而且從司法解釋和實踐上,也確立了對離婚訴訟注重調解的程序原則,遵從了温情的人道主義關懷。

合作化時期《婚姻法》的宣傳畫
對待當時的離婚訴訟,如果用四個字形容就是“寬接嚴辦”。在中下層社會的治理層面,要理順舊時代遺留的反彈性、補償性的爆發的婚姻難題,為歷史還債,同時嚴格把控羣眾對離原因陳情的可操作度,這也是對有着悠久傳統的“寧拆廟,不破婚”的尊重,而對黨內的中高層幹部的離婚案件,則更嚴加一等。


解放前的黃克功案和50年代的王近山離婚案,體現了我黨在軍內“從嚴治婚”的原則
縱觀後來1980年、2001年這兩版《婚姻法》出台的過程,無不伴隨着學界和公眾對法條中的離婚問題的爭論,一個基本的批評就是“不夠細化,缺乏操作性”。
那麼,離婚表述是《婚姻法》史上的“阿基里斯之踵”嗎?
筆者擠地鐵去工地搬磚的途中,時不時會接過工作人員分發的地鐵報隨意瀏覽打發難熬的時光。幾天前就在報紙上看到這樣一則新聞,上海市黃浦區某孫姓女士,結婚一年多之後漸漸發現丈夫的一個小秘密:喜歡偷穿女人衣服。她實在無法忍受丈夫的這種易裝怪癖,提出離婚,二人最終訴諸公堂。法院判決結果是丈夫無明顯實體性過錯,駁回了孫女士的離婚請求。這則看似不大的新聞背後指向了《婚姻法》60多年以來從不缺少爭議的一個問題:離婚的法律要件是什麼?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新版《婚姻法》,其中對離婚問題的法律條文為:“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 應准予離婚。” 這是人民法院判決或調解准予離婚的原則和程序。這一規定清楚地告訴我們:准予離婚的案件,是以感情確已破裂為前提,調解無效,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表明一方或雙方沒有和好的願望,説明了感情破裂的程度,此應當准予離婚。
再對照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版來看:“男女一方要求離婚的,可由有關部門進行調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調解無效的,應准予離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二)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三)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滿二年的;(五)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蹤,另一方提出離婚訴訟的,應准予離婚。”

在《婚姻法》基礎上,2015年底通過了《反家庭暴力法》,圖為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説話》截屏
1950、1980和2001三個版本的《婚姻法》有關“離婚”條目的規定是很清晰的,1980年版着重強調了“感情破裂”是離婚的原則界限,2001年則細化、增加了可以判定離婚的四項依據,但總原則依然是“感情破裂”。
某種意義上,2001年版《婚姻法》對離婚一條的重大修改是當時30年法學界重點研討的結果。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不少法律界權威人士就“感情破裂”的界定提出很多質疑,認為此四字難以裁量和操作。哪怕是追加的四項依據,也存在語義的模糊性,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裁定“感情”這種帶有私密性質的、精神活動範疇,而不是社會關係和法律關係等實體性婚姻關係作為法律實施的範疇?
《婚姻法》絕不應該成為“離婚指南”
十多年前北大某馬姓女法學家提出的另外兩點質疑也很有創意:婚姻內容除去兩人情感生活之外,還包含性生活和物質生活,即便是兩人的情感交流已經終結或者破裂,理論上仍葆有和諧的性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可能,那麼“感情破裂”就不能作為評判婚姻形式中止的唯一標準;還有,認定“感情破裂”作為法定離婚理由,從邏輯上講,是假設所有婚姻的形成都以夫妻雙方存在感情(愛情)為前提,難道就不存在兩人一開始就沒有感情的婚姻嗎?既然婚姻的形成都未必以感情為前提,又為何在離婚問題上糾結情感問題呢?
馬教授的質疑頗有殺傷力,意指再次修訂婚姻法,增加對離婚這一條目的具體説明,順帶離婚後的財產分割問題(或許這才是資深婚姻法學家們的理論落腳點)。最近中國青年報的一則報道,在本來就有不少爭議的《婚姻法》“二十四條”之上又澆了一把油。
贊同者認為《婚姻法》保護債權者利益是理所當然的,反對者認為此條有程序漏洞且不人性化。指向的問題仍然是:離完婚的善後處理該怎麼辦?筆者受限於知識儲備,無法從技術層面探討“情感問題”的客觀化和二十四條的完善,只能從法理上略發陋言。

去年夏天,為買房而“離婚”擠爆民政廳的某地民眾
九層之台,起於壘土,讓我們回到對婚姻法最早期版本的源與流,刳形去皮,或許能找出《婚姻法》一以貫之的真正內核。
前文已述,毛澤東將《婚姻法》視為僅次於憲法的“根本大法”,其根本性就在於實踐性、入世性。在50年代初第一次離婚潮出現時,毛澤東在和劉少奇討論《婚姻法》反饋效果時,曾引用南宋哲學家陸象山批評朱熹的兩句詩“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競浮沉。”此語甚妙。婚姻法條的紙面文字功夫終究是“支離事業”,很容易流於文字遊戲的摳摳索索,背離了當初國家文盲率較高的社會現實,也未必合乎法律本身要求的事實正義: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家庭和睦。
良法美意,布在方策落於紙上,雖典章所定,亦難保奸邪者不會隨意曲解,法不良如果法吏賢達,社會尚可為治,如果法吏否惡,法律淪為訟棍搖唇鼓舌的工具,那麼即便是良法也無濟於事。這種“貶立文字,直達本心”的法制思路充盈着整個毛澤東時代,目的一方面是降低普法成本,最終目的是給落實事實正義爭取更多的實踐空間。
誠然,毛時代結束之後,對人治與法治,程序正義與事實正義的大討論推動了法治精神的進一步發展,然而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法意導向性”則像一盞高傲的燈塔指引整個法制界在不斷反思中前進。現代法學家對離婚構成要件的質疑恰恰能反證這種高傲:只有夫妻雙方真正以感情基礎建立的婚姻才算理想狀態下的法律婚姻關係,它應該、必然也必須得到法律的保護,美滿的愛情、和諧的家庭才是《婚姻法》終極關懷所旨。

李進和二妹子,毛澤東時代“完美婚姻”的一個範本,圖為電影《柳堡的故事》劇照
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為其下。以“感情破裂”判定離婚的法律依據看似在操作形式上落於下乘,卻為操作內容留有了很大餘地。俗人皆雲:法律乃是道德之底線,道德實在管不了只好拿法律來兜底。
筆者不是法律工作者,首先坦誠是個法學外行。但也明白平時要儘量避免法律糾紛以免誤了搬磚大業。法學家們孜孜以求的在法條中能求索出起居服食、好尚禁忌、朝野習俗、里巷慣舉,最好是連婚前婚後的彩禮以及財產分割、債務清算也做好規定以便按圖索驥,也許他們忽視了《婚姻法》的最高拔的呈現應該是“日用而不知,熟狎而相忘。”知法而忘法,這難道不是對社會道德、精神文明建設的反哺和提舉嗎?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