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登·S·沃林: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
……超越一切公民束縛。——莎士比亞,《第十二夜》,1.4.21
民主制似乎在野蠻失序和躁動不安中復活了。——亞當·弗格森, 《民間社會史論》,第一部分第十節
進入正文前,我想先討論自己對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以便讀者多多少少明白到底是什麼在指引我討論的方向。
在我看來,“政治的”(the political)表達的是下述理念:當通過公共協商,集體權力可以用來推動或保護羣體福祉時,一個複雜多樣的自由社會就可以享有共同性的時刻。政治(Politics)則是指有組織但卻不平衡的社會力量之間,圍繞集體公共權威掌控的資源而展開的正當公共競爭。政治是連續性的,無休無止。相比之下,“政治的”是間歇性的,難得一見。
民主制是“政治的”許多版本之一,其特別之處在於其理念在政治的其它版本中只是空談而已。出於下文將要討論的理由,我不想把民主制稱為一種政府“形式”,或是一種以“試驗主義”著稱的“政治”[1]。我認為,民主制是一項關乎普通公民政治潛質的工程,也就是説,關乎他們經由公共關懷的自我發現及其實現方式成為政治存在的可能性。
一
邊界在概念上覆雜豐富。各種邊界都宣示着某種同類,並且隨時準備抵禦異類。它們可能意味着排外主義:“非請勿入!”,也可能意味着遏制:“不許外出!”柏林牆的衞兵既關注不讓本國公民出去,又關注不讓外國人進入。在大多數現代政治對話中,邊界通常被視同邊境,邊境被視同民族國家,國家被視同政治的擔綱者。

霍布斯《利維坦》封面
這一組概念可以用霍布斯那給人深刻印象的主權權威隱喻來展示:主權者“擺出格鬥士的態勢”守衞着他們“王國的邊境”。在霍布斯的構想中,碉堡、要塞和槍炮所保護的邊境,把反政治的自然狀態與政治社會區分開來,與“臣民的產業”區分開來,也就是説,與主權權力所保障的私人狀況區分開來;霍布斯天真地希望這種私人狀況能淨化政治激情,防止政治激情挑戰主權對政治的壟斷。[2]霍布斯的方案裏沒有公眾也沒有正當化的政治;兩者的空間都被擠壓殆盡,擠壓它們的一方是以主權形式出現的絕對政治,另一方是受主權所保護的、絕對的、競爭性的自私個體的私人領域。。
作為遏制與排外的象徵,邊界孕育出限定空間的印象,相似的東西居住於其內:當地人之間的相似性、本族人的相似性、國族的相似性、或者享受相同權力的公民之間的相似性。相似是值得珍視的,因為它看上去是統一的基本成分。而統一又被視為集體權力的必要條件。然而,在十九世紀,與邊界相關的是由歷史和文化所界定的集體認同,亦即民族。民族主義過去是、今天仍然是各種邊界活躍的擴散勢力。民族主義把政治的融入到對同質化認同的追求當中,後者有時候經由種族清洗或強加正統宗教而提速。

雖然二十世紀行將結束,對邊界的重視卻並未減弱。相反它一直在加強。後現代文化政治和民族主義一樣強調邊界,邊界既確認差異(比如性別或種族政治)又宣示一致。政治也變得關乎淨化,或者更準確地説,關乎不潔與純潔標誌之間的逆轉,賤民、受害羣體被看作純潔甚至清白,而支配羣體反而被看作不潔。[3]政治以揭開壓迫的各種偽裝為中心,不管所宣稱的行為發生在昨天,還是遙遠的過去,不管是在古典哲學文本中,還是在兒童寓言、教科書、現代小説中,亦或在參議院的任命聽證會上。
對各種邊界的追求,一直與一個同質神話緊密相關,後者尋求建立一個在其中不再存在壓迫的文化圈。生活在同類中,人類這時就可以最終享有一種真正共同的東西了。這裏的夢想是一個政治的夢想,其中相似性被視為共性,純潔/清白被視為對抗權力政治的預防針。[4]
二
邊界是情境的輪廓;或者更準確地説,邊界象徵着情境化的願望。情境化在政治上象徵着政治的雙重內化。一方面,內部政治都有其獨特的慣例和形式,不同於其它同樣圈在邊界內的社會的慣例和形式,也不同於國際政治或跨情境間政治。另一方面,政治內化(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也符合詞典對內化的定義:即“馴化、馴服”。“祖國”(domus)是“馴化”(domitus)之地。
邊界約束什麼?各種邊界所限定的空間是如何填充或建構的?這種“充實”或建構在多大程度上與民主或者--更重要的--民主前景相關?邊界是一個關於遏制的隱喻。我將嘗試證明邊界隱喻所遮蔽的現實正是民主的遏制,而最關鍵的邊界正是憲法。
邊界約束着什麼?對於現代理唸的一些經典人物(如霍布斯、黑格爾、韋伯)而言,答案是:建立國家權威和權力的憲法。在這種讀法中,“政治的”是個活性元素,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擔任領導角色的人身上。政治領導既是集體慾望、怨恨、憤怒、幻想、恐懼和希望的管理者,也是民主幻象的管理者。[5] “政治的”聚焦在權力體系上,這個體系的使命是確保國內和平與安全(包括國家安全);推進、保障、監督、嵌入公民的物質福祉賴以存在的那些大公司的權力;裁決社會衝突,懲罰違法者,保持對社會的整體監控。
總之,這個權力體系一直持續努力調和或掩飾不變的國家與變動不居的政治之間的矛盾,前者是正義、公平、社會福利的守護神的象徵,後者則體現在瀰漫於經濟和文化領域的激烈競爭。[6]為了抑制這一矛盾,國家對其公民展開政治教育,灌輸忠誠、服從、守法、愛國主義和戰時犧牲等美德。通過這些德性實踐,國家鼓勵自身認同國家權力、鼓勵參與的表象、鼓勵自我利益的昇華。
人們很容易把民主和憲法“自然地”聯想在起來,好像它們彼此離了另一方都不完整;不少人會無意識地提起“憲政民主”,假定民主是這樣一種政治現象,其目的論的、以至於意識形態的終點是一種憲政形式。

簽署《大憲章》
這究竟意味着什麼?它意味着民主(即我們所瞭解的、自稱“發達工業民主制”的民主)已被建構出來了,也就是説,有了它的形式、結構和邊界。憲政民主就是配備了一部憲法的民主。它不是民主或民主化的憲政主義,因為它是沒有人民作為行動者的民主。正如其捍衞者所聲稱的,它的政治不是基於“代議民主”,而是基於呈現民主的各種形式(various representations of democracy):即以民意調查、電子市鎮集會、熱線電話節目等形式呈現出來的民主,以及以投票形式呈現出來的民主。總而言之,憲法規範着被許可的民主政治的度。
關鍵制度是總統制。
作為首席執政官,總統是現代希望的象徵:政治例行化為政策,理性化為行政;正如教科書不斷提醒的,他同時也是人民整體選舉的政治家。因此,他就是行使管理職能的護民官;他就是民主和理性。同時,他又是人民軟弱無力的痛苦符號,更是憲政民主制下的最高職位。人民對於總統的所作所為無能為力,然而選舉結束後,選舉這個近乎神話的舉動卻被作為神壇儀式保存下來,每當總統什麼時候覺得有必要謀求公共支持時,他就會談起自己在選舉中的戰績。
投票融入了一個流暢的過程,它與人民之間的虛幻聯繫經由參眾兩院議員的定期選舉以及媒體制造的無盡評論一直在延續。結果就是一個由民主選舉啓動的永恆政治運動的幻象。與之同時,平行的過程政治(立法、行政、司法與軍事)各自主動地持續運行。選戰成為諮詢顧問們叫賣的課程,而人民很快就被全然拋到腦後。現在,他們必須通過電視明星的宣示、脱口秀的胡言亂語、以及大腕編造的政治滑稽戲來了解政治,既間接又消極。

這樣,當憲法為政治設定界線時,它同時也為民主設定了界線,其設定的界限一定與社會中佔支配地位的權力羣體合拍,並使之正當化。
憲法不僅關涉政治活動合法與否,也規制着政治的度、政治的時間節奏或週期頻率,並使之具有儀式化的形式,比如,每四年一次,在選票上這個或那個總統候選人的名字旁打上標記,據説這就是“表達人民的聲音”的機會。在政治經濟學中,選舉意味着雙重“自由”(譯註:英文中free意味着“自由”和“免費”),一方面沒人強制公民去投票,另一方面選民不必為行使投票特權直接付費。選舉的成本由社會中佔支配地位的羣體承擔,他們負責選戰的組織、運作與出資。對他們而言,選舉是投資機會,他們希望能夠從中獲得豐厚的回報。
三
但是,出於與霍布斯完全相反的理由,一些後現代作家很討厭作為邊境的邊界理念。邊界意味着,國家預設個體的關切和義務的重心應該放在在國家控制的邊境之內,儘管事實上,當代個體可能會覺得她最深沉的關切是外國女性中的特定羣體,而不是本國同胞身。
還有別的理由挑戰霍布斯式的“邊境”概念:對於主張所有人類現在都住在一個電子“全球村”的人來説,它過時了;對於關注某些嚴重問題的人來説,它是塊絆腳石,因為諸如污染、饑荒、侵犯人權、核武器和流行病之類問題,其原因與解決之道都超出了政治邊界。這樣一來,邊界對早期現代而言意味着哪裏是政治的界限,而對後現代來説,它們是其侷限性的標誌。[7]
為了努力超越各種邊界,持這些觀點的人通過一方面保留與共享的關切和價值相關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把它們擴展至包括全人類來擴大政治的範圍。但是,政治的概念複製了與代議制政府相關的概念,即一種受託人或管家式概念,他們以別人的名義或為了別人的利益而行動,外加不言而喻的假設(同樣為代議制政府的現代鼓吹者所篤信):絕大多數“別人”確有自己的“利益”,但對如何保護或促進它卻沒有條理清晰、理據充分的看法。後現代範本的最高政治表達是里約會議(Rio Conference),在那裏超越邊界的人類利益代表與主權國家的代表面對面開會。
四
由於有關邊界的疑雲重重,作為邊界的捍衞者,現代國家總是看起來荒謬、甚至過時。很多現象似乎在逃避或超越邊界,比如電子通訊就常被用來作為後現代確實存在的力證。如果真是如此,這種發展就不僅僅可以使我們對國家的未來及其有關政治的概念有更多瞭解,也可以使我們對後現代的民主或非民主傾向有更多瞭解。

在漠視邊界上,後現代並不孤單。現代國家所依賴的權力形式在邊界問題上是相當隨意的。現代國家權力與現代科學與技術是分不開的;而後兩者都是邊界超越者,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有自己的場域。此外,現代國家權力還嚴重依賴市場。市場活動也對民族邊界漠不關心,也具有自己的氣質場域。
另外,從一開始,那些聲稱擁有系統知識的傢伙們就對現代國家的形成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他們聲稱這些知識會增強國家權力並讓其根基更加牢靠。律師、金融家、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塑造了國家官僚機構;但隨着他們的技能更為系統化,甚至更科學,他們也更多地帶上了普遍主義特徵。
與古代王室一樣,現代國家也期待自己的權力獲得智識和藝術化的潤色。它給作家、藝術家、演員、音樂家和學者資助和榮譽,後者回報以自身貢獻。肯尼迪中心就像貝爾實驗室一樣是國家權力的象徵。不過,當代藝術家、學者和知識分子也是跨國際運作,在任何地方表演都顯得賓至如歸。
最終,儘管國家本身是出類拔萃的邊界維護者,它同時也是偉大的邊界挑戰者,尋求向國外投射自己的權力,上面描述的那些羣體當然貢獻良多。我們順便強調一下,國家權力的每個要件,科學、技術、經濟和文化,都是精英主義不可磨滅的展現。
祖國因此就等同於一個操作總部,一個投射現代形式的權力的發射台。祖國的憲法提供了一個穩固的基礎,為國家確保了人力和物力資源的穩定供給。“發達工業民主制”的民主化歸根結底就變成了這麼一回事:勞動、財富和公民心靈同時得到防禦與剝削、保護與壓榨、養育與榨取、獎勵與控制、奉承與威脅。
五
我們所熟悉的民主是憲法化民主,這種民主與其憲法形式難分難解。其現代意識形態理據可以從哈林頓、英國共和派、《聯邦黨人文集》和托克維爾那裏發現。它們都是民主的批判者。它們都是對革命的反應,儘管不是反動的反應。它們憲法的建構都是為了反民主;不過它們都尋求約束民主,而不是禁止民主。要為民主留下“一席之地”,如美國建國者就設立了一個眾議院,否則,打着“主權人民”幌子的正當性就會喪失其全部可信性。

美國眾議院
現代憲法化民主的理論家之所以試圖抵制民主,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古典理論的理由一模一樣,也與早期現代政治思想的理由一模一樣。因為民主的幽靈無法無天,並且傾向於暴力。據讓·博丹説,“平民國家從來都是所有無法無天的精靈、造反者、叛徒、流浪者的避難所,這些人鼓勵並協助下等人顛覆上等人。他們對法律完全尊重。”[8]麥迪遜也警告説,“[純正的]民主帶來的從來都是大動盪與大沖突;它們與個人安全或財產權完全不相容,並且通常是短命的,因為它們總是死於暴力。”[9]
托克維爾曾經抱怨説,沒有任何不經革命而生的民主;他着手創造一個民主,聲稱美國民主之所以穩定的原因在於,與法國不同,民主在美國不是革命的產物。[10]托克維爾熱衷於將民主與革命分離開來,同時他又擔心找不到這樣的先例,這就不由人不發出疑問:這兩個現象為什麼會相互關聯?這種關聯揭示了民主的什麼特徵?
這些民主失序印象所包含的事實是,歷史上現代民主和古雅典民主都是與革命混雜而生的。在所有情況下(公元前五世紀,1640、1776年和1989年),都是革命激發出民主的理念,急劇擴大了政治參與者的範圍,把過去被排斥或邊緣化的社會各階層都容納進來。
在這裏,我們可以將革命界定為將過去的形式推倒重來。它與一部固定的憲法完全處於矛盾的兩極,不管這部憲法採取成文形式(如“基本法”),還是採取不成文形式(獲得認可慣例)。民主誕生於叛逆行為,如果不打碎將自己排除在外的階級、地位和價值體系,人民就無法分享權力。
六
人們通常認為,我們稱之為成體系的政治哲學,始於公元前四世紀雅典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現代那種讓哲學為解釋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設定條件的趨向,遮蔽了古代思想家的另一個功績。他們也創造了憲政主義,創造了憲政理論和政治學。他們希望憲法可以為公元前五世紀的民主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雅典憲制民主化進行一次慎重的消毒。
憲政理論旗幟鮮明,它力促用政治的來綜合政治體的整個生活,把它封禁在一個既定的形式當中,然後在一個憲法分類框架中分佈或圈禁政治生活的多樣性。然而,這種抱負有一個內在張力,甚至在柏拉圖《理想國》的典範形式中,這個張力也很明顯。
在對話的一個當口,蘇格拉底宣稱:“我們建立這個國家的目標不是為了使某個階級特別幸福,而是為了城邦整體的最大幸福”(420c)。然而,在設想了這個理想型團結機制之後,蘇格拉底開始描繪理想社會的輪廓,在其中存在再鮮明不過的階級分野,亦即上等階級與下等階級的分野。在亞里士多德的三部井然有序的憲法中也出現了這類共同性與排斥性的問題。每一部憲法都取決於能否將某些獨特的社會成員從政治公民中排除出去。[11]最後,亞里士多德不得不承認,每一種憲制形式,都體現了一個統治階級的價值和利益,因此每一種憲法都或多或少地缺乏共同性。[12]
這些張力也很明顯地保留在西塞羅的《共和國》中。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就是西塞羅的蘇格拉底,他借西庇阿之口討論了每種常見的統治形式,包括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在現存手稿中,最長、最系統的討論集中於“人民權力最大”的城市國家(1.31.47)。在舉例説明民主制時,西庇阿宣稱只有民主(res populi)才配得上共和國(res publica)這個稱號(1.32.48)。

共和國不僅是指稱西塞羅時代羅馬政治體制,也是對羅馬人如何理解政治的精萃描繪:政治的就是人民共同關注的、屬於所有人的。具有這些含義的res publica在意思上更接近於拉丁語中“民主制”res populi,而不是指包含了貴族制、寡頭制或君主制三種成分的混合體制。【譯者注:西塞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共和”(res publica)這個詞】
幾個世紀以後,卡爾·馬克思評論説民主制是所有憲法的基礎,意思是説每部憲法都表示要尊重共同性的原則,卻從不允許人民來統治。[13]在整個歷史上,不難發現總是存在利益被剝削的社會羣體,以致於共同性本身成了一個笑柄;這些社會羣體也一直沒有積極參與政治的機會。[14]
民主與如何劃定政治的無關,而是與它如何被體驗有關。革命激活了人民,打破了禁止政治體驗的各種邊界。被排斥的社會階層開始擔負責任,協商目標與選擇,共同做出後果顯著、影響未知而遙遠的他者的決定。因此,革命反叛就是人民讓自己變成政治的方式。人民通過內部衝突(stasis)而非自然生長(physis)來獲得一種公民本性。
平等觀念就是對各種社會與政治邊界的超越,這些邊界是政治排斥的先決條件,進而也是經濟剝削正當化的先決條件。伴隨這些邊界形成的還有一些看似神聖的價值,比如高貴的出身、財富、軍事威力以及某些形式的神秘知識,擁着這些玩意就可以主張權力,從而獲得官職。被排斥者(如農民、工匠、技工、外國居民、女性、奴隸)所代表的價值和美德充其量都沒有什麼意義,儘管他們的活動是社會存在或美好社會“所必要的”,如同亞里士多德所承認手工工匠和奴隸的作用一樣。
雅典民主的故事是一連串大眾起義的故事,造反成功改造了所謂祖傳的憲法,跨越了它劃定的種種邊界,最終,用阿波羅多洛斯的話來説,就是“雅典人民對政治體內一切事務享有至高權威,可以為所欲為”(59.88)。
但是,當革命結束、政治的制度化開始後,由革命帶來的民主看上去卻顯得像是過剩的民主。
要了解政治的範圍是如何收縮的,可以看看洛克《政府論》第二篇中呈現的兩種狀況的對比:一方面,在自然狀態中,每個個體必須運用自己的判斷去執行自然法,即,參與是普遍的、義不容辭的、但又變動不居的;另一方面,洛克假定政治社會必須有三個前提:“一部確定、穩固、人所周知的法律”、“一個人所周知、不偏不倚的法官”,以及有效的行政。[15]
這也就是説,就其性質與特點而言,政治的已經專門化、例行化和行政化了。制度化就標誌着民主的衰減:領導開始出現;等級制開始形成;形形色色的專家環繞在決策中心;命令、程序和先例取代更自生自發的政治:回顧過去,後者看上去比較混亂,沒有效率。[16]民主似乎註定只是一個時刻而非一個形式。在整個政治思想史上,實際上所有作家都強調了民主的不穩定和短命的特徵。[17]為什麼民主會被形式壓扁甚至被壓得氣息奄奄?為什麼其存在如此短暫,如此難以抓住?
七
為了嘗試闡明這些問題,我想轉向現代政治理論的負重老馬:自然狀態,尤其是洛克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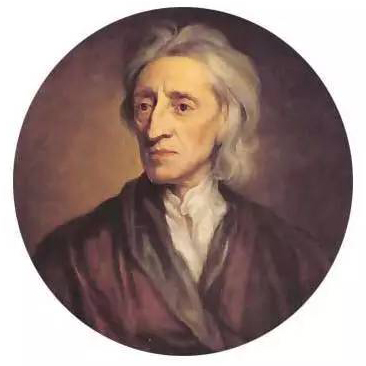
儘管在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中,邊界觀念顯然不起作用,是一塊前政治狀態的領地,但對洛克來説,自然狀態是一個被自然法“約束”的狀態。法律“約束”的是一種共同性狀態,是“沒有從屬或隸屬關係的平等”。我們也許可以把洛克的建構稱為沒有形式的民主制。在那個“自然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有義務通過執行自然法“維護人類的其他部分”(2.4.6)最初,所有人共同擁有大地,包括其自然的“果實”以及“所養活的牲畜”(2.26)。這樣,只要存在這些公共元素,只要每個人都履行護衞自然法的公共角色,這個狀態就可以稱之為政治的、民主的。
但是洛克自然狀態中“自然”的共同性似乎是人造的,因為它近乎絕對同質化。從現代的、麥迪遜式視角觀察,它看上去缺乏現代頗為常見的利益衝突。
儘管在描述自然狀態中的私人財產和貨幣起源時,洛克暗示了異質元素,但一旦他的討論開始明確契約這個主要問題,異質性就被懸置了,在共識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只有一個例外,正如我們將很快將會看到的。當締約時刻到來,財產、階級、宗教、性別、種族、種姓或語言差異就消隱了;或者更準確地説,過去承認的差異,如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主僕之間,就被洛克視為特殊情況,因為它們不是政治的(2.80-86)。洛克在準備討論契約時,他忽略了這些差異,因為如果不假定民主共性的同質化,洛克就會缺乏在相似個體中間實施協議所必要的機制。
基於同質化,非差異化的權力有了可能。在洛克提出基於單一但不出類拔萃者同意的多數理念時,同質化的力量最明顯地表現在洛克用於引入多數這個概念時,按照他的説法,多數產生於一羣同一的人而不是單一的人:“當一些人基於每個人的同意組成一個‘共同體’時,他們就使這個共同體成為一個整體,擁有作為整體而行動的權力,整體的行為服從大多數人的意志與決心”(2.96)。
洛克的假設在於,一個“有權力作為一個整體而行動”的共同體,由平等而無差異的基本單位組成,每個單位同意行動的分量具有相同的分量。它們加總在一起,讓共同體有能力作為整體而行動:“整體的行動以較大力量的意向為轉移,這個較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數人的意志與決心”(2.96)。然而,當洛克試圖應對下述觀點時:“一個整體”似乎暗示全體一致而非大多數人,“大多數人”的説法就是承認在自然狀態中,異質性而非同質性、不平等/差異而非平等/相似性大行其道,他不得不回到質疑自然狀態存在利益同質性的常識性理據。全體一致是一個不可能的行動基礎,因為“必然會有很多人因病、因事而被排斥在公共集會門外,儘管其人數遠不如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的總數”(2.96)。
但是,洛克隨後繼續從自然狀態的同質性立場後退:“意見分歧和利害衝突在一切人的集合體中總是難免的”,那麼“堅持全體一致就只會以共同體解體告終”(2.96)。因此,自然狀態的同質性原來只是異質性的懸置。
然而,自然狀態與其説是個虛構,毋寧説是個消失的共同性的隱喻,不斷出現的革命危機時期是一種例外的時刻,那時權力迴歸“共同體”, “人民”自己重新成為行動者。革命中的民主時刻是共同性的載體,是政治的良心:“每個人在參加社會時交給社會的權力,只要社會繼續存在,就決不能重歸個人,而是將始終留在共同體中”(2.243)。
現在也許可以重新闡釋同質性了。當洛克所説的個體置身於遵守自然法的義務之中,把他人視為自由而平等的存在,他們創造的是作為規範的同質性,而不是作為描述的同質性。
八
即便有任何民主制曾經繁榮過,只要人民不是數量很大,實力很強,以至於因為運氣好而傲慢,因為有遠大抱負而非招致嫉妒,其高潮只會很短暫。——Dion Cassius 44.2

異質性應該出現在洛克的自然狀態不是因為其普遍或自然,相反,異質性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個後果,自古至今這兩個價值只會與民主關連在一起。
[18]正如托克維爾對傑克遜時代美國的評論,民主的平等極大地釋放了人的能量,其後果是源於個體的自然稟賦、運氣和環境差異而產生的社會不平等。[19]再加上民主的自由特性遮蔽了反民主的權力形式,公司成為享有相同權利的“人”,其高層享受普通公民享受不了的很多豁免權,民主難以抓住的特徵也就沒什麼神秘之處了。因為民主的自由鼓勵多樣性的表達,“人民”這個説法暗含的同質性便開始碎片化了,其中某些碎片比別的更加支離破碎。多元文化主義和跨國公司不是等價物。
替代這種失去的同質性和人民權力的是多數決;但憲政主義,尤其是麥迪遜版的憲政主義,是用來盡最大可能限制民主權力的。
九
我一直在試圖確定民主的哪些方面與古代和現代憲政主義內在的組織衝動之間存在張力。這個張力表現為下述事實:
從雅典被馬其頓帝國侵吞以後,民主沒有連續的歷史。在公元前322年到十八世紀美國和法國革命所開啓的政治實驗之間,有幾個城邦共和國的例子,人民偶爾掌握一小部分權力,但壓倒性的證據表明,它們主要是富人和出身顯貴者支配下的寡頭制。再往後我們看到的是現代革命的失敗導致民主希望的破滅,是創造出民主的現代形式,民族國家組織。今天,民主被普遍視為政治體制正當性的唯一真標準,據説其實現形式由選舉自由、政黨自由和言論自由組成。當然,還有市場自由。既然説得這麼具體美國便定期派遣專家奔赴中美洲,確定這些要件是否具備。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幾乎沒有人質疑自我宣稱的“發達工業化民主制”是否真正的民主,但更少有人敢辯稱“人民”在任何此類民主中實際行使統治權力,或者人民統治是個好主意。在那些經理統治大行其道的社會,民主看上去天生粗糙,因此不適合治理的任務複雜和迅速變化的社會。同時,這些地方經常宣稱民主要求這種來自公民的高度政治修煉,從而使人懷疑第三世界人民能否領會掌握。由此説來,民主制對於複雜社會過於簡單了,對於簡單社會又過於複雜了。
民主的正當性要求實際測量的不是那些國家民主的活力,而是民主衰變後服務於其他目標的程度。這些目標中最基本的是建立和發展現代化國家。所謂當代民主困境不是人們經常所説的,古代民主概念與現代政治社會的規模和範圍不相容。而是任何植根於作為行動者的公民和參與性政治的民主概念,都與國家的現代抉擇不相容,這個現代抉擇即國家成為政治生活的固定核心,而相關的政治概念就是持續圍繞單一主導目標的活動,即控制或影響國家機構。
晚近現代世界的民主不可能是一個完整的政治體系,考慮到現代權力形式的可怕潛能,及其從社會和自然世界所榨取的東西,民主也就必然沒有希望,沒有什麼值得為之奮鬥之處。
我們需要把民主重新理解為某種非政府形式的東西:它以痛苦的經驗為前提,註定只能在短時間內成功,但只要政治的記憶存活,它就是一種讓人嚮往的可能性。這種民主經驗見證的是存在的政治模式可能、也確實會週期性喪失。波利比烏斯説過,民主迷失在了“時間流程中”(6.39)。民主是一個政治時刻,也許就是唯一的政治時刻,既是政治的被銘記和再造的時刻。民主是一個造反時刻,它可能呈現革命的、破壞性的成分,也可能不這樣。
今天,訴諸政府循環或者自然狀態的做法不再流行。然而,也許可以這樣説,相信民主的復元力量仍是美國政治意識的一部分。某些事件支持這個信念:建構政治社會和實踐的週期性經驗,始於殖民時代,貫穿革命時期,超越向西部移民,數百個新定居點和市鎮在西部建立;廢除奴隸制運動,以及根據種族平等原則重構美國人生活的失敗努力;十九世紀平民主義和地權論者的反叛;工會自治鬥爭和女權鬥爭;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最近幾十年的反戰、反核和生態環保運動。

馬丁·路德·金
對到底什麼構成了復元時刻當然一直有爭論。古代歷史學家聲稱,作為對波斯戰爭領導地位的結果,雅典之所以可以確立了對希臘的霸權,正是由於民主所激勵出來的能量和才能。在最近的波斯灣戰爭中,美國領導人把美國人的軍事勝利歡呼為一個新的復元時刻。“沙漠風暴”代表的不是民主的恢復,不是人民拿回了原本屬於自己的權力,而是某種療救,某種“治癒越南綜合症”的處方,進而恢復了美國的團結及其作為天下第一的世界地位。這種對復元時刻的理解代表着一種180度的逆轉,把戰爭狀態而不是自然狀態作為了復興的條件。
“沙漠風暴”或者憲政民主國家所打的波斯灣戰爭,證明了依靠現代國家權力尋求民主復興不會有任何結果。復興的可能性取決於一個簡單事實:普通個體有能力在任何時刻創造共同性的新文化模式。
個體齊心協力建造低收入住房、工廠工人所有制、更好的學校、更好的醫保服務、更安全的飲用水、污水排放控制以及關係日常生活的上千其他共同關切,這就是在經歷一個民主時刻,就是在為發現、關懷和照料共同關注的共同性做貢獻。這些行為不經意之間對政治的進行了復興,因為他們挑戰了不同形式的權力不平等,而這些不平等正是民主的自由和平等使之成為可能的,民主制只能通過背叛其自身價值觀念才能將其消除。
但是,復興還必須基於不太簡單的事實:存在一系列地域性的民主體制無法解決的問題和暴行。與多元主義一樣,除了訴諸一個更寬泛政治的、極易消失的同質性以外,利益集團政治、多元文化政治、地方主義都無法克服其種種侷限。
請回想一下波蘭團結工會這個引人注目的案例,這是一個其成分高度差異化的運動,包括社會主義者、藝術家、教師、牧師、信徒、無神論者、民族主義者等等。然而,團結的一個字面含義就是“共同體或利益(或利益之間)的完美一致”。[20]顯然,同質性那時不是、現在也不必等於沉悶的一致,就好比平等不等於把所有人扯平一樣。我們真正需要理解的是什麼才是政治上生死攸關的:異質性、多樣性和多重自我與權力的形式完全不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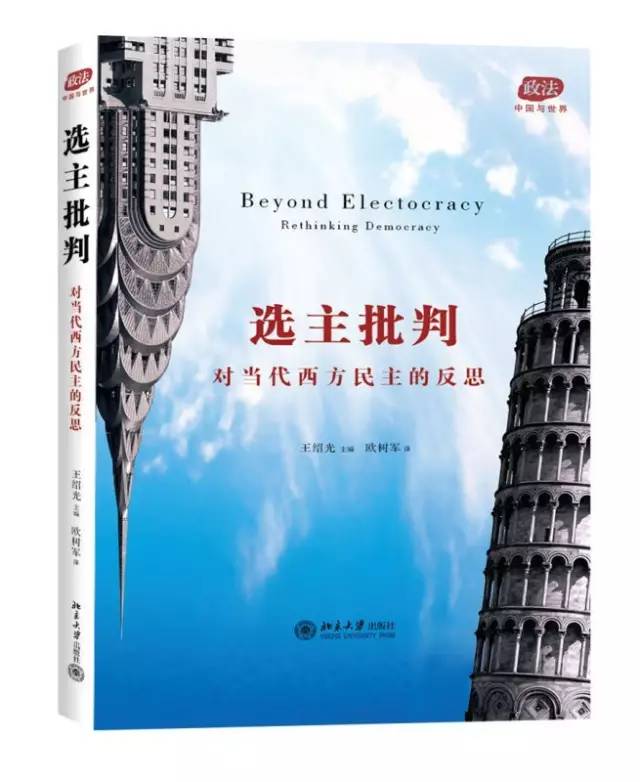
(本文選自王紹光 主編、歐樹軍 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35-151頁。)
參考文獻:
[1] 我對這一主題的更詳盡討論,見於"Norm and Form," in J. Peter Euben, John R. Wallach, and Josiah Ober, eds., 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Michael Oakeshott (Oxford: Blackwell, 1946), 83.
[3]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Harmondswonh: Penguin, 1970), esp. 137££.
[4] 更充分的討論,參見我的"Democracy, Difference, and Re-Cognition," Political Theory 21 (1993): 464-83.
[5] 對技藝(techne)概念的更詳盡處理,見於John Wallach’s forthcoming The Platonic Political Art.
[6]馬克思的“猶太人問題” 仍然是對這個矛盾的經典討論 。
[7] See William E.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Jean Bodin,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trans. M. J. Tooley (Oxford: Blackwell, n.d.), book 6, chap. 4, 192-93.
[9] The Federalist, ed. Jacob Cooke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1), 61 (no. 10).
[10] 托克維爾的抱怨,see jean-Claude Lambeni, Tocqueville et les deux dtmocrati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 180. 托克維爾將美國民主與革命分離開,參見他的Oeuvres Completes, ed. J.-P. Mayer (Paris: Gallimard, 1969-), 1.14.
[11] 我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如何處理民主制的更充分討論,參見我的文章"Norm and Form." The quotation from Plato’s Republic follows the Shorey translation in the Loeb series.
[12] Aristotle, Politics, 3.5-6.1278b6-15: “現在,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公民身體是主權;公民身體是憲法。因此,在民主制中,人民是主權;在寡頭制中,少數是主權。”Trans. T. A. Sinclair, revised Trevor J. Saunder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1).
[13] “民主制是通用憲法…它 是一切憲法業已解開的秘密。”Karl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ed. Joseph O’Mal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9-30.
[14] 古代世界對這一主題的討論,see G.E.M. de Ste. Croix,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London: Duckworth, 1981), 278-300.
[15]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1: 124-26. 當洛克討論“人民的多數”的革命權利時,放大的政治再次出現。(11.209).
[16] 五世紀雅典民主制訴諸於抽籤、輪換、陶片放逐法等大膽舉措,來維護直接民主,但在六世紀,它開始出現米爾斯的寡頭制鐵律症狀。See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 See, e.g., Plato,. Republic 7.563e-564a; Laws 70la; Polybius, The Histories 7.9; Philo, De Confusione Linguaram 23.108; De Fuga et lnventione 2.10,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4.20.8; Sir Thomas Elyot, The Book named The Governor 1.1; Claude de Seyssel, The Monarchy of France 1.1; David Hume, “Of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74; and The Federalist, no. 10, p. 61, and no. 14, p. 84.
[18] Plato, Republic, 8.557e-58a; and see Laws, 3.693d.
[19] Tocqueville, Journey to America, ed. J. P. May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51, 156.
[20]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entry 2 s.v. “solida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