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菲茨傑拉德:我們生活在中國世界,但澳中關係卻未能與之匹配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1973年4月,我帶着一份如今已成為歷史文物的信函飛赴北京。這封長達8頁的信函是時任總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1972年12月21日,在當選總理後僅幾周內,高夫·惠特拉姆總理就推動澳大利亞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與我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對20世紀70年代初還處於封閉當中但又試圖擺脱孤立境況的中國來説具有里程碑意義。高夫·惠特拉姆又被人們尊稱為“中澳建交之父”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觀察者網注)委託我——當時的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帶往北京的。這封信論述了他對澳大利亞發展對華關係的構想,以及對澳中關係的長期願景。

本文作者、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史蒂芬·菲茨傑拉德(資料圖)
這封歷史性信函的主旨其實仍然切中今天的現實。惠特拉姆總理在信中寫道:“我們希望在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礎上發展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就像我們與其他大國之間建立的那種關係一樣”。這裏“其他大國”,我想他指的是美國、英國、印尼以及日本。從這一措辭可見他當時非常重視對華關係,這意味着他希望澳中兩國在政府和民間層面能互相熟悉、緊密合作、溝通順暢、互信牢固而且兩國能夠在互動中對對方產生某種影響。
當然,惠特拉姆總理也認為,澳大利亞還應在澳中關係中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並在某些問題上對中國講出我們的不同看法。但令人遺憾的是,澳大利亞從未能與中國發展出上面描述的那種關係。而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與中國建立“像我們與其他大國之間建立的那種關係一樣”的關係。為什麼?因為今天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中國世界”裏,但澳中雙邊關係卻並未能與這一現實相匹配。
下面我介紹一下我與惠特拉姆總理1967年初次見面時他跟我講過的一個觀點:如果我們不能把美國搞清楚,也就無法把中國搞清楚(we can’t think clearly about China if we can’t think clearl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而現在美國出了一個特朗普,當下正是我們應趁機把美國好好搞清楚的關鍵時刻。
特朗普不僅把美國的體制和政府弄得亂七八糟,還犧牲了美國的安全並且使國際政治秩序遭到了破壞。對於澳大利亞來説,我們過去從沒有很冷靜、理智地思考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我們過度依賴美國,缺乏獨立性,我們對參與美國對外戰爭行動毫無疑慮,甚至有人天真地認為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高度一致,無論發生什麼,美國都會照顧我們的利益,而如今特朗普的當選已將我們上述心態所帶來的風險充分暴露出來。
如果你作為一個澳大利亞人曾毫無原則地接受美國的價值觀,比如説接受美國對槍支的態度、宗教在美國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富豪對美國政府的影響等等,那麼特朗普總統的價值觀對你這種一直以來毫無原則的接納態度來説就是一種侮辱和打臉。但是,我們的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和他手下的部長們卻對當下美國的新情況毫無察覺。這將嚴重損害澳大利亞的聲譽,我們對國際舞台上具備高度道德感的人物所表達的敬意將聽起來有些虛偽,而當我們在價值觀問題上與某些國家(比如中國)發生齟齬時,我們甚至將顯得荒謬可笑。

1973年4月,周恩來總理接見史蒂芬·菲茨傑拉德(資料圖)
在澳大利亞,沒有人認為我們與中國人有共同的價值觀,這一點在澳中關係中幾乎是個先驗的、預設的條件。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一事實意味着,我們強化與中國的關係是非常必要且非常緊要的。而且眼下這一必要性和緊要性超乎歷史上任何時期。澳大利亞現在必須重新思考我們外交政策的大方向,而且要重新評估中國、亞洲以及美國各自對於我們的重要性。
很多澳大利亞人和政治家一定都聽到過下面的事實(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真能明白這些事實意味着什麼):中國是亞洲第一強國,同時也是個世界大國;中國是美國霸權的挑戰者,一個經濟巨人;中國是澳大利亞、新西蘭、東盟、日本、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且是這些國家最重要的投資來源國。中國就在我們不遠處,是個永遠也搬不走的龐然大物。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中國在澳大利亞國內的存在,這個國家已經對我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多澳大利亞人並不理解這意味着什麼,可能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中國已經對我們產生巨大影響這一事實。
2007年,傑出的澳大利亞國際問題專家考拉·貝爾(Coral Bell)發表了一篇標題聳動的文章《西方世界支配非西方世界的時代行將結束》(The End of the Vasco da Gama Era),文章的觀點如其標題:不受挑戰的美國霸權時代已經走到盡頭了。
美國霸權時代結束之後,還沒有另一個霸權國家可以定義即將到來的全球新時代。但是在亞洲,一個可以稱之為“中國時代”(Sinic Era)的新歷史階段已經開啓。其原因不僅在於中國的財富和實力,除經濟因素之外,中國的政治動態和社會生活對我們的影響力也在與日俱增。
中國的資金和基礎設施建設能力,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所帶來的遊客、商業活動、留學生以及移民,來自中國的鉅額資金(國有資本或私人資本、合法流入資金或灰色資金),中國的商業文化,中國國家資助的各項活動及其對我國華人羣體的影響,凡此種種,中國已經對澳大利亞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們的社會如何運轉、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決策過程,甚至我們的思維方式都未能逃離這種影響。截至目前,這種影響還未體現出任何威脅或危害我國利益的跡象。其實,中國與我們的接觸大多數是友善的、對我們有利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定位並管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史蒂芬·菲茨傑拉德與江澤民總書記在一起(資料圖)
現在我們來看看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這種影響力是如何作出反應的。從政治上説,澳大利亞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堪培拉(澳大利亞首都——觀察者網注)的那些政客、某些親美智庫以及為上面兩者所利用的媒體似乎仍陷在已經過時的對華思維中無法自拔,他們將中國視為對美國的安全威脅以及對美國權威的一種挑戰,他們眼中的中國似乎是個一成不變的符號。他們拒不承認中國對我們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他們也不認為當下中國帶來的挑戰與以往有何不同。他們之所以秉持這一態度有很多原因,其中我認為有三點非常重要:
第一,目前很多澳大利亞人還難以接受中國對我們有強大影響力這一事實;第二,澳大利亞政府未能在教育體系內加強漢語學習和對中國的研究。在國會里,幾乎沒有一個人懂中文,在我們的各大政府機構裏情況恐怕也是如此;第三是政治意願,自911恐怖襲擊發生以來,澳大利亞軍方和情報部門與美國的合作日趨緊密。
除了極少數人士,澳大利亞大多數政界人物以及情報機構和軍方人士似乎都對美國看問題的視角和思路有一種極具慣性的依賴,他們似乎懶於跳出美國的框架去獨立分析世界局勢,無論伊拉克問題、阿富汗問題還是敍利亞問題都是如此。如今他們看待我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依然未能脱離美國人的視角。
我不是説要他們的態度轉變180度,一切唯中國馬首是瞻。只是現在,我們必須打破依賴美國的思維慣性,這樣我們才能把中國看清楚,我們才能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與中國打交道。現在是我們澳大利亞而非美國直接受到中國的強大影響,所以我們必須為自己負責,我們必須想辦法對中國影響帶來的衝擊做出反應。
澳大利亞必須與美國和中國兩個大國都建立緊密的互信關係,而同時我們要有自己的獨立性,既獨立於美國,也獨立於中國。若想在未來的“中國世界”裏生存下來,我們不能什麼都依從中國,我們也要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們在與中國建立緊密互信關係的同時,還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還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那麼澳中關係將會得到健康發展。一直以來,澳美關係就是如此。
下面摘譯此文部分讀者留言,以一窺澳大利亞讀者對中澳關係之見解,僅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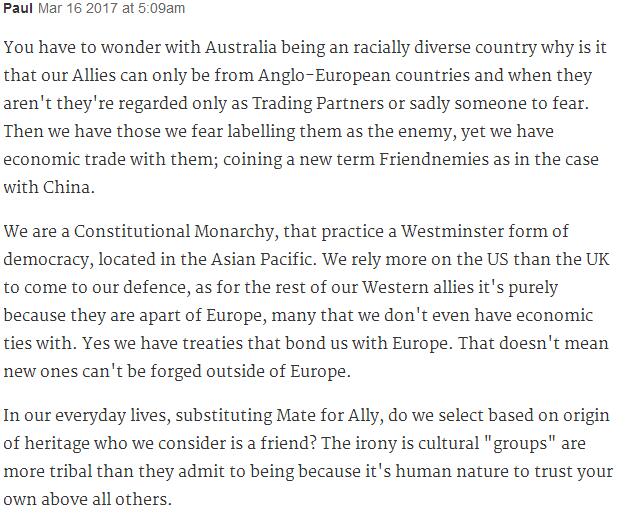
澳大利亞是個種族多元的社會,為何我們的盟友只能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而且如果不是的話就僅能定位成貿易伙伴或是敵國?我們給那些國家貼上敵人的標籤,而且還跟他們做生意。我們可以特別為中國發明一個新詞“亦敵亦友”(Friendnemies)。
我們澳大利亞是君主立憲政體,施行威斯敏斯特民主體制(威斯敏斯特民主體制是沿襲英國議會威斯敏斯特宮所用之體制而形成的民主政府體制,是供立法機構運作的一整套程序。威斯敏斯特民主體制主要在英聯邦成員國使用——觀察者網注),而且位於亞太地區。在國防方面,相較於依賴英國,我們更依賴美國的保護。至於我們其他的西方盟友,他們是歐洲的一部分,我們甚至跟他們都沒有什麼貿易往來。是的,我們的確因為與歐洲簽有協定而與他們結盟,但那並不意味着我們在歐洲以外地區不能結交新的盟友。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如果把國家的盟友換成普通的朋友,難道我們會根據他的家鄉出身來決定是否交這個朋友嗎?但這裏有些矛盾的是,雖然人們不承認,但“文化族羣”一詞的確具有很強的血統色彩,畢竟信任自己人是人類的天性。

太贊同作者的觀點了!我已經在中國生活5年,我在澳大利亞報紙上讀到的政客們的言論的確讓我感到無奈,我們的貿易部長在如何與中國做生意方面也十分無知。要知道,我們澳大利亞市場不大,但我們有豐富的資源,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專業技能。
澳大利亞曾有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國家級科學研究機構——觀察者網注),可惜被我們搞砸了,這個科研機構本該得到大筆撥款,然後把我們澳大利亞的高科技輸出到國外。可惜我們的政客們沒有眼光,過於短視了。
我們的政府只會一心迎合英國和美國,根本不為自己的國家着想。我們應該在學校裏開設課程教授商務漢語,教人們該如何在中國以及亞洲地區做生意,那裏的商務規則與我們非常不同。現在只能希望政府的官員們能有點獨立思考能力,能看得遠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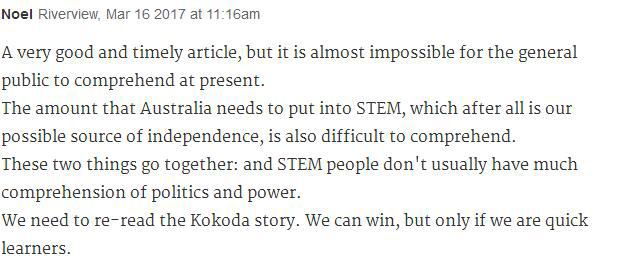
非常棒的文章,也非常及時。只是現在此文很難被澳大利亞普通民眾理解。澳大利亞需要向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大筆投資,這是我們國家保持獨立性的根本保證,可這也很難獲得人們理解。把兩個方面放在一起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的人一般對政治和國家實力沒有什麼概念。我們需要重讀科科達的故事(《科科達》是2006年上映的澳大利亞電影,講述了1942年發生在新幾內亞科科達小徑上,澳大利亞軍隊與日軍的戰鬥——觀察者網注),我們有可能贏,只要我們學得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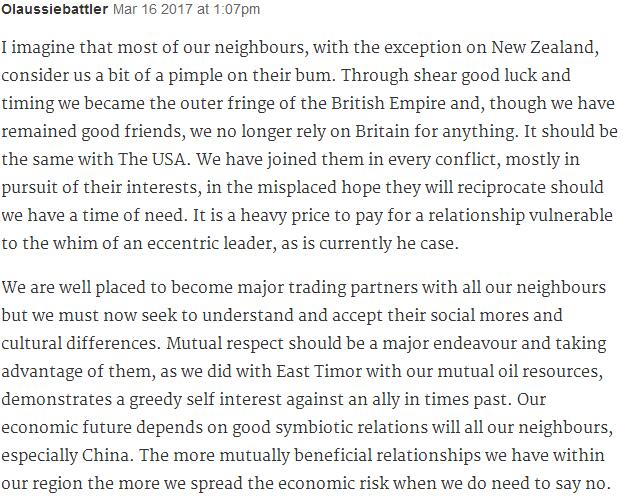
我覺得我們周邊大多數鄰國(除了新西蘭)都把澳大利亞當成是屁股上的一個火癤子。靠着好運氣和好時機,我們成為大英帝國體系的邊緣國家,但現在我們已經不再依賴英國什麼了,當然我們還是好朋友。
我們跟美國的關係與此類似。我們參加了美國人的每一場戰爭,其實大多都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我們還不切實際地盼着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美國人能對我們有所回報。維護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代價太高了,就象現在的情形,澳美關係輕易就被這個剛上台的古怪總統毀掉了。
我們天然是周邊鄰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但我們必須盡力去理解他們的社會傳統並接受他們與我們之間的文化差異。互相尊重非常重要,而利用對方則體現出我們的貪婪和自私自利,就像我們與東帝汶合作開發共有的石油資源時所表現出來的那樣。
澳大利亞的未來取決於我們與鄰國的共生關係,尤其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在這一地區,我們與各國之間的關係越是互利互惠,當我們不得不對某個國家説“不”的時候,我們就越是能分散經濟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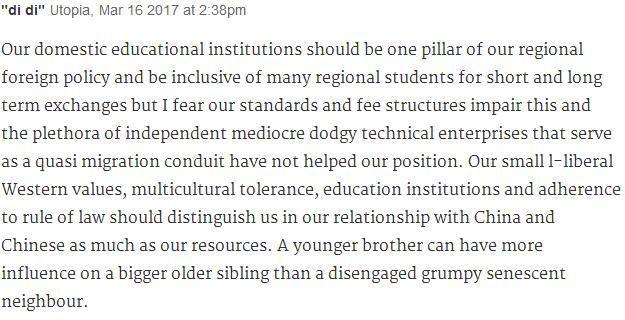
我們國內的教育體制應該在地區外交政策中發揮一定作用,我們應該歡迎各國學生來澳大利亞進行短期和長期交流,但恐怕我們的教育和收費標準會造成一定障礙,何況那些充當半移民渠道的平庸而狡猾的技術公司還給我們減了分。
我們的西方價值觀、多元文化包容性、教育體制以及對法制的堅持,就如同我們的資源優勢那樣,將在我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中為我們加分不少。一個小弟弟能比一個脱離時代的、脾氣暴躁的老年鄰居對一個大哥哥產生更大影響。

澳大利亞是美利堅帝國的一個附庸國。澳大利亞領導人對(美國在戰爭中的)暴行視而不見,卻誇誇其談什麼“共同價值觀”。新西蘭要比我們老道多了,他們很多年以前就把美國人甩掉了。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3月16日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