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涯:留學歸國從教三十年 林毅夫在孤獨中前行
【編者按:值林毅夫留學歸國任教30週年之際,林毅夫眾學友及他的弟子們紛紛撰文祝賀林毅夫。北大金融系副教授唐涯亦賜稿觀察者網,回憶她與林毅夫老師的點滴故事,讀來感人肺腑。林毅夫對觀察者網關愛有加,我們在此也一併向他表示祝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唐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章》
想起林毅夫老師,我腦子裏跳出的第一個詞語竟然是“孤獨”。閉上眼浮現出的,是一個挺拔的高大背影,不知疲倦地走在一條寬闊的、但車流稀疏的大路之上。陽光從他肩上滑落,落在地上的影子,倔強中透着一絲寂寥。
對於我們前後好幾代的經濟學子來説,林毅夫以及他創立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 ,曾經是殿堂級的現象,當年CCER幾大創始人,海聞,張維迎,易綱…..每個人都是一出波瀾壯闊的時代大劇,宋國青,周其仁等元老教授則以其無與倫比的犀利和深刻,多年如一日站在中國宏微觀經濟學的巔峯。這個機構曾代表了傳奇,熱血,和中國士大夫“經世濟民”的終極理想。

林老師毋庸置疑是個中典範。從台灣的“十大傑出青年”,鳧水渡過海峽的林正義,到北大學子,芝加哥大學博士,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所副所長林毅夫,再到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始人,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毅夫,再到“新結構經濟學”創始人和倡導者林毅夫……
在“國之重器,著名經濟學家”的耀眼光芒下,他與稚兒妻子一別四年,輾轉萬里在美國相見;他永訣家園,生不能養,死不能送,只能伏地慟哭遙祭父母;他一反“知識分子”弱不禁風的姿態,在北大校園拔拳怒懟潑皮暴發户…..
他生命的跌宕起伏,蕩氣迴腸,真真有如這個時代“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的風雲際會。
有的人,註定要和時代相遇交匯,再超越時代。

台灣海峽漂着林毅夫的鄉愁和家國情懷。圖為台灣西子灣風景
領悟《中國的奇蹟》
我第一次正兒八經讀林毅夫老師的書,是出國不久的一個夏天。當時因為SAS,機票便宜得難以置信,800加幣往返,中途在日本轉機。旅途漫長,我將從國內帶來的一本《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 放進了揹包。那個時候林毅夫的名聲已經如日中天,但是我生性懶散,除了啃必須啃的專業書外,更喜歡在網上游蕩,對於大部頭的文章,一直有點敬而遠之。這次倒是好,機艙裏被隔絕得人事兩茫茫,反而靜了心讀書。
我們這代人恰好成長在中國經濟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飛速發展的時代,父母唸叨的貧窮和童年時代隱約的匱缺記憶很快被滾滾而來的物質湮沒,“增長”對我們而言,更像是個自然的結果。作為一個金融學專業的學生,我對市場的認知是“理所當然”,很少會去思考市場背後的“制度”和“演化變遷”。
但在這次20個小時的飛行中,我將這本不算“輕鬆好看”的書讀完了,腦子裏飛速閃過的是自己從小到大的很多事情,看過的很多農村題材小説,父母唸叨過的很多歷史,甚至課堂上折磨過我的各種增長理論,Harrod-Domar模型, Solow模型,都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都湧入我大腦 ——“經濟增長”第一次在我腦中有了具象的涵義,我從小到大所經歷的一切原來都是源自一個“增長奇蹟”,而這個奇蹟,是要素稟賦與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框架性思維的重要性。大道至簡,很多事情,看似眼花繚亂,紛繁蕪雜,但是一旦立足框架,就迎刃而解。
我對寫出這本書的人充滿了敬意和説不出的好感。林毅夫這個名字,也從一個“與我無關的超級大牛經濟學家”成為了“影響我的一本書的作者”。這中間的微妙分別,大概只有當事人明白。但是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和這麼個牛人有什麼交集。
第一次見面:沒有“敷衍”二字
世界上的事情倒是很奇妙。我2010年我回國,去了北大光華教書,自然的與北大經濟學圈子裏的人熟悉了起來。
最先見到的是大名鼎鼎的“中國宏觀第一人”宋國青老師。初次見面在他藍旗營的家裏,大概只有三,五句話的功夫,老爺子對我的特點(強項和弱點)就瞭解得一清二楚。聰明無雙,大概就是指這樣的人吧。但犀利之外,他又顯得很小孩子氣,嘟囔抱怨自己的牙齒不好,但是怕疼,不願去“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種牙,充分流露出對於咬不動的食物又愛又恨的心事,逗得我哈哈大笑。
見到林毅夫老師則是2011年的夏天了,大概是7月份吧,我和徐遠在校園裏瞎逛,盛夏的未名湖垂柳依依,蛙聲零星,遠遠看見幾個人站在湖邊,徐遠突然驚呼一聲“林老師”,拉我跑過去,我這才知道,面前這個穿白色襯衣的高大的中年男子,就是傳説中的林毅夫。
因為有見老宋的經驗,我全無初次見“大牛”的侷促拘束。那時候老林還在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的任上,我記得他們在聊這幾年在發展中國家調研的感觸和經驗,我家裏做外貿和海外投資的,對有些國家略知道點皮毛,也就信口開河的插嘴亂説。林老師居然聽得很認真,然後很認真的一一給出自己的判斷,他的眼神如此專注,表達如此誠懇,我懷疑他的人生字典裏從沒有“敷衍”這個詞語——後來證明,這個懷疑是對的。

理解林毅夫的“彎道超車”
2012年之後,林老師回國。從那個時候開始,他開始力推“新結構經濟學”。在他的辦公室裏,他在《繁榮的求索》和《本體和常無》兩本書上用心的簽好自己的名字,很鄭重地遞給我,囑咐我好好讀,好好思考。
那時候我還忙着寫象牙塔的學術論文,匆匆把《繁榮的求索》看完了,大體上明白了老師是順着《中國的奇蹟》的思路在拓展衍生,他在前些年歸納總結中國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觀察到的絕大多數國家的發展路徑,討論一種經濟學的新框架性思維,這個框架把經濟增長的“前提”作為一個重要的變量考慮進來:
一個經濟體在某個發展階段的增長不是簡單的“市場化”的結果,而必須考慮這個階段的要素稟賦結構,因此,與其相適應的產業結構和市場基礎設施(i.e.,道路,交通,通訊,金融,法律,市場管制等軟硬基礎設施)就會對經濟增長起到關鍵作用。
當年我模模糊糊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想得不是很透徹,也就放下了。
2013年,我痛下決心告別純粹的象牙塔學問,開始大量地作企業實地調研。從山東的日照鋼鐵,到湖南的三一重工,從上海的上實投資,張江集團,到浙江的大批中小民營企業;2015我開始研究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從盛大,九城,完美世界,到螞蟻金服,天神娛樂——中國的企業史,就是一部改革以來的經濟史,所以被逼着將中國改革這幾十年的歷程梳理了一遍,然後我常常到老師那兒去聊會兒天,主要是聊自己在外面看到的很多現象,聽聽林老師的意見。
每次他都饒有興趣的聽我説這些微觀的事情。他參觀過三一,對於三一從德國製造的“學生”到“主人”(注:2012年,三一收購了曾被自己追趕多年的德國王牌混凝土機械製造商普茨邁斯特)的過程很感興趣,一直追問在“追趕”到“超越”的過程中,企業做對了什麼。在這些細節基礎上,他又總會回到要素稟賦和產業結構,做出自己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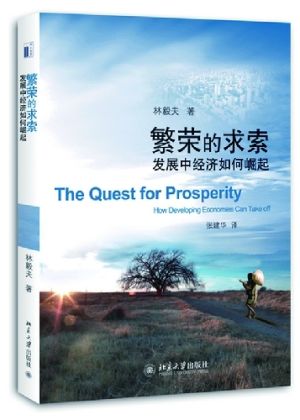
我當時已經感到在互聯網企業這一塊,中國某些企業具有自己獨特的性質和競爭力,所以問老師對現在的互聯網企業怎麼看?那次我記得林老師沉吟了一下,非常坦誠的説:
互聯網這一塊我研究不多,但是我想思路可能有某種相似。他給我仔細的講述了新結構的五類產業劃分,傳統型,追趕型,領先型,彎道超車型,以及基礎研發型。今天的中國作為中等收入國家,在人力資本方面還具有較大的比較優勢,所以某些新興科技行業,比如移動通信行業,研究成本相對較低,研發週期短,應用快,而中國具有13億人口的應用市場,技術應用型的企業可能發生化學反應,有希望實現對發達國家的彎道超車,他舉了小米做例子。
過了好幾個月,一個回國講學的朋友和我聊天,突然問我,為什麼國內生活這麼方便,點餐,購物,打車,什麼都一個手機搞定。他是個嚴肅的經濟學者,提出這個問題也是嚴肅探究的,我突然想起了老林説的“彎道超車”的概念,然後發現從這個方向上,中國很多互聯網的獨角獸企業,i.e.,美團,滴滴,都變得更容易理解。
2016年好幾件事情讓我對林老師的理論有了新的認識。第一件事是我開始瘋魔般的看螞蟻金服這個案例,雖然至今還處在魔障中,但是發現老林的邏輯是有很強解釋力的。
早期的支付寶就屬於“研發週期短,研發成本不高,應用快”的產品,因為當時的中國是深度金融抑制的國家,為淘寶的擔保交易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場景,所以支付寶迅速“彎道超車”——今天中國在移動支付方面,已經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了。
更有意思的是,因為巨大的應用場景支持,支付寶有了不停“迭代試錯”的機會和實力,又反過來促進了研發,如今螞蟻旗下的第四代支付寶,在技術上已經處於全球領先的地位,率先實現了對印度和東南亞沿線國家的“技術輸出”,在應用上“彎道超車”之後,技術上也實現了“彎道超車”。
林張產業政策理論 是解釋中國的兩個維度
第二件是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林張產業政策之爭。我是維迎老師招進北大光華的,從某種意義上説,我們這代人都受過他的市場思想啓蒙,對政府的手保持着天然的警惕。這幾年我在現實世界裏的觀察,又覺得林老師講的很多道理都特別準確。
我在上海看完了辯論的直播,其實兩位老師的理論都比較熟悉,現場講的內容倒也沒有出乎意外,但給了我一次重新審視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的機會。在要不要產業政策上,林張看似持着截然相反的態度:維迎老師認為,政府無法制定有效的產業政策,所以不應該要產業政策,毅夫老師強調,政府應該通過制定與現階段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產業政策,實現更好的挖掘增長潛力的產業結構。一個花甲,一個半百的兩位老先生在台上唇槍舌戰,加上黃益平老師風度翩翩的主持,特別有北大思辨的精神氣質。但是後來我仔細琢磨,他倆的討論其實沒有在一個頻道上。

產業政策之爭現場。從左到右:林毅夫、黃益平、張維迎
張老師是強調的是一個理想的狀態:市場不存在太多扭曲,市場價格是最好的信號,任何人為的干涉都會破壞這個信號機制。他的思路更像哈耶克,是要求“回到斯密”,回到最基本的理性。
林老師強調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發展是路徑相依的,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説,其要素稟賦有其適配的產業結構,由於外部性的存在,企業的行為不是社會最優的,政府在市場基礎設施改進方面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他的思路,更接近凱恩斯強調波動的存在,因而強調調控的必要。
哈耶克和凱恩斯之爭,也是鬧騰了近80年的話題了。經濟學講究一個“一般均衡”,哈耶克要求讓市場去尋找均衡,政府的上帝之手需要控制到最小,而凱恩斯則認為,市場存在不完美(比如動物精神),誰也不知道均衡在哪裏,所以市場會有巨大的波動,政府需要一定調控。
如果我們再往歷史的細節裏面挖掘,就會發現,其實哈耶克和凱恩斯理論都是有很強的時代特徵和地域性的。哈耶克是奧地利學派的代表性人物,這一派針鋒相對的是當時正在盛行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 1917年之後,蘇聯模式在學術圈一直擁躉不少(著名的薩繆爾森就不只一次的公開讚美蘇聯模式是最好的經濟模式 )。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在這麼一個靶子下寫出來的,“市場價格是最好的信號”是針對蘇聯政府從頭到腳的“上帝之手”而言的。而凱恩斯曾任職於英國財政部,他的《通論》的出發點和思考路徑都是在已經完成思想啓蒙和工業革命的英國的框架下進行的,一戰前後發生在英美的巨大經濟波動引起了他的警覺。讓一個被綁縛得死死的人解開枷鎖,和對一個精壯的年輕人談運動規則——這是這兩本宏偉鉅著的時代大背景。
儘管兩本書都具有跨時代的一般性,但是寫作從來不是完全客觀的描述,學術觀點更是一種主觀意識下的客觀表達而已。所以在我的腦子裏(也許是我對理論的理解膚淺吧),我從來沒有覺得哈耶克和凱恩斯不相容過,他們在我腦中不過是均衡的不同緯度,均衡本來就是複雜的,就像人性從來無法用黑白是非簡單區分。
同樣的邏輯,維迎老師針對的是中國仍然存在的各種市場扭曲,要求從根本上改變這些扭曲,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市場干預少,摩擦少,市場機制運行良好)。毅夫老師針對的是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發展中”和“轉型中”,認為從傳統農業經濟到高收入現代工業化經濟的發展不是跳躍式的,而是分佈在一個連續頻譜之上,對應着與這個階段相適應的稟賦結構,要求掌握着大量資源的政府“有為”,去改善市場基礎設施,幫助市場發育。
維迎老師希望政府放棄權力和資源,毅夫老師則承認政府擁有權力和資源的現實,希望政府合理的使用權力,配置資源。
在家裏吃飯的時候,談起對林張理論的想法,家裏正好有人經歷了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轉變,對於產業政策這一塊特別敏感。家人的闡述完全印證了我的想法,維迎老師和毅夫老師講的是中國現狀的不同維度——
一方面,盲目的產業政策害了不少產業,一個典型的是動漫行業,當年國家要求支持動漫行業,然後各級政府就開始大撒幣,她所在的產業園裏一夜之間多了無數“動漫公司”,大多是來混政府補貼,搞尋租的,然後幾年過去灰飛煙滅,動漫行業一直暮氣沉沉,反觀網遊行業,是當年不夠重視,限制,管控和“支持”都比較較少,大體上類似負面清單式的管理,反而發展得蓬蓬勃勃。
但是在另外一個方面,從傳統演化和現實發展的情況來看,中國政府歷來是強政府。從一個巨大的計劃經濟轉型,經過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土地財政之後,體制內沉澱的巨大資源和體制的巨大慣性,都是現實的約束條件,這不是一句“改革”就可以改變的。
我的家人告訴我,在現實條件下,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在土地,政策,資金,甚至人才儲備等很多微觀層面,都需要當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很多企業不是不需要產業政策,而是需要“懂企業的”的政策。但在現實中小企業和政府之間是割裂的,存在着巨大信息不對稱——中國的“熟人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結果。
因此,解決政企之間信息不對稱,讓雙方的信息可以反饋,將政府的巨大存量資源匹配到企業,通過企業的成長實現政府資源的流動性。這種“匹配”的本身就是創造價值的,是用市場的方法解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博弈——這不是一湧而上的智庫專家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些來自企業,紮根企業,熟悉政府,超越政府的專業隊伍去推動和完成。相比“改革”的呼喚,這種“行動”應該算是尋找去現實約束中的次優選擇吧。
市場理想踐行者要承擔不被理解的風險
坦白説,只要是社會科學的理論,就難免被標籤化。張維迎老師容易被貼上“反政府”的標籤,而林毅夫老師的理論則更容易被濫用,因而容易被批評為“為政府背書”。在市場被當作宗教的環境裏,林毅夫被罵的風險更高一些。但市場,卻從來都不是免費的,作為“迄今人類歷史發現的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市場)不是免費的,而且很昂貴,建立和維護都需要耗費很多資源 ”。而林毅夫理解了這個約束,併力圖在這個約束下,找出跨越約束的現實方案。
在我眼裏,維迎老師是我們這個時代市場的思想啓蒙者,具有殉道者一般的理想主義光芒,而毅夫老師則是這個時代市場理想的踐行者,在現實約束中,積硅步以致千里。他為這個理想,所付出的,不僅僅是幾十年如一日的苦行僧一般自律、嚴謹和勤奮,還需要承擔不被時代理解的風險。
幾年下來,我看到林老師修得極短極平的寸頭多了些灰白色的痕跡,眼角也多了些皺紋,但仍然温和,謙遜,自制。我看到的他從來沒有過度的情緒,永遠温言細語,即使感到不悦也只是將微笑稍微斂起。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他高大挺拔的背影中,我卻總是讀出很深的,屬於古典時代士大夫的痛苦。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