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軍師聯盟》不是洗白司馬懿,而是侮辱
有人説,最近熱映的《軍師聯盟》是司馬宣王(空一格)懿的“洗白”劇。理由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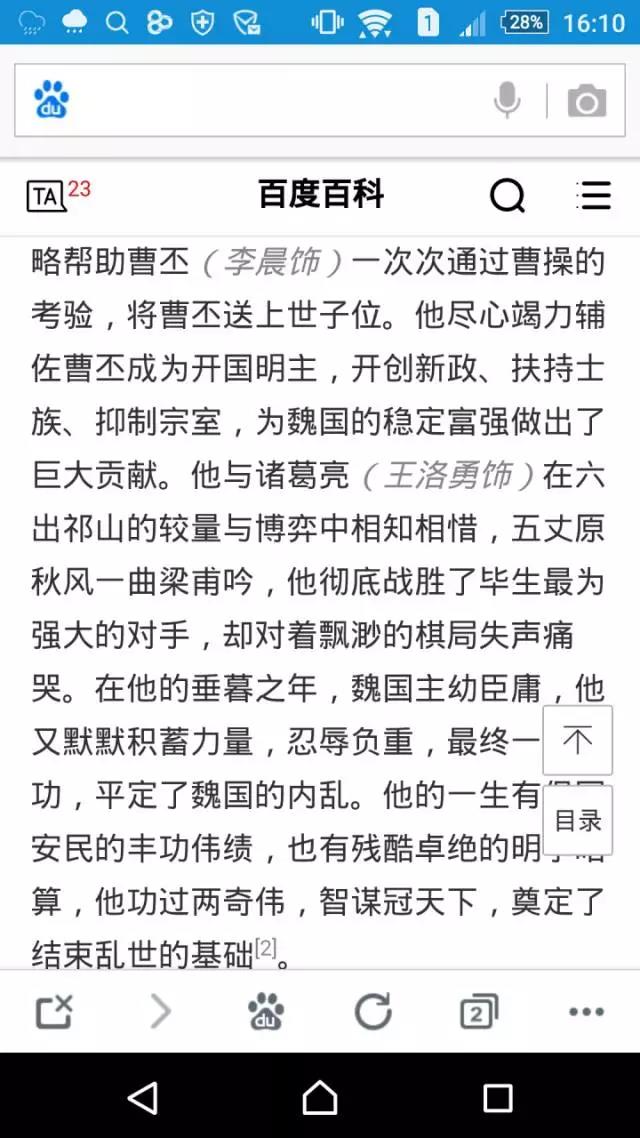
分明感動中國好宣王。但是筆者必須指出的是,這樣講故事不是“洗白”,而恰恰是對宣王的侮辱。
所謂“洗白”,應該是先承認歷史人物曾經做過的事情,然後對此做出以我為主、符合時代精神的闡釋。比如雖然魏武帝曹操屠城挖墳,但是都是時勢和姦人所迫,且符合歷史進步的大趨勢,某些沒有屠城挖墳的人,不過是缺乏格局或偽君子罷了;又比如秦公檜能及時阻止岳飛窮兵黷武的行為,挽大宋於既亡,諡號忠獻可謂恰當。這樣“洗白”才算得上真愛真知音。
以此論之,如果真的尊敬、熱愛宣王,就應該坦然地向烏合之眾大聲講出宣王之所以大名垂於宇宙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用一種我們想當然的“正能量”虛假事蹟將他包裹起來,把他庸俗化為諸葛亮、荀彧一類食古不化的二流人物。
想這所謂漢末三國,不過一割據紛爭時代爾,何以歷兩千年仍能如幽靈般始終徘徊在公共議題中?某位前人曾説過,一部水滸,好就好在投降。那麼一部三國志/演義,好就好在三分歸晉。因為三分歸晉,一台熱熱鬧鬧的全武行驟變為令人掩卷長太息的政治悲劇,後人由此知道了歷史並非全由勝利者書寫,也知道了有些“勝利”並不能長久。換言之,沒有宣王開創的晉朝基業,三國的歷史價值就蕩然無存。李宗吾先生在《厚黑學》中贊曰:“司馬懿集厚黑學之大成,……。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到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可見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這樣的評價不能不説是特別高了。
而宣王之所以成為三國風雲中最關鍵、最卓爾不羣的那個,在於當時的人,大多數內心和行動都充滿矛盾,在順應變動社會形勢的同時卻又放不下舊時代的“正義”,只有宣王能做到表裏如一,做成了一位完全忠於自己慾望的、純粹的壞人。

要知道,和漢朝一樣延續了四百年的,除了“劉”這個姓氏,還有一套成形的制度。我們中國人稱之為“大一統”;而在漢學家的外部視角,谷川道雄説這制度以道德述説政治,“合理而美好地高高聳立着”,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説它是“去軍事化”的政治,開了一個“內部同質化”的政治-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先聲。敍述這套政治的是儒家經學思想,促使春秋公羊學成為西漢第一個官學的董仲舒有個思想叫“權變”。如果要做個簡單粗暴的解釋,就是説政治行為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作出權宜變動。
但是(!)這個“權變”必須得有個“善”的前提,即符合根本性的政治宗旨和道德原則。結合“權變”與“善”的政治思想一方面使得中國政治追求的上限非常的高,要讓效率和德性在變動中實現辯證統一;但另一方面,“從權”本身的實踐標準卻並不算具體。如此一來,對“善”的具體理解和解釋者的身份也可以變動。
到了東漢時代,隨着地方勢族、知識精英和廟堂官僚這三個身份趨於合流,政治的物質力量和文化資源就難免出現一定程度的分裂。到了東漢末年,以出身地方勢族、飽讀經書、富有德行、身居高位的官員為核心構成“不富而甚有知”的“清流”與由宦官和外戚組成、被稱為“富而無知”的“濁流”對立,鬥爭結果慘烈殘酷。
而在鬥爭之中,尤其是“清流”羣體的道德、目的、行動標準都變得模糊起來。是忠君嗎?是愛國嗎?是為民嗎?是為了自己家族嗎?是為了千秋理想嗎?是為保一身嗎?是為了報答老師或者提拔者的知遇之恩嗎?在漢末變動的社會中,慣性的制度、成熟美好的理念、具有內在緊張的政治——社會共同體都在噴湧自己最大能量,使得以上動機交錯在一起,作用到每個具體的人身上,或者共同發生作用,又或者在不同的階段輪流發生作用,造成了亂世豪傑們的精神分裂,一半是理想,一般是對現實的妥協。
魏武帝曹操就是這樣一位典型的精神分裂人物。魏武帝作詩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然後屠徐州,“過拔取慮、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魏武又作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而創業期有毛玠、崔琰二人,一個獻“挾天子以令諸侯”策,一個為魏武選舉人才,所舉都是“清正”之士,然後兩個都被用很無厘頭的理由殺掉了。魏武還作詩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但赤壁敗後,魏武就望着秦嶺,有些自我安慰地引用“既得隴,復望蜀邪”的名句,而漢中一戰又為五十多歲才有自己地盤的織蓆販履之輩所破,三足鼎立遂成。魏武作詩時候當然是真誠的,否則生不出這樣的名句,但行動的時候,也必然是真誠的。
而最體現這個時代整體分裂精神的,當然是陳壽的《三國志》。當時的陳壽,至少面臨着來自三方面的物質和精神壓力。首先,在高層政治層面,魏晉是正統,無須多言;其次,在社會層面,儘管吳蜀政權滅亡,但勢族仍在,蜀倒翻不了什麼浪,但吳這邊大族基本全須全尾,如陸機陸雲兄弟陳壽可得罪麼?更不用提九品官人法加持的魏晉勢族了;最後,在精神層面,相當弔詭的是,歷經漢魏晉三朝腥風血雨的勢族知識分子在潛意識裏還是強調“氣節”的古風,背主之人往往遭到唾棄打壓——當然前提是背後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支撐——在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的整體氣氛這種,蜀人陳壽也終究要故國人民有所思了。以唐代劉知幾為代表,歷代都有懷疑陳壽黑故國而諂媚司馬氏的説法,但仔細一想,誰建立了後世對季漢的正面評價框架?莫不是陳壽乎?且體會一下下面兩段遣詞:
“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這種大蜜似黑,大黑似蜜的姿勢,後人還是要學習一個。難怪張華看了陳壽的稿子就表示“當以晉書相付耳。”(《晉書·陳壽傳》)與大多數擁有政治家、學問家頭銜的魏晉士人一樣,張華的一生,也處處顯現出精神追求與行為的分裂,限於篇幅不再多做陳述。陳壽在三重壓力下對矛盾的基本駕馭,大概是張華的理想《晉書》能夠成立的唯一途徑吧。
所以不受這種普遍性分裂機制束縛的宣王是偉大的。《軍師聯盟》中,若干年後因為一個婢女看到自己裝病的老公其實精神奕奕就殺了婢女的張春華女士如是説(見下圖),筆者完全同意。因為宣王的字典裏沒有情義二字,而他自己就是權術本身。宣王知行合一的最高光時刻莫過於高平陵。在不能保證實力和大義名分碾壓曹爽的情況下,宣王通過太尉蔣濟作保,勸曹爽主動下野可保身家富貴,順便還對着河水立了個誓。而兵權一接,就殺了曹爽全家。蔣濟很快也死了,據説是氣死的,他和曹爽都無法擺脱舊時代留給他們的、名為“信義”的精神遺毒。


非常可惜,宣王知行的內在和諧並沒有能夠繼承下去,後代的精神分裂仍然嚴重。司馬昭雖然做出了當街捅死皇帝的亙古壯舉,事後卻擔心議論,於是把青梅竹馬陳泰找來問怎麼辦。陳泰一邊抱着被殺死的皇帝哭得稀里嘩啦,一邊建議司馬昭處死自己的親(ji)信(you)賈充。司馬昭捨不得,問能不能輕點,陳泰於是説“這特麼已經是最輕的了(你要我把更嚴重的方法説出來嗎?)”。當然最後被殺掉的是實際執行的成濟,而他又不肯安安靜靜地去死而是大呼小叫説自己是被司馬昭賈充指使,當然也就被殺了全家。當然陳泰也是沒事的,畢竟他是晉王的親梅竹馬,倡導九品官人法的重臣陳羣的兒子。
而再到司馬炎建立晉朝,精神分裂達到頂峯:一方面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制度安排成熟了,皇帝對那些沒有被他殺全家的精英表現出了最大限度的“仁德寬厚”,偶爾幫個忙鬥鬥富什麼的。但另一方面,前朝中央集權“大有為”的制度幽靈仍然縈繞不去,晉朝吸收曹魏虐待宗室無人救援的教訓,分封宗室拱衞,又親信賈充等士族大家內不太被人看得上的“小人”以增進權力。而到了所謂的“衣冠南渡”後,士族大家終於找到了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把皇帝變成圖章,然後彼此之間為了爭奪圖章而輪流殺全家。這才算是部分迴歸了司馬宣王知行合一的精髓。
兩千年過去了,司馬宣王仍然未能獲得世人對他應有的理解,曾有多少自命民族忠臣孝子的人不停地對他狺狺狂吠。而到了今天,當我們想要歌頌讚美他時,竟然採用了這種庸俗的“正能量”故事!我不禁要問,我們努力地“顛覆”了歷史上那些“正能量”的人物,最大限度地挖掘了他們在歷史長河中都不為人知的猥瑣、虛偽、陰暗和愚蠢,然後卻用卓爾不羣的司馬宣王來傳達這些“正能量”,竟不惜掩蓋他的真實!作為宣王的粉絲,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而筆者,作為二流人物諸葛村夫的擁躉,從知道《軍師聯盟》這個劇開始就希望裏面千萬不要涉及諸葛村夫,萬一一定要涉及,最好描寫成一個猥瑣陰暗,企圖抵擋時代潮流、完全不是宣王對手的反面人物。但看內容介紹似乎不可能了,宣王想必將要和諸葛村夫惺惺相惜引為知音互相理解實現歷史的大和諧。這是對諸葛村夫,哦不對,對宣王最大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