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康納:美國國會為什麼不是人民代表大會?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在新著《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為原型,提出一種無關民主、重視治理質量、由專家集體領導的治理範式——“專主制”。
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翻譯全書並將在近期陸續以連載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節選自原書第四章“人民代表大會”的第一節“沒有政策的政治”。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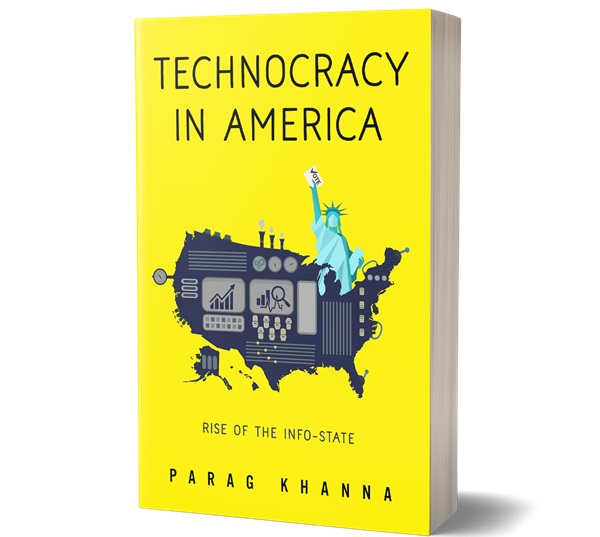
《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
得益於有效的集體領導制以及穩健的專家型公務員,信息國家的行政部門成為了強大的權力機構,國家前進的方向盤牢牢掌握在柏拉圖筆下的“衞國者”手中。但同時,立法機構也需要現代化,既要發揮制衡行政權力的功能,又要代表公民利益更好地履行立法職責。
美國本來應該努力成為一個沒有政治權術的民主國家,但不幸的是,它已墮落為一個沒有民主的權術政治體。今天的政治不再是以理服人,而是特殊利益羣體之間狹隘的討價還價;而民主也不再是公民之聲,而是某個政治階級維持現狀的統治。美國空有選舉,卻沒有實質性行動,或者即使有行動,也不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
哈佛講師雅沙·蒙克把美國的制度稱作“不民主的自由主義”,也就是説這個體制保護各種權利,但缺乏將民意轉化為公共政策的制度。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馬丁·吉倫斯和西北大學的本傑明·佩吉經過研究指出,當普通選民的偏好與精英選民的偏好發生分歧時,國會無一例外地投票支持精英。他們得出的結論得到廣泛引用轉載:美國是個寡頭統治的國家,而不是民主國家,真正的統治者是腐敗的尋租式精英。
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萊席克等法學家認為,美國的代議制民主程序等同於制度化的腐敗。事實上,美國的選舉制度沒什麼賢能政治成分可言,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推動着“金錢選舉”,決定了哪些候選人可以獲得角逐大選的資格。雖然政黨沒有出現在美國憲法的條文中,但它們已經建立起一套非正式的程序規則和政策準則。
今天,美國政黨的議程不是由黨員從內部推動,而是由捐助者從外部操縱,這些捐助者能決定候選者名單,從而影響政黨的議程。
根據“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企業和自然人一樣都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而政治獻金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不同之處在於,個人每隔幾年才有一次投票的機會,但企業每天都可以利用金錢實力行使“言論自由權”,而且所涉金額越來越大。當政黨跟隨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指揮棒起舞時,整個體制就遠離了賢能政治,成為萊席克口中的“金主制”。
美國國會議員實際花在立法上的時間少得可憐,政府支出預算在過去二十年裏從沒有一次能按時獲得通過。大約半數美國國會議員和參議員在從政之前就已經是百萬富翁,而在擔任議員期間,他們在遊説上花的時間幾乎和立法一樣多,而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準備下次競選上。從公職上退下來之後,他們又回到遊説組織全職當説客。既然現實如此,美國選舉系統又怎麼可能推進縮減競選經費、廢除初選機制、改革(或廢除)過時的選舉人團、或實行任期限制等的激進改革?
或許我們不應該把國會看作獨立的政府機構,而應將其看作某種強大力量的動因。長期研究美國國會的邁克·洛夫格林在新著《深層國家》中提出,華盛頓圈內的軍事和金融專業人士組成了一道隱秘網絡, 這套“全世界最複雜的機構”不但能操縱議員,甚至能取代立法者的資源和影響力。這個所謂“深層國家”其實是體制的蛀蟲,它通過收買議員減免税務,可能很快就會榨乾國會的利用價值。
不過,腐敗並不是單行道,而是雙向的。美國國會也非常清楚應該如何敲詐企業以維持自身“業務”:國會議員把企業捐助者當作搖錢樹,不填飽私囊就不給予新的税務優惠政策,導致暫時性抵税收抵免名目激增。
美國的間接民主體制也導致改劃地方選區(以鞏固議席)的做法盛行,這樣一來就給了茶黨激進分子劫持眾議院的機會,而參議院的結構也決定,少數農村選民就能綁架多數。美國建國初期,詹姆斯·麥迪遜曾擔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而對目前的美國而言,真正的威脅是少數人的暴政。
2013年,國會共和黨人為了廢除平價醫療法案關於支出的規定,鬧到政府關門。觀察人士伊萬·克拉斯特夫指出,美國民主已經成為一個“看誰是膽小鬼”的遊戲,反對黨給執政黨搗亂讓對方一事無成,居然成了比治理本身更重要的事。
在某些人眼裏,民主體制的混亂或許正是其美好的地方,但國家如果因此變得無法治理,則絕對得不償失。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成為自身的囚徒,無法通過制定萬全的法律使社會變得更加美好。
在聯邦、州乃至市的層面,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領域的管理層級、法定權責、開支預算都存在許多相互重疊、彼此矛盾之處,導致不透明和混亂現象時有發生,給利益團體、律師、諮詢師利用混亂鑽空子的空間。
美國當前的情況是,國會不僅拿不出好點子,反而制訂了一系列如瑞士奶酪般漏洞百出的法律,它們複雜和怪異程度好比鴨嘴獸。拿奧巴馬醫改法案來説,它在技術操作層面有巨大困難,醫療包乾項目缺少明確規定,許多人將其戲稱為“沒割乾淨的包皮”。保險公司不再受到約束,放心大膽地在合同裏做文章;本來有志從醫的人也對這個行業興趣索然。
與醫改類似,旨在改革金融監管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由於規定得過於死板,給美國企業造成過重負擔,導致它們在國內急需投資的關頭紛紛出走,向監管較松、運營更高效的海外市場進軍。
美國國會的透明度問題既降低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又迫使總統只好靠下達行政命令來治理國家,甚至導致地方政府為避免腐敗和聯邦政治的繁文縟節,不得不長期放權。基建、軍事和其他公共服務等需要大規模開支的項目,都離不開國會的批准,因此我們難免擔憂,如果立法機構得不到信任,關鍵性倡議將遭到忽視,進而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美國商業和社會生活效率低下,不熟悉權力機制的人往往會怪罪大眾視野以外的“有關部門”。 但其實罪魁禍首是操縱國會的特殊利益團體,它們故意削弱專家治理體制,干擾了井然有序的日常事務。只有專業主義官僚迴歸並重獲獨立領導權,才能從政治權術中拯救國家治理。在政治與行政、民主實踐和治理行為之間重新劃定界限,對恢復美國政府的信譽至關重要。如果美國的政府服務可以重新成為一門職業而不是某種利潤豐厚的愛好,民選領導人便可以與職能完整的政府機構緊密合作,確保政策和制度都符合民眾需求,真正為民謀利。
美國國會本來可以避免成為一個完全被民粹主義和特殊利益控制的機構。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有責任回應特定委員會或國會議員的質詢,可以授權它作為立法籌備機構,從而保證辯論限制在理性的範圍之內。哪些法案能惠及更多普羅大眾,而不是遊説組織偏愛的大企業,國會就應該審議並通過這樣的法案。
作為立法部門下屬機構,政府責任辦公室和國會預算辦公室能提供質量評估,它們應該為如何支配油氣創匯等重要決策提供情境分析,這一工作理應常態化。
然而不幸的是,由於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裏奇對政府懷有偏見,導致國會工作人員被大規模裁員,專業工作人員被經驗較少卻薪資較高的外包合同工取代。今天的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但美國國會卻越來越敷衍了事。
維繫政客與民眾之間的紐帶還有另一種方法,那就是讓立法成為一項兼職工作。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美國國會議員都是兼職的,不像現在這樣常駐在華盛頓。今天,瑞士和新加坡還堅持着這個傳統,這兩個國家的議員都另有職業,保持他們與現實世界不脱節。他們既不能利用公職非法斂財,也不能承受政績欠佳對職業生涯和聲譽的負面影響。因此他們必須深入基層,直接與羣眾交流溝通,解釋政策的必要性。
目前,美國已經開始開展政務討論,但基本都停留在民間層面,與實際立法進程沒有直接關係。例如,阿斯彭研究所的“萬眾”項目力求傳達不投票選民的觀點,而斯坦福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詹姆斯·菲什金則主導了審議式投票實驗,有助於選民在控槍等熱點問題上統一意見。 然而這些努力無法直接影響立法程序,只能在社會層面發揮修補作用,無法撼動特殊利益集團。我們是否能在想象中構建一個新時代,一個通過實時審議和直接民意確立政策的民主時代,一個排除國會代議制的時代?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