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康納:不能用數據説話的制度不是好制度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在新著《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為原型,提出一種無關民主、重視治理質量、由專家集體領導的治理範式——“專主制”。
**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翻譯全書並將陸續以連載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節選自原書第四章“人民代表大會”的第二節“**不斷的聯繫:民主即數據”。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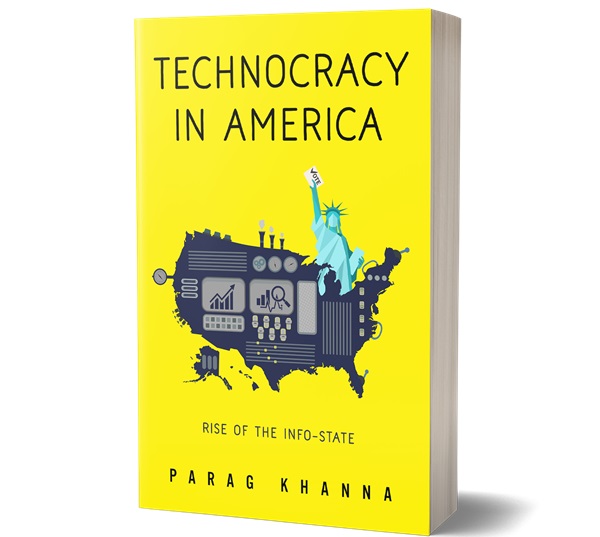
《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
強制性投票可能是最接近民主精神的專主制措施之一。目前,政客只需獲得30%適齡投票人口的支持就能贏得選舉。為減少這種情況,強制性投票則既保證了選舉人口覆蓋面,又能提升選民人羣的知情度。只要通過安全鏈接開放為時一週的網絡強制性投票,美國就可以從選民登記、機械投票站和各種選舉作秀活動中節省數十億美元。自2005年以來,愛沙尼亞一直實行全國性網絡投票,而瑞士則正在全國推廣電子投票。實現數字化直接民主並非難於登天,只需通過強制性投票法,再設計個應用程序即可。
然而,選舉具有溯回性,它往往懲罰政黨的錯誤,而不是為未來開藥方。我們可以把選舉理解為針對政客和具體事務的公投,它對於公民理解具體政策幫助甚少。因此,單純的投票遠不足以反映民眾在一段時期內對各種事務的態度變化。
因此我們需要數據:包括民意調查和社交媒體風向等定性數據,以及人口和經濟趨勢等定量數據。數據往往比選舉結果更能全面説明問題,因為它所涉範圍更廣(涵蓋所有事務,而不是被炒作出來的少數話題劫持)、更即時(收集數據的頻率遠遠高於數年一度的選舉)。測量數據不但比評估民眾信任度來的簡單,而且前者也可以成為實現後者的方式。公民和政治家之間更實質性的互動(包括虛擬環境裏的互動),能大大減輕美國政治中的不信任問題。
由數據驅動的直接專主制比代議制民主更優越的地方在於,它能動態捕捉人民的具體願望,同時防止民選代表、特殊利益集團和腐敗的政治掮客扭曲體制。這既不違背田園牧歌式的自由精神,又考慮了公眾的評議權(它在瑞士已成為現實,而在美國卻止於構想),而且數據工具還為公民提供各式各樣的信息,以便他們持續做出多重決定。瑞士的民主不是民意代表包辦代替的民主,而是開放參與,讓各方共同創造設計政策的民主。這意味着瑞士名目繁多的倡議和公投不是夾在前後兩次重大選舉之間的小事情;而是針對所有重要議題的慣常性表決。事實上,瑞士人對本國的直接民主制度高度自信,甚至開始將議會看作令人生厭的冗餘環節,所以最近有人提出徹底廢除議會的倡議。
信息國家的標誌之一便是不斷適應新技術。今天,我們把數據工具看作民主制度的輔助手段,但最終,各種形式的民主評議(包括選舉、倡議、民調和社交媒體)都將成為數據組,幫助專家型治國者規劃政策。例如,過去得不到政治代表的人羣(不投票或不參與民調的人)可以在數據中得到反映,他們的理財行為和教育狀況等數據,都是領導人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的。數據還有助於人們在慾望和利益之間做取捨。每個人可能都想要免費的含糖飲料,但沒有人想為隨之產生的臃腫的醫療系統買單。
信息國家不應把統治權讓渡給數據,而應努力在數據與民主之間起平衡作用,讓二者互為補充:通過數據確定政策的必要性,通過民主修正政策。通過呈現準確信息和現實情境,新一代數據工具有助於理性對話。IBM基於沃森數據平台的辯論技術能夠搜索大量研究資料,為燃氣管道項目、税收政策、暴力遊戲監管等棘手問題生成並總結正反雙方的立場。當數據成為公眾評議所使用的語言時,民主將變得更加理性,而不是流於情緒化。
新加坡正在開創一種持續性協商的新模式,民主和數據在其中都扮演着基礎性角色。議員每週在社區中心舉行“民眾見面會”,收集民間對於政府預算、住房政策、醫療保健和其他問題的反饋意見。新加坡讓民眾回答詳細的調查問卷,以向政府提供更好的普查數據,便於規劃混合用途住房、商業用地、地鐵和公交路線,以降低私車需求量。不管是民主制度還是威權制度,任何政權要維持合法性並獲取成功,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與公民、專家、企業、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團體進行協商,畢竟集思方能廣益,而且因地制宜遠勝一攬子政策。
同時,複雜信息的大數據可以產生相關性分析和預測,幫助政策制定者按情境推演。隨着光纖互聯網的普及,遍佈新加坡各處的物理傳感網絡提供了大量的數據,包括車輛數量、交通流量、電力消耗等,便於有關部門調節管理路燈和,在用電高峯期提高電源容量避免停電。正如新加坡前公務員首長何學淵所説,“(數據)的目標不僅是更準確地預測,也是更妥善地決策。”
相比之下,美國就比較落後了。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眼裏,數據僅僅是一種政治武器。例如人口普查數據使政黨在為選區定製動員信息時,能精確到街道和街區層面。紐特·金裏奇有個著名的論斷,那就是2008年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勝是因為他們掌握的“數據更好”。
2012年大選時,奧巴馬競選團隊的首席技術官哈帕·裏德帶領小組建立了一個基於地理位置的選舉數據庫。這樣一來,競選者便可以預測民意,並針對婦女、白人男性 、拉丁裔、老年人或其他主要選民羣體有的放矢傳遞信息。共和黨很快從失敗中汲取了教訓。在掌握更精確的選舉地理信息之後,他們利用眾議院多數地位,在威斯康星、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和佛羅里達等民主黨優勢州積極重新劃分選區。這樣一來,雖然民主黨選民基數增加,議席卻在減少。
美國兩黨都發現,在人口數據和重劃選區的影響下,決定全國選舉的關鍵因素就是六個搖擺州和以及周內的部分地區。如果只看2016的美國大選,人們會得出一個結論,整個美國都像是密歇根、俄亥俄和賓夕法尼亞的“鐵鏽帶”地區。但美國不是底特律。美國的網絡自由職業者數量兩倍於工廠工人。8000萬“千禧一代”在事業上的需要和追求難道不應該成為選舉的重要議題嗎?
數據是改善政策的途徑,其作用不應侷限於政黨之間爭奪權力的工具。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本身需要提供更多數據。通過GovTrack和Project Vote Smart等公民倡議,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實時觀看立法會議,閲覽待授權的法案,聆聽聽證會上的聲明,查詢任何議員的投票記錄,以及他們的獲得的競選獻金記錄 。這種公開化、透明化運動能夠賦予公民以實權,確保他們最關心的事項得到解決。當調查數據顯示,老年人需要醫療計劃更加多樣化,而青年希望增加教育選項時,政治家就不能僅把這些信息當作競選演講的素材,而要切實執行政策滿足人們的需求。數字化有助於提高社會透明度,促進政府責任制,而缺乏責任制的民主是毫無意義的廢話。
美國前國家首席技術官託德·樸和繼任者梅根·史密斯都堅定地倡導政府機構使用並內化數據工具,以優化工作流程並促進數據共享。他們還主導成立了數字服務團隊,吸收IT行業的年輕骨幹,將新的技術融入舊的官僚制度。(從哈佛到牛津,各大名校都在圍繞數字治理開發新的課程,以培養新一代的“數據官員”。)但儘管他們致力於提升醫療和老兵保障等聯邦服務的效率,橫在前面的官僚機構障礙仍然龐大,政府各部門之間存在多套數據系統,聯邦和州立機構之間還存在衝突,導致美國難以在中短期內搭建全國性網絡政務平台。
今天,美國的公民協會已經走向衰弱,托克維爾口中“人們關注身外之物”的那種集會逐漸讓位於社交媒體,後者應該成為一種戰略工具,幫助政府瞭解民眾最關心、最在乎的事。畢竟,托克維爾沒有把民主當作一種提高社羣歸屬感的工具,而認為它體現着個人自由和結社權利的精神。當社會實體和網絡都具有高度移動性時,民眾的情緒是否還一定需要通過劃分選區這種地理手段來體現?美國人是社交動物——華盛頓應該關注網民在數字社區中的言論。
目前來看,新加坡等專主制國家正在以比傳統民主國家更快的速度適應數字民主的需要。西方許多能言善辯者曾經提出,一旦人人都能接觸到手機、衞星電視和其他信息渠道,傳播和社交媒體技術將使中國的威權主義成為歷史。但事實上,中國正在對那些無法響應公共需求的民主國家領袖構成挑戰,同時也鞏固了那些能夠快速響應的專主制政權的合法性。
毫無疑問,政府可以通過操縱、跟蹤和審查互聯網等手段獲得侵擾性權力——但除非互聯網被用於回應公眾的關切點,否則網絡無助於政府提高合法性。中國的互聯網政策既有阻擋的一面,又有擁抱的一面。黨內幹部甚至在微博上參加在線問答環節,並接受網絡請願。中央政府卻仍密切關注批評者甚至異見人士的聲音。這的確代表着政府責任制擴大範圍,進入此前標準缺失的領域。
在中國,執政黨已經建立了便於收集想法和統一政策的內部社交媒體平台。中共不斷聽取政協會議中產生的建議。政協委員的隊伍中包括數百名商界和社會要員,光2013年的新增政協委員就包括百度董事長李彥宏、演員成龍、籃球明星姚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等人。政治學者張維為認為,政協會議的作用是幫助中共透過多變的民意,把握住相對穩定的民心。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學者達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提出,從長遠來看,包容性政治體制比非包容性政治體制更可能帶來穩定和增長。雖然他們仍然更傾向於西方民主制度,但他們羅列的證據卻表明中國是個反例。學術界應該關注中國等國家的政治協商和代表制度,理解政府衡量和回應公民需求的方式,而不是削足適履,靠忽略事實來適應理論。中國的體制雖然不民主,卻具有極高的韌性,這便是其包容性最好的證明。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