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為何放棄職守 ——知識精英階層責任缺失的社會歷史分析-曹錦清
“精英與社會責任”是一個很大的話題。關於經濟精英——這主要指的是隨市場和私有化而成長起來的企業家階層——應否及如何承擔社會責任,已有較廣泛的討論。一些能思會寫的企業家在要求社會“赫免”第一桶金的“原罪”時,願將他們已擁有的財富視為社會的一種委託。企業家不僅有義務依法納税,提供就業,且對各種利益相關者承擔社會責任,這種責任通過慈善捐助而擴及各類“弱勢羣體”。
當然宣言不等於實踐,不過,有此宣言總比沒有好。只有當上述宣言多少付諸實踐才能使迅速積累起來的私人財富獲得“赫免”證書,也才有可能獲得大眾對財富的尊重。至少會弱化普遍的怨恨。至於執掌公共政治權力的政治精英,恐怕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有效的權力監督與權力制衡。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能否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監督制衡機制,以便將普遍的腐敗與不負責任的瀆職行為降到民眾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度,這是一個關係到執政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總之,與手執大權的政治精英們談他們應該承擔什麼樣的社會責任似乎並無多大意義。餘下可談的便是知識精英的社會責任了。

曹錦清教授
為什麼知識精英未能承擔文化自信、文化創新的使命?
知識精英,就其社會功能而言在於創造與傳承知識。在龐大複雜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人們首先實踐着,感受着,當然也思考着,謀劃着。作為一個整體的有機社會或説實踐中的民族,需要從那些能思的頭腦中分離一部分頭腦來執行為“社會”或“民族”而思考的重任。故而思想的最高任務,或説知識精英(或説知識分子)的最高職責在於“用思想來守護民族”。
稍具體一點説,知識精英承擔兩項重大使命:一是用概念(理論)去切近或理解(認識)當下展開着的複雜的社會生活。尤其是批判性地揭示民族前進中遭遇到的真實問題與困境。簡言之:認識世界。二是在紛亂的個別意識中去尋找並推動社會共識的形成,尤其是核心價值共識的形成。因為説到底,社會共識是社會秩序得以建立與維繫的最終基礎。
我説“用思想守護民族”是知識精英的最高使命,意指“思想”當然還執行着其他一些職能。任何“思想”總在一切能思的個別頭腦中發生。其間呈現出極其紛雜多樣的內容。我將那些始終堅定不渝地指向社會整體生活狀態或説民族命運的思想稱為“純思”。這些被民族(或説天意)召喚來為理解自身且卓有成效者稱為思者或説**“思想家”。我將那些主要把思者的思想整理為各種“概論”並加以傳播者,稱之為“教授”。我將那些在各種經驗的專門領域有所創見的人,稱之為“專家”**。嚴格説來,一個時代的知識精英,主要由上述三類人物組成。故凡在職業分類中被歸入知識精英而不能或不願承擔其責者,只能稱之為“誤入歧途”者。
如果我們承認上述説法,並以此為標準衡量大量已發表的“學術論文”與更大量的未發表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再觀察一下被歸入知識精英(或知識分子)的人們的日常行為,或能粗略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當代思想並沒有很好地執行本該由其執行的使命。**相反,大量能思的頭腦在“告別崇高”與“告別宏大敍事”的口號下,紛紛從民族整體返回到自身,從民族整體運動的歷史敍事返回到自我當下。從指向民族——歷史的純思返回到工具理性,並要求理性較多地執行個體名利謀劃的職能。“文章”開始告別“道德”而成為謀取名利的單純的工具。於是“官八股”和“洋八股”充塞於世,一代文風因失其“精氣神”而衰敗。**這恰恰發生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綜合國力持續提高的民族崛起時。為什麼在民族物質力量崛起的過程中,“思想”卻沒有承擔起文化自信、文化創新的使命,能思的頭腦拒絕接受民族的召喚而忙碌於切己的謀劃?對這一“時代精神現象”首先要作一番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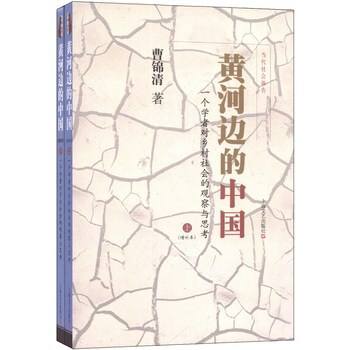
一、先從“時代精神”的聚散合分現象説起。
嚴格一點説,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真正起點是1982年廢除人民公社體制並全面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的要害在於一個“分”。伴隨此“分”而來的一系列“分化”——從所謂的產權分化(從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開,到化公為私),貧富分化,階層分化,區域分化,城鄉分化,直到所謂的“政企分開”,“黨政分開”等等——乃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化。“分”或説從整體中分離出來獲得個體行為自由也是改革開放時代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現象。
與“分”相應的是“合”,所謂“合”,即被孫中山所説的“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合”成一整塊鋼筋水泥。孫中山指出“合”的目標但沒有找到“合”的方法與手段**。真正將“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組織在各自的“單位”內,且一切單位隸屬於國家的,是中國共產黨。**為“合成一個整體”所設定的近期目標:一是為了消滅階級,實現分配平等。二是為快速推進工業化,為追趕發達國家提供“原始積累”。這樣,為了整體的民族目標,要求一切個體放棄自由。
事實上,近代中國的主流思想一直指向民族的解放與復興。這也解釋了以個人權利和自由為最高訴求的自由主義只能成為少數留洋知識分子不切實際的言談。然而,經歷文革十年的折騰,整體給一切個體設定的生活意義與未來目標,與千百萬新一代人的實際生活體驗發生日益明顯的衝突。文革後期,一股希望從整體對個體過度壓制的狀態中擺脱出來的思潮開始形成並日趨發展。的確,沒有個人利益在其內的整體利益,註定因其虛幻而被拋棄。正是這股強大的思潮推動着由“合”向“分”的時代轉換。鄧小平執行了這一時代轉換的使命:“廢除公社單位體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順應了時代潮流。
進而言之,時代精神的聚散也與社會狀態的治亂密切相關。亂而聚,治而散,或也是其常態。借用道教中的“精氣神”一説來指喻“亂聚,治散”現象,雖有點玄,但也妥帖。“化精為氣,化氣為神”,在道教中本指個人修煉逐級上升的境界。我將其用來比附社會現象。“精”在此指物慾,或一個社會一般民眾基本的物質生活要求。當一個民族長期處於動亂狀態,整個社會階層的基本物慾得不到滿足,絕大部分努力都遭到失敗,此一時代被外部世界阻擋的物慾便向內化積為“氣”。“氣”在此指積壓於內心瀰漫於社會的焦慮、苦悶、無奈、怨恨與希望之社會情緒之總稱。此“氣”的積累便會在那些生命感悟能力特強,且能思的頭腦中提煉為“神”。“神”在此指思想或精神,或意識形態。其中最有召喚力的思想家和宗教家很有可能被信眾視為在世的神或神的化身。
看看什麼中外諸“神”湧現的時代,全都出現在長期動亂與艱難的時代。被後世的學者們津津樂道的思想史上最為豐收的時代都是以民眾苦難為代價的。佛所謂煩惱即菩提:淨潔的蓮花下一定是肥沃的污泥。當社會由亂向治的轉換,我們便發現時代精神沿着相反的路向逐漸下行:“化神為氣,化氣為精”。
人們紛紛將關注的目光轉向當下的世俗生活。能思的心靈忙於謀劃自身的利益,努力改善自家的物質生活條件,處心積慮於社會地位高低的競比。如果此前被人們信奉的“神”想使偷食各種禁果的人們重新返回崇高,根據尼采的説法,眾人一定會秘密聯合起來將“神”殺死。中國人比較厚道,只是將“神”請下“祭壇”,讓他還原為“人”。至於是“大人”還是“小人”,世人至今紛爭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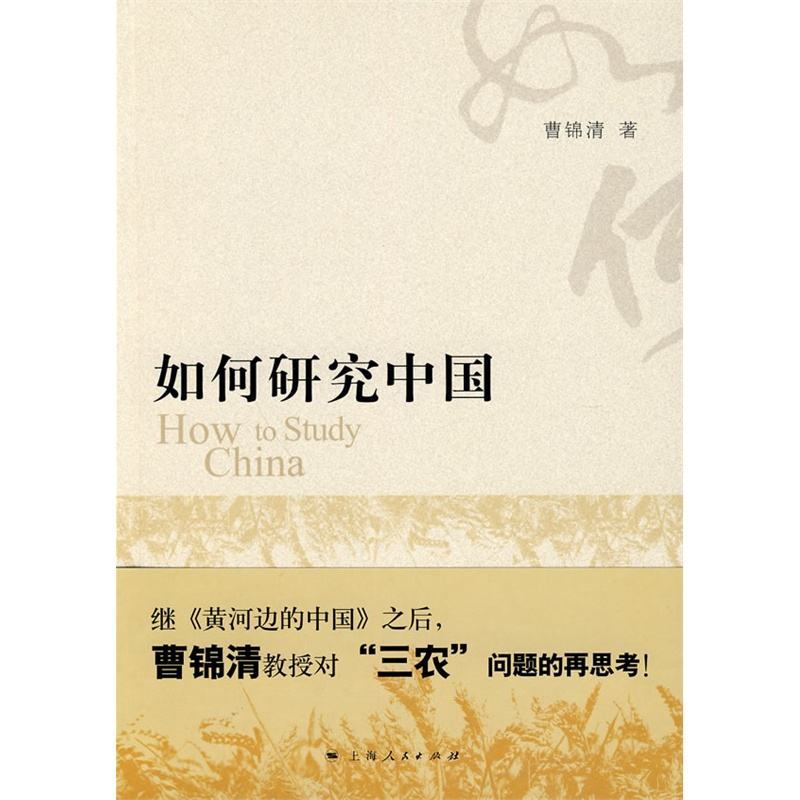
二、思想之所以拒絕民族的召喚,更與市場競爭的快速且廣泛的開展密不可分。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發展史上,商品生產一直是農業自給經濟的重要補充。在某些歷史時期,商品交換曾達到極高的程度。但經濟學家界定的市場經濟——連億萬承包制小農經濟也概無例外地為買而賣地生產——確確實實是三千年文明史的頭一遭。我們原以為市場經濟只是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政治家想用此手段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服務,自由主義想用隨市場化而來的私有制為他的心目中的民主目標服務。
直到90年代中晚期,我們才猛然驚覺,**市場經濟與競爭一旦展開,便執行起它自身的兩大目標:**一是高度簡化人們的行為動機,這是它的倫理目標;二是按個人佔有財富的多寡,重新劃分社會地位的高低,這是它的社會分工目標。人類行為背後的動機,原來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系統,否則,古往今來的哲人們也不會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了。但哲人們無法解釋的複雜動機卻被市場競爭的現實很快地加以簡化,變得極易理解。經濟學家將被市場競爭而簡化的動機概括在“經濟人”這個範疇裏。他們將經濟學的全部推理建立在“經濟人”基礎上。
“經濟人”有三個規定:一是個人主義,所謂“社會整體”只不過是實實在在的單個人的集合名詞而已。奇怪,明明是由日益加細的社會分工與交換將曾一度因經濟自給而相對獨立的家庭組織在一個相互依賴、休慼與共的經濟—社會的共同體內,然而“經濟人”的全部市場競爭體驗卻讓他意識到“我”的真實存在:他人只是我實現個人利益的工具而已;二是理性主義。“理性”原來指與天理相貫通的良知,是社會共識與規範的內化,但“經濟人”指定給理性的只有一種用途:計算個人利益的得失;三是利己主義,即所謂“個人效用最大化”。效用的外化,即是“利潤最大化”,效用的內化僅指個人肉體各種感覺器官的舒適度。於是感覺主義通過享樂主義而無可阻擋地滑向縱慾主義。
這樣,市場經濟連同為其論證的現代學説,將被宗教或“社會”約束的個人從羣體中拖拉出來,將被傳統道德禁約的“物慾”指升為“人性”,並指定它作為推動市場經濟運行的主要動力。市場競爭迫使人人為自己,那麼誰來關注社會整體與民族的未來利益呢?經濟學家説:“放心,市場經濟內在的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自動地將紛爭的私人利益調整到社會和諧。當然,這次他們在説夢話。問題是為什麼經濟學家們會陷入集體胡説呢?儘管如此,市場經濟確實將人類的多重規定(生物人、經濟人、倫理人、宗教人等等)強行簡化為單純的動機:個人利益最大化。這樣,“動機”擺脱了道德的禁束,餘下的逐利手段只得交付法律來裁斷了,即老子所説的“失德後有法”了。如果“整體”(社會與民族)及其歷史與未來在各自逐利的個人意識中消失,那麼,即令放棄追逐名利的頭腦依然存在,那麼能思的心靈指向何處呢?
私人財富執行着社會地位排序功能,中國古人或許早已發現了,否則歷代儒家為什麼頻頻發出重農抑商的指令呢?抑商的重要社會目標是防止商業財富對“道德——知識——權力”確定的社會地位的挑戰。以社會平等為價值訴求的計劃經濟時代,依然存在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但劃分的主要標準是政治權力的有無與多寡。所謂社會轉型,其實質是劃分社會地位的原則與標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單一的政治標準,向以財富為主導的多元標準轉移。
社會學家按照權力、財富和知識三大標準重新劃分社會階層,但其中最強大的標準是私人財富。權力和知識若不能或多或少地向私人財富轉換,便無法在全新的社會秩序中取得自信。權力的腐敗屢禁不止,根源或在於此。“文章”脱離“道德”而直指名利,原因或也在於此。知識精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頻頻發動對權力腐敗的聲討,甚至要求用選舉民主來更替一黨執政。然而反觀自身,尤其是對自身動機系統有所自覺的話,他們往往會因此而沉默下來。至於經濟精英們,用“都是人嘛”一句話,在寬容自己實際行為的同時,也順便寬容了以權謀私的種種罪惡。
**市場競爭,將一切人從他們的各自所屬的羣體或單位集體中驅逐出來:前有發家致富的誘惑,後有破產沉淪的恐懼。一切擺脱了單位集體約束而獲得自由,同時失去安全保護的人們,捲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私人財富的競逐之中。**於是,一個曾經相對扁平的社會僅在一代人之間演變成尖鋭高聳的金字塔型社會。那些爬升至頂層的幸運者謂之“精英”,那些在底層掙扎者謂之“弱勢羣體”,那些介於兩端之間者謂之“中間階層”。值此社會結構的急劇轉型時期,那些執行思想的頭腦也只能暫時擱置本該由他們承擔的使命而忙碌於尋找並確定自己的“社會位置”
三、相反的力量正在形成,將推動“思想”執行它的使命
如前所述,社會由“合”轉“分”。時代精神由“聚”轉“散”。人們急切地從“整體”返回到個體。從“宏大的敍事”中返回切己的當下,從“理想”返回到感官的享受。曾被“理想”禁止的“低級趣味”,如今成了人們追求的娛樂與盛宴。然而,一切能思的心靈決不會長久地駐留於此。有兩股力量推動思想重新執行被它暫時擱置的使命。
一是隨着市場化向一切領域快速推進的同時,一定會激起“社會”本身的自我保護運動。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説,市場經濟確實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有效工具;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説,市場摧毀了一切內部互助的各種羣體,使一切人成為謀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獨立的個人。這些個人之間的最主要關係不再是互助與信任,而是“冷冰冰的現金交易”。這些相互競爭,相互防範的個體感受到了孤獨、寒冷與焦慮。他們開始渴望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愛與友誼。
從純經濟學的意義上説,市場確實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但從社會學意義上説,人與自然都有內在的生命與尊嚴,無法長期忍受市場將人簡化為單純的勞動力或“人力資本”,整個自然界也無法長期忍受市場將其簡化為單純的“土地資源”。人們集合在一起進行生產活動,需要相互照料與信任,因而無法長期忍受資本將一切經濟組織簡化為資本增值的工具。沒有個人自由與利益在內的整體,遲早要被顛覆的;但沒有整體生命關聯的個人,既無法建立起有效的社會秩序,也無法提供個人的生存意義。恰如“合”久必“分”一樣,“分”久也促成新的社會關懷與合作。
為什麼四川汶川大地震激起那麼多無私的援助,為什麼那麼多互不相識的個人突然間將十分抽象的“社會”轉化為患難相恤、守望相助的真實的生命共同體?因為市場競爭將人與人之間分離得太久了:在長久的孤獨與寒冷中,人們渴望同情與温暖。我們需要市場經濟,但不允許將“個人主義與現金交易”原則引向政治與學術,引向人與人關係的一切領域,甚至引向人類最原始、最本質的生命共同體——家庭、婚姻之內。在上述普遍的個體生命感受中,能思的頭腦開始執行它的使命,逐****步形成民族生命共同體的價值共識。
二是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綜合國力的持續提高,正在崛起的中華民族必定會召喚能思的頭腦為她提供全新的思想。
這個思想要重新回答這樣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我們現處何地,從何而來,將欲何往。即現代中國在自身歷史發展脈絡中的自我定位和當代中國在全球化今天的國際定位。原有的“宏大歷史敍事”因其不再切合改革開放30年經驗的要求而被“解構”了。但“解構主義”卻是一種精神禍害。一個正在崛起的東方大國,要求思想重新擔負起重建“宏大歷史敍事”的使命。一向缺乏宗教關懷的中華民族卻有着久遠豐富的歷史感,中國的歷史(學)承載着西方宗教、哲學和史學的三重功能。歷史敍事乃是中華民族安身立命之基。先於馬列主義輸入中國的“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找不到它滋長髮育的土地,充其量只為某些知識分子提供政治批評的一套言説,究其原因在於自由主義的先天不足:缺乏歷史觀。
當然,要求當代思想有效地承擔起雙重使命,一切有幸參與純思的頭腦,首先得自覺擺脱三重束縛:一是擺脱“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二是擺脱“順着‘五四’説”的束縛,三是擺脱現有學術評審體制的束縛。擺脱三大束縛的心靈才能做到“寂而能照”。借用陸九淵的話來説,便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張”。
附錄:曹錦清丨中國崛起將引發“文化復興”
現在回頭來看,鄧小平“分三步走”發展戰略,包括了三大目標,即戰略趕超、政治民主化與共同富裕。這三大目標,各有其路線圖。
就“戰略趕超”的目標而言,我相信麥迪遜的“有條件的後發優勢理論”。當然,靠低地租、低薪酬、高投資、高污染、高出口的發展戰略已走到盡頭,中共已將“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提上議事日程。所謂轉型,首先指“擴大內需”以降低“出口與投資”在增長中的比重。而意欲擴大內需,則要着力調整內部分配結構;其次指產業結構調整,這不僅指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更主要指整個經濟在“科技與品牌”戰略的引領下,向高附加值產業不斷提升。因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創新愈加成為關鍵。對此,我持樂觀的態度。在“政治民主化”問題上,需要更加留意。如前所述,關於“政治民主化”,目前中國知識界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用西方議會民主製取代中共一黨執政制,這不是“政體改革”,而是一場“政治革命”。一是在維持“一黨執政地位”的前提下,在執政方式上推進“民主化”進程,尤其是逐步擴大“基層參與式民主制”。如將村民自治擴大到鄉鎮自治。
在未來十年,中國發生一場類似蘇聯、埃及那樣的“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極小。1989年發生的“政治動亂”,與其説是民眾對“自由、民主”的要求,還不如説是高通脹的產物。至少到目前為止,“政治革命”還停留在理念或思潮運動的層面,如果沒有被大規模且持續的失業或持續高通脹而“動員”起來的民眾街頭抗爭所支撐,是難以實現的。
至於對“民主”的第二種理解,我以為在“轉型”的壓力下,中國會逐步推進。看來,中國的現行政體根本無法納入西方主流政治分析的框架,尤其無法納入“專制政體”的分析框架。“共同富裕”是近年來逐漸成為政策和輿論的焦點。如果將“共同富裕”理解為“平均、平等”,這是不現實的。如果將“共同富裕”理解為“讓低收入階層也能分享改革開放成果”,這不僅應該,且是可能實現的。在市場經濟條下,“取不足而補有餘”會引發“社會革命”,相反,“取有餘而補不足”達到財富均等,亦會引發社會動亂。事實上,中共已從“共同富裕”向“民生建設”退卻,將社會主義主要理解為“社會保障”。
近些年來,中央新增財政重點向中西部傾斜(2011年,西藏自有財政收入約為90億,而中央轉移支付770億,且不包括各省市的對口援助經費)。城市財政向農村傾斜(城鄉一體化建設),公共財政向事關民生的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傾斜。這些政策調整,使百姓受益。據我的觀察,中國億萬中老年農民是十分滿意的。
在上述三大戰略目標不斷推進的前提下,中國要實現追趕目標,還有賴於民族自信與文化自覺的發展。
亨廷頓曾提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前後兩階段論”,並指出了“西方化”與“現代化”的區別。亨廷頓認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要經歷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西方化引領現代化;第二階段,去西方化,迴歸本土化來引領現代化。兩階段交接的時機:一是該民族自身在第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中取得足夠的“民族自信”,同時,在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人際關係、社會心理發生重大變化而出現大量問題。因此,這兩大動力推動着整個民族“去西方化,迴歸本土化”,實現新的民族認同。
有諸多跡象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似乎正在接近“兩階段”交替的臨界點,在文化上處於一種過渡的狀態。
在思想界,文化保守主義日漸興起;在學術界,費孝通等人提出了“文化自覺”論,社會學領域本土化的呼聲增強。
但總體上講,中國主流知識界依然是“西化論者”。高等教育幾近“全盤西化”。文化上,中國至今依然是一個“單向輸入國”,留學運動亦然。此外,西方“普世論”,如自由主義、馬列主義的長期影響,給中國考察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帶來了諸多困境,比如“政體論”與“社會經濟階段論”一度流行但説服力不足。
回顧歷史,近代以來,“中-西”關係中交織了“古-今”關係的敍事,“中-西”地位關係的變動,將直接影響中國自身“古-今-未來”結構敍事。這是一件大事情。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追趕目標的實現將增強民族自信,從而引發“中國文化復興進程”,建立新的“中-西”關係,以及“古-今”關係的敍事。
注:本文為作者在2012年5月中國力研究中心費城論壇上演講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前面三個部分分別是“從鄧小平的‘分三步走’發展戰略説起”、“中國‘趕英超美’意味何在 ?”以及“向左、向右,中國向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