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戲曲界的新戲拿什麼能讓九零後走進劇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2017年10月20-21日晚,浙昆攜看家戲《十五貫》,並彙集“世、盛、秀、萬、代”五代浙昆傳承人的強大演出陣容,作為今年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的參演劇目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隆重上演,這也是浙江崑劇團首次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
在演出前,浙昆在上海虹口區某大酒店舉行了演出前的新聞發佈會。筆者在現場有幸目睹了幾位國寶級的表演藝術家,比如世字輩的王世瑤先生、沈世華先生,還有參與助演的滬昆的頂樑柱計鎮華先生。
提到《十五貫》這出戏,其本身的沿革史和它的各摺子內容本身一樣精彩。它在整個崑劇史上有“女蝸補天”的意義——這一點在1956年的《人民日報》著名社論“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已經有了很精煉的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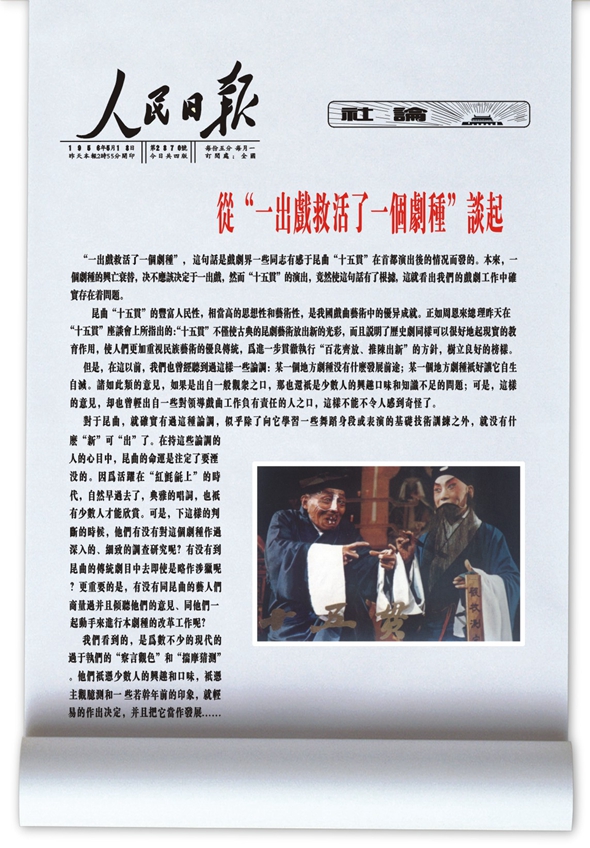
人民日報當年的社論
60多年之後,此文凸顯問題意識仍極具有最前沿的時代感,即是戲曲界是否還需要推陳出新,抑或是向文中提到的某些領導所言,不如遵循曲藝達爾文法則,讓某些劇種自身自滅。那麼,假如當時崑劇沒有國家力量強推,會不會像現如今的山東呂劇一樣處在棺材板即將合上的邊緣?扛起崑曲復興大旗的是又為何是《十五貫》,這是個偶然嗎?
以筆者愚見,不但崑劇涅槃重生是一種必然,而且《十五貫》可以充當崑劇救世主的角色,這一現象也絕非偶然。
一個劇種的變遷發展,離不開該劇藝術表達手法的自我演進的努力,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十五貫》在50年代能火遍廟堂街巷,不能不説也一種歷史的選擇。首先,其演藝題材契合了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對民國時代粗濫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氾濫的批判,劇中人物無非是基層官員,平民百姓,和市井無賴;其次,它“極高明而道中庸”,避免了“曲高和寡”對崑曲的慣常揶揄;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十五貫》跌宕起伏的故事脈絡,有着足夠的戲劇衝突,起承傳合自然連貫,而且劇本歷經了大約一個世紀的打磨,連台本戲基本分成了八折,每一折單獨拎出來都有特色行工挑班,能成為獨當一面的摺子戲。

《十五貫》演出劇照
而且《十五貫》的文本來源有着深厚的歷史底藴,較早的底本可以追溯到馮夢龍整理編纂的《三言兩拍》。在整個80年代各種振興民族傳統戲劇的風潮下,《十五貫》重新被髮掘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總之,這出戏能夠成為崑劇這一劇種的扛鼎大戲之一,絕不僅僅是外部行政因素的助推,而是符合了戲曲與時代相結合的曲藝發展規律這一內在理路。
除此之外,另一種不得不注意的現象是,為了響應曲藝界創新的號召,過去十幾年來每年都有大批量的新編歷史劇平地起高樓式的出現,屬於完全原創的新戲,給了更多曲藝界的從業人員一試身手的機會,也鍛鍊了各個劇團梯隊的舞台技巧和出演經驗。
但有一點很遺憾的是,不少新排演的新戲良莠不齊,藝術表現手法單一匱乏,觀眾反響平淡,而且“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僅離“長青戲”的要求差的遠,而且連混個臉兒熟的標準也沒有達到。
箇中原因何在?筆者以崑劇《十五貫》的經典傳承為參照,再加上極為貧瘠的戲曲知識,斗膽分析一下原因。
戲曲內核扁平化
2010年4月,筆者在北京東城區的長安大戲院現場觀看了新編歷史劇《鄭和下西洋》。這是筆者有生以來目前唯一一次進帝都大戲園子看戲,而且買票的錢創下了以往的看戲記錄——460元,坐在了第五排靠左邊的位置上。
對比京滬地區各大戲院各個戲種的票價看,這個價位應該算是比較高端的了。開演前10分鐘筆者掃了一眼現場,差不多坐了四分之三的觀眾,應該説賣相很不錯了。首先這得益於前期的宣傳很賣力,演出的海報還特意突出了“交響樂京劇”這個概念,噱頭很足;而且這是一出天津京劇團推出的重頭新戲,登台的是天津團裏的大角兒,也是長期活躍在京劇舞台的一線演員:幾乎年年在春晚登台獻唱的著名銅錘花臉孟廣祿,和早在90年代末就被戲迷們評選為“五小程旦”之一的劉桂娟,還有中生代老生的佼佼者張克。

銅錘花臉孟廣祿飾演鄭和
在戲幕拉開之前,筆者突然聞到陣陣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味,還在猜測這是不是新京劇在搞視覺衝擊的同時,也要強調嗅覺衝擊。開幕之後終於明白了,這是灑出來的特色“香味乾冰”的味道。
陣陣煙霧,嫋嫋婷婷的羣舞者,還有不同於鑼鼓傢伙的大小提琴,《鄭和下西洋》就這樣開場了。筆者承認,在大約兩個半小時的時間內確實享受了一番視覺盛宴。但卻不得不問一個孔乙己似的老頑固問題:這還是京劇嗎?
對於京劇來講,除了最基本的舞台表現手法唱唸做打和手眼身法步之外,曲調、詞牌與唱詞的嚴絲合縫,能不能做到高度統一(這還不算京劇演員對舞台空間的深刻理解),是評價一齣戲藝術價值的重要標準,正所謂“聲依永,律和聲”。廣義上來看,説《詩經》是中國最早的戲曲唱本也未嘗不可,因為有詞有調,是用來唱的,比如“鄭風”算是原生態的豫劇,而“秦風”則是中國最早的秦腔。
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發聲方法,這也使得韻腳的把握要符合音律的高低婉轉,甚至包括曲頭的“過門兒”(所謂過門兒,筆者認為這相當於《詩經》賦、比、興中的“興”)也要拿捏好為整個曲譜奠定節拍和演唱情緒的微妙作用。比如一首歌按照粵語和普通話唱出來完全可能是不同的感覺,譜子不變,但唱詞可以改,所以很多填詞者不得不調整“詞韻”去適應既成的曲譜。
筆者在這裏以馬派和《甘露寺》和麒派的《甘露寺》唱詞做一個對比,讀者可以自行體會一下不同的感覺,同樣是西皮原板(麒派稍微調整了節拍,變成了西皮慢二六版)轉西皮流水版,但是韻變了:
馬派:勸千歲殺字休出口,老臣與主説從頭,劉備本是那靖王的後,景帝玄孫一脈留,他有個二弟,漢壽亭侯,青龍偃月神鬼皆愁,白馬坡前誅文丑,在古城曾斬過老蔡陽的頭,(轉流水)他三弟翼德威風有,丈八蛇矛慣取咽喉,鞭打督郵他氣充牛鬥……
麒派:勸千歲休要出此言,老臣有本奏君前。劉備本是那中山靖王后,漢室宗親一脈傳。他有個忠義二弟關美髯,青龍偃月刀神鬼皆寒。刀劈那文丑又把那顏良斬,保皇嫂斬六將闖過五關。老蔡陽聞此言領兵追趕,拖刀計斬蔡陽就在那古城邊。(轉流水)他三弟張翼德豹頭環眼,丈八蛇矛慣取喉咽。曾破黃巾兵百萬,虎牢關三戰過呂奉先。在那當陽橋一聲喊,喝斷了橋樑退曹瞞。他四弟子龍渾身膽,蓋世英雄天下傳……
很明顯,馬派的韻是“ou”,麒派的韻是“an”,前者這個流派清亮灑脱,再加上坊間對這個派別有善意的羣嘲,唱的時候一定要大舌頭,用ou押韻不但更利於氣息連貫,而且真假聲的轉換銜接也更自然;後者沙啞低滄,壓在“an”上顯得更清脆,沙而不澀。
除此之外,由於歷史流變的原因,京劇的唱詞還受到尖團字的規範和限制,所謂尖團,是現代漢語中j,q,x聲母,古音(至少京劇中保持了這種音,很多方言也有,如河南的中州音)中有些字是讀成 z, c, s 的。類似於平翹舌,有些方言不分都讀平舌。尖團在普通話不分都讀團。因為古代j,q,x聲母出現前,那些字以前要麼是z,c,s聲母,要麼是g,k,h聲母z,c,s聲母變來的叫尖字,g,k,h聲母變來的叫團字。
正是有了這些較為原始的規範作為基本創作邊界,才能保證京劇的發展的內部統一性和穩定性,雖然同一工種的流派不一,但不至於出現大水浸灌,散漫無章的狀況出現,這正如播種插秧時,必須要考慮種子埋土的深度種子間距一樣——喜看稻菽千重浪,即將豐收的稻菽背後是上千年總結出來的科學的播種方法。
那麼,《鄭和下西洋》符合這種“播種方法”嗎?沒了四擊頭,沒了快長錘,沒了小鑼,大腕兒們亮相起調門兒的時候怎麼看怎麼不自然,張克老師好像不得不用一種“老生美聲”去適應西洋樂器中的管絃類和彈撥類的樂器;至於唸白就更不用説了,跟普通話的賽詩會幾乎已經沒有區別了;這還不算,劉桂娟老師的“幽蘭”這個角色過於突兀,在鄭和身邊活脱兒是個多餘角色。

程派演員劉桂娟飾幽蘭
但就是這個劇不但斬獲國內多項頂級戲曲類大獎,而且成了京劇革新的典範。有了這部劇做開路先鋒,之後京津兩地的京劇院聯合排演的《新三國》就“更上一層樓”了,據説其演出預算是《鄭和下西洋》的5.5倍,佈景、燈光、音箱絕對可以媲美國內頂級的演唱會標準。
老生諸葛亮於魁智,花臉曹操孟廣祿,小生周瑜李宏圖……這樣的演出大腕兒你還矯情什麼?是啊,你沒發現舞台“鏡頭”轉換之快是老三國戲的三四倍都不止嘛,大段的流水版加上慷慨激昂的唸白,有這麼一個嘻哈版京劇又有何不可?

新編京劇赤壁之草船借箭(圖片來源:鳳凰娛樂)
像《逍遙津》那種二黃導板“父子們在宮苑傷心落淚”短短十個字,高派的李和曾唱了足足110秒,估計要被“新京劇”愛好者們噴成毒瘤糟粕和癌症唱法了。
而且新派“京劇行家”喜歡拿文革樣板戲的“創新”激勵自己搞新編歷史劇,乍一看有些説服力。樣板戲的成功確實有非常強的特殊年代下政治推動的因素的加成,但有一點必須指出,八大樣板戲,除了文革後期的某一兩個的活有點糙之外,之前的幾部無論《紅燈記》、《沙家浜》還是《智取威虎山》,從一開始立項到最後登台,劇本台詞和譜調的打磨不下數千次,而且底本都是諸如像汪曾祺這樣的一流文學家負責把關,而且唱唸做打的設置一板一眼,將舞台的內核藝術性和外在表現力革命性做了高度結合。

僅舉一例,《沙家浜》智鬥這一折,馬長禮老師的一句“這個女人不尋常”,這一西皮搖版,將刁德一的多疑和陰損狡黠表現得淋漓盡致讓人回味無窮,而且很難唱,到今天也是老生進階的標準考試科目之一。
而今的京劇新戲往往見錢而不見人,而且從根本上有意無意地迴避甚至畏懼對一些戲曲舞台基本規範的瞭解和鑽研,這一點上看,60年代的新戲質量,能讓當下的新戲跪下來打call三次也不算過分。
觀眾中產化
不過行文至此,從業者們估計也有一肚子苦水要吐。面對大量觀眾對新戲的挑剔和吐槽,他們的怨言很多時候也不乏合理性。比如劇團考核KPI,新戲的排演創新的量就是指標之一,而且立新戲是拿到項目資金的重大來源,這就跟大學裏的科研院所立山頭搞項目是一個道理,時間緊任務重,打磨劇本的心思也就被嚴重弱化了。拿到了錢,花的要有個交代,最便利的莫過於從舞台佈景和演員的行頭着手。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很多劇種都有強烈的地域色彩,比如受限於方言基準,豫劇很難過長江以南,崑曲很難過長江以北,一個廣東人喜歡聽二人轉或者一個東北人痴迷粵劇,都是很難想象的,不論唸白唱腔都很難普遍化地為各地戲迷所接受,所以説地域和方言本身就為戲曲的推廣製造了各個門檻。
另外不得不説的是,就是各個曲種都面臨着受眾的迭代問題。這很現實,當下的娛樂文化模式下,戲曲要和電影、球賽、演唱會、電子競技等分一杯羹,何其難也。你如何能説服九零後們花錢買票走進劇場,平心靜氣地去看一場戲?

江蘇省崑劇院演出的《1699桃花扇》被圈內外公認為新才子佳人戲的典型代表(圖片來源:新浪娛樂)
讓年輕人走進戲院是十幾年以來圈內人的共識,這種危機意識不僅是在市場化大潮下如何養活自身的問題,而且涉及到娛樂生態食物鏈的構成,於是大小劇團為了取悦年輕一代的戲迷,不惜使出渾身解數,而且他們發現,有錢有閒進場看戲的非老戲迷,都有一種中產階級的生活樣態,那麼與此相應的,戲曲改革也有濃重的“中產化”傾向。
前文中舉的《鄭和下西洋》和《新三國》的例子已經部分地説明了這個問題,即要在兩個小時的有限時間內滿足觀眾的視覺衝擊感,新老佈景的轉換,就好比電影用3D代替畫面,路線是一樣的。

蘇崑著名花旦單雯的《長生殿·小宴》
而且戲碼也在中產化,50年代批判的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劇再次大批量地充斥在各個舞台上,崑曲中的《牡丹亭》、《桃花扇》、《長生殿》反覆上演不斷改編,花旦和小生也成了最紅的工種。
戲碼的偏科、行工的傾斜正在不斷的扭曲着整個戲曲行當的發展態勢。新老戲迷們突然發現,現在的舞台上,文武丑和老旦甚至花臉從未如此地被邊緣化。筆者多年前看過北京京劇院新一輩老旦演員康靜的訪談,她在接受採訪中提到,當初學戲時被老師逼着要唱老旦是多麼地不情願。為什麼其他小姑娘扮地漂漂亮亮的出演花旦青衣,自己卻要又老又醜地唱“滄腔”?
花旦易找,老旦難尋是京劇界多年來的話題,市場化、商業化默默地把控了劇團的人才培養導向,如果説京劇歷史上“生旦淨末丑”中的“末”被“生”這一工吞掉是京劇舞台內在理路自然演進的結果,而今天“醜”和“老旦”的弱化則有太多的外力因素。
正如此,筆者才能體會《十五貫》新聞發佈會上,計鎮華老師不下五次反覆提及“《十五貫》是一出老生戲”,因為崑曲的才子佳人戲目前已經氾濫到無法收拾的地步了。
餘論
新聞發佈會上,計鎮華老師還有很多分量很重的話:“我當着各位媒體朋友和同行的面,可以這樣説,新戲花的錢越多,失敗的概率就越大,現在有太多年輕演員忽視基本功的訓練。”本來坐在對面的王世瑤老師不想發言,聽到後也激動地拿起了話筒:“我老了,80多了,牙齒都掉光了説話漏風,本來不想説什麼。看看以前京劇《三岔口》,台上就只有桌椅板凳,兩個人打來打去,這是傳世的經典。佈景越是簡單,台上的演員越是少,就越吃功夫越難演。現在台上人一窩蜂,我不愛看,今天我懷着感恩的心,向支持老戲《十五貫》的在場的朋友們表示感謝。”


計鎮華、王世瑤、沈世華等崑劇前輩在新聞發佈會現場
在新聞發佈會結束之後,筆者在和浙江崑劇團的某俊美的女小生演員閒談,也聊到了目前的新戲困境問題。這位80後萬字輩的坤生提到,目前很多新戲都是為某一兩個角兒量身定做的,本身也沒有推廣和傳承的意圖,而且她還提到對新戲的心態要放寬:看看目前的影視界,多年下來又有幾部是經典呢?
筆者不想再多對新老兩輩人的觀點做蛇足的評判,只是一直認為新戲的編排者恐怕嚴重低估了國內新一代觀眾的欣賞水平,難道收入水平的中產化帶來的不是審美情趣的中產化?
在京劇推廣過程中,也不斷有新老戲碼走出國內邁向海外。但很搞笑的是,國內外的版本往往有差別:某大劇團的程派拿手戲《鎖麟囊》,在美國巡迴演出時,為了照顧洋觀眾,居然加了三段武打。隱含的信息是,洋鬼子看戲往往傻眼,怕你們看得悶,加段武打熱鬧一下。他們不但低估了國內年輕觀眾,其實也低估了洋鬼子們——進場看戲的外國人很多都有歌劇欣賞水平打底,京劇的舞台劇設對他們未必是陌生的,馬鞭代馬,翻手推門,以虛代實,以近代遠,這是人類戲曲共通的語言。

兩個瑞典小夥也上台體驗了一把京劇(圖片來源:北歐時報)
2009年年底,某北方知名京劇團組織海外巡迴演出,瑞典是其中一站,在美輪美奐的斯德哥爾摩藍色音樂大廳內,京劇《白蛇傳》開演了。現場演出的火爆超出了筆者的想象,過道上也站滿了人,就差賣掛票了。如前所述,給洋鬼子演戲是要加武打的,於是有了許仙在斷橋相遇之後和法海對打的“尬戲”。不料坐在旁邊的一個瑞典老太太扭頭對我説了一句:“det är ett nytt avsnitt”(這段是新加的吧),我只能尷尬而不失禮貌地點點頭。
筆者也不想把本文寫成新戲吐槽專場,浙昆的那位小姐姐曾對我説的,你如果想吐槽,最好也是先買票進了園子再説,正所謂“褒貶是買主”。
進了園子,你可以很有範兒的,裝作老戲迷一樣,輕拍着大腿對身邊一同看戲的女票裝逼:“《霸王別姬》這出戏怎麼味兒不對啊,楚霸王回營亮相一出,本應該走八步,他只走了五步,楚霸王乃是六國貴族之後,氣度雍容華貴,可不是綠林的黃天霸。”
舞台上就這三步,便可以讓楚霸王變成黃天霸。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