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沙特槓上伊朗,卻為巴以問題提供新契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隨着沙特國內政治紛爭不斷,沙特國王薩拉曼和王儲穆罕默德罷黜王室成員,“軟禁”黎巴嫩總理、沙特國王薩拉曼要“禪位”給自己的兒子、當前王儲穆罕默德的消息不斷傳出,一個國內政治危機若隱若現,且與地區國家伊朗形成“對峙”的沙特,似乎即將出現。
與此同時,以色列總參謀長艾森考特近日接受採訪時表示,以色列正在考慮與沙特建立“情報分享”機制,此言一出,更是讓人們普遍猜想,一個“以色列+沙特”的地區聯盟,似乎正在成型。而巴以問題,也似乎隨着以色列和沙特關係的緩和,迎來了新的契機。
共同的“威脅”——伊朗
沙特與以色列之間的“聯盟關係”,在近些年不斷顯現。沙特和以色列都是中東地區“反伊朗”的重要國家,都視伊朗為自己地緣安全的重要敵手。
以色列認為,伊朗支持周邊的地區政治軍事團體,如加沙的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武裝,這些團體都直接對以色列形成威脅;與此同時,以色列還認為,伊朗不斷散步要“消滅以色列”的聲音,伊朗的核武器和導彈技術,也直接威脅着以色列的安全,因此以色列需要尋找地區或域外盟友,一起遏制伊朗的“擴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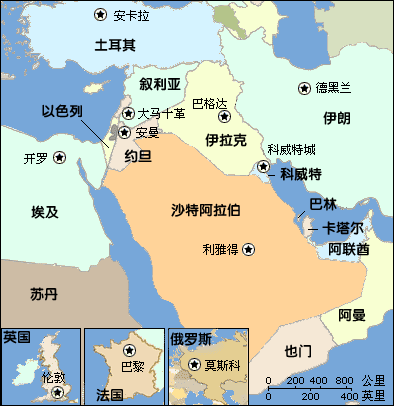
與以色列相比,沙特認為自己所受到的“伊朗威脅”更為直接。沙特和伊朗的距離更近,沙特國內的產油重鎮東方省有大量的什葉派民眾,這些什葉派民眾的信仰,與沙特所秉持的主流遜尼派瓦哈比教義相差不小,而對伊朗則報以同情甚至信任。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發生後,不少東方省的什葉派民眾高舉霍梅尼的頭像,希望能效仿伊朗,提升什葉派宗教派別在社會生活中的話語權和合法性。
而在地區爭奪中,伊朗強大的軍工實力,則是沙特單純的“石油紅利”無法比擬的。從黎巴嫩到敍利亞,從伊拉克到也門,能夠決定未來局勢走向的並不是“出錢”的沙特,而是強大的伊朗。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尤其是近些年隨着薩勒曼國王的上台執政,沙特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也就顯得“惺惺相惜”。比如今年年初有消息傳出,以色列正在國內“培訓”沙特的情報和軍事官員,而沙特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也少不了美國的“影子”,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其女婿庫什諾,都似乎成為了沙特和以色列未來可能“走近”的重要外部保證。
心存芥蒂的沙以關係
作為自視為“伊斯蘭世界領導人”的沙特,如果確實與以色列在伊朗問題上不斷“走近”,則少不了巴以問題實現突破這一前提。事實上沙特正是巴以問題解決的重要一方,無論是在各個國際組織和雙邊平台上,還是在重要的歷史文件和倡議中,沙特都積極鼓勵巴以建立“持久的和平”。
比如在2002年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舉行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峯會上,沙特是第一個提出“承認以色列”,以此換取以色列外交讓步,“建立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的國家。而2002年沙特關於巴以問題的提議,也得到了來自於阿拉伯國家聯盟和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廣泛贊成。2002年在巴以問題上的“沙特倡議”,也成為了巴以和談重要的外部激勵措施,至今仍然代表着廣大阿拉伯國家解決巴以問題的重要立場。
但是,如果像很多分析人士所言,沙特和以色列關係的“趨近”必然帶來巴以和談的突破,那麼這就顯得太過“樂觀”。首先,沙特和以色列的“趨近”仍然有限,至少在公開場合的“趨近”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從沙特角度講,積極推動與以色列的“準聯盟”關係,無論是私下的還是公開的,勢必面臨巨大的外交和道義風險,尤其是在當前中東地區輿論話語權多元化的背景下,貿然推動與以色列的“合作”,勢必被伊斯蘭保守人士、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泛伊斯蘭主義者視為“異端”和“背叛”,這對於沙特王室合法性將會形成致命的挑戰。
而從以色列的角度講,大規模的、公開的推動與沙特的關係,儘管有助於“遏制”伊朗,但是卻容易陷入內部的巨大爭議。儘管“反伊朗”是當前以色列國內政界和學界的“共識”,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以色列要必然推動與沙特的“合作”。
事實上以色列對於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合作”,心存疑慮,而如果這些“合作”必然涉及到“巴以和談”,則更會帶來以色列國內的普遍反感,因此任何政治人物(而不是如以色列總參謀長這樣的軍事人物)很難在公開場合談論與沙特“合作”。
複雜的巴以問題
以色列在當前也並不需要“沙特倡議”,來推動與巴勒斯坦的和談進程。“沙特倡議”儘管提出了阿拉伯國家“承認以色列”這樣“誘惑條件”,但是對於以色列來説,這樣的“外交承認”,在國內的“政治魅力”卻難以彌補相關政治議題。“沙特倡議”要求以色列承認東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國家的首都”,要求以色列“妥善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這些議題對於當前的以色列來説缺乏足夠的動力。
以色列已經長期佔領耶路撒冷,而且難民“迴歸權”問題又十分敏感和複雜。比如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在2000年的巴以談判中,曾經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卻仍然在難民“迴歸權”議題上沒有滿足時任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的要求,結果在談判失敗後,談判細節被公之於眾,以色列民眾對於巴拉克的讓步憤怒不已。
而且難民“迴歸權”問題,在以色列國內右翼陣營又被與“猶太難民迴歸權”問題(第一次中東戰爭之後,不少阿拉伯國家也開始驅逐國內的阿拉伯猶太人)掛鈎,認為“巴勒斯坦難民迴歸權”應當與“猶太難民迴歸權”共同解決。因此“沙特倡議”只不過顯示出了阿拉伯國家希望能夠解決巴以問題的“願景”,而難以成為巴以問題解決的“具體方案”。
巴以問題的談判,事實上當前難以開展。無論是2014年雄心勃勃的美國國務卿克里,還是現在特朗普身邊的“中東通”格林布拉特,要麼在巴以談判中“無功而返”,要麼就是忌憚於巴以問題的複雜性而不願“啓動”。事實上當前巴以和談的具體情況,不再是“如何談”,而是“如何解決談判的先決條件”。

傳統的幾個比較複雜的議題,比如約旦河西岸猶太定居點議題、耶路撒冷歸屬議題、巴勒斯坦難民迴歸議題等等,都是老生常談。事實上從過去尤其是2014年美國國務卿克里主持的巴以和談來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和談事實上已經很難“正式開啓”。
巴以和談當前的難點已經不再是討論幾個“老議題”,而是如何達到彼此的“先決條件”的問題,以此為“善意舉措”,隨後開啓正式的直接對話的問題。對於以色列來説,“先決條件”無外乎是“巴勒斯坦停止針對以色列和猶太目標的襲擊”,“巴勒斯坦停止資助襲擊者家屬”,而巴勒斯坦的“先決條件”,無外乎“釋放被以色列關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停止(或者暫時停止)在約旦河西岸修建猶太人定居點”這兩項。
無論是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的“先決條件”,事實上都成為了新的難以解決的“老議題”。
從以色列方面來説,要求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停止資助和幫助“恐怖分子家屬”,在事實上難以實行。巴勒斯坦民眾普遍將“恐襲分子”視作反抗以色列的“英雄”,如果與之決裂,則意味着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合法性的喪失,這在當前巴勒斯坦內部派別並爭的背景下,尤其是阿巴斯政府威望日衰的前提下,無異於“政治自殺”。所以在此問題上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很難滿足以色列的願望。
從以色列角度看,“停止修建約旦河西岸定居點”,則意味着內塔尼亞胡政府將會面臨右翼和極右翼的巨大壓力,在當前以色列國內政治和社會右翼佔據主流的前提下,這樣的舉動具有很大的風險;而“釋放巴勒斯坦囚犯”,尤其是按照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要求“全部釋放”,則意味着很多囚犯,尤其是一些在以色列人眼中確實犯下恐襲罪行的囚犯,將要被釋放,這對於以色列來説難以接受。
沙特和以色列的“趨近”,在當前雙方共同將伊朗視為“敵手”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按照“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似乎十分“現實”和“合理”,而巴以問題的解決也似乎因此迎來了一個“新契機”。但是以色列和沙特,要麼“無心”,要麼“無力”去推動巴以問題的解決。諸多巴以和談中的結構性矛盾,也仍然存在且“越來越多”。巴勒斯坦人,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民族主義世界下,被阿拉伯國家遺忘的角落。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