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談如何在網絡時代生存:超連接的虛假預言-尼爾·弗格森
【在哈佛的畢業演講中,扎克伯格展望一個“每個人都有意義感的世界:通過共建一個偉大的有意義的項目、通過重新定義平等,從而使每個人都有自由追求意義,並最終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社區。”
**網絡世界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句話已經不是預言式的將來時,而是一個完成時。網絡技術和政治格局又有怎樣的關係?**如何用網絡結構來理解政治層次和人際關係?
在尼爾弗格森的新作之中,他對這些問題給出了絕妙的回答。本文發表於《外交事務》九/十月刊,節選自其新著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Networks and Power, From the Freemasons to Facebook, Penguin Press, 2018.翻譯:杜中華】
一個普遍公認的事實是,世界前所未有地連接在一起。不久之前,人們還相信,每一個個體和這個星球上的任何人之間的分離度可以用6度的指數來表示。對於今天的Facebook用户來説,平均的分離指數為3.57。但也許這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正如埃文•威廉姆斯(Twitter的創始人之一)於2017年5月告訴紐約時報的,“我曾經想過,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交流信息和想法,世界將自動地成為一個更好、更宜居的地方。但我錯了。”
在同一個月的哈佛學位授予儀式上,Facebook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Zuckerberg)回顧了他本科時期的“連接世界”的野心。“這個想法對我們來説很清楚,”他回憶説,“所有人都想彼此聯通……我的希望永遠不是去建立一個公司,而是要改變這個世界。”扎克伯格一定做到了這一點,但這個結果是否如他最初在他的宿舍中料想的一樣,是值得懷疑的。扎克伯格在他的講話中指出了一系列他們這一代面臨的挑戰,其中包括“數千萬的工作被自動化替代”,“不平等”(“我們的體制存在問題,我可以離開這裏, 在十年內賺取數十億美元,但是數百萬學生卻無力償還貸款”),和“權威主義,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力量”,“反對知識流動,貿易和移民”。

馬克扎克伯格的哈佛演講
但他沒有提到的是,他的公司和硅谷的同行對這三個問題都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
世界上沒有一家企業比加州的技術巨頭更加努力地消除像卡車司機這樣的工作。沒有人比硅谷的商業大亨們更加鮮明地體現出擁有最多財富的百分之0.01的人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也沒有公司比Facebook——儘管是在無意中進行的——更加有力地幫助民粹主義者在英國和美國贏得2016年的政治勝利。沒有Facebook關於其用户的數據寶庫,對於相對來説預算較低的英國脱歐(Brexit)和特朗普來説,贏得大選肯定是不可能的。不知不覺中Facebook在流行了一年的“fake news”故事中扮演了關鍵的作用。
扎克伯格絕對不是網絡世界和他的“全球社區”夢想的唯一信徒。自1996年以來,Grateful Dead的歌詞已經成為網絡活動家約翰•佩裏•巴洛(John Perry Barlow)發表的“網絡獨立宣言”的一部分,其中他呼籲“工業世界的政府,你疲憊的肉體和巨人”,“不要管我們”;而為了通用連接,已經有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的啦啦隊遊行。“當前的網絡技術…”,Google的Eric Schmidt和Jared Cohen在2013年寫道:“是真正有利於公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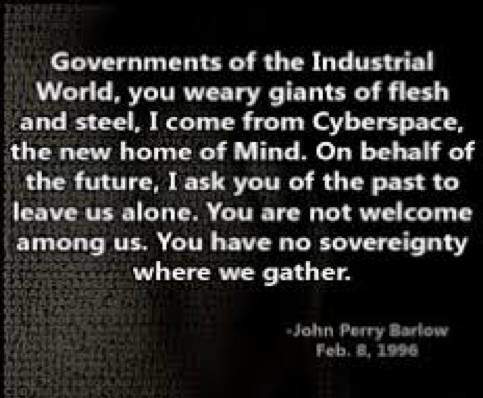
約翰佩裏巴洛的網絡獨立宣言
“從來沒有這麼多人通過即時響應的網絡連接起來。”他們認為,這對於各地的政治來説都將具有真正的“左右遊戲全局”的影響。阿拉伯之春的早期階段似乎證明了他們樂觀的分析;但隨後敍利亞和利比亞的後裔進入內戰,似乎沒有特別説明他們的判斷。
正如約翰•列儂的“Imagine”所唱的,一個網絡世界的烏托邦幻想是在直覺上很吸引人的。例如,在他的哈佛演講中,扎克伯格認為“人類歷史正在畫一條偉大的弧線——這就是,前所未有的眾多人數,從部落到城市再到國家的人,正在實現我們不能僅靠自己完成的事情。“然而,這個願景,一個有如鐵板一塊的單一的全球社會,在歷史弧的盡頭,與我們所知道的關於全球社會的一切是不一樣的。
網絡不再是新的,而是一直在自然世界中並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東西。對於今天的社交網絡而言,唯一的新鮮事物就是它們以有史以來最大的規模,最快的速度,在幾秒鐘內連接數十億人。然而,在Facebook成立前很久的大量研究顯示,社交網絡正在縮減到越來越小的範圍,效率也越來越低。他們的發現不能給對未來完全聯通的網絡世界運營的樂觀主義提供任何支持。
不是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
六個基本見解可以幫助那些沒有網絡理論專業知識的人更清楚地思考關於巨大的高速社交網絡可能的政治和地緣政治影響。
首先涉及網絡中連接的模式。
自十八世紀的瑞士學者Leonhard Euler以來,數學家將網絡視為節點圖,通過鏈接點連接在一起,或以網絡理論的説法,通過“邊緣”相互連接。社會中的個人只是網絡通過邊緣連接的節點,我們稱之為“關係”。
不是所有的節點或邊緣都是平等的,然而,因為很少的社交網絡類似於一個簡單的網格(每個節點與所有其餘節點具有相同數量的邊),通常,某些節點和邊緣比其他的更重要。例如,一些節點具有較高的“聯通度”,這意味着他們有更多的邊緣,有些具有更高的“中間性”,這意味着他們是充當着許多網絡流量必須通過的繁忙路口。不同的是,幾個關鍵邊緣可以充當橋樑,將不同的節點簇連接在一起,否則將無法進行溝通。即使如此,“網絡隔離”依然總是存在——這就是尚未連接到網絡主要組件的單個節點。
同時,有着相同羽毛的鳥傾向於聚集在一起(相近相吸)。這種現象被稱為“同情”或吸引相似性,社交網絡傾向於形成具有相似性的屬性或態度的節點簇。研究人員發現,當他們研究美國高中時,可以沿着種族隔離或其他形式的兩極分化形成相應的中心隔離。最近,將美國公共領域分成兩個隔間,每個隔間完全不能聽到對方的聲音,就是完美的例證。
關於社交網絡的大量寫作的常見錯誤是將網絡和等級區分開來。這是一個虛假的二分法。等級只是一種特殊的、具有有限數量的水平邊緣的網絡,它使單個統治節點成為一個高度的中心。任何專制統治的本質,都是讓組織圖上的每一個節點不能彼此溝通,並且除了和中心節點發生關係外,彼此之間無法組織起來。正確的區別是在等級網絡(Hierarchical networks)和分佈式網絡(Distributed networks)之間。
對於大多數歷史來説,等級網絡主導分佈式網絡。在相對較小和衝突相對頻繁的社區,集中領導享有較大優勢,因為通過集中的命令和控制,戰爭通常更容易。此外,在大多數農業社會,識字是少數精英的特權,所以只有幾個節點是和讀寫世界相聯繫的。但是,500多年前,印刷機出現了——它使得馬丁•路德的異端變得異常強大,並催生出一個新的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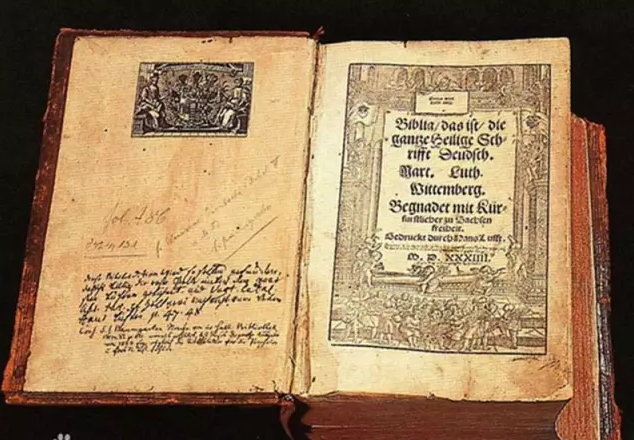
馬丁路德翻譯的聖
路德認為,他改革羅馬天主教會的運動的結果將是一個被稱為“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東西,它是扎克伯格的“全球社區”的十六世紀等價物。實際上,新教改革產生的不止是一個世紀血腥的宗教衝突。這是因為路德和後來的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的新教義,在歐洲的傳播並不是均勻的。
雖然新教迅速形成一個網絡結構,但它也使得歐洲的同質性被分化,那些在人口密度和識字率方面和德國城市比較類似的歐洲地區開始擁抱新宗教,而大多數農村地區則反對它,並且擁護教皇的反宗教改革。然而,事實證明,即使通過大規模的處決,天主教統治者也不可能摧毀新教網絡,正如不可能在採納宗教改革的國家全部拔除天主教一樣。
薄弱關係點的強度
第二個見解是,薄弱關係點非常有力度。正如斯坦福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3年的一篇精采文章中證明的,熟人是朋友圈之間的橋樑,正是這些薄弱的關係點,讓世界變得很小。在心理學家斯坦利•米拉格(Stanley Milgram)在1967年發表的連鎖信件所顯示的著名的實驗中,在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一名遺孀職員之間和和波士頓的一位她不認識的股票經紀人之間只有七度分隔。
像宗教改革一樣,科學革命和啓蒙運動是網絡驅動的現象,並且它們的傳播越來越快、越來越遠。諸如伏爾泰和本傑明•富蘭克林的通信網絡,反映了熟人網絡的重要性,不然的話這些社區可能仍然被侷限在各自的國家內部;它也反映了社會組織新的方式——特別是共濟會——增加了志同道合的男人的聯繫,儘管建立了社會地位的分歧。這麼多關鍵人物同時完成一場美國革命不是偶然的,從喬治華盛頓到保羅•雷維爾,都是共濟會的成員。
衝啊病毒
第三,網絡的結構決定了其病毒性。最近,社會科學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的研究都表明,一種疾病或一種想法的傳染性依賴於社會網絡的結構,與病毒或模因(通過模仿方式傳播的文化或文化因子)的固有屬性一樣。
十八世紀末的歷史表明了這一點。啓發了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樣的,而且兩者都通過通信,出版和社交性網絡傳播。但殖民地美國和法國法國的網絡結構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前者缺乏一個大規模的文盲農民羣體)。一場革命產生了一種相對和平,去中心的民主,儘管它還包含一個奴隸制的過渡期,而另一場,則締造了一個充滿暴力以及間或的無政府的共和國,它很快就追溯古代羅馬的步伐,走向了暴政和擴張(的帝國之路)。
在1814年拿破崙法國的陷落之後,等級秩序被艱難恢復。大國主導的維也納和會次年在歐洲重新確立了君主制政府,並且以殖民帝國的形式向世界其他地區出口。使帝國主義的蔓延成為可能的事實是工業時代的鐵路,輪船和電報技術,它使得倫敦作為最重要的節點成為超級中心(superhubds)。換句話説,新工業時代的網絡結構發生了變化,是因為新技術帶來的集權控制遠甚於印刷和郵政服務的能力。第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就是1815年至1914年間,火車和列車時間表出現的時代。
網絡永不眠
第四,許多網絡是複雜的自適應系統,其形狀不斷變化。
即使是所有時代中等級最為森嚴的極權主義的帝國也是這樣,阿道夫•希特勒時代也是如此。
在20世紀50年代,基督教民主的歐洲和企業主導的美國也是等級性的,只要看看通用汽車公司的中期組織圖表就可以發現,但它並沒有達到相同的強度。一個類似於民權運動的基於網絡的改革運動在蘇維埃俄國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在美國南部反對種族隔離的人曾經被騷擾,但是壓制他們的努力最終失敗了。
20世紀中葉是一個傾向於等級治理的時代。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變化開始了。很容易假設這是因為技術的進步。然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硅谷是弱的中心控制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互聯網被美國人而不是蘇聯人發明出來,正是因為美國國防部被越南災難性的戰爭糾纏,才給了加利福尼亞的計算機科學家隨其所好建立一個計算機通信系統(的機會)。這在蘇維埃的情況下並沒有發生,當時一個由控制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ybernetics)負責的類似項目,一言不合就被財政部關閉了。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見證了發動冷戰的兩個超級大國的巨大變化,它預示着第二個網絡時代的黎明。在美國,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的辭職似乎代表着新聞自由和代議制政府反抗帝王總統的偉大勝利。但即便如此,水門事件,越戰的失敗,以及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社會和經濟危機都沒有帶來整個體制的全線崩潰。
的確,羅納德•里根總統非常輕鬆地恢復了行政部門的聲望;相比之下,蘇維埃帝國在東歐的崩潰是由幾乎沒有任何先進通訊手段的反共產主義異端者的網絡帶來的。事實上,即使政府拒絕給他們印刷的權利,被稱為“samizdat”的地下文學卻越來越強大。波蘭案例説明了網絡良好的作用:團結工會成功只因為它本身被嵌入了一個雜多的反對派團體之中。
網絡以網絡聯通
第五個見解是網絡間相互作用,並且互相競爭。當網絡之間相互連接時,常常導致創新。但網絡也可能相互攻擊。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一個被稱為使徒團體的劍橋大學思想協會(Cambridge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society)在1930年代受到克格勃的襲擊。作為20世紀最成功的情報運作之一,蘇聯設法從使徒團紅招募了幾個有頭銜的人,並因此在二戰期間和之後獲取了大量英國和聯軍的高級機密文件。
這個例子展示了分佈式網絡的核心弱點之一。蘇聯不僅向劍橋知識圈滲透,他們還入侵了在二十世紀運作英國政府的整個老男孩網絡。他們能夠這樣做正是因為英國政治建制不言而喻的假設和不成文的規則,使得背叛的明顯證據被忽視或者遮掩。不同於對安全充滿不信任的偏執的等級網絡,分佈式網絡通常不利於自衞。
同樣,9/11襲擊是一個網絡對另一個網絡實施的:基地組織反對美國的金融和政治制度。但美國在這方面的真實損失並不是恐怖襲擊帶來的直接損失,它甚至不是未曾預料到的國家安全國家的對此事的回應。 在2002年8月,在入侵伊拉克還並不明朗之前,政治學家約翰•阿基利亞就在《洛杉磯時報》上刊文指出了這種做法的缺陷。
他寫道,“在一個類似於我們正處於其中的網絡戰中,戰略轟炸意義很小,因為大多數網絡都不是依靠一個或幾個偉大領袖來維持和指揮的。” 他指出了布什創建國土安全部的錯誤,他認為:“一個等級體系是用來對抗一個靈活網絡的笨拙工具:需要利用網絡來打擊網絡,就像在以前的戰爭裏是用坦克來打坦克一樣。”

黑客組織向恐怖主義宣戰
美軍在入侵伊拉克後,花了四年時間才領悟這一道理。反思美國兵力激增的2007年這個決定性階段,美軍總司令麥克克里斯坦(Stanley McChrystal)總結了經驗教訓。為了摧毀阿布穆薩布扎卡維的恐怖主義網絡,他寫道,他的部隊 “必須複製其分散性,靈活性和速度”。他繼續説道:“隨着時間的推移,‘用一個網絡打敗另一個網絡’變成了我們整個行動的核心總結。”
網絡不平等
第六個洞見是網絡的異常不平等。
一個持久的難題是,儘管不曾有人用陰毒的想法來謀劃這場金融危機,為什麼2008年金融危機對美國及其盟國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了2001年的恐怖襲擊。(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失估計在5.7萬億到13萬億之間,而反恐戰爭的最大開支可能也就是4萬億。)這個解釋要點在於隨着信息技術引入銀行業,世界金融結構發生的戲劇性變化。金融體系變得如此複雜,以至於傾向於放大它的週期性波動。這不只是金融中心之間更多和更快的相互連接,而且是許多機構多元性不夠,安全性保障不充分。
當美國財政部,美聯儲等監管機構在2008年拒絕救助雷曼兄弟時,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儘管雷曼兄弟的首席執行官理查德•福爾德(Richard Fuld)是華爾街中的一個孤立的網絡節點,並且也被包括Goldman Sachs前總裁,美國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所討厭,但這個銀行本身確實一個危險易碎的國際金融網絡中的一個關鍵節點。那些沒有受過網絡理論訓練的經濟學家們最終可悲地發現自己低估了讓雷曼兄弟破產的後果。
在金融危機之後,金融世界的運作方式被普遍化:這個社會的其他部分都開始按照10年之前銀行家的那種網絡構建自己。這個變化預示着一個全新的全球社區的新世界的到來,在其中每一個公民都是一個網民,它們被技術武裝起來,向權力講述真理,並對其進行問責。
然而再一次地,網絡理論的教訓被忽視,因為對於巨大的社交網絡來説,甚至連最低程度的平等都沒有做到。準確地説,比起一個隨機建構的網絡,它們有更多有大量邊緣的節點和更多沒有大量邊緣的節點。這是因為隨着社交網絡的擴大,節點會根據網絡的數量成比例地增加新的邊緣。
這個現象是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所説的“馬太福音”的一個表現。馬太福音25章29節指出“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比如,在科學領域,成功培育成功:對已經有引用和獎項的科學家來説,成功會更加容易。這個趨勢在硅谷也許是最明顯的。2001年,軟件開發人員Eric Raymond自信地預測,開源運動將會在三到五年內取勝。他註定會失望。隨着壟斷和雙頭主導的興起,以及它們對本可能對其加以抑制的政府監管的規避,開源夢想死於搖籃之中。蘋果和微軟建立了對軟件業的雙頭壟斷,亞馬遜主導了網上零售業,谷歌也很快確立了搜索引擎業的近乎壟斷地位,當然,Facebook也在社交媒體的爭奪戰中勝出。
在撰寫本文時,Facebook擁有11.7億活躍的日常用户。然而公司的所有權卻高度集中,扎克伯格本身擁有該公司的28%以上股份,使他成為世界上十大最富有的人之一。這種人還還包括比爾•蓋茨,傑夫貝佐斯,卡洛斯•斯利姆,拉里•埃裏森和邁克爾•布隆伯格,他們的財富全部來自於信息技術的各個方式。由於強大的“富者更富”效應,他們的生意回報有增無減。大量現金儲備使他們有能力買斷任何潛在的競爭者。

失敗的開源軟件運動
在哈佛的畢業演講中,扎克伯格展望一個“每個人都有意義感的世界:通過共建一個偉大的有意義的項目、通過重新定義平等,從而使每個人都有自由追求意義,並最終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社區。”
但扎克伯格不過是經濟學家所稱的 “超級巨星的經濟學”的一個表徵。作為一個領域的頂尖人才,他的成功和財富遠遠超過了後來者。而矛盾的是,扎克伯格在他的演講中提到的大部分針對不平等的補救——普遍的基本收入,負擔得起的兒童保育,更好的醫療保健和持續教育——只有在二十世紀福利國家的國家政策支持的情況下才可行。
此時、彼時
互聯網帶來的全球影響和16世紀歐洲的印刷帶來的影響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個人電腦和手機給個體更多力量,就好像路德時代的宣傳冊子和書本。確實,美國在1977年到2004年個人電腦的生產和價格軌跡,和英格蘭1490年到1630年印刷書本的生產和價格軌跡有着驚人的相似性。但這兩個時代仍然有很多差異。首先,最明顯的是,今天的網絡革命比起德國印刷機革命浪潮來説要快得多,地理範圍更廣。
第二,當前革命的分配後果是截然不同的。早期近代歐洲並不是執行知識產權的理想場所,因為在那時它只可能存在於技術能夠行會秘密壟斷的時候。出版業沒有創造億萬富豪:約翰內斯•古騰堡不是蓋茨(1456年,其實他是真正地破產了)。此外,出版業只使得包括報紙和雜誌在內的一小部分社會媒體可以通過廣告盈利,而互聯網則使得幾乎所有重要的網絡平台成為可能。那就是數十億的美元的來源。不同於過去,當前世界只存在兩種人:那些擁有和運行網絡的人和那些只使用它們的人。
第三,出版社在攪亂其他事情之前,首先是攪亂了西歐基督教世界的宗教生活。相比之下,互聯網從破壞商業開始;只是在最近才開始攪亂政治,並且通過激化遜尼派原教旨主義最極端的教義,它僅僅真正攪亂了一種宗教,那就是伊斯蘭。
然而,我們的時代與出版業帶來的革命時代也有很多明顯的相似之處。一方面,正如出版業那樣,現代信息技術不僅正在轉化市場——例如,促進短期公寓的出租,而且也轉化了公共領域。過去從來沒有這麼多人連接在一個即時網絡中,通過這個網絡,模因(memes)可以比天然病毒更快地傳播。
但是,認為整個世界的網絡化能夠創造出一個所有網民一律平等的烏托邦的網絡空間卻是個虛幻,正如路德的“信徒皆祭司”也是一個幻覺一樣。現實是,全球網絡已經成為各種狂熱和恐慌的傳播機制,正如印刷的出現和識字率的提高增加了千禧年教派和巫婆狂歡的流行率。伊斯蘭國的殘酷行為在這種視野下顯得似乎不那麼特殊;今天,充滿虛假新聞的公共領域不那麼令人驚訝,紙媒傳播關於魔術的書籍和關於科學的書籍給人的印象,似乎也沒有什麼差別。
對於學者安妮•瑪麗•斯勞特來説,“超網絡世界”在總體上是一個好場所。她寫道:如果其領導人想出不僅僅是在傳統的國家間外交的“大棋局”中,而且是在新的網絡的空間中運作權力,充分利用後者的優勢(如透明度、適應性和可擴展性),“美國”將逐漸找到網絡權力的中庸之道。但其他人卻沒有這樣自信。
在《第七感》(The Seventh Sense)中,約書亞•庫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支持建立真實的虛擬的“大門”,以便阻擋俄羅斯人,網絡犯罪分子,青年網絡破壞者和其他破壞因素。繼而拉莫引用了由國家安全局特工羅伯特•莫里斯設計的計算機安全的三個規則:“規矩一:不要擁有電腦。規則二:不要打開電源。規則三:不要使用它。”如果大家繼續忽視這些要求——特別是政治領導人,其中大多數甚至沒有啓用他們的電子郵件帳户的身份驗證——即使是最複雜的網絡門户也是無效的。
那些想了解今天的政治和地緣政治影響的人需要更多地關注網絡理論的重要見解。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會明白,網絡不像廣告宣傳所説的一樣好。營造全球社會烏托邦夢想的技術人員有充分的理由將他們的Kool-Aid分配給他們如此專業挖掘的數據用户。不受管制的硅谷的寡頭,也繼續通過聯網來實現他們的壟斷。而除了他們之外的我們——他們擁有的網絡的僅有用户——應該對他們的的願景保持這願景本該得到的懷疑。
(本文原發於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部分內容有刪節,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