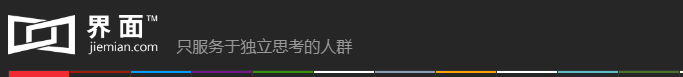眾籌教師:一個貴州山村的9年教育史
據界面新聞31日報道,25年來,貴州省黔東南州黎平縣弄團寨的村民們眾籌錢、米,聘請教師為孩子們執教。現任老師賀雲華已經在這個偏僻的山村裏度過了9個年頭。經過志願者們的努力,2015年,這個未被公立學校納入教學範圍的鄉村通上了電。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但志願者們搭建的木樓學校和眾籌教師是存是留,誰也説不清楚。

眾籌教師賀雲華家訪途中爬上一座山,望着對面山上弄團小學。攝影:翟星理
一
為了遲交的50元學費,賀雲華跟家長髮生了激烈的爭吵——這學費也是他工資的一部分。
爭吵發生在2013年的一個晚上。當時,賀雲華帶着樊閩——一位來自福建的志願者來到弄團寨一户人家做客。吵到一半,旁觀者樊閩有些不耐煩,掏出一張百元鈔票遞給他。“你出去吧。”
但這天晚上臨睡前,樊閩想明白了,開始同情賀雲華。“一個不是老師的老師,一年只拿三千元工資,窮怕了。”
外鄉人賀雲華來到弄團寨已經9年了。2008年,他接替表哥接受村民的眾籌,擔任這個村子的自辦校老師。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西南一隅,弄團寨是民樂村委會轄下自然村。很少有人聽説過它,也很少有外人進入。在這裏,14户共87口人分佈在3個彼此相望、平均海拔約為900米的山頭上。
從九潮鎮到弄團寨的20公里山路,步行需4個小時。公路從山腳沿平緩的坡地伸展到雲霧繚繞的山頭,即使在約3米寬的水泥路路段,臨溝的一側也極少安裝護欄,溝底枝葉茂盛的墨綠色松樹看上去只有火柴那麼大。單車道水泥公路在距離弄團寨10公里處被替換為一條更窄的彈石路,石塊會讓轎車底盤一路“砰砰”作響。
村子的歷史不足百年。當地村民説,3個兄弟從大約200公里外遷徙至此,在原始森林刀耕火種,開山立寨。
直到現在,這87個村民迄今沒一個讀過初中。“一是因為太偏,沒幾個人知道還有個弄團寨。二是因為超生,2015年9月之前全寨47個人沒户口,大部分是超生的孩子。”52歲的村小組長龍永生説。
在這個苗族村寨裏,人們無法流利地用漢語交流。龍永生五年前才學會一些漢語。他並不理解“人均年收入”的意思。按照傳統,村民們會種植水稻和玉米,也會栽培杉樹,但龍永生也説不好每家到底有多少田、多少樹,自然也無法統計村民們的收入。
二
2010年,來到弄團寨兩年的賀雲華與村民們簽下一份合同,約定每年教書的工資為3000元。這份寫在筆記本上合同,簽了全寨9個男家長的名字。
眾籌教師的辦法是龍永生想到的。1992年,他召集全寨的男性家長,宣佈聘請老師自辦學校,各家均攤錢米,每年給老師2000元工資和700斤米作口糧。
1992年至今,包括賀雲華的表哥在內,一共有3位擁有初中文憑的教師在此執教。他們沒有教師資格證,也沒有在公辦學校教書的經歷。
距離弄團寨最近的小學,遠在從江縣的便秀寨,兩地相隔一個半小時的山路。上學的路程雖遠,尚能被人們克服。但沒有户口,成了孩子們無法就學的主因。
“沒有户口的原因,主要是超生。”龍永生説。比如他自己的妻子便生了15個孩子,活下來9個。
“不能讓下一代再受沒有知識的苦。”龍永生説,這是他眾籌辦學的主要原因。
但現實卻不盡人意。15年間,3位老師一共執教了4年半,實在無法忍受弄團的生活條件而先後離職。其餘的時間,適齡的學生只能輟學。弄團寨小學也從未被納入當地公辦學校的序列。
賀雲華的表哥剛來弄團小學一年,便向村長提出辭職。那時,表哥的年收入只有2000元。

2017年12月22日中午放學,學生幫賀雲華做飯,這是他們的營養午餐。攝影:翟星理
時隔多年,賀雲華還是覺得表哥騙了他。
“他給我打電話,説弄團是個800多人的大寨子,趕緊來教書掙錢。”賀雲華到了之後才發現,當時全寨不足80人,學生只有18個,年齡最大的學生是一個剛讀三年級的15歲男孩。更讓他難以置信的是,寨子沒有通電。
34歲的賀雲華身高約1.6米,體重只有92斤,看起來很虛弱。在貴州山村的冬天裏,他穿着咖啡色的緊身毛料西服,右側袖口和衣襟下襬堆積着白色粉筆末。他的解放鞋已經被洗得褪色——沒有穿襪子。
“我得過6年的貧血。”賀雲華將身體衰弱歸因於貧血。2001年,他初中畢業後考入黔東南州衞校,入學一個月即被查出營養不良導致的貧血。棄學之後,他在從江縣的家中卧病6年,而後奔赴弄團寨。
三
2017年12月22日,冬至。上午九點四十分,賀雲華在給三年級的9個學生上課之前,講起孫悟空向菩提祖師學藝的故事。“孫悟空學了七十二變,我們這節課只學萬以內的加減法,比七十二變簡單多了。”
9個學生第一次聽到《西遊記》裏的故事。另外5個六年級的學生和5個學前班的學生也是第一次聽。他們停下手中的作業,抬起頭盯着賀雲華。
賀雲華轉身在黑板上寫下一道“8+8=?”的題,拿起一截細樹枝,敲擊着黑板。
教室是弄團寨唯一使用漢語的地方,學生極少外出,在家也只説苗語。“語言是最大的障礙,”侗族人賀雲華説,2008年8月他來到弄團寨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學苗語,“第一節課上完,我的話他們一句沒聽懂,他們説什麼我也一個字沒明白。”
“8+8等於多少?以前我們是不是講過?”賀雲華放下樹枝,拿起粉筆,在兩個“8”的兩側劃下16條短槓,“是不是數一數就知道了?”從遠處看,16條短槓彷彿兩個“8”發出的光芒。
一個年級上課時,另外兩個年級就在教室中做練習題。大部分時間裏,學前班的5個孩子無所事事,他們被安排坐在三年級和六年級學生的附近,“這樣方便照顧。”他們只能聽懂一小部分賀雲華授課使用的普通話。但他們似乎並不沮喪,一邊看教科書一邊相互用苗語交流,不時發出笑聲。賀雲華也沒有阻止。
上午十點二十分的時候,課程安排學前班上課。賀雲華先用苗語教他們説“一二三四五”,發音類似漢語的“jiu o ba luo zui”。學前班學生的朗讀聲從全木結構教室的地面湧向天花板,匯入三年級學生的討論聲,構成雜亂無章的和聲部。
學生跟着賀雲華反覆朗讀,抑揚頓挫。可賀雲華對學生的接受效果並不滿意,他讓學生自己讀一遍,但沒人能完整讀下。

2017年12月22日上午,賀雲華在上課。學前班、三年級、六年級共19個孩子在一間教室上課。攝影:翟星理
時至今日,三年級的學生對教科書的理解仍然有限,他們不明白數學課中“加數”的概念。
弄團小學每天只上四節課。賀雲華會優先保障三年級、六年級的課時,一兩天才給學前班上一節課。他為這兩個年級開設語文、數學、品德與社會三門科目。曾有公立學校的老師建議他開一門英語課,“我已經沒有精力再學英語。”他坦承。
他必須在週末給孩子們補課,否則便趕不上公立小學的教學進度。
來到弄團小學之後,他在領教材的時候去公立小學旁聽過一節課。他迴避了對授課水平的自我評價,“我只能説,我已經盡我所能在提高自己的水平了。雖然我連代課教師都不算,但是我會堅持。”賀雲華平靜地説。
四
想起尷尬的身份,他難得有平靜。準確地説,眾籌鄉村教師賀雲華的身份焦慮是從2012年年底開始的。
那時,志願者樊閩第一次進入弄團寨,善意地提醒他:“農村基礎教育的趨勢肯定是向好的。可你沒有教師資格證,這可能有點麻煩。”
樊閩從汶川地震時開始從事志願者服務,2008年下半年從汶川進入貴州進行公益活動,堅持至今。目前他沒有加入公益組織,但能聯繫各地愛心力量幫扶貴州部分貧困地區。
那一年,樊閩到黎平縣九潮鎮定八村組織公益活動時,隨口問村幹部,“這裏有沒有比你們更窮的地方?”
幾個村幹部告訴他,聽説過弄團寨的貧窮,但沒人去過那裏。在樊閩的堅持下,當地的嚮導扛着開山刀,帶着他在沒有路的山林中走了8個多小時。
貧窮和過度生育的景象令樊閩震驚:就連村小組長龍永生的家裏,4個孩子也是躺在一間露天木屋的地板上睡覺。樊閩説,當時在下雨,龍永生為木屋蓋上一層塑料布。“那些沒錢蓋木屋的,就用樹枝搭一個蒙古包式的四面漏風的居所,屋裏的孩子沒鞋穿,腳被凍成醬紫色。”
令樊閩記憶深刻的是那時的弄團小學。校舍由一間廚房改造:傳統的全木結構房屋,房頂覆以一層樹皮,再蓋上一層塑料布。
樊閩找到弄團最貧窮的一户人家,留下300元現金。男主人不敢收,把錢交給村小組長。龍永生把這300元按户平分給大家。
樊閩家鄉——福建泉州的愛心組織為弄團寨募得一筆善款。2013年六一兒童節前夕,樊閩用這筆善款搭建的弄團小學竣工——它只是一座兩層木樓,樓下是兩間教室,樓上有一間閲覽室和一間供來訪者使用的客房。但弄團寨學生太少,導致一間教室至今閒置。被使用的教室也僅配備了12套課桌椅。

弄團寨小學僅是一座兩層木樓。攝影:翟星理
賀雲華也從這次募捐中受益。愛心人士每年年底為他資助一萬元的善款作為在弄團小學講課的報酬,弄團寨不再負擔他的工資,每年供給他700斤大米。
2015年年中,經過志願者們的努力,當地鋪設了從九潮鎮至弄團寨的輸電線路。電力第一次進入弄團寨的家家户户。
五
也是這一年,經過志願者們與當地民政部門的溝通。孩子們的户籍問題在9月得到了解決。
在此之前,這個難題也曾經困擾着賀雲華。
“如果沒有我,弄團寨就會多一些文盲。可就算有了我,這9年我教過的40多個學生,也沒有一個能上初中。”他説。
如今户籍有了,賀雲華覺得自己也有了更多堅持的理由。
孩子們人生的選擇也多了條路。在公益人士的幫助下,千年古剎泉州少林寺接收了6名弄團寨的孩子,為他們開設了為期5年的文化課和武術課。
2015年,龍永生的兩個兒子和弄團寨其他4個男孩在愛心人士組織下赴南少林寺學習。攝影:翟星理
2015年,這6名孩子乘坐着大巴車,離開故鄉,遠赴福建。按照計劃,他們在黎平縣城歇腳一晚。那天半夜,樊閩到他們的房間查看,發現6個孩子沒有睡覺,都趴在窗户上看大街上閃爍的霓虹燈——那是他們第一次見到霓虹燈。
賀雲華也跟着孩子們去了泉州。回到弄團寨後,他告訴學生:“讀書是走出弄團寨最好的方式。”
2017年12月22日下午,在六年級的品德與社會課上,賀雲華在他的知識限度內講解了英國和葡萄牙的概況,並描述了他來弄團教書之前在浙江、湖南打工經歷中的見聞。最後他總結道:“中國真的很大,我希望每一個同學都能到外面去看看。”
“那些地方離弄團多遠?”一個學生小聲問同桌。
“有那麼遠吧。”同桌張開雙臂比劃出一張課桌的寬度。
六
賀雲華還在講課的時候,龍世海在教室的窗户上探出半個身子,他朝賀雲華點頭示意,轉過頭看着一個六歲的學前班小女孩。當天傍晚,龍世海就要和妻子去廣東打工。
30歲出頭的龍世海有7個弟妹,那個女孩是他最小的妹妹。她聽力極差,至今不會説話,只能發出一些模糊而短促的單音節。賀雲華手把手教會她寫字,龍世海認為“這是奇蹟”。
下午放學之後,賀雲華家訪,最先去的就是龍世海家。
賀雲華爬上超過60度坡度的山腰,站在一片高大茂盛的芭芒草叢之中,剛好能看到弄團小學那座兩層小樓的黑色房頂。
他久久沒有離去。
“你知道嗎,我最怕的就是人家説弄團小學非法辦學,我得失業,孩子們一天得走一個多小時山路去最近的公立小學教學點上課。”他説,最近這兩年,他經常一個人爬上這座沒有路的山,每次望着學校,就像一次告別。
志願者的進入改變了弄團寨。賀雲華的身份焦慮也日漸加重。他發現自己甚至不具備教師資格證的報考資格:報考小學教師的最低學歷要求是大學專科,而他只讀了一個月的中專。
“志願者給我講了很多,我有責任像公立學校的老師那樣把書教好。”賀雲華期待有朝一日他的身份問題能得到解決,儘管這希望太渺茫。
除此之外,他的焦慮也來自沉重的家庭債務糾纏。他的兩個孩子雖然各自成立家庭,但父母都卧病在牀。去年,他給家裏蓋房子,又向銀行貸了5萬元。
他曾經想過考個學歷。但“自考是需要錢的”。
這天晚上,他做完家訪回到學校廚房,攏起一堆柴火。
“可我的日工資只有27元3角9分……單槍匹馬吧,堅持到最後。只要弄團小學還存在,我就繼續在這裏教。”他説。
在昏暗的白熾燈光照射下,搖曳的火苗在地面上投出一團擺動的黑影,像水在流動。
(應受訪者要求,樊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