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古內特·阿瑪普里特·考爾·蒙加如何改變了寶萊塢 - 彭博社
bloomberg
 古尼特·蒙加(左二)在 孟買電影 首映式上,時間是2013年5月19日,地點是戛納電影節。
古尼特·蒙加(左二)在 孟買電影 首映式上,時間是2013年5月19日,地點是戛納電影節。
攝影師:維托里奧·祖尼諾·切洛託/蓋蒂圖片社
古尼特·阿瑪普里特·考爾·蒙加相信奇蹟。她的旅程至今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解釋。考慮到生活給她帶來的打擊,很難相信這位三十四歲的電影製片人,留着短髮,配戴着一副深色邊框眼鏡,眼睛大而閃亮,並不感到憤怒。她很平靜——實際上是如此平靜,以至於當古尼特説話時,孟買那種瘋狂的能量和高分貝的噪音似乎都減緩了。
古尼特住在海邊。她窗外的棕櫚樹輕輕搖曳,阿拉伯海拍打着海岸。凝視海洋和呼吸新鮮的鹹味空氣對她來説很重要——“這讓人平靜,寧靜,並且平衡你的能量。”古尼特在高檔朱胡的海濱公寓與她在法裏達巴德附近的蘇拉傑昆德租住的5000盧比一個月的謙卑童年形成了鮮明對比。每天早晨,“Om namah shivay”的吟唱充滿了她在孟買的家。“當我在這個公寓醒來時,我感謝宇宙,”古尼特説。“我每天都感恩。”
根據 綜藝,這本廣受歡迎的美國電影雜誌,古尼特是娛樂行業中做出“非凡成就的五十位女性”之一。在2018年3月,該雜誌發佈了首個 國際女性影響力報告,古尼特是其中僅有的兩位來自印度的女性之一。另一位是演員迪皮卡·帕度柯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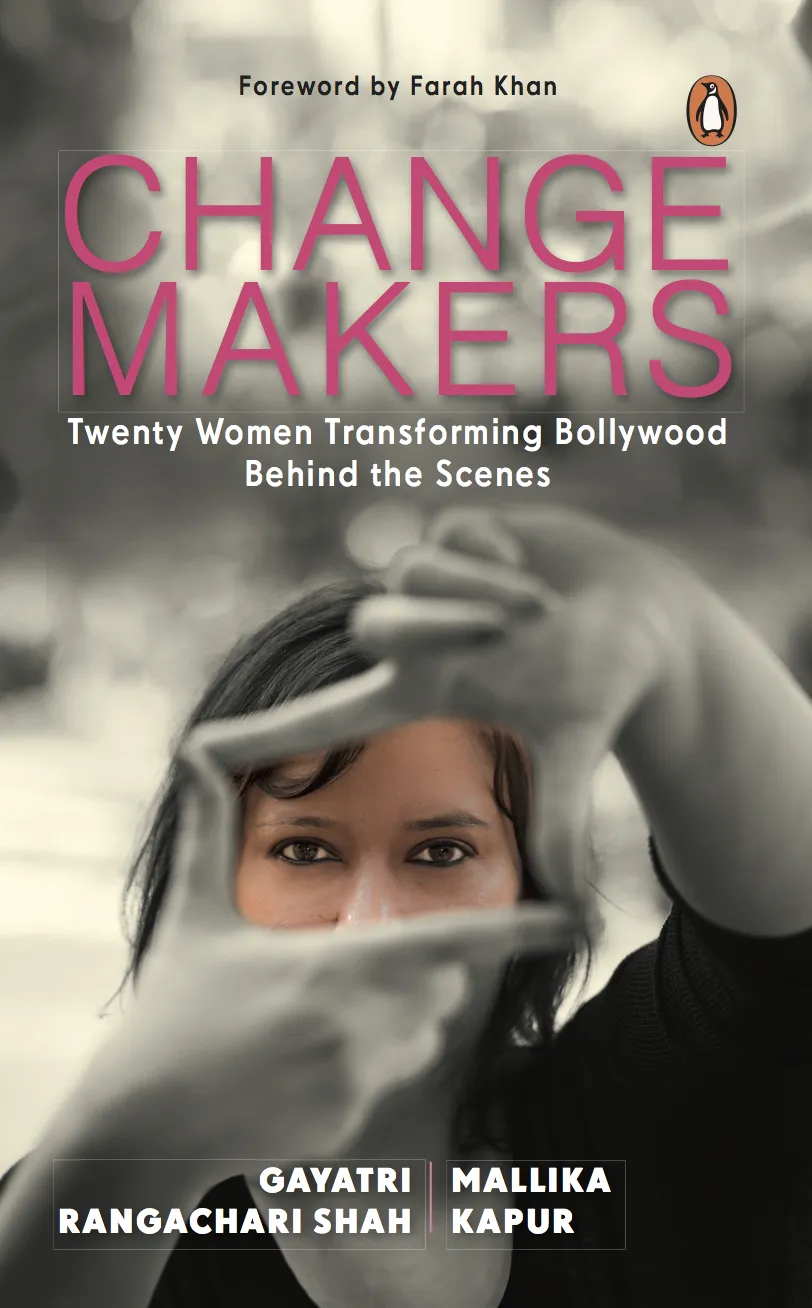 報告的介紹中提到:“讓我們面對現實:在這個世界上,做一個女人並不總是容易,更不用説成為一個恰好是女性的娛樂業領袖了。需要克服通常的領導障礙,還有某些地區的明顯性別歧視和抵抗。然而,這些女性依然堅持。”
報告的介紹中提到:“讓我們面對現實:在這個世界上,做一個女人並不總是容易,更不用説成為一個恰好是女性的娛樂業領袖了。需要克服通常的領導障礙,還有某些地區的明顯性別歧視和抵抗。然而,這些女性依然堅持。”
古尼特因其作為寶萊塢開創性女性製片人的工作而上榜,成為一波新的印度電影製作人之一,對全球產生影響。她以支持強大、獨立的內容而聞名,這些內容在商業娛樂和藝術電影之間遊刃有餘,古尼特的作品超過三十部,其中包括一些當代印度最受好評的電影,如午餐盒、瓦賽浦爾的幫派和馬桑。通常,這些都是低預算的電影,劇本強勁,聚焦於前衞、另類的主題。這些獨立電影在內心深處根植於印度文化,卻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午餐盒是古尼特的皇冠上的明珠。簡單來説,這部電影讓她引起了關注,併為她和她的聯合制片人贏得了2015年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BAFTA)的提名。這部感人的愛情故事圍繞着一個送錯人的食物盒子展開,首映於2013年戛納電影節,獲得了觀眾的起立鼓掌。它在全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一部罕見的印度跨界熱門影片。《衞報》給了它四顆星,稱“《午餐盒》處理得非常完美,表演也很出色;是一場情感積蓄的靜默風暴。”這部電影以1億印度盧比(約150萬美元)的低預算製作,成為2014年美國最高票房的外語電影之一,收入達420萬美元。
關於午餐盒,古尼特説:“那是夢想——那部能在全球銷售的印度電影。”它創造了歷史,但這並不令人驚訝。古尼特的很多事情都不循規蹈矩。她不是一個會堅持傳統的人。她打破了它。
 伊爾凡·可汗在午餐盒(2013)。攝影師:邁克爾·西蒙茲/索尼影業經典/埃弗雷特收藏“我是一個顛覆者,”她説,聲音低沉中透着自信。在她的個人或職業生活中,很難找到她遵循過的傳統路徑。“你必須在角落裏做別人不願做的工作,並製造足夠的噪音讓人注意到你,”她堅持道。訣竅就是堅持下去。
伊爾凡·可汗在午餐盒(2013)。攝影師:邁克爾·西蒙茲/索尼影業經典/埃弗雷特收藏“我是一個顛覆者,”她説,聲音低沉中透着自信。在她的個人或職業生活中,很難找到她遵循過的傳統路徑。“你必須在角落裏做別人不願做的工作,並製造足夠的噪音讓人注意到你,”她堅持道。訣竅就是堅持下去。
古尼特於1983年11月21日出生在新德里,她的生活中充滿了失落、抑鬱和死亡。作為一個小女孩,她目睹了家庭暴力。她的第一部電影慘敗。她的父母在六個月內相繼去世。然而,這位2008年創辦的Sikhya娛樂公司的負責人並不感到苦澀。你不會聽到古尼特抱怨生活不公。她説她有很多值得感激的事情。
這包括沒有人來看她的第一部電影。古尼特滿懷雄心,夢想在德里學習大眾傳播後搬到孟買。她想拍電影,講故事。她第一次接觸電影——作為法德印獨立電影花谷的實習生——讓她着迷。
她的工作包括複印和掃描文件,將電話號碼輸入數據庫,以及為製作團隊做雜活。這是 grunt 工作,但她喜歡每一分鐘。這段經歷是在她嘗試了無數其他工作之後。到她二十一歲時,古尼特已經做過 DJ、保險代理人、Laughing Cow 奶酪的銷售代理人、活動策劃人、拉力賽車手和她已故父親的房地產銷售員。然而,一旦她發現自己身處電影拍攝現場,她就知道再也無法回頭。古尼特想自己拍一部電影。
孟買在召喚。但她需要資金來搬遷和拍攝電影。她在德里的鄰居卡姆萊什·阿加瓦爾願意通過投資 50 萬盧比來幫助她的電影項目。作為交換,他建議古尼特拍“可愛的兒童電影”。古尼特耐心地聽完,然後回答:“叔叔,我覺得這是個非常糟糕的主意。”她大膽地提出了另一個建議:為什麼不給她錢,讓她搬到孟買拍一部電影——關於她選擇的主題。*這是一個很大的要求。*阿加瓦爾最終同意了。他給了她資金。
“我從未懷疑過她的誠信,”他在多年後説,親切而欽佩地談論古尼特,他從她十幾歲時就認識她。“她的態度誠實而真誠,可能正因為如此我才投資了她。我知道她絕不會欺騙我。”
這位有抱負的電影製作人在印度的電影之都帶着口袋裏的錢、心中的火焰,但對從何開始一無所知。她唯一知道的是她要拍一部電影。沒有什麼能阻止她。她積極社交,儘可能多地結識人,確信總會有人有值得講述的故事。“我曾經在美食廣場、商場裏遇見人,問:‘我有 50 萬,你有故事嗎?’”她二十一歲,天真而又大膽。
她的堅持得到了回報。她找到了一部讓她興奮的劇本。它講述了四個資源有限但對板球充滿熱情的男孩的故事。她決定通過她創辦的第一家制作公司,Speaking Tree Films,投資這部電影。電影名為Say Salaam India,於2007年上映。這是一部應該讓熱愛板球的印度人瘋狂的電影。
 但命運有不同的安排。在電影上映幾天後,印度板球隊在西印度羣島的世界盃中出局。沒有人預見到這一慘敗。板球迷們非常憤怒。他們向板球運動員的家扔石頭,媒體也開始攻擊。關於板球的勵志電影不會吸引觀眾,因此電影院將電影膠捲退還給了Guneet。她的第一部電影失敗了,她感到崩潰。
但命運有不同的安排。在電影上映幾天後,印度板球隊在西印度羣島的世界盃中出局。沒有人預見到這一慘敗。板球迷們非常憤怒。他們向板球運動員的家扔石頭,媒體也開始攻擊。關於板球的勵志電影不會吸引觀眾,因此電影院將電影膠捲退還給了Guneet。她的第一部電影失敗了,她感到崩潰。
讓Agarwal失望讓製片人的良心感到沉重。Guneet拿了他的錢,卻看着它打了水漂。不管怎樣,她都要償還他。“我一直告訴他,如果我不把你的錢還給你,我就不該在這個行業裏。”Agarwal並不指望能收回損失。“我投資了這筆錢,她是合夥人。利潤和損失都是要分享的。我從來沒有逼Guneet來承擔她的損失。”
但Guneet已經在制定B計劃。她確信,總會有人想看這部電影。她決定把電影帶給一羣總是對板球感到興奮的人:學生。她在印度北部的小城市和城鎮間旅行,為學校安排私人放映,並收取象徵性的費用。這不是一種傳統的策略,但Guneet就是一個跳出框架的思考者。在九個月內,她賺到了足夠的錢來全額償還Agarwal。“我只是非常渴望把那筆錢賺回來,甚至不惜千辛萬苦去實現。”
回首往事,古尼特説這次挫折教會了她作為電影製片人需要學習的最重要的一課——每部電影都有觀眾。“你只需要找到它。”商業中有起有落,古尼特從她的父親,一位房地產顧問那裏學到了這一點。
“我父親總是説,‘商業中就是這樣的,’古尼特説。但她的父母也在她心中植入了深深的誠實感。“我母親常常説,‘無論你做什麼,你都要對自己的良心負責。’”這些關於誠實和清白良心的教訓促使她償還阿加瓦爾。
古尼特在談到她的父母時放慢了語速。這讓她想起了母親在父親家族手中遭受多年虐待和家庭暴力的痛苦回憶。
作為一個年輕的孩子目睹那種暴力,讓古尼特對大聲的聲音產生了恐懼,並對不公正有了深深的不能容忍。她無法忍受任何人尖叫,且很少提高自己的聲音。喧鬧的聲音把她帶回了童年,那時蒙加一家住在新德里大凱拉什的一座寬敞的家庭住宅裏,她看到母親遭受言語和身體上的虐待。十二歲那年,一個晚上,暴力幾乎奪去了她母親的生命。“他們試圖在我面前把我媽媽點燃。屋裏有警察,人們抱着我。
“那真是瘋狂,”她顫抖着説。那晚,她的父母逃離了,搬進了當時遠離的南德里的蘇拉朱坎德一間小租賃公寓。古尼特一直避免公開談論她的童年創傷。可悲的是,她的母親在2008年因癌症去世,幾個月後,她的父親因腎病去世。古尼特當時二十四歲。除了一個父親的姑姑,她沒有其他親戚和兄弟姐妹。這個空缺由她的朋友填補。
“她珍惜友誼,喜歡把朋友留在身邊,”梅揚克·賈説,他住在同一個城鎮,位於蘇拉金德的查爾姆伍德村,古尼特在這裏度過了她的青春歲月。這個封閉社區名副其實——它有幾棟別墅、一棟高樓、一座池塘和許多公園。搬到那裏後,古尼特第一次感到安全和平靜。她身邊都是同齡的朋友,成為了這個社區的一部分。
她説那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幾年。
 蒙加在2013年4月11日於加利福尼亞州西好萊塢舉行的洛杉磯印度電影節第六屆年度行業領導獎頒獎典禮上。攝影師:伊梅·阿克潘烏多森/Getty Images“回想起來,我現在可以把這些點連起來,”梅揚克説。“古尼特是個很好的講故事的人。她總是非常生動和健談,講故事時會情感投入。可以説,她很戲劇化!”儘管她有戲劇天賦,但她的朋友們都沒有猜到她會從事電影事業。如今,她的學校、大學和蘇拉金德的朋友們是她最忠實的支持者。她把他們視為家人。
蒙加在2013年4月11日於加利福尼亞州西好萊塢舉行的洛杉磯印度電影節第六屆年度行業領導獎頒獎典禮上。攝影師:伊梅·阿克潘烏多森/Getty Images“回想起來,我現在可以把這些點連起來,”梅揚克説。“古尼特是個很好的講故事的人。她總是非常生動和健談,講故事時會情感投入。可以説,她很戲劇化!”儘管她有戲劇天賦,但她的朋友們都沒有猜到她會從事電影事業。如今,她的學校、大學和蘇拉金德的朋友們是她最忠實的支持者。她把他們視為家人。
“這是一條雙向街。古尼特從她的關係中給予的和她所獲得的同樣多,”她的童年朋友普雷爾娜·賽戈爾説。這兩個女孩從幼兒園到12年級一直在德里的藍鈴學校一起上學。
“她非常忠誠,”普雷爾娜説。“有一次,我們在學校打籃球比賽,我受了重傷。古尼特從場地另一邊跑過來,搶走了球,把球遞給我,説,‘普雷爾娜,拿着這個。’”她這樣做是為了讓朋友有機會把球扣進籃筐。“在那一刻,某種東西點擊了,”普雷爾娜説。“我知道她支持我,我知道我們會成為很長很長時間的朋友。”
她是對的。普雷爾娜和古尼特建立了如此緊密的聯繫,以至於普雷爾娜説古尼特的父母對她來説就像第二對父母。當他們去世時,真是殘酷。“我記得凌晨三點接到的電話,叔叔去世了。這是最糟糕的電話。我哭了出來。但古尼特沒有。我一直告訴我的其他朋友,她沒有哭,她沒有哭。她那麼年輕,卻一夜之間長大了。”
在接下來的五年裏,古尼特與自己的情感作鬥爭,經歷了許多黑暗的日子,直到她接觸到尼爾馬爾·辛格吉·馬哈拉傑的教義,他更為人知的是古魯吉,一位精神領袖。儘管他在2007年去世,但世界各地數百萬虔誠的追隨者仍然繼續崇拜他。他們相信,正如古尼特所相信的那樣,他帶來了奇蹟。據説他治癒了人們的疾病,消除了痛苦,併為信徒們指明瞭擺脱苦難的道路。他迅速成為古尼特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她説他改變了她。
一幅古魯吉的大幅肖像掛在她家一個面朝大海的房間的桌子上,這個房間已被改造成一個寺廟。窗户上掛着仙女燈。夜晚,小燈泡讓房間發光。房間的焦點是一把大型豪華椅子,周圍被懸掛在天花板上的裝飾性奶油色帳篷包圍。椅子腳下放着一雙 juttis,裝飾着花朵。沒有人坐在上面——這就是信徒們標記古魯吉存在的方式。“這是他的達爾巴爾,”古尼特説。任何古魯吉的追隨者都可以隨時來這裏祈禱。這裏舉行聚會。古魯吉的弟子們在這個空間裏做 seva——他們曾坐在地板上,拿着碗和刀,剝了16公斤的胡蘿蔔來準備哈瓦。對於古魯吉的崇拜者來説,這個房間是一個避難所。
“我們都知道有某種更高的能量,我們以不同的形式來定義它。我感到非常幸運,因為我找到了一個可以與這種能量相對應的面孔,”Guneet説。她時刻佩戴着一枚有Guruji照片的項鍊。信仰是Guneet生活的核心支柱。作為一個錫克教徒,她最早的記憶圍繞着家庭去德里的一個gurudwara(錫克教寺廟)的拜訪。每年,Mongas家族都會在這裏迎接新年。Guneet期待着這一時刻,並享受在康諾特廣場的Gurudwara Bangla Sahib舉行的12月31日的服務。
慶祝活動在晚上11點30分開始,伴隨着音樂——鼓、塔布拉和1萬人齊聲吟唱Wahe Guru,這是一個用來召喚全能者的錫克教咒語。臨近午夜時,音樂家們會逐個放下樂器,直到只剩下吟唱Wahe Guru, Wahe Guru的聲音。這在大廳中創造了一種強烈而情感的震動。“那是神奇的。我不知道該如何定義它,但作為一個年輕的孩子,我感到極其高昂,極其連接。我感到不知所措,淚水奪眶而出。”
多年後,她發現自己渴望再次感受到那種感覺。
那是2014年。在與她的導師和老闆Anurag Kashyap以及企業家Arun Rangachari共同製作的The Lunchbox取得成功後,Guneet跌入了谷底。“表面上,世界在祝賀我The Lunchbox的成功。但內心深處,我正在死去。”
她失去了父母,沒有給自己機會去悲傷,名下有五部未發行的電影,並且失去了工作——一份她全心投入的工作。在Anurag Kashyap Films Pvt. Ltd (AKFPL)擔任首席執行官四年後,Kashyap突然決定關閉公司。
那個決定感覺很個人。“我投入了很多,就像是從我身上奪走了什麼。這確實讓我很受傷。”古尼特曾經工作到凌晨4點,然後在早上9點回到辦公室,她的生活中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洞。她感到孤獨。“因為阿努拉格,我並沒有真正面對失去父母的痛苦,因為他佔據了那個位置。他是保護者,父親,導師。”失去工作和榜樣讓她感到失落。古尼特説她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我覺得自己不夠好。這是一年半的完全幻滅。我還沒有準備好開始自己的事業,也不知道它會如何發展。”
心煩意亂的她訪問了幾處古爾德瓦拉,尋找與她童年新年夜相同的精神能量。沒有一個地方能接近,直到她的姑姑帶她去新德里的古魯吉的阿什拉姆參加一個薩特桑。立刻,她覺得這裏很對。
古尼特向古魯吉求助。她請他幫助她擺脱為她正在製作的電影《老虎》所借的貸款。一個星期內就解決了。這感覺像是一個奇蹟。“但這不是交易關係,”她解釋她與神聖力量的關係。“我把它歸因於簡單的原則:向宇宙請求,它就會實現。我們必須請求。我能夠做到很多,因為我在請求時毫無畏懼。隨着你不斷請求,你的需求會不斷減少。我學會了請求正確的東西。”她的臉上露出了微笑。“最初,你是為了物質的東西而開始請求,然後你請求其他的東西,生活的演變就發生了。”
古內特感受到與古魯吉的強烈精神聯繫,並深信他會照顧她。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她環遊世界尋找答案。“就像,為什麼是我?我所有的朋友都有正常的生活,有結構,有父母。”她感到孤獨,想念她的父母。“你只想要那些眼睛看着你,説我為你感到高興。”她訪問了阿什拉姆,嘗試了阿育吠陀來解決健康問題,在本地治裏學習了武術卡拉里帕亞圖,甚至剃了頭。“我非常沮喪,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曾經有過自殺的念頭——我討厭自己,討厭自己的樣子,特別討厭我的頭髮。”剃光頭是她逃避身份的一種方式。
 蒙加在2018年4月11日洛杉磯第16屆印度電影節開幕夜首映的在陰影中。攝影師:蒂莫西·諾里斯/蓋蒂圖片社“抑鬱是你對自己的感覺。你無法控制它。”她相信古魯吉讓她恢復了健康。她開始定期訪問他的阿什拉姆,並與他的追隨者互動。隨着時間的推移,她開始感到自己重新獲得了一個家庭。她產生了歸屬感。黑暗開始消散。慢慢地,非常慢地,她掙扎着走出了疾病。“這是一個緩慢的自我賦權過程,”她説,形容這是一場巨大的個人勝利。
蒙加在2018年4月11日洛杉磯第16屆印度電影節開幕夜首映的在陰影中。攝影師:蒂莫西·諾里斯/蓋蒂圖片社“抑鬱是你對自己的感覺。你無法控制它。”她相信古魯吉讓她恢復了健康。她開始定期訪問他的阿什拉姆,並與他的追隨者互動。隨着時間的推移,她開始感到自己重新獲得了一個家庭。她產生了歸屬感。黑暗開始消散。慢慢地,非常慢地,她掙扎着走出了疾病。“這是一個緩慢的自我賦權過程,”她説,形容這是一場巨大的個人勝利。
今天,Guneet 感到平靜並顯得滿足。她正在自己旗下的 Sikhya Entertainment 製作多個電影項目。Sikhya 是一個旁遮普詞,意思是“持續學習”,Guneet 對她的工作充滿活力。“我錯過了這一點。我錯過了被激勵的感覺。現在我祈禱:‘每天都讓我保持靈感。’”
Guneet 的目標是製作能夠在印度和美國之間找到觀眾的內容。具體來説,是在印度設定的英語電影,能夠引起全球共鳴——類似於傳記電影 Lion 或 Ang Lee 多次獲獎的 Life of Pi。她在 Anurag Kashyap 旗下的 AKFPL 或她自己的公司 Sikhya 製作的大多數電影,都具有挑戰與寶萊塢通常相關的歌舞刻板印象的另類內容。
那女孩在黃靴子裏(2011),例如,是一部揭露孟買陰暗地下世界中的腐敗、亂倫和絕望的印度驚悚片。瓦賽普爾的幫派(2012)是一部基於煤炭黑幫的 gritty 現實犯罪電影。小販(2012)講述了兩個年輕人陷入孟買毒品交易的故事。哈拉姆科爾(2015)講述了一位老師與他的學生之間的禁忌愛情故事。馬桑(2015)是一部關於種姓、死亡、愛情和慾望的強大黑暗電影。
這些故事的多樣性反映了現代、充滿抱負的印度正在發生的變化。這些電影描繪了當代生活故事的陰暗面,而這些故事在商業娛樂中並不常見。緊湊的引人入勝的情節,是對寶萊塢數十年來提供的可預測的明星電影的華麗與魅力的清新解藥。
今天,支持Guneet所支持的內容的人已經足夠多。自1997年印度首個多廳影院出現以來,它讓觀眾發展了更廣泛、更復雜的品味,併為獨立電影製作人提供了展示作品的渠道,鼓勵他們在情節上冒更大的風險。
“多廳影院開啓了更多電影放映的對話,是的,”Guneet説。“它們幫助創造了一個更大的市場,但問題是,電影放映的時間不夠長。”這對於大製作的大片和小型獨立電影都是如此。屏幕數量實在不夠。根據研究公司ICRA的數據,印度目前大約有2200個多廳影院屏幕。但這個國家需要更多。作為世界上最繁榮的電影產業和龐大人口的家園,印度目前每百萬人僅有六個屏幕,而中國每百萬人有23個,美國每百萬人有126個。
Guneet的電影有必要傳達信息嗎?她同意這開始顯得重要,因為她感到對來到電影院的公眾有責任,他們無意識地在尋找答案。在一次商務旅行期間,她在自己最喜歡的洛杉磯餐廳吃生菜沙拉時説:“我幾乎覺得,我們在浪費人們的時間和金錢。”如果他們選擇把錢花在電影上,這位前衞的製作人希望他們覺得這是值得的。
她憑直覺工作。如果一個故事打動了她,她會不惜一切代價去製作它,即使有人警告她這可能在經濟上不可行。在印度,獨立電影製作人的資金仍然是一個挑戰。中央政府並未為印地語電影提供任何税收減免或重大補助。午餐盒的一半資金來自印度,其餘來自法國和德國。
古內的電影季風槍戰(2013),是一部警匪驚悚片,是國際合拍的又一個例子。它的資金來自法國和荷蘭。當由於資金短缺而停滯時,她賣掉了家裏唯一的財產,那是一棟她為母親建造的德里房子。當她需要資金製作哈拉姆科爾(2012)和小販(2011)時,她轉向社交媒體,通過Facebook進行眾籌。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行動者。
當那個穿黃靴子的女孩在2010年被選為第六十七屆威尼斯電影節時,古內和團隊帶着超過一百張海報和1000張明信片抵達意大利,這些超重行李的費用高得驚人。他們準備大展身手。她不知道海報的位置需要提前幾個月購買,且價格昂貴,已經沒有剩餘的地方。古內感到困惑。“我説,‘我來自印度,我們把海報貼在牆上。’我帶着剪刀和膠帶來做這個工作!”她笑着説。她訪問了咖啡館、熱狗攤、比薩店,懇求經理:“您能幫我貼上我的海報嗎?”她去了威尼斯著名的廣場,那裏人們正在用餐,並在那裏丟下了一堆明信片。她有一部電影要出售,她需要宣傳。古內就是古內,最後她把海報貼在了她能找到的唯一空閒地方:她朋友和同事的T恤上!
她缺乏經驗,感到無所適從。電影放映後,古內站在劇院裏,等待人們上前購買電影。沒有人來。“沒有人跟我説話,我想,發生了什麼?”她感到沮喪,去找當時的電影節導演馬爾科·穆勒,問他:“買家在哪裏?他們為什麼不買我們的電影?我們被選中了,對吧?”
她再次被提醒自己有多麼沒有準備。穆勒告訴她,製作人應該在節日之前幾個月就安排與買家的會議。“我説,‘你應該告訴我!’”穆勒給了她市場手冊——一本大約1500頁的鉅著——列出了所有節日參與者。隨後,他給了她一個建議。“‘儘可能多地見這些人,’他説,‘給自己三年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古內特把這個建議銘記在心。她環遊世界以瞭解國際市場。她去了法國、英國和美國。她睡在別人的沙發上。她見到了買家、製作人、銷售代理、分銷商和製片廠。她向他們展示了她的電影。她學習了節日的運作方式。她建立了人脈,結交了聯繫人。並且以她標誌性的風格,她冒了險。
一天,當陽光照耀着紐約天際線時,她毫無預約地走進了索尼經典影片在曼哈頓的辦公室,該公司在全球發行、製作和收購獨立電影。她懇求那裏的高管,“請您能看我的電影嗎?請您能看 黃色靴子嗎?”
一個月後,她接到了回電。高管們觀看了電影,並準備好了反饋。他們為沒有準備好購買而道歉。古內特並不介意。她建立了聯繫,開始了一段關係。多年後,這段關係結出了果實。當古內特在為 午餐盒尋找美國合作伙伴時,索尼經典影片收購了它。
普雷娜説,這不是一個輕言放棄的女人,她的童年朋友。她記得古內特需要讓伊爾凡·可汗簽字時的情景。普雷娜調侃她説:“那阿米爾·可汗呢?”古內特回答:“如果我有機會,我會的!”“如果他説不呢?”普雷娜問她。古內特回答:“但如果他説是呢?”
憑藉這種態度和膽略,古尼特成為國際電影節的常客,建立了令人羨慕的國際銷售聯繫人名冊。她迅速獲得了作為印度和西方市場之間聯繫的聲譽。
著名作家、編輯和電影評論家巴拉德瓦傑·蘭甘(Baradwaj Rangan)在filmcompanion.com上説:“大多數在印度工作的人在國外沒有那種網絡。”由於她廣泛的網絡,古尼特在全球電影製片廠中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聯繫。“歸根結底,節日和其他人依賴一個人,並依靠那一個人提供通往特定電影製作社區的門户,因為節目策劃者無法跟蹤每個國家的每一個動態。古尼特幫助建立了印度獨立電影與外國發行商之間的橋樑。”
獲得信譽並不容易。年齡和性別對古尼特並不有利。她有一張年輕的面孔。在職業生涯的早期,她會把頭髮染成灰色,並在會議上穿着紗麗。“否則,一個二十六歲的人怎麼會被認真對待?我只得假裝——我知道我的事情。”她常常被公司的市場主管、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拒之門外,他們對一個年輕女性推銷故事沒有耐心。
如果她是個男人,他們會聽她説嗎?“也許,”她説,但補充説她所面臨的歧視更多是由年齡而非性別驅動的。
寶萊塢仍然是一個男性俱樂部嗎?她在回答之前停頓了一下,“有很多男孩。”然後又停頓了一下。“我逐漸意識到這是一個男性俱樂部。我不是男人。我不抽煙。我一直羨慕那些去抽煙的人——那麼多交易都是在那裏達成的。”但她也相信,電影行業內的一些男性是性別平等的倡導者。她説,電影行業中女性人數的增長部分是因為有支持的男性。
“看看Anurag,他每次都會把我放在隊伍的最前面。”Guneet説她常常看到人們被處於權威地位的女性所嚇倒。“我認為有一代男孩在成長過程中感到自己有特權。他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獨立的印度女性。他們看到身邊的女性在為他們服務,滿足他們的需求。突然間,當他們長大後遇到不這樣做的女性時,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這位獨立電影製片人堅定地瞄準奧斯卡。
“宇宙正在密謀。我相信它會引導我走上一條道路,並讓我為之努力。”她能成為第一位將夢寐以求的金像帶回家的印度製片人嗎?相信奇蹟的Guneet説:“它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