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幸福研究與國防情報奇怪交叉?這種幸福不用了,謝謝_風聞
萨拉力曼-233332018-04-19 16:09
不僅是我們被控制和操縱,而且是“幸福”的人們隱秘而虛偽地要求以“為他們好”的名義被操縱。真相和幸福不能共存。真相是疼痛的;它帶來不穩定;它破壞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平穩流動。選擇在我們自己手裏:我們想要被幸福地操縱,還是讓自己暴露在真正的創造力的風險中?

齊澤克
【本文原載於2018年4月2日《洛杉磯書評•哲學沙龍》,原標題為:《幸福?不用了,謝謝》,譯者/盧南峯,譯文刊於澎湃新聞,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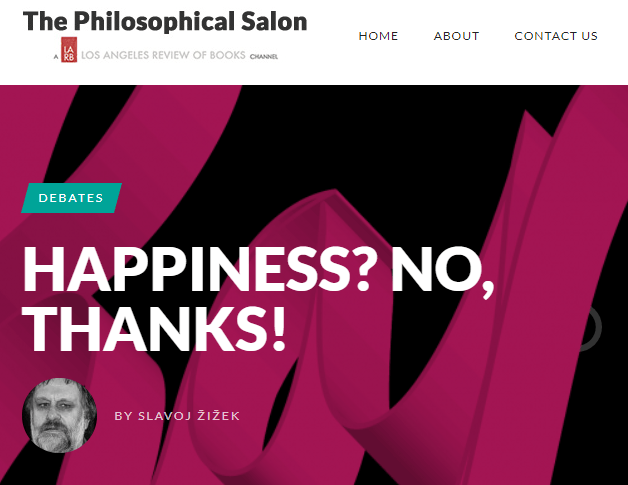
截圖來自《洛杉磯書評•哲學沙龍》
新的“認知-軍事聯合體”
如果有一個人物脱穎而出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那就是克里斯托弗·威利(Christopher Wylie),他是一個加拿大素食主義同性戀,在24歲的時候想到了成立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主意,這家數據分析公司聲稱在英國脱歐公投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後來威利在特朗普的競選活動中成為數字運作的關鍵人物,製造了史蒂夫·班農的心理戰工具。威利的方案是打入臉書(Facebook),獲取了美國數百萬人的臉書個人資料,利用他們的私人信息和人際信息創建複雜的心理和政治檔案,然後針對他們特定的心理構成,設計並投放政治廣告。在某一時刻,威利真的被嚇壞了:“這太瘋狂了。這個公司創建了2.3億美國人的心理檔案。現在他們想和五角大樓合作?這就像嗑了藥的尼克松。”(It’s like Nixon on steroids,譯註:此處引用的是2018年3月18日威利接受英國《衞報》採訪的話,尼克松是保守、老派、老氣橫秋的形象,人們無法想象他嗑藥。)
這個故事的迷人之處在於,它結合了我們通常認為對立的元素。另類右翼把自己打扮為一場解決辛勤工作的普通白人所關切的問題的運動,這些人擁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信奉簡單的傳統價值,憎恨像同性戀和素食主義者這類腐敗分子,還有數字技術宅(nerd)。現在我們得知,他們的選舉勝利是由這樣一個技術宅策劃和組織的,這個技術宅代表了所有他們反對的東西。這一事實可供玩味的價值不只一點**:它清楚地表明另類右翼民粹主義的空虛,它不得不依靠最新的技術進步來維持它廣受歡迎的紅脖子(redneck)吸引力。**此外,**它還消除了一種錯覺,也就是身處邊緣的技術宅自動站在“進步”的反體制立場。**在更基礎的層面上仔細研究劍橋分析的背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對人類福祉的冷靜操縱與熱愛關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紐約書評》題為“大數據心理戰中新的軍事-工業聯合體”的文章中,塔米辛·肖(Tamsin Shaw)討論了“私營企業在開發和部署政府資助的行為技術方面的作用”。當然,這些公司的典型案例就是劍橋分析:
“兩個年輕的心理學家是劍橋分析故事的核心。一個是邁克爾·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他和劍橋大學的同事大衞·史迪威(David Stillwell)設計了一款應用程序,通過分析臉書的‘點贊’(likes)來衡量人格特質。然後,它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積極心理學中心(Positive Psychology Center)的一個小組世界福利項目(the World Well-Being Project)合作,該小組專門研究利用大數據衡量健康和快樂,以提升幸福感。另一位是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他也在積極心理學領域工作,寫過關於幸福、善良和愛的論文(根據他的簡歷,其早期論文叫做‘鑽進兔子洞:愛的統一理論’)。在劍橋大學幸福研究所(Cambridge University’s Well-Being Institute)的支持下,他還主持了親社會與幸福實驗室(Prosociality and Well-being Laboratory)。”
**這裏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關於愛和善意的研究與國防和情報利益之間奇怪的研究交叉”。**為什麼這樣的研究吸引了英國和美國情報機構和國防承包商的極大興趣,以至於晦氣的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總是潛伏在幕後?這一交叉的人格化身是研究者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1998年,他“創立了積極心理學運動,致力於研究促進真正快樂和幸福的心理特徵和習慣,催生了一個龐大的自我幫助暢銷書行業。”與此同時,作為士兵恢復計劃(soldier-resilience initiative)的核心部分,他的工作吸引了來自軍方的興趣和資金。
這一交叉並不是“壞”的政治操縱者從外部強加給行為科學的,而是行為科學隱含的內在取向:“這些計劃的目標不是簡單分析我們意識中的主觀心態,而是積極心理學家找到一種方法,把我們向他們所理解的‘真正的幸福’方向‘輕推’一把,包括快速恢復的能力和樂觀情緒。當然,問題是,這種‘輕推’並不是在幫助人們克服科學研究所認為的‘非理性’意義上影響個人。現代行為科學的‘目標’是利用我們的非理性,而不是克服它們。”一門行為技術發展取向的科學,必然會把我們狹隘地看做是可操縱的對象,而不是理性的能動主體。如果這些技術正在成為美國軍事和情報網絡運作的核心,那麼看起來,我們將不得不更努力防止這些趨勢影響我們民主社會的日常生活。
劍橋分析醜聞爆發後,所有這些事件和趨勢都被自由派大眾媒體廣泛報道,從其中浮現出來的整體圖景,加上我們對生物遺傳學最新發展之間的聯繫的瞭解(比如連接人類大腦),提供了一種豐富而可怕的新形式社會控制圖景,相比之下,20世紀“極權主義”變成了一種相當原始和笨拙的機器。**要把握這一控制的整體範圍,就應該超越私營企業和政治黨派之間的聯繫(如劍橋分析案例中的情況),進入谷歌和臉書等數據處理公司與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的相互滲透。**阿桑奇那本關於谷歌的關鍵書籍被離奇地忽略,裏面説的是對的:為了理解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如何被監管的,以及這一監管如何被誤體驗為是我們的自由,我們必須關注那些控制我們日常的私營公司與秘密國家機構之間的隱秘關係。我們自己接受監管,與此同時我們還堅信我們保留了完全的自由,媒體只是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目標。新的認知-軍事聯合體的最大成就是,直接而明顯的壓迫不再是必要的:當個體繼續以為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是一個自由和自主的主體時,他們更容易被控制和“輕推”。但所有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我們還需要更進一步。

我們要幸福地被操控嗎?
去神秘化的解釋是最有力的批判:在對幸福和福利看似人畜無害的研究中,我們揭露了私營公司和國家機構的聯合勢力進行社會控制和操縱的黑暗隱藏聯合體。而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另一種相反的做法:我們不應該僅僅質問隱藏在科學研究形式之下的黑暗內容是什麼,而應該關注研究形式本身。關於人類福祉和幸福的研究主題真的那麼無辜嗎(至少在今天實踐的層面上)?還是它本身已經滲透了控制和操縱的立場?如果在這裏,科學不只是被誤用了呢?如果在這裏,它們恰恰是找到了自己正確的用武之地呢?**我們應該對最近興起的新學科“幸福研究”提出質疑。在這個精神享樂主義的時代,我們的生活目標是如何被直接定義為幸福,而焦慮和抑鬱被推翻?**正是這種自暴自棄的幸福與愉悦之謎,讓弗洛伊德的教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真實。
正如經常被舉例的不丹,這個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天真地闡釋了這種幸福概念導致的荒謬的社會政治後果:20年前,不丹王國決定專注於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縮寫GNH),而不是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縮寫GNP);這是前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的點子,他試圖將不丹帶入現代世界,同時保留其獨特的身份。現在,隨着全球化和拜物主義的壓力與日俱增,加上這個小國迎來了有史以來第一次選舉,廣受歡迎的牛津新國王、27歲的吉格梅·凱薩爾·納姆耶爾·旺楚克(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命令國家機構計算這個王國67萬人口的幸福程度。官員們説,他們已經對大約1000人進行了調查,並擬製了一份幸福指數列表,類似於聯合國追蹤的發展指數,主要問題已經被確定為心理健康、健康、教育、良好的治理、生活水平、社區活力和生態多樣性……這就是文化帝國主義(如果真的曾經存在過文化帝國主義的話)。
在這裏,我們應該冒險再進一步,探究幸福概念本身隱藏的一面。確切的説,什麼時候人們能稱得上幸福?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像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國家,人們實際上是幸福的。幸福的三個基本條件在那裏都得到滿足。(1)他們的物質需求基本滿足,但不是過度滿足,因為過度消費本身會產生不幸福。市場上一些商品時不時暫時短缺一下是件好事兒(幾天沒有咖啡,然後沒有牛肉,然後沒有電視機)。這些作為例外的短暫短缺時期提醒人們,他們應該為商品的普遍供應感到慶幸;如果隨時供應所有東西,人們會把這種供應看做生活中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實,而不再感謝他們的運氣。因而生活以一種常規的可預測的方式進行,沒有任何巨大的努力或衝擊,一個人被允許退縮進他自己的私人空間。**(2)第二個極其重要的特點:只要任何事情出錯了,都有一個他者(the Other)可供指責(在當時就是“黨”),因此沒人覺得自己真正負有責任。如果有一些商品暫時短缺,即便是暴風雨天氣造成重大損失,那也是“他們”的錯。(3)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還有一個他方(Other Place)可供人們夢想(在當時就是消費主義的西方),甚至有時能夠去參觀。**這個地方正好在合適的距離,不算太遠,也不算太近。脆弱的平衡被攪亂了——被什麼攪亂呢?準確來説,是慾望。慾望是迫使人們繼續前進的力量——最終形成了一個絕大多數人都不那麼幸福的體系。
因此,**幸福本身(在其概念上,正如黑格爾所説的)是不清楚的、不確定的、不一致的。**回想一下那個段子,德國人移民到美國,美國人問: “你幸福嗎?”德國移民回答:“(英語)是的,是的,我很幸福,(德語)但我不高興(aber glücklich bin ich nicht)。”這已經是一個異教徒的範疇:對於異教徒而言,生活的目標是過上幸福的生活(“從此過上幸福生活”的觀念已經是異教的基督教化版本),宗教體驗或政治活動本身被認為是更高級形式的幸福(參見亞里士多德)。幸福依賴於主體的無能或沒準備好完全面對慾望的後果:幸福的代價是,主體仍然陷於慾望的反覆無常之中。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假裝)渴望一些我們並不真正渴望的東西,因此到了最後,可能發生的最壞的事情是我們接受了“官方”的渴望。因此,幸福本質上是虛偽的:這種幸福是我們夢想得到我們並不真正想要的東西。
在許多左翼政治中,我們沒有遇到過類似的姿態嗎?當一個激進左翼政黨錯失贏得大選和掌權的機會,許多人暗地裏鬆了一口氣:感謝上帝,我們輸了,如果我們贏了,誰知道我們會陷入什麼麻煩……**在英國,許多左翼分子私下承認,上次選舉中工黨的功敗垂成是可能發生的最棒的事情,遠遠好過工黨政府試圖實施其計劃時可能發生的不安全情況。**這同樣適用於伯尼·桑德斯最終獲勝的前景:如果真的要對抗大資本的猛攻,他有什麼機會呢?
所有這些姿態的母親是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它粉碎了布拉格之春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希望。讓我們想象一下,在沒有蘇聯干涉的情況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會是怎樣的:很快,“改革派”政府將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在那個歷史性的時刻,民主社會主義並沒有真正的機會。因此,它必須在重新確立黨的控制——也就是説,為自由設定一個明確的界限——和任由捷克斯洛伐克成為西方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在某種程度上,蘇聯的干涉拯救了布拉格之春:它把它拯救為一個夢想,一個希望,也就是在沒有干涉的情況下會出現一種新的民主社會主義形式。**難道類似的事情沒有在希臘發生嗎?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政府組織全民公投,對抗布魯塞爾的緊縮政策施壓。許多內部消息人士證實,政府秘密地希望公投失敗,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下台,讓其他人來執行緊縮的髒活。自從他們獲勝後,這項任務就落在他們自己身上,結果是希臘激進左翼的自我毀滅。毫無疑問,如果公投失敗,激進左翼聯盟將會更高興。
所以,回到我們的起點,不僅是我們被控制和操縱,而且是“幸福”的人們隱秘而虛偽地要求以“為他們好”的名義被操縱。真相和幸福不能共存。真相是疼痛的;它帶來不穩定;它破壞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平穩流動。選擇在我們自己手裏:我們想要被幸福地操縱,還是讓自己暴露在真正的創造力的風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