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種族問題為什麼如此根深蒂固?(下)_風聞
北山浮生谈古论今-来跟我一起打开脑洞,认识世界2018-04-25 08:37
美國意識形態的宗教色彩
美國建國綱領《獨立宣言》中高喊“自由、平等、人權”,實際上仍然是來自於清教信仰。
所謂“天賦人權”中的“天”,其實是上帝(原文中是Creator,造物者,在西方語境中是上帝的同義詞),而所謂的“人”,並不是指的所有人類,而是指的是信仰新教的白種男人,後來這個含義被歸納為“WASP”,即信仰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WhiteAnglo-Saxon Protestant)。

《獨立宣言》是WASP價值觀的集中體現。WASP價值觀是美國上流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是美國的立國基礎。美國依靠延續三百年的種族滅絕立國,在立國之初特別強調血統及信仰的純潔性,這就為日後的種族歧視和種族衝突埋下了種子。
弔詭的是,WASP價值觀作為美國的立國之本,如今已經隱藏在水面以下,與之完全相反的“多元文化主義”,已成為美國的“政治正確”。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隨着世界移民的湧入,特別是大量黑人作為奴隸販入,血統的純潔性已無法保證。為了建立和諧的美國社會,人權的概念逐漸擴大到所有美國人(其中經歷非常曲折,這裏不再贅述)。由於盎格魯-新教價值觀自帶種族歧視屬性,在一個多種族移民社會中無法自洽,因此已經被主流輿論層層掩蓋,取而代之的一種拼盤式的多樣化價值觀。甚至不能在明面上説任何種族歧視的話,而且這種要求逐漸強化,已經到了任何可以被理解有歧視含義的話都不能説,一旦説了,就被打上“政治不正確”的標籤。種族歧視,已經異化為“少數種族優待”、“非法移民優待”等。
沒這方面意識的中國人初到美國,經常感到怎麼説都錯,常常有不敢説話的感覺。
在今日的美國,WASP羣體是唯一能夠讓大家隨便嘲笑,又不會激發嚴重抗議的族羣。一説到WASP,人們通常就會聯想起一些典型的形象,如古板、貪婪、自私、節儉、勢利、冷淡、工作狂、無表情、高傲等等。
然而,WASP精英階層始終牢牢佔據着美國的上流社會。一個典型的WASP精英的人生軌跡是這樣的:居住在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憑藉父母的蔭庇,從私立中學直接升入常春藤盟校,學習上流社會的習俗、禮儀、舉止,與其它名門望族建立關係,掌控着美國的財經、文化和政治等重大領域。族內通婚防止遺產外流;馬球、遊艇等是有錢、休閒階層的獨有娛樂方式。他們流連於相同的私人俱樂部,去相同的教堂,居住在一起(費城的Main Line和波士頓的Back Bay富人區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一切都和暴發户嚴格區分開來。隨時間推移,這些人也逐漸在美國中西部和西部定居,開始分散至全國。
WASP價值觀不僅存在於WASP這個階層,也影響到其他階層。這種價值觀和膚色無關,甚至和黨派無關,和社會地位有關,和教育背景有關。
換句話説,一個已經走向上流社會的黑人精英,他的文化屬性可能與底層的黑人羣體完全沒有關係,而是持有徹頭徹尾的WASP價值觀,甚至比純種的白人還要純粹。這在《聖雄甘地在南非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這篇文章中,有過很清晰的論述:
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歸化者”的心態,或者俗稱的“二鬼子”心態。
香港“佔中"運動中,言辭和舉動最為激烈的是招顯聰,然而招顯聰卻是越南移民; 對外地人言必稱“硬盤”的上海人,多出現於剛獲得上海户籍的新上海人; 明末屠嘉定的李成棟,其實是一個漢人; 反對女權最強烈的,幾乎都是熬成婆婆的媳婦。
這些歸化民,他們跟天生的”白人“”香港人“”滿人“”北京人“”上海人“不同,歸化民的言論和行為必須過激,他們的一切,是靠不斷的否定過去的自己來定義的,所以他們必須給自己貼上各種標籤,從心理上和行為上更加強烈的否定自己的過去,向心目中的“上等人”靠攏,才能更加辨識自己的身份。
對了,前一陣網上鬧得很兇的“精日分子”,也是這樣的心態。

《文明的衝突》的作者薩繆爾·亨廷頓,是對美國影響極大的國際政治學者,他在《我們是誰?》一書中寫道:“美國的核心文化向來是,而且至今依然主要是17-18世紀創建美國社會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即盎格魯-新教文化。

薩繆爾·亨廷頓
為論證盎格魯-新教文化在美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亨廷頓把北美大陸早期的殖民開拓者定義為“定居者”,而不是“移民”。
他寫到:“定居者和移民有根本的區別。定居者是離開一個現有的社會,通常是成羣出走,以便建立一個新的羣體,建立‘山顛之城’,其位置是在一個新的、通常遙遠的疆域。他們充滿了一種集體目的感。他們或明或暗地恪守一個協約或章程,它構建他們所建立的羣體的基礎並界定他們與自己祖國的關係。相比之下,移民並不是建立一個新社會,而是從一個社會轉移到一個不同的社會,這種人口流動通常是個人採取的行動,涉及的是個人及其家屬,以個人的方式界定他們與原居國和新居國的關係。”
在他看來,美國的核心文化就是這些早期的“定居者”創造的,後來的移民只是順應和接受了這種文化,也就是前述的“歸化民”。
在美國的清教先民的觀念裏,不同於陳舊,腐朽,專制的天主教統治的歐洲,新大陸的清教徒是上帝新的選民,所以他們試圖用一套“應許之地”的“聖約”政體,建立一座“山巔之城”——只受上帝統治的自由平等世界,並且承擔着向世界傳播自由和正義,把人類從罪惡之路引導到人世間新的耶路撒冷的神聖使命。
在“哥倫布發現美洲”300週年紀念日,埃爾赫南•温切斯特牧師讚美上帝為所有國家受迫害的人準備了一個避難之境:“這是一扇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大門,在北美的費城率先被開啓……它將擴大到整個世****界”。
美國的神權政治色彩從殖民地開始一直貫穿始終,從其總統的宗教信仰就可以看出來。美國曆史上出現過45位總統(包括特朗普),只有肯尼迪信奉天主教(被暗殺),其餘全部信奉新教。(有人説傑斐遜是無神論者,奧巴馬是秘密伊斯蘭教徒,均未經證實)。
早期的美國總統暫且不論,在21世紀的三位美國總統中,除了奧巴馬,另外兩位都是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小布什在911事件之後發表的演説中,使用了諸如“十字軍”、“聖戰”等宗教詞彙,來號召美國人向基地組織復仇。2006年9月11日,布什在紀念“9.11” 5週年全國電視講話中,首次把反恐戰爭提升到“文明之戰”的高度,聲稱要“為維護文明世界的自由生活方式”堅持戰鬥到底。
研究聖經的學者布魯斯·林肯,在小布什宣佈對阿富汗採取軍事行動的講話中注意到,雖然在長達970個詞的講話中,只有3個詞顯然是宗教詞彙,但對於熟讀聖經的人來説,這一演講中充滿了聖經中的比喻和《啓示錄》中的暗喻。奧巴馬正因為基督教色彩不濃,因此被許多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是一個秘密的穆斯林,甚至是“卧底”,“內鬼”,所以他才不那麼熱衷於打擊恐怖分子。
事實上,美國一直用一種狂熱的宗教熱情,向全世界推銷“普世價值”,履行其作為”山巔之城“的終極普世使命。在美國人眼裏,其它國家不僅僅是文化不同,種族不同,更重要的是信仰不同。儘管“大中東民主化”是一個非常不現實、甚至對美國有害無益的計劃,卻仍然被積極推動,正是出於這一原因。
至於中國,這個不信上帝、種族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也不同的無神論國家,是真正的異教國家,是註定要被顛覆的,否則不能證明一神教上帝的“全知全能”。 於是,中美博弈不僅僅是地緣和利益博弈,更是文明的衝突,唯有中國發生“顏色革命”,或者政治經濟大崩潰,才符合美國人的宗教想象。沒有發生,就要千方百計地讓它發生。
只要美國不崩潰解體,它就必然會以中國崩潰解體作為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説,中美矛盾是不可轉移不可調和不可避免的,必須以一方倒下作為結局。
正因為如此,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聽起來彷彿是來自古老中世紀的呢喃,與全球化的現實相距甚遠,卻迅速被美國政治家所接受。
然而,亨廷頓的論述中存在一個致命的bug:這些來到北美的WASP們,並不是最早的定居者,他們也是移民,而且是殘酷滅絕了原本的定居者印第安人之後,反客為主,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WASP通過種族滅絕獲得主體地位之後,為了保持自身的“純潔性”,對於後來的移民也長期執行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例如對於黑人的認定是“一滴血”原則,也就是如果一個人只要混有一丁點黑人血統,那麼無論他經過多少代白人混血,那麼他也被認定為黑人。
後來者在融入美國之後,顯然不會只繼承盎格魯-新教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其黑暗面也會一併繼承。在社會秩序崩潰、面臨資源嚴酷競爭的環境下,他們會不會效仿當年的WASP們,再對先來者舉起屠刀呢?
除了WASP之外,最符合亨廷頓所定義的“定居者”的人羣,則是與WASP最格格不入的穆斯林羣體。他們同樣“成羣出走”“充滿了一種集體目的感”,“或明或暗地恪守一個協約或章程”。這些不同種類、彼此仇恨的“定居者們”碰到一起,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大家可以想象。
特朗普不顧一切推出“限穆令”,遭到美國公眾輿論的譏笑和嘲諷,也許在若干年後,他會被重新定義為“先知”。

用宗教話術來説,盎格魯-新教價值觀中帶有種族滅絕與種族歧視的“原罪”,已經刻入骨髓,即使傾盡密西西比河的水也無法洗淨,只有等待最終的命運審判。如今美國各種匪夷所思的“政治正確”,其實也是宗教“救贖”心理的體現。
借用某位微博大V的語言,在這個“惡之花綻放的土地”,最終結成了惡魔的果實,那就是種族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種族主義思想,來自北美清教徒的實踐經驗總結,並最早由第三任總統,也是《獨立宣言》的作者托馬斯·傑斐遜形成系統的理論(意外吧?參見《弗吉尼亞,美國夢開始和凋零的地方》)。後來納粹德國的種族清洗理論的淵源,實際上都是受到了美國的這些先行者的啓發。
傑斐遜晚年的時候,曾用飽含着對美國的熱愛、同時對美國未來深感恐懼的複雜心情,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
“上帝在給予我們生命的同時,也給了我們自由。當我們漠視這個信念(即上帝給了所有人以自由)的時候,難道一個國家的自由還是有保障的嗎?每當我想起上帝是公正的,他的公正是不會永遠休眠的時候,我就為我的國家顫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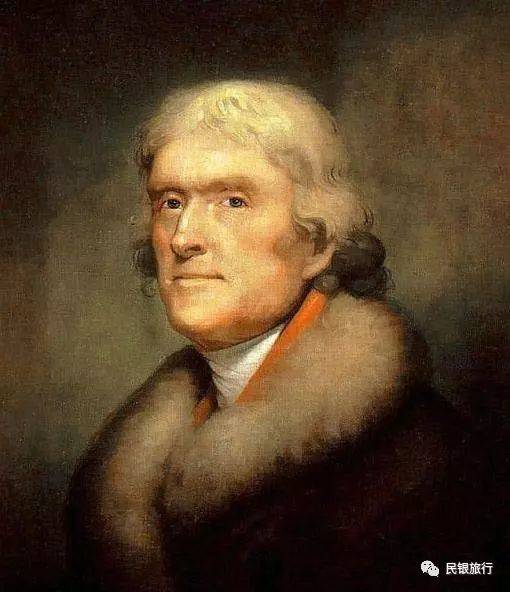
托馬斯·傑斐遜
傑斐遜所恐懼和擔憂的,是美國難以化解的種族矛盾與種族仇恨,將來會化成滔天的烈焰,將美國這座滿載着光榮與夢想的“山巔之城”燒成灰燼。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邁克爾·曼教授,在《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一書中寫道:蓄意謀殺性的種族清洗,在本質上是現代現象。儘管它在歷史上也曾發生,但只有到了近代後才變得更加多發、同時更為致命:在20世紀,因為種族衝突而死亡的人數大約7000多萬,遠超過前幾個世紀的數字;此外,常規戰爭也越來越將敵對國家的全部人口作為敵人;“一戰”期間平民佔死亡人數比重不到10%,“二戰”期間躥升至一半以上,而在1990年代進行的戰爭中,佔比已超過80%開外;本來大多是族羣間性質的內戰,現正在取代國家間戰爭而成為主要殺手。
邁克爾·曼將種族屠殺的元兇歸結到現代民主政治理想的醜惡一面,民主政治原本就是來自清教徒的政治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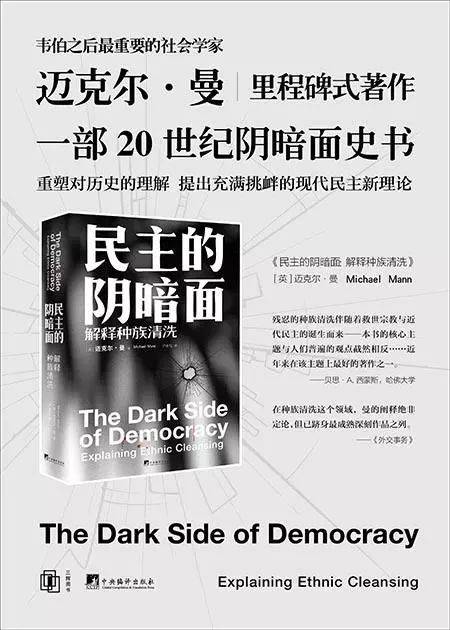
對比而言,華夏文明形成之初依靠的是多個民族的相互融合,因此不太強調血統純潔,而是強調文化的認同。“夷狄而華夏者,則華夏之;華夏而夷狄者,則夷狄之”的意思就是説,外國人如果認同了華夏的文化,就是華夏人;而如果華夏人認同了外國的文化,就不再是華夏人,而是外國人。中國的這種包容思想貫穿了幾千年歷史,基本沒出現過漢族對不同信仰者的大規模屠殺。
華夏文明的基本特性本就不是什麼多民族共存,而是消滅原本的民族特質,基於文化認同的融為一體!一些無傷大雅的細枝末節則可以保留,但是原則問題不能含糊。這就是“求大同存小異”。實事求是地説,只有這種價值觀,才可能真正做到多種族和諧共存。
美國的種族問題日趨惡化
“越是缺啥才越強調啥”,美國種族歧視的思想根源是其立國之本《獨立宣言》,建國過程就是種族屠殺過程,前後綿延了幾百年,WASP高人一等的心理狀態根深蒂固,非裔等少數族裔長期受歧視受迫害形成的心理保護意識也由來已久,除非能用科幻小説裏的“思想鋼印”直接洗腦,不是政治上喊兩句口號就能解決的。
繼續堅持WASP價值觀會導致社會共識瓦解,反之也是行不通的。過分地強調“政治正確”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病態,正是説明了歧視思想已經深入骨髓血脈,融入每一個美國人的內心深處。要想根除這種歧視思想,就要完全抹除盎格魯-新教價值觀,徹底否定美國建國的歷史,否定開國先賢,實際上就是挖了美國立國的文化根基。
國家共識,跟鈔票、房子、收入無關,看起來是一個無關切身利益的小問題,但實際上這才是關係到一個國家生死存亡,每個國民生存的大問題。國家不是警察、法庭、軍隊這些有形的東西,而是人們想象的共同體,共識瓦解,實際上就是國家解體的先兆。蘇聯曾經那麼強大,但是共識一旦瓦解,灰飛煙滅也就是頃刻之間的事情。

蘇聯解體時拆除斯大林雕像
美國的白左們極為強調“政治正確”,企圖化解這一問題,實際上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得問題進一步複雜化,甚至發展下去會否定主體民族,進而否定美國自身,最終導致共識瓦解,國家解體。
正反兩方向都會瓦解國家共識,而民主制度又不可避免地導致政治極化,這才是真正的騎虎難下!
美國每一次陷入經濟危機,社會矛盾加深,都伴隨着種族衝突加劇,甚至出現種族暴亂。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在美國國內也越來越多以種族衝突、種族仇恨的形式表現出來。2017年的弗吉尼亞騷亂、推倒雕像運動以及奏國歌下跪,都是美國種族衝突日漸激化的明證。



雕像先拆起來
事件發生後,特朗普在推特上寫道:
通過拆除我們美麗的雕像和紀念碑,我們偉大國家的歷史和文化被撕裂了,令人悲傷。 你不能改變歷史,但你可以從中學習。羅伯特·李、傑克遜,誰會是下一個?是華盛頓,還是傑斐遜?太愚蠢了!
字裏行間,分明看到了一個老愛國者心底深深的悲哀,但是面對一個高度撕裂的社會,他又能做什麼呢?
冬季太冷,不適合上街,如今春暖花開,又到了上街的季節。特朗普搶在羣眾上街之前,先把貿易戰打起來,敍利亞戰火燒起來,也不失為轉移國內矛盾的機智策略。
美國的種族衝突可不僅僅是黑白之間,而是存在於各個種族之間。除了WASP之外,美國的幾大種族的表現盤點:
拉丁裔:來自拉丁美洲,主要是墨西哥,從歷史上看這算是跟美國仇恨最小的一羣了(也就是國家被侵略,土地被搶佔,這在漢族人看來是天大的事,但是拉丁人的守土意識不強,他們巴不得全體併入美國),髒活累活全歸他們,但是卻被WASP歧視得很厲害,特朗普所説的修牆就是針對他們。

非裔:也就是黑人,不説了,説多了都是淚,這也是目前種族衝突表現最明顯的種族,但黑人沒什麼組織紀律性,單打獨鬥可以,羣體戰鬥力太差,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但是白人警官的傲慢表現,也是一再挑戰黑人的忍耐極限。

印第安人:最苦大仇深的一羣,不過人太少,沒什麼話語權。而且美國把遺留的印第安人圈在保留地裏當家畜養,已經讓他們喪失了反抗的鬥志,除非確實損害了他們的切身利益。

穆斯林:前面説了,最有戰鬥力的羣體,然而人少,相對於非裔來説不太顯山露水,主要來自中東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北非等地。但前面也説了,伊斯蘭教的擴張性是最強的,擴張速度僅次於共產主義。這些穆斯林的祖國都被美國禍禍得不要不要的,苦難深重的經歷,讓其信仰純潔性堪比當年踏上北美大陸的清教徒。不一樣的是,新教徒當年對印第安人可是無怨無仇,穆斯林則是跟美國苦大仇深。幸好人數少,幸好。

亞裔:主要包括印度裔、華裔等,這幫人在種族衝突中基本屬於醬油黨。華裔由於文化原因,基本是最沒有種族意識的,屬於人畜無害小白兔,是最佳的移民,然而卻常常被當作犧牲品,經常以受害者面貌出現。從1882年排華法案到今天一直是如此,扮演了類似中世紀猶太人的替罪羊角色。
印度裔:繼承了印度“非暴力不合作”的光榮傳統,有很強的被殖民自覺,暴力的事基本與印度裔無關,白人對印度人要比華人放心得多。但是相對於華裔來説,印度裔祖國意識很強,搞搞吃裏扒外,向祖國印度輸血比較拿手。美國印度裔一般都是精英,由於語言文化原因,很容易混到高科技公司高層,有從內部掏空美國的傾向,對美國實力的實質損害不容小覷。

猶太人:人數雖少,但是掌控經濟命脈,能量最大,猶如星際爭霸中的“神族”。歷屆美聯儲主席都是猶太人,猶太精英控制着美國的金融、科研、傳媒娛樂等諸多領域。猶太人雖然擁有莫大的財富與權力,卻是寄生在美國國家肌體之上,隨時有可能跑路的一羣人。

在美國的各個種族中,只有WASP是真心把這片土地當作自己的祖國(哦,好像把土著忽略了,他們實在是存在感不強),自己的家園,其他種族要麼把這裏當成避難所,要麼當成淘金地,所謂“以利聚人,利盡則散”。
自美國獨立戰爭建國以來,WASP在美國總人口中一直佔有優勢,但是最近比例急劇下滑。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WASP將在二三十年內失去美國優勢種族的地位,淪為少數種族。
從2000年到2010年,10年中美國人口淨增長9.7%。然而WASP的淨增長只有1.2%。作為對比數據,同時期的中國,從2000年到2010年,人口增長5.84%,其中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10年增長5.74%。
非裔,淨增長12.3%,是同時期中國的兩倍,是同時期WASP的十倍!拉丁裔,增長43.0%,是WASP的三十多倍!
2000年,白人69.1%,拉丁裔12.5%,非裔12.3%,亞裔3.6%
2010年,白人63.7%,拉丁裔16.3%,非裔12.6%,亞裔4.8%
2010年,在19歲以下的人口中,WASP佔55.8%;5歲以下的人口中,白人佔51.7%。
WASP比例雖然在下滑,美國社會前1%的富裕家庭中,仍然有超過96%是WASP家庭(剩下4%基本是猶太人)。而總人口比例中佔比越來越高的拉丁裔、非裔,基本處於社會底層。因此,美國的種族對立還混合了階級對立,使得美國社會的撕裂性進一步加深。
特別是美國民間還擁有幾億只槍,任何有極端思想的人都可以很方便地發動恐怖襲擊,近些年來日益頻繁、規模日益增大的槍擊案就是明證。
隨着WASP人口比例不斷下滑,WASP精英們憂心忡忡。亨廷頓認為,美國能否重振國家特性,捍衞和保守盎格魯-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攸關他心目中的美國能否存在,以及它的國際地位能否得以延續和維持的問題。如果美國摒棄了“美國信條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們所認識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終結。實際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終結。”亨廷頓實際上把美國及其在世界地位和整個西方文明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了。
相對於文明的興衰這種宏大命題,作為個體的WASP,更加關心自身生命財產安全以及社會福利的問題。按照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隨着人口比例的下滑,WASP越來越難以選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這對於掌握了社會資源的WASP精英們是難以接受的。
WASP心中的恐懼在日益加深,自身安全問題越來越成為WASP,特別是上層WASP們的一塊心病。隨着國內矛盾的一步步激化,在生存問題面前,用於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所謂“政治正確”,越來越成為一塊可以隨時丟棄的抹布。
美國的政教合一趨勢將越來越強
唐納德·特朗普,這個億萬富翁,站在美國金字塔尖上0.01%的WASP男人,靠大談種族對立等“政治不正確”的話題參加美國競選,甚至講出了”穆斯林是美國的潛在威脅“這種話。
他的大受歡迎,就説明他説出的正是大多數WASP心中所想。特朗普能夠在媒體一片唱衰聲中上台,恰恰證明了他背後堅實的羣眾基礎。他上台後,一定會採用強硬措施改變WASP人口下滑的趨勢,重塑主體民族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因此,在美墨邊境造牆、限制穆斯林移民都是應有之義。
特朗普總統採用的維護主體民族利益的政策,卻遭遇本國精英階層與主流輿論的一致反對,除了主體民族比例下降這一因素之外,這實際上體現了美國的另一個深層次的矛盾。
美國擁有三億人口,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稱為海島明顯説不過去,它其實就是一片大陸。美國的領土規模和人口規模,以及人口來源的複雜性,決定了它必須具有很深的大陸文明屬性。但是美國的絕大多數文明基因來自英國的海洋文明傳統。這就好比一個人,他的身體明明是個男人,但是心理卻是一個女人,這種認知矛盾會造成行為錯亂,國家的實際情況與文明不匹配也會造成混亂。
大陸文明國家之所以大多采用中央集權,是因為國土廣大,地域差異十分複雜,利益差距很大甚至南轅北轍,必須強調各部分求同存異團結為先,一切從全局出發維護公共利益,才能維持內部穩定以及領土完整。如果像海洋文明那樣強調個體自由,對抗式民主,內部矛盾就會越演越烈,最終不可收拾。
以美國為例,其東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利,但是中部地區卻從經濟全球化中受到傷害,兩者利益截然相反,必須通過某種妥協或者利益重構(例如中國的財政轉移支付、扶植落後地區建設),實現妥協,求同存異,但是在美國現有的民主政治的框架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衝突會沒完沒了。
海洋文明活力有餘而穩定不足的缺陷,過去被美國經濟高速增長、勢力範圍不斷擴張以及利用金融工具從全世界吸血掩蓋住了,如今世界經濟停滯,這一問題就會爆發出來。
如果不進行內部改革,從歷史經驗上看,像過去對付蘇聯那樣找一個外部敵人(夠分量的也只有中國了),把它打倒搞殘,釋放的財富紅利能讓美國再次滿血復活,並且也能夠轉移人民視線,緩和內部矛盾。這是為什麼特朗普一再操縱中國議題,將美國人失業的鍋背到中國身上、挑起貨幣戰、貿易戰的根源。
中國躺槍,不是因為中國犯了什麼錯,而是源於美國內部治理的失敗與無能。不理解這個邏輯,就無法理解中美矛盾。
但是中國既不存在蘇聯當年那樣的硬傷,也沒有蘇聯那樣的擴張野心,更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那樣的領導人,美國慣用的幾板斧都不好使。而且就算全力對付中國,沒有二三十年看不到效果,但是美國目前的狀況可能都撐不了那麼久,就先崩潰了。這是特朗普着急上火的根源。
為解決內部矛盾衝突,美國必須對自身政治制度進行調整,增強大陸文明屬性使其與實際情況相適應。
我們看到,特朗普從現實情況出發採取的各項政策,看上去與美國的政治傳統是那麼的格格不入,不僅將奉行多年的自由主義全球化路線棄之如敝履,而且將美國優先、羣眾路線、貿易保護、行政干預市場等等掛在嘴邊。至於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看起來毫無章法,更不可能對中國造成什麼實質的傷害,與其説是遏制中國,更像是藉着外戰整合內部的伎倆。
中國顯然不能接受像日本那樣被打倒,更不能接受像蘇聯那樣崩潰解體,必然全力以赴面對挑戰。假設中國扛住了美國的挑戰,那麼美國遲早要面對自身存在的嚴重問題。
這一問題曾經引發了羅馬文明的消亡,如今輪到美國這個“新羅馬”來接受考驗了。文明的生存,不在於順境中有多風光,而是在於逆境中有多堅韌。很多文明連一次這種考驗都沒挺過去,就消散在歷史中。
只有通過這一試煉,美國才能真正成為偉大的文明。
在文明危機這一層級的劫難面前,如果其他手段都不好使,最後的救命手段就是宗教,這是凝聚人心,重建共識,實現羣眾自組織最後的手段。
最初,宗教是伴隨着文明的出現而同步出現的,原始文明都是政教合一的。隨着早期文明的進化,宗教也跟着進化,在這個階段,宗教是文明身上的盔甲。但是文明成長到一定階段以後,這層盔甲會變成文明的束縛,因此文明最終都要拋棄掉宗教的保護,即實現世俗化。
從這裏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歐洲歷史上曾長期陷入中世紀黑暗。因為在那段時間,基督教文明處於落後狀態,始終被先進的伊斯蘭教文明壓制着,因此它必須用政教合一的這層盔甲把自己重重保護起來。如果沒有這層保護,處於落後地位這麼久,基督教文明早已被歐洲人拋棄,就像歷史上消失的無數落後文明一樣。
歷史上印度文明遭受的苦難最多,面對連綿不斷的外來侵略與壓迫,印度文明不斷跌倒,最後乾脆躺在地上不起來了,從宗教中尋求安慰。印度人是最不容易走極端,但是想要擺脱宗教的束縛,實現整體崛起,目前來看也是比較難。
由於歷史上的地緣優勢,伊斯蘭教文明實際上是順風順水的時間最長,經歷的苦難最少。我們看現在伊斯蘭教文明最保守最落後,也是因為他們苦難受的太少,還處於宗教的青少年期,連政教分離這一關還沒過。從十九世紀末到現在,才是伊斯蘭教的經歷的第一次苦難期。
華夏文明綿延時間最長,歷史上最為輝煌,經受過的苦難也十分深重,跌倒後復起的意識也最強。在周代商以後,就完成了整體上的政教分離。伊斯蘭教文明目前所處的癲狂狀態我們歷史上早就經歷過,而且不止一次。五胡亂華是第一次,在黑暗中沉淪了幾百年才走出來。後來五代十國又經歷了一次;元朝入侵又一次,清朝入侵也是一次,近代以來又是一次。其中每一次都是沒頂之災,幸好,華夏文明有了多次被扔到水裏的經驗,已經養成了一身游泳技能,在危險的關頭還是存活了下來。通過文明的融合,吸收外來文明的優點重現輝煌。
即使是華夏文明這種世俗化最徹底的文明,在最黑暗的年代,政教合一仍然會不同程度的死灰復燃,例如黃巾、白蓮、天師、明教、義和團、太平天國等,這是文明尋求消極自我保護的一種機制。
基督教文明在羅馬帝國的危機中誕生,還沒有經歷過輝煌,又趕上伊斯蘭文明的崛起,此後就一直處於被壓迫地位,屌絲了上千年,也掙扎了上千年,經歷多次宗教改革,多次十字軍東征,結果都不理想,最後借地理大發現才實現逆襲。上千年的苦不是白吃的,至少政教分離是完成了。但是在歷史記錄中,基督教文明在面對異種文明時,都是以滅絕對方來應對,還沒有經歷過多文明融合,因此還沒有學會如何實現多文明共存。
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其實一直都是在打順風球,趕上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擴張的順風車,始終沒有在長期停滯甚至逆境中生存的經驗。美國勢力範圍的全球擴張目前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在中東目前卡在敍利亞,在東亞則卡在台灣和北朝鮮。
正如當年的羅馬帝國一樣,帝國一旦擴張到極限開始收縮,帝國紅利轉而變成了負累,政治內鬥加劇,種族矛盾激化,人們的心靈得不到安放,於是基督教像野火一般傳播。世俗的羅馬逐漸變成了政教合一的宗教國家。
其實不止美國,處在文明衝突前沿的歐洲國家,其宗教保守勢力紛紛回潮。曾經因抵禦穆斯林入侵立下汗馬功勞,被稱為“基督之盾”的波蘭,最近通過了一項法律,將耶穌加冕為國王。

可以預言,隨着文明衝突的加深,種族矛盾的激化,美國的宗教氛圍將不斷加深,甚至重新變成政教合一的國家。
那時,人類的理性之光,就要看東方了。
作者微信公眾號:北山浮生談古論今(BSFS_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