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一條牢固而清晰的樂器“鄙視鏈”?_風聞
阴山贵种-典午当涂2018-06-14 13:27
近日有兩大國際新聞熱點。一個是青島的上合會議,一個是G7峯會。前者的和諧和後者的不和諧,之間的反差引起了國內外網友們的熱議。
在上合峯會正式召開之前,在人民大會堂有一個“友誼勳章”頒授儀式,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俄羅斯總統普京授予首枚“友誼勳章”。這次普京訪華,他收穫的還不止這枚勳章,還有兩個物件:習近平總書記向普京贈送一把中國古老的樂器——古琴,和一尊天津著名陶土雕像--塑有普京面部的“泥人張”。
兩國最高領導人之間送禮物,也本是外交環節的慣常操作。不過,在筆者瞭解到的民樂圈裏卻炸了一下下,古琴粉們興高采烈地懟同樣是彈撥類的古箏粉:哈哈,看到沒有,習大大送給普京的是古琴而不是古箏哦。

古箏粉們不得不再噴回去:送古琴是因為這個樂器體積小,古箏身長快1米七了,不方便普京攜帶啊。一輪輪罵戰開始了……
不過不同樂器之間以各種標準分出高下長短,恐怕要比同行內部之間的比拼還要“陰損”一些,因為這無疑直接挑明專業行工的地位問題。

古箏
一個喜歡拉小提琴的妹子説過,圈裏玩西洋樂器的鄙視玩民樂的,玩鍵盤類的鄙視玩彈撥的,玩彈撥的鄙視玩吹打的,玩貴的樂器的鄙視玩便宜的,玩學習程度難的鄙視玩相對容易的……
樂論和樂器乃是毛和皮或者唇和齒的關係,於是話題極為容易被轉化為民樂與西洋樂器的高下之分。那麼,在民樂和西樂之間,以及在民樂內部是否真的存在一條牢固且清晰的樂器鄙視鏈?
如果你在各種搜索引擎和問答類社區論壇中發出這樣的問題:哪一類樂器可被稱為樂器之王?有一個詞將會極為頻繁地跳出來:鋼琴。
就鋼琴的形體而言,鋼琴一起復雜的機械裝置和碩大、器宇軒昂、雍容華貴的樂器形體,超越了絕大部分樂器,完全就是一架音樂機器;而且從性能上講,鋼琴有着近乎樂器中最寬廣的音域,從大字二組的A到小字五組的c,跨度達七八度零四個音,頻率可以從27.5到4186赫茲不等——音域之霸;鋼琴還有宏大的音量和可塑空間,牛x程度直逼一直交響樂隊。
所以説, 鋼琴能勝任多聲部復調與和聲的自由演奏的特性,以及在獨奏時的悉尼、豐富的表現力,吸引了大批一流音樂家的青睞,所以鋼琴除了在純音樂界之外,還被附有了濃重的社交屬性(成了高雅、精美、時尚的禮器)。
鋼琴沾染的文化身份的魅力讓廣大的中國中產家庭趨之若鶩,連BBC都曾經多次撰文,分析為何中國人的孩子都有“鋼琴癖”。

而且樂器的製造水平特別能看出一個國家的工業能力,而鋼琴這時候就會被選出來當樂器代表。
對此,筆者曾不斷諮詢過滬上音樂系多位專業西洋樂器演奏者,無論教師還是學生對此皆哂笑,有位桃李滿天下的老教授還打趣:“樂器之王我看就是嘴和舌頭,一個口哨什麼調調都能吹出來。”
無疑,無論各種樂器越彈越深,奏樂者都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之感。但鋼琴作為各類樂器中的“奠基性”作用卻也是業界共識,寬廣的音域,極富有彈性的音色和高度標準化的音準讓它不但能自帶體系,而且在和其他樂器的配合中兼容性極高。
BBC的某專欄作者驚訝於在中國有高達四千萬的小孩在學這種樂器(筆者不知道這個數據是否精確),並且撰文探討“為何中國中產階級家庭對鋼琴如此迷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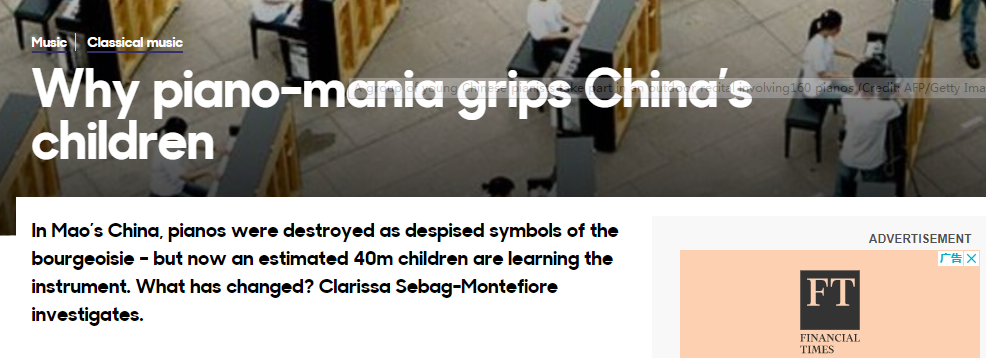

BBC的報道
於是,我們可以較為大膽的做出結論,鋼琴作為樂器類“食物鏈”的頂端層面問題不大。但對於其他可以“知萬物之情”的樂器呢?
如果你具有基本古代中國樂器史知識,便可知“軸心時代”的中國,打擊類樂器享有崇高的地位,有關這一點,可以參照有關對8年出土的超期國寶“曾乙侯編鐘”的有關介紹(對打擊類樂器的介紹);另外先秦史籍中對打擊樂器的描述非常繁盛,著名的就有藺相如逼秦王擊缶,荊軻刺秦之前,“高漸離擊築,荊軻和歌”,更別説在春秋戰國時代戰場上的鉦和鼓。從樂器的使用頻率和普及度上,那個時代的打擊樂器絕對是獨領風騷,更重要的一點是,它是當時“雅樂”演奏時的主角。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便是在那個孔夫子痛心疾首的“禮崩樂壞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年代,被降格的周天子之禮成了諸侯僭越的文宣陣地,但很多場合打擊樂仍然可以居高臨下俯視管絃樂同儕,八佾舞於庭的主要的合作對象據研究就是鍾和磬。
幾百年後的魏晉時代,優孟衣冠南遁,缺文少質的北地鮮卑政權雖自詡“陰山貴種”,但缺急切想要繩天命之德宣示華夏正統,遷都洛陽後才發現文獻易尋,鐘磬難覓,樂譜的失傳和長期戰亂對樂師生存環境的戕害讓周禮的復興之路很是艱難,但鼙鼓鐘磬等打擊類在樂器“食物鏈”中的頂端地位並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但正所謂不是所有的摩登舞都能登大雅之堂,成為歐洲19世紀晚期的宮廷舞蹈一樣,也不是所有的打擊類樂器理直氣壯地鄙視彈撥類或者吹奏類的小夥伴。
上文提到的藺相如逼秦王擊缶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在重大外交場合中,任何可能一個不經意的道具都有潛在可能被解讀為有一種特別的“縱橫術”的用意,比如説安倍的這把椅子。歷史愛好者讀這段記載時,往往被藺相如五步濺血的凌然氣概所傾倒,也要看到這次澠池之會的兩個樂器道具:瑟和缶。秦王挑撥趙王鼓瑟,最後卻被迫擊缶,欲侮人卻自辱。
即便是拋開秦趙兩國這一彤雲密佈的“第二戰場”這一背景賦予的瑟和缶的附加含義,僅就這兩種樂器的構造成本和演奏的技術含量談,作為彈撥類樂器的瑟碾壓打擊類樂器的缶是毫無問題的。本來在東方六國眼中,祖先靠給周王室養馬放牧的秦地本就是尚武輕文的禮簪荒蠻之地,成本製作低廉,演奏技巧單一的缶在設計相對精巧很多的瑟面前有自卑感實屬正常。

藺相如請秦王擊缶
這麼看來,廟堂之上的打擊樂在鄙視鏈中的地位也最多隻能籠統的講。
按照《呂氏春秋》推演的諸夏上古先王制作樂器的初心來看,樂器高下之分的鏈條確實存在:“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 “拌瞽叟之所為瑟,以明帝德”,在華夏文明的初創階段,打擊樂(祭上帝)能排在管絃樂(昭帝舜之德)之上,筆者大膽推斷很可能出於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承接上古蠻荒時代打擊樂之通靈功能,畢竟管絃類樂器因為製作成本和技術精細劃分問題而晚出;而俯拾皆是,製作成本相對簡單原始石器便可以承擔音律和聲的大部分功能;第二點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是,相比管絃樂和吹奏類樂器,製作精良的高端打擊樂器幾乎是唯一能充盈飽滿地演奏“三分損益法”帶來的十二律,比如深埋地下兩千餘年的,號稱“天下第一樂器”的增乙侯編鐘,中心音域內具十二半音,而且每個鍾可以敲出呈三度音程的兩個樂音,同時代的其他樂器很難做到這一點。

增乙侯編鐘模擬圖
換句話説,雖然不同種類的打擊樂器的製作成本和技術含量之間可能有云泥之別,但高端打擊類器械確實有一覽眾山小之感。
音域的寬廣度,音律的精確度和其他樂器配合的兼容性,是不是可以拿來校驗樂器鄙視鏈的硬核?以筆者愚見,上述標準確實有很強的合法性,尤其是在組樂配合曲目演出時,器械之間的重要性有明顯的區隔感。比如一個草台京劇班子,由於受到資金和人員配備的限制,樂種不齊,那往往缺席的是月琴、笛和鈸,而京胡和二胡卻是必備的;而且演員在吊嗓打板的時候,一把京胡就足夠了,因為這是整個樂隊最核心的樂器器械,過門兒定弦全靠它。
讀者提出的其他幾個參照系,比如製作和購買成本的高低和學習難度(包括入門和進階)算不算不可缺少的考慮因素?
雖然同一種樂器基本都有低中高等不同價位,但其中的市場價值的中位數還是很明顯可以一較高下的。價格高昂的樂器無疑會極大地限制那些預算拮据的器樂愛好者的選擇,但必須要指出的是,對於有志於進階的玩樂器的人來説,花在購買樂器上的錢只佔真正的財力投入的一小部分,而大頭則是後續的學費。
以滬上古箏課的價位來看,一般情況下是90分鐘250元上下,如果要請名師一對一指導,價格要至少翻2.5倍左右,從零基礎到練到七八級左右所需的花費,秒殺碾壓了樂器本身的成本,所以説單純靠價格評判樂器高端與否有失精確。
在器樂的業餘愛好者們經常撕x的一個話題是各類樂器之間的學習難度,而且這一點在票友圈裏幾乎成了樂器食物鏈的基本構成標準之一。
筆者在很多年前鄉下旁觀過一個出殯的場面,白事會自然少不了吹吹打打,無意間聽到應堂會的喪樂隊財會人員在討論酬勞分成,吹笙的師傅説他的酬金應該是吹嗩吶的兩倍,這是行規,因為“半年的嗩吶一年的笙”。

笙與嗩吶
同樣,有民樂皇冠上的明珠之稱的“二胡”被拔高到如此地位,也是因為其特點在於門檻高,上手比較難。此外,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古箏和古琴的比較。
滬上徐彙區某器樂學習社區曾做過一個實驗,讓幾十個個從未接觸過古箏和古琴的孩子站在樂器旁邊,聽專業的音樂老師分別彈奏三首古箏曲和三首古琴曲,結果居然有近乎九成的孩子被古箏清脆活潑的音色和演奏技巧所吸引。對彈撥類民樂的受歡迎度市場調研的反饋也證實和此實驗的結果的有效性。

百鳥朝鳳,讓我們確實見識了嗩吶的威力
箇中的緣由恐怕就是古琴“範兒”現代感比起古箏來講是比較弱的,雖然大批的古代工尺譜的流傳都是琴譜而非箏譜,但在國內外各大視頻網站上,中國民樂彈奏西洋曲目其中以古箏的熱度最高,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僅憑這一點,古琴愛好者吐槽古箏入門太水門檻太低就有些酸葡萄心理了。
焦慮感找錯了地方,恐怕還輪不到民樂。舞蹈即是鮮活的例子。如果説樂器尚有實物作為載體而能傳承下來,那麼真正失傳的則是純粹的肢體語言的表達,道理並不複雜:古代沒有活動的影像資料,雖然有考古學者在敦煌冊卷中發現了一些舞譜的殘卷,但由於舞蹈本身和音樂結合的獨特屬性,導致舞譜基本不可太可能被大批還原。
即便是存在一條清晰牢固的鄙視鏈, 不代表很多民樂可以和西洋樂器和諧共存,筆者放出這麼自認為民樂和西洋樂很經典的一段配合……央視版《水滸傳》插曲:注意聽41秒左右的嗩吶,讓人立刻汗毛豎立,當時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反了他孃的:
世界大同,音樂先行。
(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