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起,書寫俾斯麥船長與普魯士被湮沒的樂章(一)_風聞
余亮-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2018-07-23 15:45
【文/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餘亮】
何為俾斯麥,何為普魯士
**——“鐵與血”背後的精緻樂章(**一)
【世界盃德國隊早早回家,帶走無數粉絲的魂魄。然而德國人的靈魂早已無處安放,自二戰以來,戰敗的德國人就生活在勝利者的歷史敍述裏。近些年,一些西方媒體熱衷於將崛起中的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類比,釋放中國威脅論的幽靈。國內也有不少人喜歡做類似影射。隨意類比是無聊的,我所關心的是,那個被詛咒的德國,究竟被流行的歷史話語遮蔽了什麼?】
1847年,未來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一世的哥哥,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決定在柏林召集一個“聯合議會”,以便為其修建東部鐵路的計劃籌款。各等級議員匯聚首府,開始吵吵鬧鬧。
會議本身乏善可稱,但是一位叫做布勞希奇的平庸的地主議員,無意中做出了他這一生最偉大的舉動——生病告假。因此,坐在替補議員席上,此前籍籍無名的俾斯麥先生得以意外登場,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終成德意志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
在那之前,時人眼中的俾斯麥只是一個心猿意馬的地主之子,先後在軍隊、公務員隊伍、鄉村地主羣體裏百無聊賴混日子。在他輝煌之後,則因為“鐵血宰相”四個字被刻板印象包圍,與專制、強橫、好戰、兇狠等詞彙聯繫在一起。今天的人們看到他一身軍裝的照片,就彷彿嗅到血腥氣和火藥味,不由生厭。“血腥氣”也是威廉國王一開始對他的評價。即便今天,B站上喜歡高呼“德意志科技世界第一”的二次元們,恐怕也未必清楚這個短命帝國的歷史細節及其偉人人物的艱難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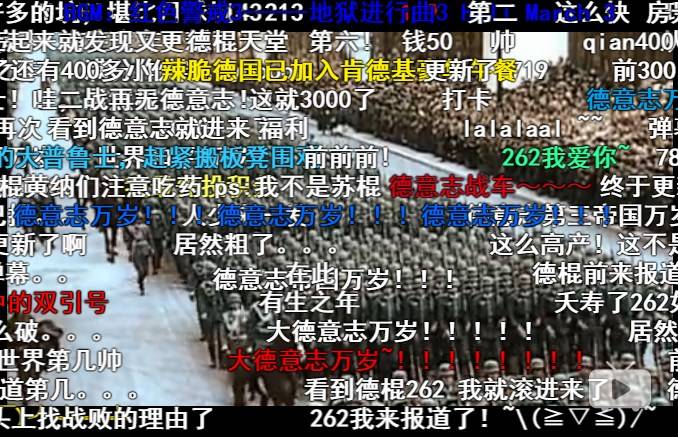
B站彈幕截圖
如果對比那個時代的政治家,我們總會下意識覺得拿破崙是青春的,俾斯麥是老邁的。除了畫像藝術與照片藝術的區別,還因為拿破崙被認為代表了啓蒙、自由、反封建的法蘭西精神,俾斯麥則被按上了強權和老舊政客的帽子。

拿破崙畫像

俾斯麥照片
實際上拿破崙兵敗滑鐵盧那一年,俾斯麥剛出生。在他出生前兩年,耳聾的同鄉貝多芬寫出了《戰爭交響曲》歌頌惠靈頓擊敗拿破崙。在他出生前三十年,康德已經在“專制”的普魯士首府柏林發表了著名文章《什麼是啓蒙》,號召普通人走出不成熟狀態,自己為自己做決定。俾斯麥自己,24歲做公務員的時候就説:“政府的人員像管絃樂隊的成員,但我只希望演奏我喜歡的樂章,否則我就什麼都不演奏。”説這話的俾斯麥好像康德附體。很快他就辭職了。
俾斯麥與海涅、叔本華、瓦格納、費爾巴哈乃至馬克思等著名思想家、藝術家是生活在同時代的人,他比瓦格納小兩歲,比馬克思大三歲。他的國王威廉一世,時常用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被資產階級起義民眾砍頭的事情提醒自己要謹慎從事,時刻願意對新階層表示尊重與關懷。所以某種意義上,俾斯麥與國王都是半新半舊之人,正是新舊之間的張力,讓他們用現代人日漸消逝的隱忍決斷和謀略藝術完成了新階層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情。

(俾斯麥與李鴻章:在中國,因為李鴻章曾被拿來比作東方俾斯麥,就更添加了俾斯麥的老派屬性)
看着俾斯麥蒼老的臉,我在想,這略嫌粗暴的面貌背後的歲月是什麼。今天很多年輕人都補過了《三體》的鈣——“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回望現實的近代歷史,在啓蒙、人道、自由、民主等好詞的背後,還有什麼在推動事物的發展?在鐵血、強權、陰謀等帽子背後,又有什麼難以言説的衷腸?
比俾斯麥年輕三十歲的尼采看出了一點,世界並非按照理性的概念和華麗的辭藻運作。但他找到的世界本質卻是純粹意志。這位身體的弱者,偏愛倡導超人意志,以為意志可以脱離實踐自我生長,俾斯麥一定會對他的鄉愿發笑。恩格斯也看到了俾斯麥的意志,認為當時德國統治階級已經失去意志,唯獨俾斯麥沒有失去。這是批判的語言,未必全是事實。難道一個階級會在沒落時分才出現自己的偉大人物?俾斯麥只是歷史的偶然而不可能是不滅的星火?俾斯麥與歷史條件的交織更值得品味。在那個風雲變幻、列強角逐的年代,俾斯麥和普魯士是怎麼做到後發制人,異軍突起的?這也是我開始對俾斯麥好奇的原因之一。
要了解俾斯麥,先要了解一下普魯士,另一個被誤解的角色。
普魯士究竟是什麼
普魯士,很多中國人對這個名字的印象恐怕來自初中語文課文《最後一課》。法蘭西的都德先生扮演了一個被欺凌民族的受害者角色。他們的國土被侵佔,語言被剝奪。罪魁禍首是普魯士,那似乎是一個陰沉的國家。之後,法國政府血腥鎮壓巴黎公社,也少不了普魯士做幫兇,更加深了這個印象。都德筆下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的法國人不忘祖國,正好契合了中國人的反殖精神和愛國主義。

不過在時人眼中,印象未必如此。當時的法國才是歐陸霸主,普魯士則是個初出茅廬的第五強國(在1815年的維也納和約中,普魯士排五強之末)。拿破崙軍隊侵佔普魯士的時候,費希特用長篇哲學演講來表達德意志愛國主義,比不了都德的法國小説寫法有煽動力。試想,如果普法戰爭法國勝利,破碎德國的藝術家又該怎樣書寫被欺凌者的聲音呢。
普魯士給人的印象似是而非。它是德國的一部分,卻不知道是從哪冒出來的,然後又不知不覺地消失,像是某種完成歷史穿越的道具而已。
普魯士的歷史確實不長,連國名都是撿來的。羅馬帝國解體後,在漫長的日耳曼民族縱橫史裏都沒有過這個名字。起初,短暫的法蘭克王國雄踞歐洲,很快分裂為三。東法蘭克王國居民以日耳曼人為主,逐漸演化為“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卻被內部的封建割據以及與羅馬教會的糾纏關係困擾不已,未能完成統一的、普世的帝國建構。到了15世紀已經積貧積弱,眼睜睜地看着國土兩側法國、俄國、西班牙等王權國家紛紛崛起,自身淪為列強的獵場,生靈塗炭。
普魯士本身則是德意志變奏曲主旋律之外的一個意外插曲。大約一千年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出於對領土的渴求、對異教徒的打擊願望和應對農業危機等因素的考慮,派出王公經營北方苦寒地帶的勃蘭登堡邊區。幾經繼承轉手,勃蘭登堡最終落入霍亨索倫家族手中。同時皇帝提倡反向殖民,鼓勵日耳曼人回到千年前的東北出發地,與斯拉夫人爭奪故土。於是教會背景的條頓騎士團東進,征服和統治了那裏較為落後的普魯士人——這個名字原本指稱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與波羅的海民族的混血族羣。他們説着日耳曼人聽不懂的雜糅方言。這塊地方被稱作東普魯士。
天高皇帝遠,條頓騎士團實行準共和制,體現出最初的理性國家面貌。騎士團中一個教團長是霍亨索倫家族遠親。一次聯姻和隨之而來的繼承,導致東普魯士與勃蘭登堡在1618年合併成一個侯國。普魯士這個名字也被新侯國借用了。因為勃蘭登堡公侯腓特烈三世想稱王,卻不敢在勃蘭登堡登基,畢竟勃蘭登堡還在神聖羅馬帝國傳統勢力範圍之內,要稱王就需要經過皇帝和各個王公的同意,成本太大。腓特烈聰明地跑到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登基,那裏之前還是波蘭王國的屬地,不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管轄。
於是在1701年1月18日,某個腓特烈搖身一變成為“在普魯士的國王”。普魯士國家就這麼瞞天過海誕生了,成為德意志境內諸多王國中的一個。可以説,普魯士國家的創立就已經體現出創業者在夾縫中求機會的性格特質。有實力,無名分,遮遮掩掩,不屈不撓,最終靠實力達成名實合一。
新生的普魯士始終處在國家安全的緊張焦慮中:
第一,領土分散狹長,堪稱歐洲的智利。而智利是連貫的,東普魯士和勃蘭登堡則是遠遠分開的。那時的歐洲戰火不斷。普魯士沒有縱深,隨時可能被敵人切成數段,現實中也不斷被北方的瑞典蹂躪。不前進,就會死亡。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定的歐洲版圖,注意勃蘭登堡與普魯士的相對位置。圖片來自烏爾夫·迪爾邁爾《德意志史》)
第二,人口稀少。到1713年也只有160萬人口。
第三,普魯士沒有神話也沒有歷史來維繫民族自豪感。沒有神話和歷史感的國家,是完全抽象的國家。所以它自己必須就是自己生存下去的理由。我猜想,這個自我循環自我維持的意識才是康德《什麼是啓蒙》誕生的土壤,也是康德式“啓蒙”所隱藏的國家理由。
為了把這個國家經營下去,統治者採取了不同於歐陸主流的治理方式。
在人口方面,為了吸引勞動力,政府廣納移民並採取宗教寬容政策。於是宗教戰爭年代的歐洲,各國被迫害教徒紛紛移民普魯士。新教徒、舊教徒、異教徒,在這裏都能夠相安無事。需要提及的一點是,柏林很多人口來自未來的宿敵法國,他們為普魯士殫精竭慮。
在國家治理方面,普魯士率先採用垂直的官僚機構,規範法律和紀律,通過“戰爭總署”實現高效的徵税以籌集軍費。同時期的歐陸多數國家還處於封建狀態,只能通過境內大小諸侯來進行統治,深陷於各種扯皮、鬥爭之中,效率低下。不要忘記,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能得到神聖羅馬帝國皇位,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家族最弱,而強橫的諸侯們只願意推選弱者來當皇帝,由此積貧積弱。
2011年,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裏盛讚中國早於西方兩千年建立了垂直高效的行政官僚機制。而普魯士則比一般西方早了幾百年。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佩裏·安德森認為,普魯士由於地主之間的貧富差距不大,相對平等,城市經濟不發達,腐敗相對較少,統治階層更團結,整個社會較為均質,由此便於發展行政官僚體系(見《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普魯士軍隊也率先現代化,強調常備軍的訓練和紀律,發明了列隊操練等先進軍事技術。軍隊是保證普魯士安全和擴張的首要條件。普魯士不斷在領土擴張中尋找安全,並最終把兩大塊國土連接起來。
著名的德國曆史書寫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納認為,普魯士是一個非常理性的國家,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維持這個國家機器的理性運轉,塑造力量之一是戰爭(參見《不含傳説的普魯士》)。每一個腓特烈國王都認為自己熱愛和平,每一個腓特烈都還是要通過戰爭來為本國贏得安全。腓特烈大帝自是一代名將,他的先祖早已孜孜以求於獲得領土空間。三十年戰爭(1618—1648)、法國荷蘭戰爭(1672-1678),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奧地利王位繼承戰(1740-1748),七年戰爭(1756—1763)……最不被看好的新國家堅韌不拔,險中求勝,屢次面臨亡國危險,卻每每絕處逢生,就像膽大妄為又工於算計的企業家一樣,每次都獲得了最大收益。(如果有機會,我再闡述普魯士和德國的創業史。)
軍事只是一面。這樣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國家,較早接納人文主義和啓蒙主義的影響,誕生了不少文化名人。經濟改革、義務教育法等都在這裏率先推行。普魯士在後世被法國啓蒙運動和大革命光芒掩蓋,其實在法蘭西共和國建立之前,時人眼中普魯士更符合啓蒙主義現代國家的理想,具有法治、理性、效率和較高程度的形式平等,堪稱當時歐洲的理想國。弗里德里希大王(通常被譯作腓特烈大帝,但他不是皇帝)更是經常和伏爾泰先生通信討論人權、和平以及腓特烈的論文,不過最終對文人的散漫蹈虛產生了厭惡。

無憂宮裏的伏爾泰與腓特烈
最近,中國在開展大規模紀念馬克思的活動。可惜,我在各種相關文章、節目裏但凡看到提及普魯士,一概稱做“專制的普魯士”。青年馬克思以在報刊上批判普魯士專制而偉大,但是後人一味延用馬克思的話則只是一種偷懶。對普魯士的僵化印象本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畢竟,那麼多專制國家並沒有能誕生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普魯士產生了那個條件。
我們最好把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法治、專制、議會、傳媒、戰爭、工業、農業等等互相沖突的要素看作普魯士乃至歐洲內在矛盾綜合體。割裂和對立式的認識,正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裏所極盡嘲諷批判的,無法認識事物的全貌和根本動力所在。普魯士的進步性顯而易見,當然也包含了落後因素。佩裏·安德森認為普魯士綜合了德意志南北經濟、文化、政治差異,擁有最多的矛盾性和發展潛力。
而當時的德意志正處在迷茫中,地處歐陸中央,列強環伺,地緣政治環境複雜,自身內部大大小小封建王國和自由商業城市林立,經濟社會屢遭戰爭破壞。教會與世俗權力相愛相殺,宗教衝突無處不在。皇室哈布斯堡家族只顧經營自己的領地,無視德意志利益,無法建立已經在英、法、西、俄建立的統一王權。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空有名號,卻“既不神聖,也不羅馬”(伏爾泰語)。到了1830年,歌德還憂鬱地説道:“沒有一個城市,甚至沒有一塊地方使我們堅定地指出:這就是德國。如果我們在維也納這樣問,答案是:這裏是奧地利。如果我們在柏林提出這個問題,答案是:這裏是普魯士。”
1806年,拿破崙軍隊在耶拿戰役中擊碎了普魯士的自尊,曾經的啓蒙國家在法國新式國民軍面前不堪一擊。柏林和維也納被攻佔,神聖羅馬帝國被消滅,德意志人陷入既屈辱又羨慕的狀況中,普遍的心態是:“我們不能再次被法國羞辱,但我們必須成為法國那樣”。民族主義高漲,普魯士的改革派得以施展手腳。模仿拿破崙法典的普魯士法典頒佈,之前被延宕的改革在各領域展開,當然,並不徹底。有趣的是,改革人才大多來自文化更先進的德意志西部。
1815年,反法聯盟徹底擊敗拿破崙,普魯士改革也就放慢了腳步。在維也納和約中,普魯士獲得了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地區。當時那裏的豐富礦產還未被發現,無人知道未來會發展為魯爾鋼鐵工業區,也成為俾斯麥説出“鐵和血”這句話的底氣。
拿破崙死了,但民族主義和改革風潮不會被消滅。德意志人把目光投向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大強國,由誰來統一德國並建立現代國家,現在提上了歷史日程。
德意志是民族國家的遲到者。俾斯麥在1868年説過:“德國若還能夠在19世紀達成自己的民族目標,那在我眼中將是難能可貴的事情。”要締造這個奇蹟,哈夫納認為,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最缺乏的是外交保障和作戰意願,只有一個人為他們補足了這兩部分。
就在拿破崙的落幕聲中,這個人出生了。(待續)

本文系觀察者網風聞社區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