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美中的性別想象:純粹的男性之愛,抑或強化的權力關係?_風聞
000000000000-不以美貌动天下,但以风骚惊世人 的番老板2018-07-28 16:20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作者:王婧如
7月25日,《鎮魂》收官,累計至結局,播放量已突破26億,社交網絡也紛紛被“鎮魂女孩”刷屏。這部由在晉江文學城連載的耽美文改編而成的劇作,迫於題材的敏感,將兩位男主之間的愛情改為兄弟情。雖然特效製作簡陋、配角演技尷尬,但因為主演對於原著中的曖昧情感還原得當,該劇還是收穫了許多原著粉絲和女性粉絲的喜愛。如今,在互聯網流量思維和商業邏輯的介入下,耽美圈內的有名作品正成為一個又一個待商業開發的網文IP:不管是已結束的《鎮魂》,還是正在熱映的由耽美名作《魔道祖師》改編的同名動畫,在微博話題榜單上,熱度均居高不下。耽美及其改編作品已然是一類重要的網絡文化現象。
那麼,什麼是耽美?熟悉網絡語言的人並不陌生,不熟悉者則對此有不少誤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網絡文化研究團隊編寫的網絡文化關鍵詞合集《破壁書》中,“耽美”一詞被解釋為女性作者寫作的、以女性慾望為導向的、主要關於男性同性之間的愛情或情色故事,一般在流行文化領域內流通。耽美屬於“女性向”文化,其女性受眾羣體一般被稱為“腐女”。然而,在流行文化領域,“腐女”的目光並不只停留在耽美作品本身,比如前些年熱播的電視劇《偽裝者》、《琅琊榜》,腐女們熱衷於討論明樓與明誠、梅長蘇與靖王這些男主角之間超越普通友情的曖昧情感。
有趣的是,在對喜愛的男性角色之間的感情進行想象時,腐女們常需要在兩個男性之間劃分與男女性別模式相近的攻受關係。這一關係也是耽美寫作的基礎,一般根據二者在性行為中的關係而劃分,最早在日本女性的寫作中誕生。“攻”可理解為角色男性化的一方,“受”則是女性化的一方,其區分附帶着一系列模式化的行為特徵。但是,真實的寫作並不只侷限於此,如《破壁書》所指出,“本質上,攻和受的性質和表現可以在雙方間自由流動和交換”。以《鎮魂》為例,儒雅的大學教授沈巍在原著中的定位是“温柔內斂美人攻”,留着鬍子看似粗獷的警察趙雲瀾則是“暴躁精分受”,他們的形象並不遵循男性化一方要強硬,女性化一方要温柔的傳統性別模式,卻因性格反差而帶給讀者閲讀的新鮮感和快感。

網劇《鎮魂》劇照,左為趙雲瀾,右為沈巍。
正是因為攻受氣質的不同組合,情感表達在耽美寫作中拓展了豐富且多樣的可能,並因之而勝於傳統的言情書寫,獲得了女性受眾的青睞。對於男性在攻受關係中表現出的多樣化性別氣質的接納,似乎慢慢成為腐女這一羣體具備性別自主意識的例證,並且被納入了女性主義學術討論的目光。網絡文化研究者肖映萱,便在其《“女性向”性別實驗:以耽美為例》的研究論文中指出,“‘女性向’網絡文學進行的種種以耽美為代表的性別實驗,通過‘攻受’等設定,破除了關於‘男人’和‘女人’的刻板印象,顛覆了固有的性別秩序”。但是,對男性之間情感的另類書寫,可以作為女性主義意識覺醒的一種表現嗎?攻受關係模式在在哪些方面勝於傳統言情,滿足了腐女羣體的想象?這些想象又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為對既有的異性戀愛模式和男女關係框架的顛覆?
唯美主義:
更加純粹的男性之愛?
在談論攻受關係之前,有必要先回顧耽美文化的發展脈絡。耽美並非中國青年亞文化的孤例,它所指的文學和文化現象,在日語、英語中分別稱為BL(日式英語“boys love”的縮寫)、slash(斜線小説)。中文的“耽美”一詞源自英文詞aestheticism的日語譯名,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行於歐洲文壇的唯美主義文學。在70年代的日本,因描繪男性少年間愛情的漫畫多追求唯美風格,“耽美”一詞被出版商短期地用於指代日本流行的BL小説類型,傳到中國後,成為這個文類在中國的最常用名稱。在《破壁書》的記敍中,耽美文化最早由日本傳到台灣和香港,之後,以地下渠道的方式傳入大陸。當年,一部結局悲慘且帶有虐戀情節的漫畫《絕愛1989》,是影響了一代中國同人女審美和敍事的名作。
因此,唯美主義傾向奠定了早期耽美創作的基本座標。正如耽美流行初期,在女性受眾的圈子裏廣泛流傳的一句話,“世上最精彩的男孩我肯定得不到,那麼我也不希望其他女孩得到,不如就讓他們自己永遠在一起吧”,多少可以説明女孩子們對於美好男性和美好感情的執念。這份唯美的執念,在既有的異性戀模式的書寫中很難獲得滿足,因為王子公主的幸福結局往往是結婚生子,同性之間的戀愛終點卻可不止於此。無法繁衍子嗣,在傳統敍事中是批駁同性戀情不符人倫、應以禁止的重要依據,但在腐女看來,則是感情純粹性的保證。男男之間的愛情,鬆綁了性別身份帶來的刻板印象,排除了如男女對愛情的理解不一致、在愛情中的需求不一致的論調,使愛情的催動只依賴個性差異碰撞而來的火花,基於個體之間的感受,成為了判斷相愛與否的唯一標準。同時,在創作和閲讀耽美的過程中,女性不大會質疑男男愛情故事中的不真實性,也不會為自身性別在異性戀愛關係中的弱勢而糾結。她們在一個與故事保持着一定距離的安全區內,欣賞美貌男性之間的愛恨糾纏。這種距離,或者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腐女沉湎耽美的同時,真正的男同性戀羣體中往往不歡迎這些描寫,並斥責它們不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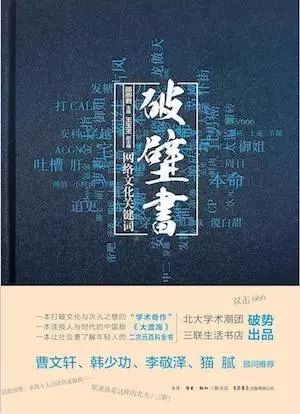
對愛的唯美主義式追求,同時貫徹在了耽美對戀愛雙方的社會身份設定中。耽美寫作者戎葵,在談到為什麼寫這一題材時,説法是,耽美小説中,主人公可以同時參與感情和參與歷史,言情小説的女主角卻只能參與感情。毛尖在《資產階級二代的美學語法》中對此的解釋為,耽美小説的主角相比普通言情,身份設定往往更加高貴。比如,在大量耽美現代文中,不少霸道攻是軍人後代,或者家族生意是房地產這些重鎮;在耽美仙俠中,主角地位常常是“上仙”“上族”角色,一舉一動關涉着整個族羣的命運,這些設定加上耽美書寫中特有的細膩唯美的修辭方式,將現實的國家、產業、道德審美化,“以這種方式……宣告未來的烏托邦只受感情的統治,而在這個烏托邦裏,霸道總攻通過把所有的話語變成審美話語,他們便愉快又便捷地掌控了所有的話語權”。在這一層面上,耽美的唯美主義追求既化解了腐女對於現實生活中男女關係不平等的某種不滿心理,也通過設定更高貴的主角身份、構建更宏大的現實背景去迎合腐女們對純粹且至高無上之愛的想象。
攻受關係:
無法逃脱的性別想象?
耽美作品中看似凌駕於性別特質之上的唯美主義傾向,在一開始便與同志文學與現實同志情感的沉重背道而馳,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女性創作者和閲讀者對於攻受關係想象的侷限。正如耽美文中同時能夠參與歷史和感情的人,以霸道總攻這一男性氣質的強勢展現者佔據多數。研究者肖映萱曾總結大陸原創耽美的攻受模式變遷,**自1998年最早的一批耽美作者開始寫作以來,大體經歷了從“強攻弱受”,到“強攻強受”,再到“美攻強受”的轉變。**在這一轉變歷程中,“強攻”始終佔主導。但她同時把“美攻強受”模式作為對以往耽美書寫中對男女性別模式不成熟模仿的突破,視之為耽美寫作的性別實驗場,並以2016年的《魔道祖師》作為這一階段的成熟代表作加以論證。“美攻”這一氣質的出現,調合了過於強勢的男性氣質,確實有助於性別表達的多元化。
但是,攻受關係的多元想象並不能等同於性別氣質的多樣表達,更關鍵的,是攻受模式與現實性別秩序之間的關聯。《魔道祖師》中不同於以往“強攻”設定的“美攻”藍忘機,儘管不具備攻這一角色常有的典型強勢和主動形象,在小説所建構的客觀世界中依然處在極高的社會地位之上,擁有着令人豔羨的能力、財富和聲望。《鎮魂》中同樣具備“美攻”氣質的沈巍,作為地獄斬魂史,能力超絕但堅定地守護着愛人。這或許可説明,儘管耽美文學在發展中賦予了“受”這一角色更多元的氣質,但“攻”佔據優勢地位這一點卻並無改變。攻受關係的闡釋,在排除了生理性別差異的影響後,一定程度上仍反映着現實社會生活中男女關係的經驗,難以突破現實性別秩序的潛在規約。比如,現實中普遍認為在婚戀中男性應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優於女性。

網劇《鎮魂》劇照,左為趙雲瀾,右為沈巍。
現實性別秩序對攻受關係想象的深刻影響,亦表現在特定文化語境下攻受關係的區分上。《破壁書》指出,“在東亞耽美愛好者的粉絲圈中,攻受區分被貫徹得非常徹底”,而英語圈的“耽美”Slash就沒有如此嚴格的區分。關係區分的嚴格有多種表現,比如,當討論中出現A✖️B的時候,代表着A是攻,B是受,B✖️A則代表B攻A受,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感模式,排列順序因此不可逆轉。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攻受關係組合相對現實男女關係的多樣化,卻也潛在地標明攻受身份的穩定性。換言之,攻可以有多種氣質表現,但一旦某一氣質表現被設定為攻,在性關係中便必須表現出霸道和主動,這一基本的秩序是不能被顛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強化的。同樣是《魔道祖師》,“美攻”藍忘機温柔沉穩,“強受”魏無羨行為乖張、無所顧忌,但在性關係中,藍忘機的表現被形容為“粗魯”“惡狠狠”,魏無羨則是“迷迷糊糊”“討好”“毫無尊嚴”。更關鍵的是,這樣的一種攻和受分別帶有“性虐愛好者”和“受虐愛好者”特點的敍述模式,在耽美的性描寫中十分常見,甚至在早期,對被虐一方的性感受,往往從被迫、不情願轉變為獲得強烈愉悦。比如,2004年的耽美大作《鳳於九天》,便不乏“攻”容恬對“受”鳳鳴的性侵犯,書的第四章有這樣的描寫“鳳鳴悲哀自己的命運,又知道自己現在的身體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火熱的感覺在口腔內此起彼伏,酥麻和快感交織起來……”。

《魔道祖師》劇照,左為藍忘機,右為魏無羨。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向”文學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們對於女性性慾望的滿足,而在這一點上,相比傳統言情的規矩,耽美文中性書寫的開放更能滿足女性的多樣化需求,體現了女性對於男性的主動觀看和想象。也因此,耽美在一開始便與女性對男同性戀羣體的理解無關,而與對自身慾望的認知相關。耽美寫作中對於“施虐”與“受虐”的區分和描繪,某種程度上意味着,在性關係這一區分攻受的基本標準中,女性寫作者和閲讀者表現出了在性關係中建構權力秩序的偏好。戴錦華在《後革命的幽靈》的演講中,亦曾論説了在中國的耽美文學的主流寫作當中,攻與受的關係確認清晰明確,恰恰意味着,青年女性們在耽美的寫作和閲讀中表現出的“一種強烈的權力意識和權力自覺”,也就是“在更換了愛情故事或情慾關係的性別身份之後,這一亞文化中的小説創作不是剝離了,而是凸顯甚至強化了的權力和等級階序”。更具體而言,現實性別秩序對攻受關係想象的影響,不在於腐女們是否代入攻受角色或者代入攻受角色的哪一方,而在於,她們仍然需要通過攻受區分去想象一份情感,且很有可能會在這份想象中建構“施虐者”與“受虐者”的形象,以期通過對性關係中的不平等狀況的觀看或代入,去實現快感。
然而,隨着文化工業對於網文IP的介入和改造,現實性別秩序的滲透不再只是存在於耽美創作內部了。當這些作品走出因趣緣結成的小羣體,進入大眾主流視野時,其寫作成果也在不斷地被蠶食。文章開頭,《鎮魂》中的兄弟情改造是一例,而在《魔道祖師》被改編成電視劇《陳情令》的過程中,因編劇添加了兩位男主同時喜歡上一位女孩的情節,原著粉絲紛紛通過微博等更具公共性的平台表示反對,使這部劇作在拍攝過程中便已登上了多次微博熱搜。這些被資本收編的耽美製作,被重新置於異性戀言情故事的框架中,性別想象的空間日趨狹小。
參考資料:
邵燕君 主編 、王玉玊 副主編,《破壁書:網絡文化關鍵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6月。
毛尖,《資產階級二代的美學語法》,《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3期。
肖映萱,《“女性向”性別實驗:以耽美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8期。
戴錦華,《後革命的幽靈》,微信公眾號“海螺社區”,20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