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湯普森與“理論的危機”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8-08-21 13:18
冷戰的結束無疑宣告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潮,但它至少使我們有餘裕來重新思考這場影響深遠的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並與各種傳統碰撞、對話,對今日世界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梳理、反思上世紀以來經典的和“異端”的左翼思想,其重要性至少不亞於對新思潮的關注。作為英國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E.P.湯普森的思想中對於文學的政治作用的關注,對現實運動而非種種圖示的重視,以及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他身上曖昧地結合而產生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這些既是英國的思想家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可以看作上述碰撞的表徵。新西蘭學者斯科特•漢密爾頓所著的《理論的危機:E.P. 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後英國政治》一書聚焦E.P.湯普森的重要著作《理論的貧困》,“意在通過將《理論的貧困》的文本放歸到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和傳記的語境”當中,來試圖理解湯普森身上的矛盾。該書對我們開展一些不甚“前沿”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保馬今日推薦這本著作,希望有助於我們認識英國馬克思主義這一重要傳統。本期推送內容共三篇,分別為《理論的危機》的前言、結語和該書書訊。題目為保馬所加。
本書已於今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譯者程祥鈺。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程老師授權保馬刊載相關內容。
理論的危機:E.P. 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後英國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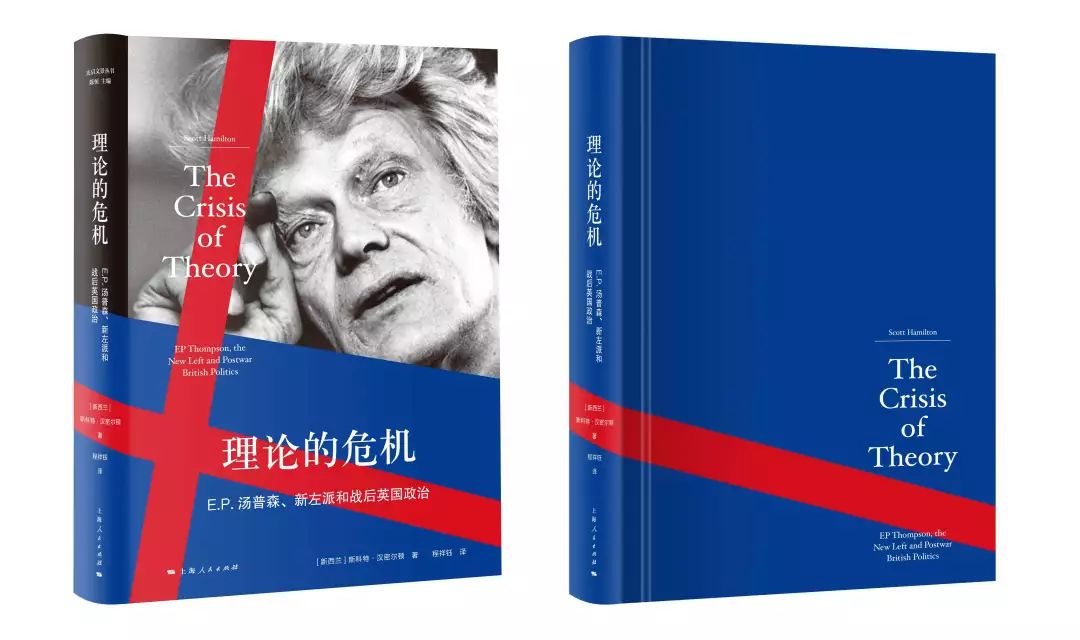
引 言
E.P. 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是一個充滿熱情、學識淵博的人。他的學術研究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他寫糧食暴動和研究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手稿一樣遊刃有餘,對蘇聯的着迷程度絲毫不亞於對華茲華斯(Wordsworth)。湯普森因其研究18 、19 世紀英國的著作而聞名於世;而在生涯晚期,他又嫺熟地深入研究了巴爾幹地區和印度的20 世紀曆史。至少到1960 年代為止,湯普森一直認為自己主要是一個詩人,他的文學遺產包括了大量詩歌,一些短篇故事,以及一篇科幻小説。
湯普森既是一位學者,又是一位實幹家。無論身處象牙塔內還是象牙塔外,他都充滿自信。湯普森的政治生涯開始於1930 年代後期,當時他由於為英國共產黨做宣傳,幾乎被所在的衞理公會寄宿學校開除。他在“二戰”期間率領一隊坦克登上亞平寧半島,也將英共反納粹的修辭轉變成了真實的行動。1956 年脱離英共之後,湯普森成了第一代新左派中的公眾人物。新左派運動是一場短暫而充滿活力的運動,它對冷戰雙方的正統政治觀念都提出了質疑。1980 年代早期,湯普森又作為在英國復興的反核運動中最雄辯的領導者而為年輕一代所熟知。湯普森的行動總是包含寫作、演講和抗議。
學者們常常傾向於用一種“篩選”的方式來研究湯普森——選取他事業中的某一方面加以討論,而不涉及其他方面。湯普森本人不會欣賞用這種方式來看待他的一生和事業。他認為他全部的活動和寫作是有機相連的,並且不止一次地拒絕“專攻”其中任一領域。在1950 年代早期,湯普森拒絕深陷黨政活動的日常業務,轉而一頭扎進對威廉·莫里斯和19 世紀的研究。1970 年代初,湯普森為了拒絕終身教職的誘惑不惜從華威大學辭職。1[1] 儘管缺少鼓勵,有時甚至是受到勸阻,湯普森一生都在堅持着自己的文學事業,始終把自己視作一個詩人。
這本書考察了湯普森生活和事業的不同方面,並將它們聯繫起來。我認為這些個方方面面被湯普森年輕時代採納的一系列信念連成一體,儘管之間略有齟齬。這些信念形成於1936 年到1946 年之間,湯普森稱這一時期為“英雄的十年”。這一願景俘獲了湯普森,並將引導他直到1970 年代末的全部事業,且將持續影響他直至生命終點。湯普森的事業與他的願景相統一,但也包含着矛盾。事實上,湯普森的許多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將其年輕時代的信念與20 世紀下半葉的事件和理念聯繫到一起的嘗試。湯普森的嘗試最終並未成功,但卻激勵他寫出了自己最優秀的著作。
這本書可以被看作一次思想史或知識社會學的實踐。[2]我們不僅將思考湯普森的觀念和主張,還將探尋他何以採納這些觀念和給出這些主張。我們勢必將在湯普森的傳記、其身處時代的社會史與政治史,以及他的著作之間穿行。當我們回顧湯普森非凡的一生時,我們會發現它打開了觀察20 世紀英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生活的一串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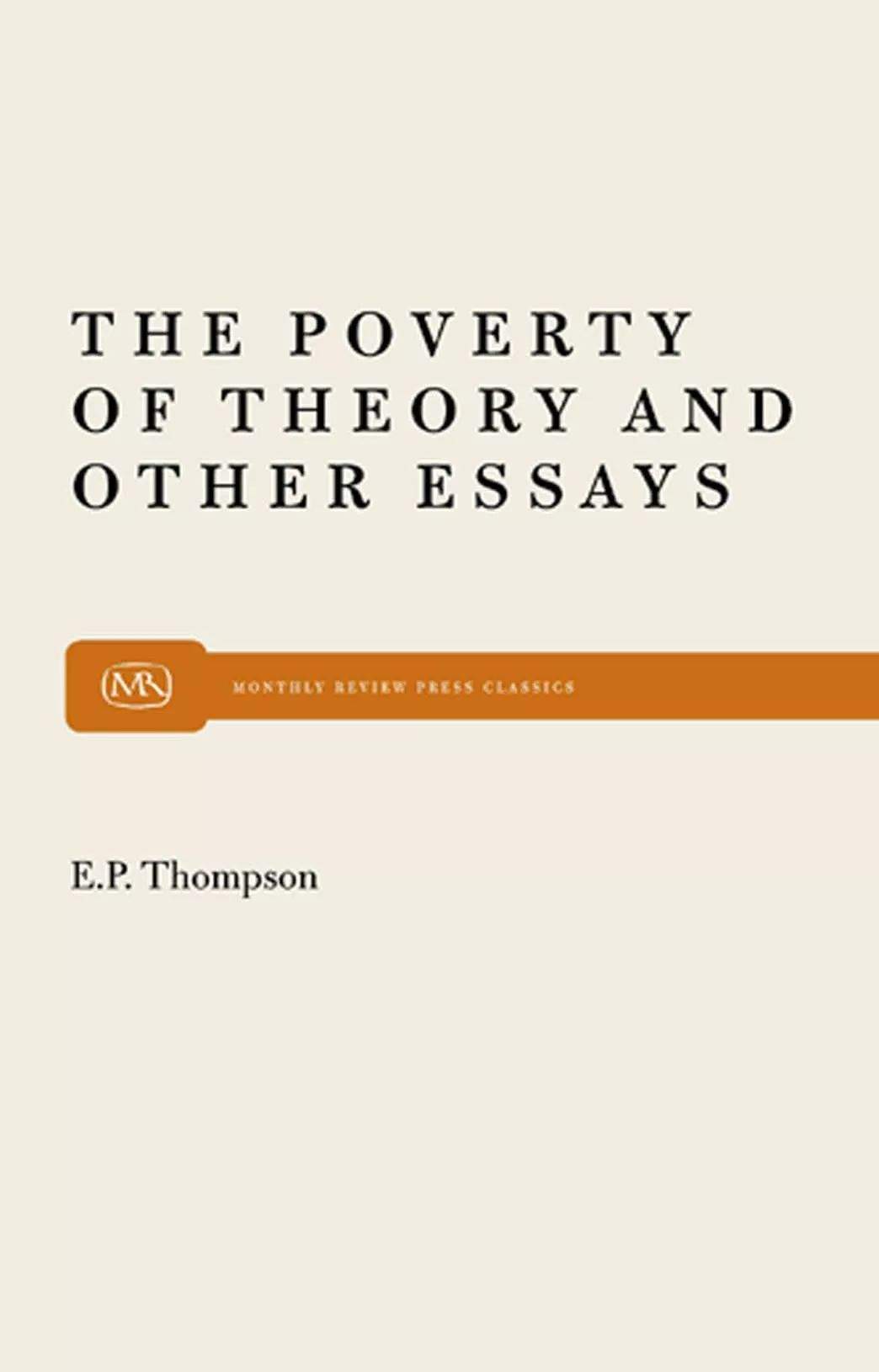
我們將用湯普森1978 年的書《理論的貧困及其他文章》(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來聚焦問題。[3]這本書之所以特別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它的寫作跨越了將近20 年,這其中包括了湯普森人生中最為重要的一些年份。書中最早的文章《在鯨腹外》(‘Outside the Whale’)寫於1959 年,當時早期新左派運動正處於頂點,那時的湯普森似乎夢想着激進的政治文化變革能夠被實現。那篇長長的、飽含激憤的結論文章則寫於1978 年,當時湯普森幾乎要放棄所有實現其夢想的希望了,而這一夢想自青年時代便支撐着他。
另一方面,《理論的貧困及其他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的文本彙集了湯普森的諸多關注點,以及他的多種寫作方式:討論奧登(W.H. Auden)的詩歌和斯大林的馬克思學,討論入侵匈牙利事件和達爾文的事業——這些文章或極具論辯色彩,或頗有學術氣質,或急切,或深沉,或類乎自傳,或身在事外。
在本書第一部分中,我們將探討湯普森的家庭和社會背景,以及那些有助於決定其未來人生道路的早期經歷。在第二部分中,我們將考察湯普森在英國新左派運動中度過的那段動盪歲月,並觀察他政治上的挫折如何轉變成為學術上的成就。第三部分則將跟隨湯普森經歷關鍵性的1970 年代,考察其政治思想的危機如何將他逼入幾近絕望的境地,但又同時激勵他用高度創新的方法進行思考。本書第四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關注的是湯普森最後的歲月,他在晚年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聲譽,也承受着智力的衰退。我在全書的結論部分提出,湯普森政治上和知識分子意義上的失敗是與他的成功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的失敗與成功都使之成為對21 世紀有着極為重要意義的人物。
本書的研究開始於2002 年中期,當時成千上萬的抗議者走上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街頭,抗議一場由中情局幕後支持的顛覆左翼政府的政變。我在2003 年初寫下了第一份略顯笨拙的章節草稿,當時英美軍隊正聚集在伊拉克南部邊境,而反戰抗議人羣也正走上世界各地的街頭。當我在2009 年完成書稿的修訂時,一場八十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了像冰島和斐濟這樣相互迥異且相距萬里的眾多國家。中東地區的新殖民戰爭景象,社會主義理念在一些南美國家的新近流行,金融市場的混亂,所有這些都在削弱一種信心:美國式資本主義優於任何可能的對手。這種論調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年中非常流行。這本書可以説是對一個卒於1993 年的人的研究,但它的主題和論點不可避免地受到了21 世紀全球世界的影響。
當我閲讀湯普森的著作時,我不斷地強烈感受到他的關切所在與我們自身時代的關聯。當我讀到湯普森譴責右翼“現代化理論”在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對第三世界造成的影響時,我想到了當今的反對全球化運動對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團體背後的意識形態的控訴。當我讀到湯普森對1970 年代英國政府的陪審團制度的抨擊時,我便知道,在“反恐戰爭”的時代,他會如何看待發生在英國土地上的削減公民自由的現象。當我思考湯普森的大量反對美蘇在冷戰期間在歐洲部署核武器的文章時,我想起美國和俄羅斯的新一代領導人正忙於在東歐和中亞進行軍備競賽。像奧登和華茲華斯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對左翼的幻想破滅後便成為了權力和特權的代言人,但湯普森仍然會兼具同情心和批判性地去對待他們。聯繫到當下的“迴歸派馬克思主義者”(‘recovering Marxists’),如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大衞·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和諾曼·吉拉斯(Norman Geras)等人,對帝國主義在中東的軍事冒險行動的支持,便可知湯普森的這一態度在今天依然會意義深遠。湯普森對庸俗主義興起的再三憂慮,以及認為詩歌對人類進步的重要意義可與經濟等同的信念,在一個文學和藝術被市場和大眾媒介當作商品(而非思想與論爭之機緣)而獲得繁榮和被消費的時代,更是顯得前所未有地關乎宏旨。

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 2.4 - 1993.8.28)
使得湯普森在今天依然有意義的不僅僅是他的關切。年輕時的湯普森為抗議斯大林主義的暴行而離開了相對安逸的英國共產黨。面對遠離絕大多數激進工人,缺乏確定的政黨路線指導的情形,湯普森只能將各式各樣的、常常支離破碎的資源整合成一種新的、切實可行的左翼政治。威廉·布萊克的詩歌、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烏托邦、東歐異議者轉瞬即逝的文字,以及早期英國工人運動中的英雄們,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例子。湯普森轉向這些資源來努力尋找一種能夠實現其價值觀的政治,這種價值觀是他年輕時從身為激進自由派的父親和身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哥哥那裏學到的。
在我看來,21 世紀的每一位社會主義者都面臨着年輕的E.P. 湯普森在1956 年主動選擇的那種困境。1989 年到1991 年之間蘇聯及其附庸國的垮台,以及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向被稱作“第三條道路”的新自由主義的退卻,都意味着舊式的左翼正統資源已經消失殆盡。對於在普京和布萊爾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而言,宣揚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甚至宣稱通過社會民主主義必定可以改善資本主義最為糟糕的特徵,聽上去都十分荒謬。過去那種認為社會主義能夠極大地增加這個星球的工業產量從而拯救人類的傳統信念,在新的一代人眼中更像是一種時代的錯誤。他們感受到的危機來自全球變暖、過度砍伐以及其他工業主義的副作用。和湯普森一樣,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們被迫在形形色色的領域探尋新的方案來替代斯大林主義和舊式社會民主主義的教條。
在2005 年赴英研究時,我深入研究了湯普森的老同志約翰·薩維爾的許多文章,並且發現了大量未公開發表的相關文本。[4] 但我是在奧特亞羅瓦(或者説新西蘭)[5]寫下這本書的,因此這本書毫無疑問受到了南太平洋的歷史與文化的影響,這裏遠離現代世界的政治與經濟權力中心。南太平洋對我而言是書寫E.P. 湯普森的好地方,因為它使我對湯普森所擁有並擁護的那種傳統的複雜性保持一種批判性的警惕。在奧特亞羅瓦,以及其他南太平洋的社會中——例如湯加——知識分子面臨的挑戰是調和歐洲的觀念與古老的、錯綜複雜的本土知識分子傳統。很多理念和實踐在歐洲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在那裏它們彷彿是“自然的”、毋庸置疑的,但在這裏,它們必須作出調整,並證明自身的合理性。
我們同樣可以認為,許多南太平洋社會的社會學研究可以與湯普森最重要的關注點之一直接相聯繫。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序言中提到,對於“世界大部分地區”而言,工業化以及與之相伴的災難與變革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而不是一種歷史記憶。湯普森是在1963 年寫下這些話的,但他的觀察仍然適用於今天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這其中也包括南太平洋的許多地區,在這裏一種以土地集體所有和集體勞動為基礎的波利尼西亞生產模式(Polynesian mode of production)正與舶來的資本主義不穩定地共存着。
湯普森自己總會被邊緣地帶及其人民所吸引。他在倫敦、紐約這樣的大都市和權力中心會覺得不自在,因而選擇生活在哈里法克斯、伍斯特、匹茲堡這種單調乏味的省級城市。身處現代世界危險邊緣的民眾,如19 世紀早期西賴丁地區工廠裏的工人們,或1970 年代被英迪拉·甘地政府冷酷的技術官僚們侵佔土地的印度農民們,他們的遭遇總是吸引着作為學者的湯普森。
激發湯普森對邊緣民眾和社會的興趣的遠不僅僅是同情。就像馬克思在最後十年中那樣,湯普森同樣相信,正是在資本主義的邊緣,才有可能發現某種針對這一體系的最強有力的替代物。因此,他一定不會感到奇怪,21 世紀第一波大規模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出現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這類“半發達”南美國家。而若想避免重蹈20 世紀的覆轍,21 世紀的社會主義者需要從E.P. 湯普森這裏學習很多東西。
註釋
[1] 大衞·蒙哥馬利對此有很好的見解。在描述了湯普森與共產黨和與學院之間的緊張關係後,他指出,湯普森“拒絕做一個一邊在體制內謀生一邊又憤世嫉俗地譴責體制之虛偽的人”。見David Montgomery,‘Across the Atlantic’,Labour History Review,59,1,Spring 1994,p.5 。
[2] 我將這兩個子學科看作是連貫相通的。
[3]《理論的貧困及其他文章》收錄有《在鯨腹外》《英國人的獨特性》《致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開信》《理論的貧困》四篇文章。每月評論出版社同步發行了該書的美國版,其中文章順序有所變動,標題文章《理論的貧困》出現在第一篇的位置。在1978 年的英國版中,《理論的貧困》位於第193—406 頁。1995 年梅林出版社再版了《理論的貧困》,但不再包含其他三篇文章。除另有特別註明,我在本書中提到《理論的貧困》一文時,參考的都是1978 年版。
[4] 我在讀完薩維爾的自傳(John Saville,Memoirs from the Left,Merlin Books,Monmouth,2004 )後開始搜尋湯普森的未發表文章。薩維爾在書中提到湯普森寫給他的信保存在自己的文件資料中,並交給了赫爾城的布林莫爾·瓊斯圖書館,還提到湯普森本人的文件資料藏於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博德利圖書館的資料未能得見,但薩維爾的資料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未公開發表的湯普森手稿,以及大量的信件和來自第三方的與湯普森有關的有趣素材。除了薩維爾的文件之外,還有一些能找到湯普森未發表著述的可用資源。彼得·西爾比和安迪·克羅夫特各自對利茲大學的校外非全日制教學部門的檔案進行了研究。湯普森擔任西賴丁地區工人教育協會的流動導師長達15 年,其間都是以該部門為基地。參見Peter Searby and the Editors,‘Edward Thompson as a Teacher: Yorkshire and Warwick’,in Protest and Survival,The New Press,New York,1993,pp.1—24 以及Andy Croft,‘Walthamstow,Little Gidding and Middlesbrough: Edward Thompson the Literature Tutor’,in Beyond the Walls: 50 Years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ed. Richard Taylor,University of Leeds,Leeds,1996,pp.144—156 。邁克爾·肯尼在寫他關於第一代英國新左派的權威研究時,從華威大學當代檔案中心保存的湯普森的老同志勞倫斯·戴利的文件中發掘了一些有用的未發表的文字。見Michael Kenny,The First New Left: 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Lawrence and Wishart,London,1995 。2007 年,卡雷·戴維斯,一位謝菲爾德大學的研究生,在曼徹斯特工人階級歷史博物館的英國共產黨檔案中發現了超過20 份的由湯普森所寫的或關於湯普森的文獻。在湯普森退黨之後,英共有時會派間諜監視湯普森的政治活動。戴維斯的發現中包括了對湯普森在各種政治會議和集會上露面的詳細彙報,這些彙報都是在倫敦各個大廳的後排角落裏,伴着颼颼冷風潦草記下的。
[5] 奧特亞羅瓦(Aotearoa),是毛利語中新西蘭的名稱,意為“白雲綿延的土地”。原文中作者用“Aotearoa / New Zealand ”的寫法,下文不再刻意指出,遵照作者的用意,譯為“奧特亞羅瓦”。——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