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革命與綠色革命,社會主義中國如何科學種田?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8-08-24 14:58
易蓮媛 | 紅色革命與綠色革命
**【編者按】**當世界各地都在尋找人類社會的未來出路時,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也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點,而本文所提及的《紅色革命與綠色革命: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種田”》一書也正是如此。本文作者易蓮媛老師認為該書的問題意識在兩個層面上展開:從研究對象來説,是在作為美國“冷戰”策略之一的“綠色革命”的對照之下,重新梳理“紅色革命”毛澤東時代的“科學種田”運動;從理論反思來説,是由此探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科學”與“政治”的關係,質疑了“什麼是科學”,“什麼是科學權威”以及“農業應當如何發展”的主流觀念。該書作者認為,較之美國“綠色革命”的目的在於試圖用這些力量來消滅社會革命,而中國提出的“科學種田”運動則是將紅色革命與科學、技術結合起來,從觀念與實踐上成為推進社會繼續革命的工具。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華南農村研究中心”,由作者易蓮媛老師授權推送,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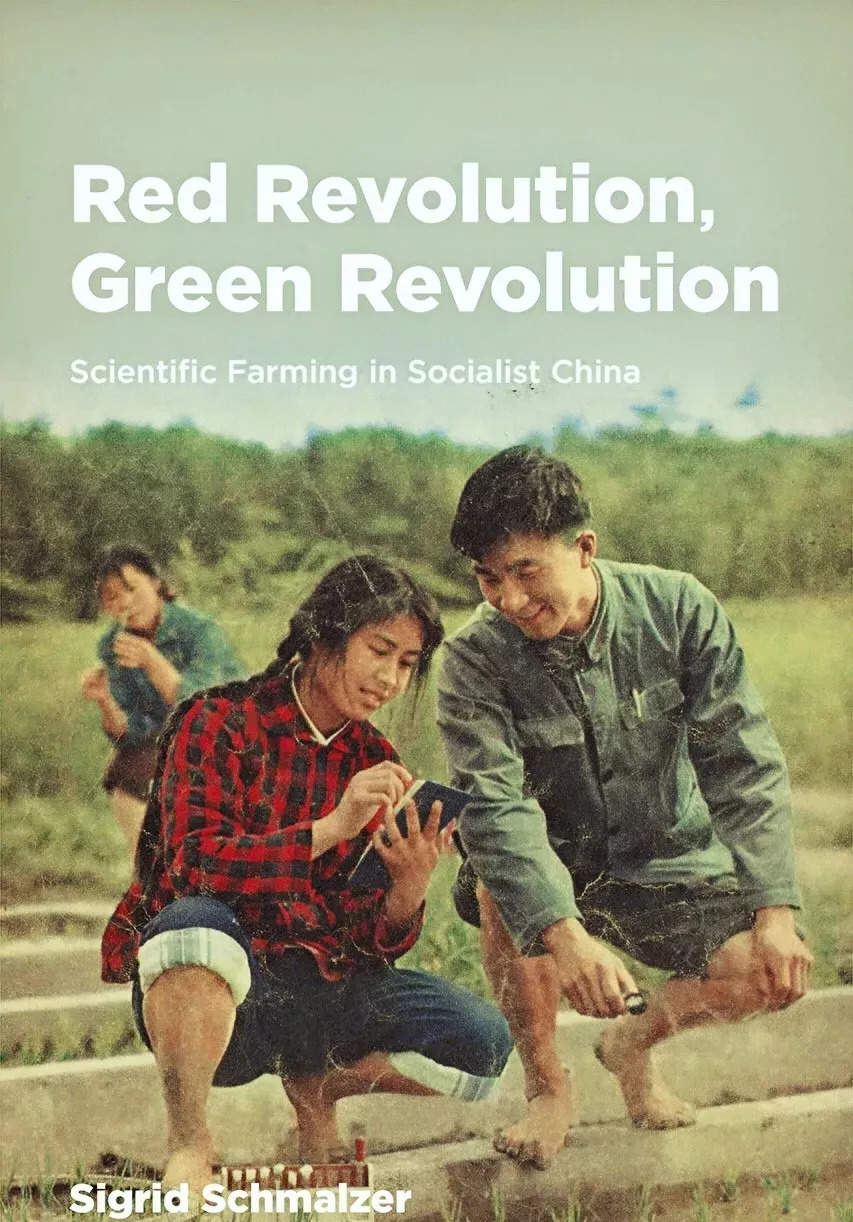
《紅色革命與綠色革命: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種田”》(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2016),Sigrid Schmalzer ( 舒喜樂 )著
近年來,學術界開始重新思考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從現實層面來説,這是對當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危機的正常反應:當“歷史終結”的應許之地成為夢幻泡影,過去的烏托邦實踐是否潛藏着通向未來的道路?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安默斯校區歷史學教授Sigrid Schmalzer ( 舒喜樂 )的近作《紅色革命與綠色革命: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種田”》(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2016)就是其中的探索之一。
本書的問題意識在兩個層面上展開:從研究對象來説,是在“綠色革命”的對照之下,重新梳理“紅色革命”毛澤東時代的“科學種田”運動;從理論反思來説,是由此探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科學”與“政治”的關係,質疑了“什麼是科學”,“什麼是科學權威”以及“農業應當如何發展”的主流觀念。
所謂“綠色革命”,是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威廉•高德在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革命高潮期的1968年用來指稱20世紀50、60年代,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支持,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農業生產技術改革活動。核心是培育和推廣高產糧食作物,大面積地使用化肥、農藥和農業機械,加強灌溉與管理,提高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而達到滿足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這一活動是美國冷戰計劃的一部分,在以高德為代表的官員看來,充足的糧食供應緩解了發展中國家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防止了共產主義的“紅色革命”的爆發,因而可以稱為“綠色革命”。而在當時正處於“文革”的中國,對這個詞有着高度的警惕性,認為是保守的資產階級政府用來矇蔽廣大人民、使他們放棄革命鬥爭的工具。
然而,問題在於,這是否説明,當時的社會主義中國反對“綠色革命”或者農業現代化的新技術?作者認為,與通常的印象相反,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最激進的革命者也是熱切地擁抱其中的科學與現代化——當時的中國存在着與“綠色革命”類似的農業技術改良運動,希望通過機械化、良種選育、農藥和化肥的使用等手段改進農業生產的物質條件來增加產量與提高生活水平。這一活動當然受到了蘇聯五十年代援助的影響,但同時,又與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二十世紀前半期在國外的推廣農業技術的方式非常相似——研究機構從地方的需求出發,並在地方進行試驗以檢測與推廣新技術。
當然,社會主義中國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美國推動的“綠色革命”在哲學內核上有很大的區別。因為“綠色革命”有着明顯的技術專家治國的精英立場,**而在中國,科學與政治、現代化與革命是不能分離的。中國之所以譴責“綠色革命”是因為它將科學與技術視為非政治的力量,而且“綠色革命”的推動者試圖用這些力量來消滅社會革命。因此,中國從來沒有使用“綠色革命”的説法,而是用“科學種田”。**對中國的革命者來説,科學是與階級鬥爭類似的“革命運動”,“綠色革命”中的農業技術必須與“紅色革命”結合起來,成為社會革命的工具。因此,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了“農業科學實驗運動”,在全國範圍內以“三結合”的形式建立起大量的“科學實驗小組”,其中包括有經驗的“老農”,有革命熱情的“知識青年”以及能夠把握正確政治方向的“地方幹部”。這一運動的目的在於推翻科學精英和“走資派”的“技術治國”道路,即“政治掛帥”。在這個運動中,政治、社會與科學、技術是密不可分的。比如,一個由年輕女孩組成的“三八科學小組”用豬糞施肥就可以被視為是“科學種田”。這不是因為技術是新的,也不是因為這種方法是“生態”的,而是因為這一做法推翻了那種“女性不適合從事農業勞動”的陳舊觀念。可以説,在中國,“科學種田”不僅不是非政治的,而是激進的社會革命工具。

為了更深入地探討“科學種田”是如何將科學與政治相聯繫,本書的作者從參與者出發呈現了“科學種田”。在文本結構上,全書分為七個主要章節,其中,第一章主要討論關於農業科學技術的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第二章和第三章講述兩個專家蒲蜇龍和袁隆平的故事,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主角分別為農民和地方幹部,第六章和第七章則留給了“知識青年”。按照作者的説法,這是因為“科學種田”對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義,這樣的安排可以更好地揭示身處不同位置的個體如何處理政治與科學的關係。儘管沒有明言,這一安排卻有着明顯的“結構-行動者”框架,從作者的行文中也可以看到,每個章節關注的也是個體在現有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框架內,如何運用自身的能動性處理結構性的矛盾。而正文第一章,探討的就是本書兩個最關鍵的結構性矛盾:從下到上的實驗活動所總結的地方經驗與國家從上到下推廣的“模範”;大眾科學與精英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即“土”與“洋”的問題。而國家的解決辦法則是“土洋結合”與“三結合”。而後面六個章節,都是圍繞着不同的“行動者”們如何處理地方經驗與全國性的模仿、處理“土”與“洋”的問題而展開。
第二章中的蒲蜇龍對於今天的中國大眾來説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字,但在文革時期,被視為是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結合的典型。他本科畢業於中山大學農學院,博士畢業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是國際知名的昆蟲學家,從這一點來説,他是“洋”的代表。新中國成立後,蒲蜇龍及其夫人回國,在20世紀50年代成功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蟲,並在文革期間於四會的大沙開展水稻害蟲綜合防治試驗,蒲蜇龍的研究小組中,基本都是地方幹部和當地農民,是“三結合”的典型,而且蒲蜇龍從甘蔗、荔枝的蟲害防治轉向水稻害蟲防治,也是受到大寨“以糧為綱”的影響,是將地方經驗與全國模仿結合的典範。進一步説,蒲蜇龍的“以蟲治蟲”延續了20世紀上半年期美國昆蟲學界的研究。但是殺蟲劑和農藥的普及,使得這一研究在美國反而沒有中國興盛,而且中國在50-70年代,對於“以蟲治蟲”的熱情,很大程度上也來自於殺蟲劑與農藥的匱乏,而不是環保考慮,這也使得隨着20世紀70年代現代農業技術的普及,殺蟲劑濫用問題在中國嚴重起來。而在袁隆平的故事中,雜交水稻培育中最關鍵的一步“雄性不育株”的發現,也並非作為技術專家的袁隆平的個人成就,而是“四級農科網”及全國範圍內“農業實驗小組”集體的力量,依賴於被吸納入其中的廣大農民的尋找,可以説雜交水稻是非常典型的社會主義時期“大眾科學”的產物。然而,文革結束之後,儘管袁隆平本人一再強調他的成就來自於集體的力量,有關袁隆平的敍事依然將他歸為文革當中不被政治風潮所動的孤獨的科學家。

與蒲蜇龍和袁隆平的故事類似,其他平凡的地方幹部、老農與知識青年在科學種田運動中,也都需要平衡地方經驗與國家模範、土與洋之間的衝突。然而,在這一部分當中,還有一對雖然沒有這麼重要,但是富有啓發性的概念——“技能”(skilling)及“去技能化”(deskilling)。“技能”並非一個孤立的概念,它實際上是生產技術,以及附着在這些生產技術上的生產關係及一切社會關係的反應。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農民擁有豐富的“技能”,但是隨着農業技術的現代化,農民面臨着普遍的“去技能化”。比如在農藥和殺蟲劑唾手可得的時代,以往防止蟲害的技術便失去了有效性,擁有這些技術的農民被“去技能化”,當現代育種技術普及、改良種子必須通過市場購買的時候,傳統的育種技術也被“去技能化”,相應地,被“去技能化”的勞動者成為了可替代性極高的廉價勞動力,不僅對市場風險的抵禦能力下降,而且生存也嚴重依賴於大型種子公司。這實際上也從技術的社會性角度説明了轉基因的真正問題。事實上,轉基因的作物是否有害,是個很難確定的問題,而且從目前科學的角度,也實在找不到對人類的害處,而對轉基因技術的反對,除了宗教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轉基因作為一種複雜的技術,只能被大公司所擁有及壟斷,小農在其面前毫無抵禦能力,失去了大公司也無法生存。因此,對轉基因技術的反對,實際上是對技術壟斷的反對,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作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波動不應當被看作是科學與反科學之間的鬥爭,因為技術專家與政治上的激進派只是在對科學應當如何起作用這件事情上面存在分歧,但他們都承認科學的價值。因此,“政治掛帥”並沒有從環境保護的角度批判綠色革命中的科學技術,也沒有落在勞工和社會正義的議題上,事實上,激進的革命者和技術專家都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後果。由此,作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科學中不是政治太多,而是政治太少了。也是因為“科學種田”與“綠色革命”內在的一致性,今天中國農業的諸多問題,都可以視為這種事實上將去政治化的“科學”與“現代化”作為重要價值的“科學種田”的遺留,作為對它的反思與繼承,今天中國的鄉建運動、“人民食物主權”運動也與國際上反思“綠色革命”及其後果的環保運動一脈相承。
當然,這種對毛澤東時代激進政治表面之下的發展主義或者技術精英導向的批評與揭示早已不是新鮮事物,就是與本書幾乎同時的Miriam Gross的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2016)也認為20世紀的50年代的羣眾性血吸蟲預防運動並沒有有效降低血吸蟲的發病率,反而是60-70年代隨着知識青年和下放幹部進入農村,技術精英路線與大眾科學的結合才控制了血吸蟲病的肆虐。然而,問題在於,僅僅在結構上指出技術精英與羣眾運動之間的關係是不夠的,更關鍵的,在某些歷史時刻,為何這些結合能夠成功,這可能是在今天更需要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