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井岡山到全球秩序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8-08-26 08:52
《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一書收入了佩裏·安德森2016年訪問北京大學發表的四場演講、在清華大學與中國學者的圓桌討論文字記錄以及《上海書評》對其作的訪談。”大國協調“是此書的核心關鍵詞,在21世紀,一個資本的國際主義佔主導地位的國際形勢下,它基於資本的力量,服從資本統治的基本原則,與“霸權”觀念緊密聯繫。這種“大國協調”和中國所提倡的“既保持自身獨立性又加強各國溝通協調,加快發展道路”的民主化的國際關係截然不同。本文為編者之一章永樂對於該書內容的進一步思考。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經略網刊”,感謝作者章永樂老師和“經略網刊”授權保馬推送!每日一書|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佩裏·安德森訪華講演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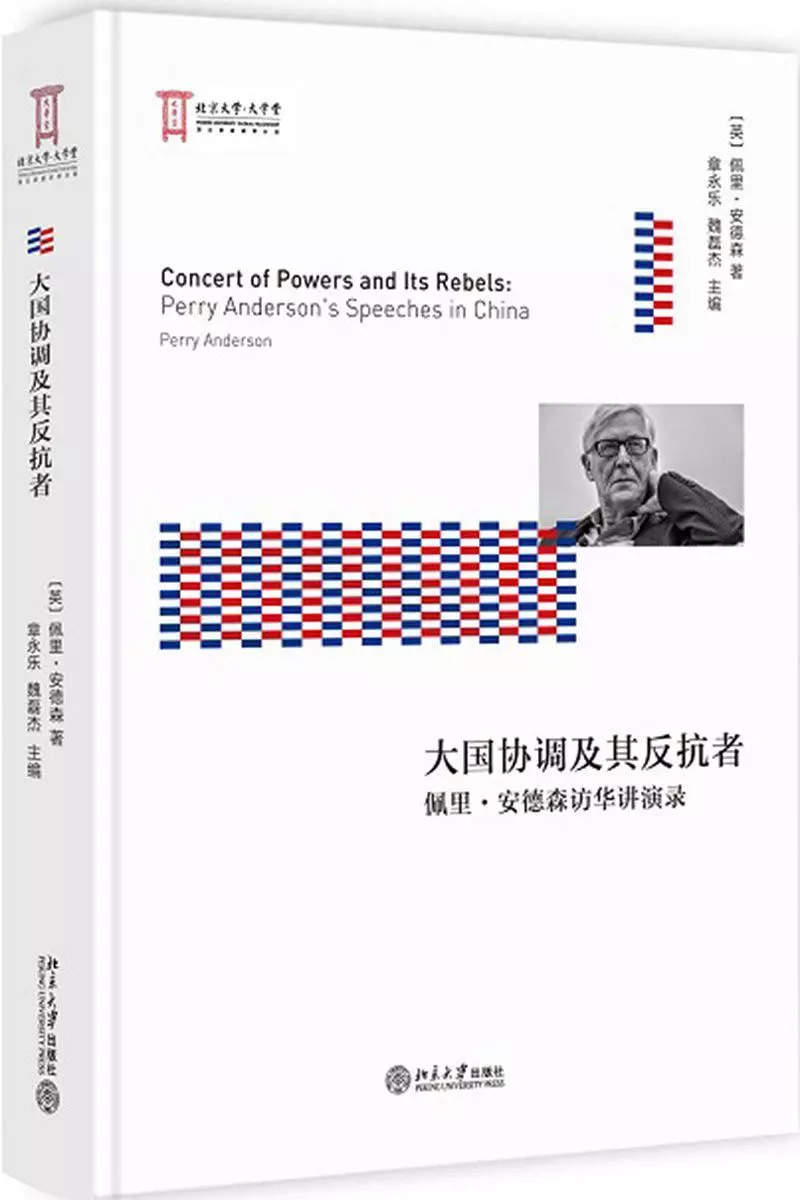
從井岡山到全球秩序:《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的視野
1927年,面對大革命的失敗,共產黨人先後發動了南昌起義與秋收起義,但佔領城市的計劃受挫,紅軍不得不撤退到深山密林之中。這在很多人看來,與“做山大王”似乎也沒有多少差異,“紅旗還能打多久”的質疑之聲連綿不絕。然而毛澤東卻不斷地鼓舞他的同志們,革命具有光明的前途。他的目光穿過井岡山的密林,投向了全球秩序。

星星之火映天紅——井岡山道路
在1928年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與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兩篇文章中,毛澤東以類似的理論邏輯,對革命隊伍中的悲觀乃至失敗主義聲音做出回應。他指出,作為半殖民地的中國有一個獨特的現象: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着繼續不斷的戰爭。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為紅色政權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毛澤東的理論分析中暗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秩序觀察:那些在華劃分勢力範圍與扶植代理人的帝國主義勢力,相互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可以設想,如果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利益一致,那麼他們能夠以某種聯合的方式來宰制中國,而他們的代理人之間也不會出現連綿不斷的戰爭。正是“大國協調”的破裂,為井岡山的革命根據地的生存與發展壯大,準備了基本條件。
“大國協調”,對應的英文表述是Concert of Powers。“concert”有“協調”的意思,但人們更為熟悉的涵義是“音樂會”。如果一羣大國在一起,像一個樂隊一樣,你打鼓,我拉琴,他吹簫,協調一致,其樂融融,這世界可不就太平了嗎?但毛澤東顯然不會這麼看,如果帝國主義列強協調一致了,中國作為半殖民地的命運,就很難發生改變。
英國曆史學家佩裏·安德森會非常贊同毛澤東的這個邏輯。北大出版社新出版的《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收入了佩裏·安德森2016年訪問北京大學發表的四場演講、在清華大學與中國學者的圓桌討論文字記錄以及《上海書評》對其作的訪談,是目前為止漢語世界中將“大國協調”作為核心關鍵詞的第一本理論論著。佩裏·安德森對“大國協調”提出的問題是,這究竟是什麼力量的協調?如果這種力量是壓迫性的,那麼它就可能阻礙更進步、更具有生產性的力量的生長。

佩裏·安德森在北京大學進行的第一次講座,題為 “大國協調:十九世紀”
“大國協調”的歷史經驗基礎是19世紀的“歐洲協調”。所謂“歐洲協調”,其起源是各王朝國家合力打敗拿破崙,於1814-15年召開的維也納會議。維也納會議確立了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與法國“五強共治”(Pentarchy)的局面,其直接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再一次發生法國大革命,從而維護歐洲貴族的統治。在19世紀上半葉,歐洲各國貴族相互通婚,形成一個跨國的階級,但很少與他們所統治的民眾通婚。但法國大革命卻“以下犯上”,試圖推翻法國貴族的統治,這就不能不引起法國貴族在其他國家的親戚的憤慨與恐懼。“五強共治”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加強歐洲貴族大家庭內部的團結,避免相互之間的戰爭,當法國大革命的苗頭在任何一個國家冒頭的時候,各國統治者將合力進行鎮壓。
從1815年到1914年,歐洲大陸並沒有發生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爭,與“歐洲協調”有着分不開的關係。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讓中國人也感受到了“歐洲協調”的威力。但是,在這一百年之中,協調體系卻在逐漸衰變。在安德森看來,“五強共治”格局有着內在的缺陷:首先是沒有把奧斯曼帝國拉進來,因此當奧斯曼帝國在19世紀迅速衰落時,歐洲列強紛紛侵蝕其歐洲舊地,並在其上不斷衝突;其次,“五強共治”形成之初,海上霸主英國與陸上霸主俄國分列歐洲大陸兩側,給歐洲大陸各國留下了騰挪的空間,但隨着1871年普魯士完成德國統一,中歐崛起一個強大的國家,從而打破了原有的勢力均衡。“歐洲協調”逐漸讓位於列強之間的角逐與競爭,直到1914年徹底破裂。
一戰之後的20世紀充滿了動盪。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化突飛猛進,因此也有人琢磨,21世紀的世界,是否也能夠出現一個“大國協調”格局呢?當然,21世紀的生產關係與19世紀已經發生了很大關係,貴族作為一個社會階級已經淡出了歷史舞台。21世紀如果有大國協調,安德森推測,其基本原則有二,其一是防範全球自然環境的惡化,其二是實現全球市場的穩定。毋庸置疑,支撐這個“大國協調”的基本力量,是資本的力量,其基本原則是資本統治的原則。而最有可能加入這個“大國協調”的五個政治單位,分別是美國、中國、俄羅斯、歐盟與印度。
然而,安德森懷疑新的“五強共治”在當下的可能性。原因有二,第一是冷戰之後,美國並沒有像維也納會議對待法國一樣,將俄國納入到西方秩序之中,而是對其進行了羞辱,迫使俄羅斯與西方形成對立;其次,在五強之中,美國視中國的政治社會制度為異類,而這同樣會引發中國的反彈。
與此同時,安德森還討論了另兩個與“大國協調”密切相關的話題,一個是國際主義的演變歷史,另一個是國際法的性質。19世紀,歐洲各國的統治者努力用民族主義將下層民眾整合到既有政治秩序之中,但新登上歷史舞台的歐洲工人則建立橫向聯合,以本階級的國際主義來對抗統治者的民族主義。但在1945年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方各國在美國領導之下進行了整合,從而發展出了一種資本跨國聯合的國際主義,但新生的社會主義陣營卻未能實現各國工人的橫向團結,而是因民族主義的上升而走向分裂,最終成為冷戰之中失敗的一方。目前佔據主導地位的國際主義,主要還是資本的國際主義,而非勞動的國際主義。而在安德森看來,國際法從其誕生以來,就在很大程度上服務於國際秩序中霸權的需要,它既非“國際”,也很難稱得上真正的“法”。因此,問題仍然在於如何突破霸權,建立更為平等的秩序。
在這一系列演講中,安德森將“大國協調”與“霸權”的觀念緊密關聯在一起。無論是基於貴族利益的“大國協調”,還是基於資本利益的“大國協調”,在安德森看來都缺乏正當性。而從晚近的發展來看,基於資本利益的“大國協調”還受到了各國內部民粹主義勢力的挑戰。在安德森發表演講的時候,特朗普還沒有在美國贏得總統大選。這位具有很強右翼民粹主義色彩的新總統上台之後,逆轉了美國的國策,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向“低端”移民關上美國大門,在經濟上薅盟友的羊毛 …… 凡此種種,都降低了基於資本利益的“大國協調”的可能性。但安德森在書中所做出的一個判斷,迄今仍然富有洞見,那就是近年來世界各地左翼的或右翼的民粹主義運動,雖然聲勢很大,但尚未能提供新自由主義之外的秩序道路。新自由主義的理念與建制,儘管未能完成“大國協調”,仍然是居於主導地位的一方。
安德森的“大國協調”論述中對中國着墨較少,但一個基本判斷是,美國對中國的政治社會制度從未放鬆警惕,而這就使得中國很難加入一個現成的美國主導的“大國協調”格局。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後,連美國自身都喪失了推動“大國協調”的意願。中國反而變成了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維護者,並高高舉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那麼,中國要推動建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意味着接過美國已經無心推進的基於資本的“大國協調”方案,只不過將領導者換成了中國呢?這一解讀很難成立。十九大報告對於中國經驗與中國道路的定位:它們“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期許的世界秩序,不是將一個原則強加給各國,而是尊重各國家各民族對自身獨立性的追求,這是一個體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語)精神的方案。當然,從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中國需要加強與世界主要大國的溝通與協調,但這與基於某個單一原則的“大國協調”,本質上並不相同。
《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對於19世紀以來“大國協調”的興衰的論述,也為我們理解過去一百多年的中國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啓發。在一戰爆發之前,歐洲列強牢牢地統治着世界上大多數地方,自居一等國家,將中國、土耳其這樣的弱國視為二等國家,將那些缺乏健全國家組織的原住民掃入第三等級。當時中國的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派,多數人能夠期待的不過是像日本一樣,在既有的等級秩序之中,從二等國上升為一等國,與歐洲列強談笑風生。同時,在一戰結束之前,歐洲的主導政體仍然是君主制。1911-12年,君主退場,民國肇建,但人們仍然很容易論證,君主制是世界主流,而共和制只是例外。

俄國十月革命
但到一戰結束之後,情況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德意志第二帝國、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紛紛“走向共和”,共和制從邊緣政制一躍成為主流政制。中國的共和主義者獲得了更大的信心來捍衞共和制度,而君主立憲從此很難再獲得廣泛的精英支持。一戰中爆發了十月革命,產生了新的蘇維埃國家,蘇俄對於新社會制度的探索,對列強產生了極大的衝擊。1919年的巴黎和會排斥蘇俄,但也未能建立列強之間新的“大國協調”,在巴黎和會上大出風頭的美國甚至沒有加入和會決議建立的國際聯盟,而受到和會懲罰的德國仍然具有復仇的願望與力量。與1814-15年的維也納會議相比,巴黎和會在重建穩定國際秩序方面表現相當失敗。
然而,帝國主義列強重建“大國協調”的失敗,對像中國這樣的受到東西方列強壓迫的國家來説,卻是一個突破帝國主義壓迫的機會。1933年,曾寫作名著《西方的沒落》的德國保守思想家斯賓格勒在其新作《決斷時刻》(Jahre der Entscheidung)中回顧一戰的時候,就曾稱之為白種人的失敗。他指出,西方世界正在經歷着階級革命與種族革命兩場革命,而蘇俄一方面鼓動西方內部的階級革命,另一方面,也聯合有色人種,發動對白人的“種族革命”。歐洲列強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正在動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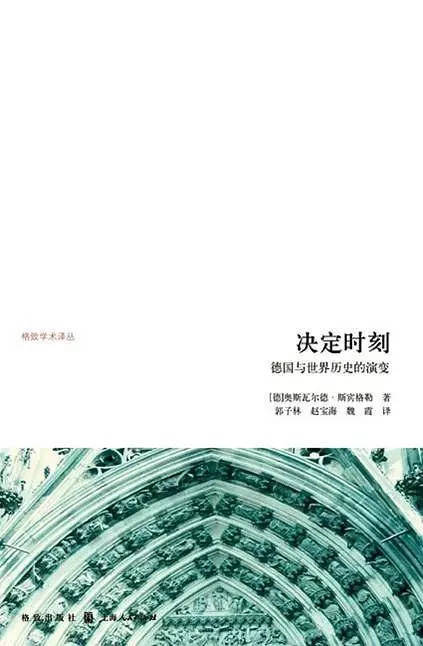
《決定時刻(德國與世界歷史的演變)》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德] 著
正是在這一條件之下,中國民眾的革命風起雲湧,不僅深刻改造了中國的國內秩序,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新的力量,使得中國能夠參與新國際秩序的重塑。毛澤東站在井岡山上預測紅色政權能夠生存並發展壯大,實踐證明他的預測完全正確——在相互提防、相互拆台的各路軍閥的夾縫之中,黨與人民軍隊不斷開拓革命根據地,哪怕在遭遇到第五次圍剿的沉重打擊後 ,仍然能夠利用各路軍閥的矛盾,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徵,在西北開闢新的根據地,之後經過抗戰與解放戰爭,取得革命的全面勝利。這個過程,是中國“舊邦新造”的關鍵過程,浴火重生的中國軍隊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而是有決心、有能力與美國領導的所謂“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展開鏖戰,將後者逼回“三八線”。在雅爾塔體系之中,中國是屈指可數的具有獨立自主品格的國家,既能夠聯蘇反美,也能聯美反蘇。中國支持了世界上其他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的鬥爭,推動了一系列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建國,為今日中國在亞非拉廣大地區的廣泛影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安德森在著作中提示我們,思考“大國協調”的關鍵在於探究這種協調所基於的原則是什麼。中國曾經是帝國主義列強“大國協調”的受害者,同時也因為這種協調的破裂,獲得了獨立自主的機會。在今天,中國已經是一個廣泛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大國,但單極霸權秩序只是鬆動,並未消亡。在這一情境下,我們需要記得來路,堅持促進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並以自己的發展道路探索,為“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更為進步的選擇,贏得更多國際朋友的支持——在此,國家利益的實現與對道義的堅持不可分離。這,或許是《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能夠為我們帶來的重要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