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政府如何組織抗洪救災?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29575-2018-08-27 17:21
在世界各國曆史中,中國曆朝歷代的救災制度可能是最突出的。事實上,在研究中國國家制度起源過程中,很多學者認為治水的需要是催生國家起源的重要因素,德裔美國曆史學家魏特夫就是其中的代表學者,他將中國視為“治水社會”。
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的建立源於大禹治水。據史記記載,在原始部落聯盟時代,黃河發生特大洪災,肆虐中原,民不聊生。面臨大洪災的威脅,個體的力量,乃至小規模的集體難以應對。為此,部落聯盟首領堯帝和舜帝先後任命鯀和禹領導與組織治水工,開展大規模地治理水患活動。鯀採取“水來土擋”的策略治水,花費9年卻失敗。
鯀治水失敗後,由其子禹繼起主持治水大任,他創造性採用“因勢利導”的疏導方式,整治黃河氾濫區域,花費13年之久,才終於平定水患。這是中國史籍記載的歷史第一次大規模的曠日持久的治水活動。依靠在治水活動中建立起來的功勳和威望,大禹順利繼承部落聯盟首領的位置。而集體抵禦洪水災難的記憶,為建立起權力更加集中、繼承更加穩定的王朝政權培植了民意的基礎。由此,大禹之後,其子啓建立夏朝,開啓了從“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王朝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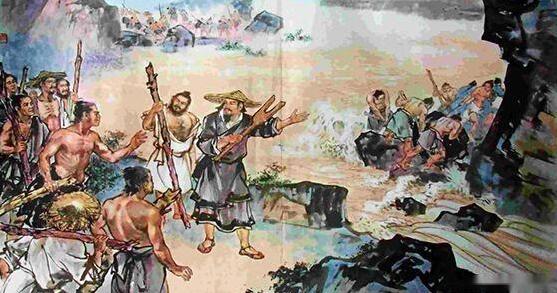
“大禹治水”
可以説,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國家制度起源於治水,反過來,古代國家也一直將包括治水等在內的救災事業作為重要的政府功能。中國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作為一個農耕社會,“靠天吃飯”,水災、旱災、蝗災、瘟疫等災難對社會影響極大。因此政府無法做無為而治的“守夜人”,必須要積極有為才能減緩災難對社會民生的影響,進而達到鞏固長久統治的目的。所以,中國很早就發展出一整套對應災難的機制與政策,歷史上稱之為**“荒政”**。根據學界的一般看法,中國的“荒政”在西周就已初具雛形。
自宋代以降,就出現了一批以總結民間與官方救荒經驗的荒政書籍,較有名的有《救荒活民書》、《康濟錄》、《籌濟篇》等。明嘉靖年間編撰的《湖廣圖經志書》,就將正德十一年,湖廣大水災賑救的方法和程序,一一詳述。內容涉及急賑、初賑、報災、勘災,以及煮粥、放賑,乃至於如何防範百姓多報、官府瞞報都有明確的評述。 清代救荒書《賑豫紀略》中,用18幅圖畫向朝廷彙報了他奉命主持河南饑荒賑濟到賑濟任務完成回朝覆命的全過程。即:恩賑遣官、宮闈發帑、首恤貧宗、加惠寒士、粥哺垂亡、金賙窘迫、醫療疾疫、錢送流民、贖還妻孥、分給牛種、解散盜賊、勸務農桑、勸課紡績、民設義倉、官修常平、禮教維風、鄉保善俗、覆命天朝。救災制度的程式化、規範化有助於地方官員更好地抗災、救災,救荒書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古人通過對自然災害規律的總結,以及平日中積累的救災經驗,無疑對日後的防災、減災都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一、**災前預防
古人很早就意識到災前預防的重要性,事先做好預防工作,救災時才能有備無患。“民以食為天”,災年到來,對百姓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糧食的欠收,因災年而導致餓殍遍野的記載不絕於史。故而“建倉積糧”就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至明清時期,倉儲體系日趨完備。從省會乃至州郡俱建有常平倉,鄉村則建有社倉,市鎮有義倉,而在邊疆地區還有營倉。
常平倉首創於西漢,是由官方出資建設的糧倉,豐年時出陳易新,災年時通過平糶或散濟的方式救濟災民。明清兩朝的户部規制每年春夏出糶,秋冬入糴,平價生息,遇災年時按數發給散貧户。同時屢頒詔旨,要求各地鄉紳富民捐輸,或按畝徵攤,或截漕糧以補缺,或開貢監名額以捐納,以此充實倉儲,常平倉因而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普及。在救助範圍上,常平倉也並非囿於本地,如某地發生重災,以致本地倉谷入不敷出,也可調外地積穀支援。如清乾隆二十三年,山西寧武等州縣就籌備4萬石糧食協撥陝西,撥後缺額,以截漕糧補足。

常平倉
社倉源於隋代,因“立於當社”,故名社倉,但多見於城市。至南宋時期,朱熹創立社倉法,因而在鄉間也興盛起來。社倉往往由民間推舉的社長管理,用春借秋還的方式賑濟貧民。社倉的穀米來源有二:一是官府的調撥,二是民間的捐輸。
如果説常平倉和社倉是官方救濟行為,那麼義倉則多半是由民間捐建的,是民間慈善活動的一種。如清雍正四年,富甲一方的兩淮鹽商,捐銀二十四萬兩,在揚州建倉積儲,名曰鹽義倉。鹽義倉由兩淮鹽商來經營,每年青黃不接之際,按照“存七糶三”出陳易新。清道光十五年,蘇州府創立長元吳豐備義倉,一度發展到田產上萬畝、積穀十數石,存銀十幾萬兩的規模。
此外政府還積極發展農業生產,鼓勵墾荒,重視推廣農業技術,以及大力興修水利設施等,作為災前防災、減災的重要措施。
**二、**災中勘按
明清兩朝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體系完備的救荒制度,對報災、勘災、救災的程序都作了嚴格的規定。
首先是報災。限於當時通訊手段的制約,朝廷很難及時通曉全國的災情,因此朝廷將報災視為地方官的責任,發生災荒時,地方官必須及時上報災情,層層彙總,上達中央。如清政府在曉諭地方督撫的奏章就載有明文,“地方督撫巡按即行詳查頃畝情形具奏”。如果在管轄區域內發生災情,地方官員逾期不報、懈怠延誤者,將受到朝廷的嚴厲責罰。大明律就明文規定,逾期一月未報者,從巡撫到州縣的各級官員都要罰俸銀;超過一個月的將貶謫一級:遲緩延宕併產生嚴重後果的將革職。
地方官員除了上報災情外,還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周詳地勘查受災的程度,作為實施救濟的依據,這就是勘災。為了能督促地方官有效勘災,朝廷將受災程度的大小與官員的品級相聯繫,層層落實。如遭重災,督撫大員必須親自勘查和奏聞賑恤事宜;如受災不重,則由知府、同知、通判會同州縣官員勘核,然後逐級上報。**在勘災過程中,受災州縣需預先刊刻“簡明呈式”,即受災表。開列受災民眾的姓名、家口、住址、被災田畝數量等細則,先由災户自行填報,經地方官核實後,按行政劃分裝訂成冊,作為底本。**然後查災官員赴莊查災時,以此為藍本,核查受災情況,之後將底冊上繳州縣,由州縣官員造總冊,繪出本地受災地圖,嚴重地區以色筆描出,最後附上州縣賑濟意見一併上報。
三、災後救濟
查勘災情是為了能對症下藥,針對受災程度的不同,採取相應的救濟措施。
首先採取的是災蠲和緩徵。所謂災蠲是指免除災年時民眾錢糧的賦税。如順治二年,直隸霸州等8縣受水災,清政府當即蠲免受災縣域的額賦。清代道光二十一年,浙江大雪,受災面積波及德清、仁和、錢塘、嘉善、海寧等多個州縣,成災田畝逾數萬頃,朝廷接報後當即恩准蠲免下半年浙江受災州縣的賦税。
所謂緩徵就是當年應收錢糧延緩至災後重徵,緩徵的年限與受災程度的多寡有關。明清兩朝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先勘明災地錢糧,勘報之日起即行停徵。如被災達十分、九分、八分者,三年帶徵;如七分、六分、五分者,分二年帶徵;如五分以下,不成災,有奉旨緩徵及督撫具名緩徵者,至次年麥熟後,逐年徵繳。當然,在具體實施蠲免和緩徵的過程中,也極易造成官吏舞弊尋利,為此明清兩朝政府都制定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如清代就規定膽敢舞弊者,將“照侵盜錢糧律治罪”,或以“違旨計髒論罪”,或“以違旨侵欺論罪”。據李向軍的《清代荒政研究》一書統計,清政府共蠲免15713次,總計約白銀一億二千餘萬兩,如果加上蠲免災欠的數額,竟達2億兩白銀之多。
災蠲和緩徵實際上只是有地農民受益,但廣大的失地農民或佃農卻很難直接受惠。因為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一遇災年,這些農民就立即陷入困境,造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的局面。為此,政府只有通過設立粥廠,煮粥散米給饑民。清康熙四十三年,直隸巡撫李光地在賑濟河間府水災時,就採取設立粥廠的方式救濟災民,起到了途無餓殍,小民得以存活的良好效果。後來,當地的鄉紳也加入到賑濟的行列中,施粥、散米給予受災百姓。由於設立粥廠一法收效甚大,使得施粥設廠的方法漸成定製,且不限於受災百姓,對大城市中的流民和乞丐也定期施捨。如蘇州府每年“於六門諸寺院”等地“自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止,每朝作糜以食貧民”,成為蘇州府的慣例。

倘遇冬季,災民無衣禦寒,政府還發帑購買棉衣賑濟災民。清嘉慶二十二年冬,北京聚集了大批受水災而逃難的災民,時至隆冬,清政府購棉衣數萬件,在順天府等5城分地同日散給貧民。
發生災荒時,大批百姓生計無着,如果放任自由,必定危害地方治安,倘若處置失當也會激發民變。為此,政府往往將災民組織起來,興修農田水利和其他公共工程,計工給酬。一方面可以解決災民日蹙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穩定生活秩序,加以控制。當然,客觀上也建設了許多有益於社會的公用設施,較之單純的救濟無疑更具意義。如清嘉慶六年,清政府就召集災民共5萬多人,修築永定河工程,實行以工代賑的政策。
總之,中國是一個災害頻仍的農耕社會,早期國家制度的形成得益於大規模治水活動的需要。**而秦漢之後,由於郡縣制的確立和中央政府的強大,救災成為國家的統籌行動和重要功能,並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荒政治理體系,這是中國大一統體制的優勢。**在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的時間裏,只要沒有戰爭割據,一地遭災,鄰近各地政府必須援助,這是慣例。乾隆年間,山東省遭遇水災,鄰近的河北、河南、江蘇、安徽甚至關外的遼寧都大力援助。如果災情重大,除了周邊省份必須援助外,朝廷也會在全國範圍內截留其他地方的漕糧以支援災區,等災情緩解後朝廷再對被截留糧食的主人進行賠償。今天,人們通常把中國政府在救助災區時採取的“對口援助”和“對口建設”理解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其實,中國社會的這種全國統籌的社會主義救災機制在歷史上有着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
總結本章所述,儘管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產生出成熟的社會主義理論。但中國社會兩千多年前就走出了以血緣為基礎的貴族等級制度,平等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最強大的歷史基因,社會的流動性遠遠高於當時的世界各國。而中國社會的平等精神又決定了歷代中國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視社會的國計民生,不得不用政治力量來平衡經濟上的貧富懸殊,並且不斷嘗試由政府出面來解決無節制的商品經濟帶來的兩極分化弊端。正是由於中華民族強大的平等基因和政府調節市場以利民生的傳統,所以當西方的各種思潮湧入中國後,唯有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思想能夠跟中國傳統文化產生強烈的共鳴與對接,能夠迅速中國化。所以,今天中國的發展道路既不是蘇俄版的社會主義,也不可能是西方版的資本主義。在數千年時間中形成的強大歷史基因決定了中國的道路仍然是在歷史與傳統的軌跡中延續。
參考文獻:
1.《史記·秦始皇本紀》。
2.《史記·平準書》。
3.《漢書·食貨志》。
4.(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
5.《漢書·武帝紀》。
6.《漢書·宣帝紀》。
7.侯紹莊:《中國古代土地關係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漢書·王莽傳》。
9. (英)崔瑞德、(美)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史》(第1卷),楊品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10.胡適:《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會主義者》(1922年)。
11.(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12.(法)魏丕信:《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徐建青譯,2003年版。
13.葉依能:《清代荒政述論》,《中國農史》,1998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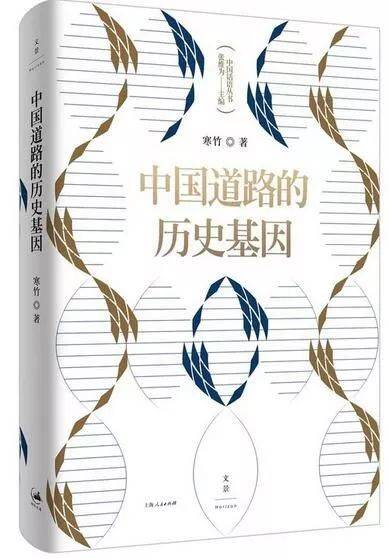
《中國道路的歷史基因》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文摘選自作者最新力作《中國道路的歷史基因》第四章“古代中國樸素的社會主義”。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