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候加重互聯網平台的法律責任了(一)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7417-2018-08-29 10:14
原創: 慕峯(太陽照常升起:The_sun_also_rise)
再次出現殞命事件之後,在巨大社會壓力之下,滴滴們能主動改過自新嗎?我認為很難。**儘管有看起來真誠的道歉,但這個世界從不因為道歉而改變。**相反,客觀上講,滴滴僅需承擔極其微小的法律責任,忍受到下一個社會熱點爆發,將其影響上市目標的部分業務做出切割和調整,就可以繼續靜待其700-800億美元的上市計劃逐步推進了。對受害家庭和民眾而言,這是殘忍的事實,但對於資本而言,則幾乎是確定的事實。

做出這個判斷,不是基於揣測,而是基於多年以來對中國資本市場的親身參與和細緻體察,以及對互聯網時代中國立法情況的充分認知。**只要我們的立法思維仍不改變,無論是服務類電商平台引發的人身傷害事件,還是商品銷售類電商平台引發的假冒偽劣所致傷害事件,都只會更多,不會更少。**而在這樣的體制缺陷下繼續發展的中國經濟,最終將實現互聯網平台企業對整個線下生產製造、服務提供(供給端)和消費者(需求端)的兩頭控制。馬老師在這個終極問題上從來沒有開過玩笑。所謂的“去中心化”,不過是使其他所有主體都成為“平台中心”的附庸,而這些平台最終是否良善,全在於今後的立法是否詳加規制。很難想象,在快要迎來2020年代的今天,平台的控制,竟然可以在幾乎沒有約束的自由放任之下實現。
如果今天某些人還認為實體經濟的平台化才代表人類經濟的未來,認為十幾億人的就業問題將主要是依靠幾家互聯網平台企業才能得以解決,只有以舉國之力支持幾家平台企業才能提升國民信任度和幸福感,或者認為只要幾家平台企業繼續做大就能“倒逼”其他傳統企業“成功轉型”,那顯然是對“科技進步+自由放任”正在和將要產生惡果的巨大無知。
**這是一篇關乎每個國人未來的長文,並非針對某個具體事件的應景之作,我希望所有讀者留出足夠的時間,冷靜閲讀,細細體察。這篇文章的存在價值可能將長達數年甚至更長時間。**或許其中部分內容稍顯複雜,但已足夠通俗,請儘量逐句閲讀。我們的目標,不僅是希望讓更多人瞭解到問題的根源,更是希望藉由所有人的關注和參與,開始推動改變。
一、平台時代,傳統法律保護機制已然失效
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進步,在商品和服務供給大幅增加基礎上所實現的民眾幸福感提升,是依靠市場競爭和社會保護性立法兩個手段去實現的。**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的內涵,**一方面在於通過具體法律制度去塑造良性的市場環境,包括對土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知識產權、股權等財產性權利的確立,也包括對合同、擔保等基礎性市場行為的認可,還包括對各種財產性權利金融化的制度確認;另方面,則在於通過社會性立法去抑制自由放任市場的危害,這主要體現在以侵權責任追責、產品質量保障、消費者權益保護、環境保護和反壟斷為核心的一系列立法方面。這兩類立法並行,並非中國獨創,談不上中國特色,是每個市場經濟國家所普遍採納的。
社會保護性立法,其直接目標在於使市場服務於社會目標,而非經濟利益。如果僅以經濟發展目標為唯一追求,那麼只要能以數據證明某種經濟模式在整體上有助於經濟發展,個體或者部分羣體的利益就完全可以被犧牲。如果以經濟發展目標或者個別企業利益為最優先,那麼社會保護性立法的缺失,必將導致市場之惡成為現實,遭受損害的,是無力對抗巨頭企業的普通民眾。對於平台新貴和身後的投資人而言,這種情況並不陌生,因為大多數所謂的政策風險或者法律風險,不過都是經濟成本而已。
在此,我們以滴滴事件為例,來檢視每一位乘客都可能面臨的風險。
在絕大多數乘客都不會閲讀的滴滴APP協議中,有所有滴滴司機和乘客都已經簽署同意的《專快豪華車服務協議》和《順風車信息平台用户協議》。

《專快豪華車服務協議》第8.1條約定,“在網站或滴滴出行平台上向您提供的信息、推薦的服務僅供您參考。我們將在合理的範圍內盡力保證該等信息準確,但無法保證其中沒有任何錯誤、缺陷、惡意軟件和病毒。對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網站或滴滴平台導致的任何損害(但排除死亡或人身傷害),我們不承擔責任(除非此類損害是由我們的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第8.2條約定:“……為提升服務品質,保障平台用户(包括駕駛員和乘客)安全,並更好的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我司將通過個性化的安全保障產品為標有保障產品的訂單服務中的平台用户提供相應的**安全保障服務,例如對於交通事故和車內衝突等與平台訂單相關聯的意外事故,在實際責任方無力賠償或在合理時間內未賠償的情況下,可以按照相應的安全保障產品説明規定的內容提供先行墊付、住院探望等服務。**對於存在侵權責任人、違約責任人的,在提供安全保障服務後,提供安全保障服務的相關方有權向有關實際責任方追償。”
上述兩個條款稍微複雜的部分,簡單講即是,對於滴滴專車、快車、豪華車服務:1、乘客若因使用滴滴APP死亡或者遭受人身傷害,除非是因為滴滴的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否則滴滴不承擔責任。而如果乘客通過法院訴訟去主張滴滴擔責,則乘客要去證明滴滴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2、對於出現交通事故和車內衝突等與訂單相關的意外事故時,滴滴可以按照“安全保障產品説明規定”去對乘客進行先行墊付或住院探望,但這份“安全保障產品説明規定”,在滴滴的平台或者APP中始終無法找到。根據滴滴曾經公開的網絡新聞稿,對乘客合理醫療費的先行墊付和住院探望是確有的,至於墊付額度、覆蓋範圍則一概沒有明確的書面説明。如果不是因為交通事故或車內衝突等出現的意外事故,僅僅是騷擾或者沒有出現需要赴醫院治療的其他事故情形,那麼乘客只能通過“投訴”去反應,而乘客本身還負有證明投訴屬實的責任。
那麼《順風車信息平台用户協議》是怎樣規定的呢?該協議第4.7條約定:“順風車平台無法保證其所提供的信息中沒有任何錯誤、缺陷、惡意軟件或病毒。對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信息平台導致的任何損害,順風車平台不承擔責任(除非此類損害是由順風車平台的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
換言之,**如果説滴滴專車、快車、豪華車服務還因為承諾了找不到具體內容的意外事故“先行墊付”制度需要投入額外的管理成本,那麼順風車則沒有任何額外承諾可以使滴滴有動力去進行足夠的順風車管理。**顯然,除了前置的司機審查的區別外,這種最終責任上的區分,也是順風車問題更為嚴重的原因。順風車真的是滴滴為乘客提供的“免費”服務嗎?如果真的是,那麼還真不能苛責滴滴。然而,儘管滴滴沒有向順風車抽取20%的服務費,但在所謂“羊毛出在豬身上”的互聯網時代,以極低的成本讓用户更多的打開自己的APP,這種所謂的“免費”,真的不帶來經濟利益嗎?所以當順風車出現非常多的風險而不可控時,對滴滴來講最佳的方案,就是一關了之。已經有那麼長的時間以所謂的“免費”和“無責”來獲取足夠的流量了,關就關吧。
那麼普通民眾一定會問,難道法律對滴滴這樣的平台就沒有額外的約束了嗎?仔細閲讀2016年11月1日起實施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服務經營管理暫行辦法》,你會發現,“未按照規定製定服務質量標準、建立並落實投訴舉報制度的”網約車平台公司,“可由縣級以上汽車行政主管部門和價格主管部門按照職責責令改正,對每次違法行為處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款”。**頂格行政處罰,就是3萬元,還是人民幣,而這一條,還是唯一能與滴滴諸多事故沾得上邊的。****所以直到今天,你只能看到監管部門的同仇敵愾、厲聲譴責和約談,因為從依法行政的角度,他們無法做得更多了。**我們可以看到交通運輸部以官方名義發出了《不保障乘客生命安全的企業不要也罷》這樣看似痛快的文章,但其中最關鍵一句則是:“除了將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作為平台企業的滴滴及其負責人,要不要承擔法律責任,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有關方面應該認真研究,今後不能再模稜兩可。”是的,立法到今天為止,還沒有授予監管部門更多的權限。
**那對於受害的乘客,從法律上而言,可以通過訴訟向誰獲得賠償呢?**這個問題,在還沒有網約車的出租車時代,根本不是問題。任何人不加思考都知道,如果出租車司機對乘客侵權,乘客當然可以要求出租車公司來賠償,這是人之常情常理。非常明顯的是,出租車司機是“有單位、有組織”的,出租車司機與出租車公司存在勞動合同關係。立法也正是如此規定的。《侵權責任法》第34條第1款規定:“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合同法》第302條規定:“承運人應當對運輸過程中旅客的傷亡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可以檢索到大量按照上述法律作出判決的案例。這不代表出租車司機就一定沒有問題,但這樣的責任設定,一定會讓出租車公司更加謹慎的選擇自己的員工。説到底,傳統的法律設定,是通過加大出租車公司的責任,使其盡到更多的注意、付出更多****的成本,來替乘客把關,相應的,乘客也多了一層救濟。當然,整個制度不僅僅限於這兩條規定,我們後面會充分討論。

那麼在平台約車時代,受害的消費者及其家屬能直接讓滴滴來進行賠償嗎?2013年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增加了對網絡交易平台的責任,第44條第2款規定:“網絡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應知銷售者或者服務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依法與該銷售者或者服務者承擔連帶責任。”以滴滴事件為例,司法實務中,消費者要以這條規定向平台企業索償,需要滿足以下條件:一是消費者要證明平台明知或應知滴滴司機利用其平台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權益,這個證明,最直接的是現場錄音、錄像並提供給平台,次直接的是對平台客服的留言或投訴,在緊急情況下,如果無法錄音、錄像或者留言會怎樣?平台可以直接辯稱,無法證明緊急事件的出現是因司機利用平台所造成。即便有相關證據,平台也可以辯稱,已經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例如接到了乘客的留言並進行了內部處理,開始調查車輛情況,或者接到了自稱乘客親友的電話投訴,開始驗證乘客親友的真實身份,至於要處理多久、驗證多久,法律並無規定,滴滴與乘客的協議也沒有約定。
此時,能否要求滴滴賠償,最終是由審理案件的法官來判斷的。如果不是一個公開事件,沒有民意的支持,這種事件將很大程度上變成平台巨頭與乘客或乘客家屬之間的討價還價。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乘客的訴訟成本和可能得到的賠償,你會發現,任何個體,最終都將在敗倒在平台腳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於2003年公佈的《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因人身侵權導致受害人死亡的,需要賠償的費用包括“喪葬費、被撫養人生活費、死亡補償費以及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同時近親屬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這其中主要的是死亡賠償金和被撫養人生活費,這兩部分有多少呢?上述司法解釋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但六十週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七十五週歲以上的,按五年計算”,根據官方統計數據,2017年度,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是101,599元,上海市職工平均工資是85,582元。以二十年計,如果在北京法院起訴,那麼死亡賠償金約為203.2萬元;如果在上海起訴,死亡賠償金就變成了171.16萬元。撫養費方面,“被撫養人生活費根據撫養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計算。被撫養人為未成年人的,計算至十八週歲;被撫養人無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計算二十年。但六十週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七十五週歲以上的,按五年計算”,根據統計數據,北京和上海的2017年度人均消費性支出分別為37,425.34元和39,791.85元,以最長時間撫養費十八年計,在北京起訴能夠獲得的最高撫養費賠償為67.37萬元,在上海起訴能夠獲得的最高撫養費賠償為71.63萬元。對受害人的近親屬而言,還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個賠償金額大概是多少呢?以能查詢到的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2006年制訂的指導意見為例,“造成公民死亡的,精神撫慰金一般不低於5萬元,但不得高於8萬元”。加上其他諸如喪葬費、誤工費等賠償費用,因侵權事故死亡,在北京和上海起訴能夠獲得的賠償總額,大概也就在300萬元人民幣左右,而其他地區則要更低,甚至低非常多。無論是年薪千萬還是年薪十萬,無論是擁有一套房還是十套房,一條人命300萬,這就是企業要計算的成本。
如果你認為這就是全部,那就錯了。因為這還沒有計算訴訟成本,包括律師費用支出和短則幾個月多則數年的訴訟審理期限。有多少個體能夠走完這漫長的流程去討要一個説法,而不是接受估值5,000億的平台巨頭私下和解的“恩賜”呢?一條人命300萬,對資本而言,這不過是用來計算風險和收益的成本罷了。
你以為真的是300萬嗎?按照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即便證明了滴滴應當承擔責任,但對滴滴而言,它所要承擔的責任只是“連帶責任”,並非直接責任主體。對出租車公司而言,因出租車司機侵害乘客合法權益,是由出租車公司直接向乘客賠償,這個責任主體是公司而非司機。而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下,**在費勁的向平台討要了賠償之後,滴滴作為連帶責任一方,可以立馬向涉事滴滴司機提起追償,因為在這樣的立法下,最終責任方是司機而不是企業。**那些大量轉載關於消費升級、消費降級去反思犯罪成因的人們,有沒有想過,在這樣的追償制度下,犯罪者接下來會怎樣?當然,平台也可以大度的放棄這樣的追償,如同另一種“恩賜”。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僅能檢索到一個關於滴滴作為被告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侵權案例,這則案例充分説明了上述立法帶給乘客的困惑。青島市“廉某訴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2017)魯0203民初1697號)一案中,乘客廉某在遭受滴滴司機毆打併將滴滴公司訴至法院後,**滴滴公司辯稱:滴滴公司沒有實施對廉某的侵權行為,且滴滴公司作為網約車經營者,和網約車司機構成新型的合作關係。**一審法院最終認定,廉某無法證明網約車司機為滴滴公司工作人員,滴滴也否認與滴滴司機存在僱傭關係,因此廉某以滴滴司機執行公務致其損傷為由要求滴滴公司承擔賠償責任,未能得到法院認可。在二審時,廉某直接撤回了上訴。以司法實務經驗來看,滴滴與廉某極有可能進行了和解,滴滴進行了賠償,但這種基於和解的賠償,內容是不會公開的,換來的結果,往往是受害者承諾不就相關事項再次起訴平台。廉某的選擇是理性的,因為在現行法律之下,除非廉某能夠證明滴滴明知或應知司機侵權,且未採取必要措施,否則根本不可能獲得滴滴公司的任何賠償。而就我的瞭解,即便是中國最好的律師,只要沒有太關注過這方面的立法,他的認知與普通民眾完全是一致的。
出租車和網約車在法律性質上加以區分,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無論出租車還是網約車,真正的勞動者都是司機,出租車公司和網約車平台都從司機那裏抽取費用,出租車公司是以“份子錢”為名義,而平台是以“信息服務費”之類的名義。勞動性質和消費者沒有任何不同,僅僅因為向勞動者抽取費用的名義不同,消費者在網約車平台那裏的安全保障就大打折扣,怎麼會有這樣的立法呢?反過來看,如果網約車平台不對乘客承擔此等責任,它會像出租車公司那樣有足夠的壓力去對司機進行管理嗎?**當然,滴滴們對此的解釋是,它自己並非出租車公司,司機也不是自己的員工,因此也無法像出租車公司那樣去做管理。進一步,難道出租車公司天生就應該承擔這樣的責任去管理司機嗎?事實上,出租車公司需要承擔這樣的責任,正是因為《侵權責任法》、《合同法》和出租車相關立法所確立的多項原則,包括員工執行工作任務對他人造成的侵權損害,以及承運人對運輸過程中旅客的傷亡,出租車公司都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滴滴平台之所以不需要承擔這樣的責任,只是因為立法沒有將其納入而已。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滴滴們接受這樣的責任嗎?毫無疑問,所有平台,都會盡最大努力去抵制被納入這樣的立法規範中。因為一旦受此約束,平台們將被迫花費更多成本去管理司機、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救濟,換言之,這將損害平台們的經濟利益。
那麼平台們怎麼去論證自己觀點的合理性呢?平台往往會説,互聯網平台模式跟傳統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有本質區別,平台企業沒有直接提供商品銷售和服務,而只是通過信息化手段搭建平台,連接商品銷售者、服務者和消費者兩端,為供需雙方提供信息化服務,商品銷售者和服務者並非平台的員工,沒有勞動合同關係,而平台與消費者並沒有簽署任何的商品買賣合同或由平台員工向消費者提供服務,因此平台上的商品銷售者、服務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糾紛,平台不應當承擔任何責任,因為平台只是在“撮合交易”而已。
那出租車公司是否哪天也可以與所有司機解除勞動合同,簽署所謂的“新型合作協議”,不用承擔這麼多責任呢?請問,一個出租車公司利用線上平台去提供約車服務,和一個互聯網企業利用線上平台去提供約車服務,真的完全是兩回事嗎?我們的就業,真的要依靠這樣的“平台+零工”模式才能得到解決嗎?
在我看來,**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傳統立法已經將出租車公司的責任予以明確。二者的區別,更在於出租車公司無論如何做大,都不可能具有網約車平台的運量規模;在於出租車公司無論如何做大,都不可能坐擁5,000億人民幣的估值;在於出租車公司無論如何做大,都不可能使其投資人、管理層和員工在上市之後獲得鉅額資本回報。**如果説曾經的出租車行業利益限制了公共交通供給的擴大,而政府通過政策傾斜容忍網約車平台以種種方式去加大供給,那麼今天來看,網約車平台的問題要比曾經的出租車問題大得多得多。資本衝動在立法滯後的庇護之下,滴滴們成為了制度套利的最大獲益者。以平台為名,對司機和乘客都儘可能的不承擔責任。
滴滴和出租車公司,真有那麼大的區別嗎?如果沒有,為什麼不讓滴滴們承擔出租車公司那樣的責任?一個估值700多億美元的巨獸,難道連一家小小出租車公司的責任都承擔不起嗎?如果承擔這種責任會導致滴滴成本大幅提升、估值大幅下降,難道正是因為滴滴沒有承擔這樣的責任才維持起其估值的嗎?説好的高科技帶來成本下降、推動社會進步呢?進一步,是滴滴估值下降帶來的股東損失跟普通民眾更相關,還是滴滴們承擔更多的安全保障責任跟民眾更相關呢?我們不過是要求這隻巨獸去承擔一家你連名字大概都不知道的、可能只有幾十輛車的出租車公司的相同責任,你覺得這隻巨獸連這個都做不到嗎?那它憑什麼估值5,000億呢?難道中國只有通過這樣才能擴大交通出行供給?難道除了這種扶持個別企業的模式之外,其他國家的交通問題都沒法解決了嗎?
至此,滴滴們唯一可以用來抗衡立法約束的理由,就只剩“保障就業”了。所有人都不用驚訝,今天中國所謂的代表人類未來的互聯網平台巨頭們,往往最終都要淪落到以“保障就業”這個理由去進行立法遊説,來換取自己繼續擴張的可能,以此來維持GMV為基礎的估值穩定。“保障就業”,這難道不是曾經“落後的”國企用來談判的理由嗎?這算哪門子未來呢?難道平台不如此,就真的無法“保障就業”嗎?在稍後的篇幅中,我們將揭下平台這最後一塊遮羞布。
回到出行市場這個話題,出租車就不會出事嗎?並非如此。出租車公司一定比滴滴好嗎?也並非如此。但所有人容忍平台的壟斷,是因為曾經所有人都認為平台能做得更好。既然它做不到,還有多少能夠容忍?所謂的平台模式,很多時候,不過是掩耳盜鈴、制度套利的藉口罷了。
是的,我們的傳統立法在新的經濟形態面前已經開始失效。接下來,我們要更深入的探討,這種失效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二、社會保護性立法對市場經濟的重要作用
互聯網平台出現之前,是典型的工業時代經濟形態。由於中國從計劃經濟轉軌進入市場經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法學界都將法學研究和立法重點放在了私法領域,也就是在公權過大、私權不倡的時期,去呼籲確立私權、保護私權。這與中國經濟學界在轉軌初期所做的努力,實質是相同的。如何培育和保護私有企業、私人產權,是過去幾十年來立法關注的重點。這個過程異常艱辛,不少法學學者和法律人為之付出了畢生心力。
**正是因為處於轉軌這一歷史階段,中國私企保護、就業保障與消費者權益保護,不時產生矛盾和衝突。**從工業革命後歐美的社會經濟發展歷史來看,在自由競爭過程中,大型企業逐漸集中化,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理念支配下,對社會造成了直接衝擊。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詳細考察了工業革命的歷史後提出:“社會中存在兩種組織原則的作用,兩者各有其特殊的制度目的,各有特定社會力量的支持,而且根據本身的特殊方法行事。其中之一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自律性市場,受到商人階級的支持,而且以自由放任與自由貿易為手段;另一個原則是社會保護的原則,其目的是人類、自然與生產組織的保護,受到最直接被市場制度傷害的人所支持。”(Polanyi,1944)
中國絕大多數言必稱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大都不知曉,在哈耶克的同時代,除了有巨匠凱恩斯和熊彼特外,還有對自由主義市場的內在缺陷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卡爾·波蘭尼。**波蘭尼提出,在整個19世紀,“現代社會的原動力是由一種雙重傾向支配着:一方面是市場不斷擴張,另一方面是存在一個相反的傾向——把市場擴張侷限到一個特定的方向——與之對抗”,“社會會保護自己,以對抗自律性市場所具有的危害”;波蘭尼還認識到,雖然“進步是必須以社會變動的代價來換取的”,但“如果變動的速度太快,社會就會在變動的過程中瓦解”,而“變遷速度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變遷本身的方向;雖然變遷的方向經常並不由我們的主觀意願來決定,但我們所能忍受的變遷速度,卻允許由我們來決定”(Polanyi,1944)。**波蘭尼觀察到了放任的自由市場對勞工、消費者、社區甚至生態環境造成的極大負面影響,進而又洞察到了社會自我修復的內驅力。波蘭尼將這種自由放任對傳統社會結構造成的衝擊瓦解與後來社會保護的極端化(從民粹到納粹)相聯繫,深刻分析了兩次大戰發生的經濟因素和社會背景,這樣的洞察力,是同時代的經濟學家都未曾具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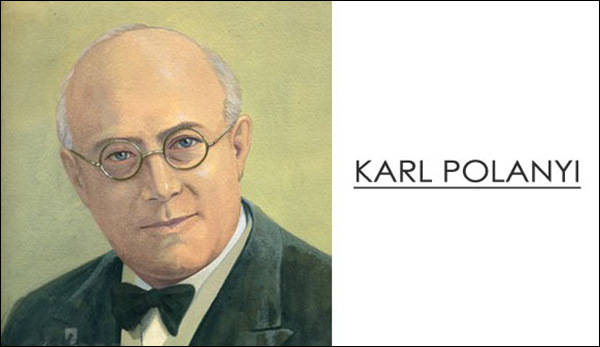
卡爾·波蘭尼
正是在這種思潮下,西方文明掀起了以社會保護性立法去排除市場之惡的各類運動。在歐美髮達國家,社會保護性立法囊括了反壟斷、競爭、食藥品安全、交通汽車安全、包裝標識、分期付款銷售、醫藥、廣告、環保等諸多方面。這些立法,對19世紀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對社會造成的衝擊進行了修復,將市場規制在適當的範圍內,使市場與社會相互容忍。
以消費者保護為例,1891年全球第一個消費者組織“紐約消費者協會”在美國成立。1899年美國消費者聯盟成立。1906年美國掀起清潔食品運動,國會通過了《肉類檢查法》和《聯邦食品和藥品法》。美國和德國分別在1936年和1953年成立了消費者同盟。英國在1957年成立了消費者協會,同年日本“全國消費者大會”發表了《消費者宣言》。1960年,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比利時的五家消費者組織發起,成立了國際消費者協會。1962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在《關於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國情諮文》中,將消費者權利表述為:安全的權利、瞭解的權利、選擇的權利和意見被尊重的權利。1983年國際消費者協會把每年的3月15日確定為國際消費者權益日。1985年聯合大會一致通過了《保護消費者準則》。1984年中國消費者協會成立,並於1987年加入國際消費者協會。1993年,中國製訂頒佈了首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我們今天沒有任何資格去嘲笑先發國家在面對“科技進步”帶來的“速度需求”時所選擇的“放慢步伐”,因為在兩三百年前就經歷過“速度優先”所造成的“社會撕裂”後,先發國家的民眾,有足夠多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也有足夠多的思想供給,使他們能夠主動選擇一種更為適當的進步速度,使他們的社會與市場能夠協調,使人能夠成其為人,而不是資本或權力的附庸。所以當地命海心的中國年輕人,宅在“家”中感受着租金上漲,嘲笑着歐盟的GDPR會拉慢歐盟互聯網經濟發展的速度時,有沒有想過,有些緩慢,其實正是別人主動的選擇,而你想慢,能慢得下來嗎?是的,曾經發達的歐洲正在老去,可是當我們老去時,是否能如他們今天一般?
回到現實,我們需要知道的是,今天中國尚待完善的社會保護性立法,也是由《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來共同構築的。這不是中國的特色和發明,這只是人類社會共同經驗在本國的反應而已。但由於從計劃轉軌到市場,儘管我們在形式上有了上述立法,但從經濟社會發展經驗而言,其實並未真正明白這些法律為什麼重要。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並沒有自發生長起來的私有壟斷企業,更沒有平台化的經濟形態,也當然沒有類似企業對消費者的侵害。既往國有壟斷企業存在的尋租等問題,更多是個體通過權力索取個別利益,也不曾出現私人資本這樣通過精確的成本計算來“主動承擔風險”以獲得高額資本回報的先例。
在工業時代的經濟形態下,存在企業、勞工和消費者三個主體。先發國家在對自由放任市場進行社會性保護立法的修復後,企業對勞工的責任及對消費者的責任,構成了整個現代社會穩定的基石。大企業對利潤的索取,應當能夠維繫適當的勞工權益和消費者權益,也應當能夠給中小企業以生存發展的空間。這不僅是靠市場競爭去實現的,也是靠社會保護性立法去實現的。
對大企業而言,與勞工的關係是由勞工法去調整的,勞資關係和社會保障是兩個關鍵,在這個關係之下,勞工只是企業的僱員,勞工對外的責任由企業去承擔,企業及社會對勞工提供足夠的保障,並對勞工予以相應約束;大企業與消費者的關係是由前述一系列與消費者相關的法律去調整的,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安全保障權和受尊重的權利是關鍵。
無論是製造業企業、商貿企業還是服務業企業,勞工只是其組織體的一部分,這種內在契約關係與企業管理結合,大幅提高了生產效率,創造了經濟價值。而在對外時,消費者只需面對企業,當企業的僱員行為導致消費者權益受損時,消費者只需追究企業的責任,不需要先去找企業的僱員索償,再去找企業索償。再進一步,當大型商超興起之後,城市生活形態發生進一步改變,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將商超責任納入其中,當在商超購物時或因商超所購商品遭受人身損害時,作為銷售者的商超將與商品生產者一同向消費者承擔連帶責任。這些今天人們習以為常的城市生活形態,正是規範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除此外,對食藥品、汽車交通等涉及人身安全的商品,還會有特別法加以規制,以設置准入和事中監管、增加生產者和銷售者違法成本的方式,來促其盡到足夠的安全保障義務。在這樣的社會保護性立法下,資本和企業將會放棄損及消費者利益和勞工利益的惡性競爭,因為這只是一個成本收益的分析就能得出的結論,相應的,會轉而促進將科技和管理應用於良性競爭。
然而,上述這一切,在平台時代,開始歸零。
普通民眾並不瞭解互聯網時代開始後形成的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即所謂**“避風港原則”(Safe Harbor Rules)**。避風港原則本是西方立法上的一個概念,意指當滿足某些條件後,即可免於承擔某些法定責任。1998年,美國在《千禧年數字版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DMCA)的第二章,即《在線版權侵權有限責任法》(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Limitation Act)中,將這一原則納入,對互聯網平台的發展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二十年後,這一立法原則深刻的影響着我們每個人。
接下來,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請各位讀者打起精神,仔細閲讀。
鏈接:是時候加重互聯網平台的法律責任了(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