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八十週年】毛澤東“理一分殊”思想發微 (下)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8-09-09 08:45
今天是偉大的革命導師毛澤東同志逝世42週年紀念,今年也是毛澤東同志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八十週年。保馬特推出一篇追溯毛澤東思想源流的文章,以此懷念這位中國革命的領導者。
此為(下)篇,(上)篇請點擊這裏查看
4
列寧主義淵源與朱子理學底藴
考稽馬列典籍,毛澤東最重要的理論依據當為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簡稱《幼稚病》)。
1927年7月,斯大林論及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路線時曾提出三條“列寧主義策略原則”。其中,第一條指出:“在共產國際給各國工人運動作出指導性的指示時,一定要估計到每個國家的民族特殊的東西和民族獨有的東西。”據此,他激烈抨擊(托洛茨基等)黨內反對派“機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罔顧“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結果招致革命失敗。斯大林説:
他們真誠地相信:根據共產國際的某些公認的一般原理,不用顧到中國經濟、中國政治制度、中國文化、中國習俗和傳統的民族特點,所謂用電報就能領導中國革命。……把共產國際的一般原理和每個國家革命運動的民族特點結合起來的問題,使共產國際的一般原理適應於各個國家的民族-國家的特點的問題,對他們來説是不存在的。
他們不懂得,現在,當各國共產黨已經成長起來併成為羣眾性的政黨的時候,領導的主要任務就在於發現和掌握每個國家的運動的民族特點,並善於把這些特點和共產國際的一般原理結合起來,使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目的易於實現並得以實現。
斯大林援引的理論依據正是列寧在《幼稚病》一書中的論述:
只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在每個國家通過具體的途徑來完成統一的國際任務,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和左傾學理主義,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都必須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點和特徵,這就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
《幼稚病》這部作品是1920年四五月間列寧為迎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而專門寫就的,批判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思潮。該書的論點與結論成為大會決議的基礎。列寧在這部作品中提出,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要與各個國家的民族特點相適應。1938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七週年之際,延安《解放》雜誌刊載了陳伯達的長文《我們繼續歷史的事業前進》。文章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偉大的特點之一,便是應用在各民族的具體歷史鬥爭中,能夠善於考察、研究、探索和熟悉各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點,能在各民族的具體歷史鬥爭場合中,對於‘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結構……殖民地、宗教派別等等之特質所形成的、所必然形成的具體特點,加以估計。’(列寧:《左派幼稚病》)”毛澤東對《幼稚病》這部著作也非常鍾愛。1932年他得到這本書後,愛不釋手,長征途中一路攜帶。不少人回憶,毛在延安時期還曾反覆研讀。據此可知,毛澤東對列寧關於基本原則與民族特點相適應的一段論述無疑相當熟悉。
至於“表現形式”這一術語,應是來自斯大林。1925年,他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演講中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內容與民族形式的著名論斷。面向蘇聯的各東方蘇維埃加盟共和國,斯大林提出他對無產階級文化與民族文化關係的看法:
社會主義內容的無產階級文化,在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不同的民族當中,依照不同的語言、生活方式等等,而採取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方法。……內容是無產階級的,形式是民族的——這就是社會主義所要達到的全人類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化與民族文化並無矛盾。無產階級文化並不廢除民族文化,它給予後者內容;而民族文化也不廢除無產階級文化,它給予後者形式。不同民族應該基於不同的語言和生活方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採用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表達社會主義的內容。
這裏順帶提及關於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毛澤東在研讀蘇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李達等譯)時一度留下諸多疑問。隨後,他又在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時,仔細研究了這一部分的相關內容。例如,書中講道:“在機械唯物論者方面,認為形式對於內容是受動的東西,否認形式的積極性、能動性,否認形式對於內容的反作用,因而把形式溶解於內容之中,因而不能理解事物的運動的特殊諸形式的發展法則。……因此,他們不能理解內容的發展中形式的積極性的作用,把形式和內容看成抽象的同一物,以至不能理解各種特殊現象的特殊發展法則。”毛澤東在“形式的積極性、能動性”,“事物的運動的特殊諸形式的發展法則”,“內容的發展中形式的積極性的作用”,“各種特殊現象的特殊發展法則”等語句下加了下劃線,更進而在“形式的積極性”“特殊諸形式”“各種特殊現象的特殊發展法則”之下加了雙下劃線。因此,“形式”在毛澤東心目中絕不是次等重要的東西,而恰恰是能發揮歷史行動者的能動性、創造性的地方。
以上可見,毛澤東關於基本原則與表現形式的思想方法是以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論述為依據的,並在中國革命經驗基礎上加以創造性地發揮而成。
不過,筆者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毛澤東的思想源自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思想文化兩大知識傳統,已是海內外學界的主流認識。如果僅僅停留在追溯其馬列淵源,則恐對毛澤東思想方法的理解尚有未盡之處。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毛澤東思想方法本身的中國文明底藴或“民族特點”何在呢?換句話説,其可能的中學淵源是什麼?
青年毛澤東在接受馬列主義之前,一度潛心鑽研“國學”。他進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以下簡稱“一師”)求學期間,曾主張“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他還跟學友表示“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並交流自己如何“通國學”的學習方法。1920年,他與新民學會會友討論研究中、西文明的先後問題時仍然認為:“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説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由此可見,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對中國傳統思想與學術的高度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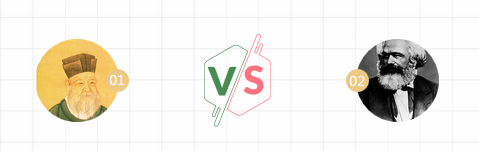
在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深受留英歸國的教員楊昌濟的影響。在業師的引導下,他認真研讀過《近思錄》《朱子語類》《四書集註》等書,對朱熹哲學相當欽服。毛澤東的早期哲學思想,多方面地顯現出朱熹理學思想的深刻影響。筆者認為,這構成他接受、吸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思想基礎。本文着重要勾勒的是毛澤東對朱子“理一分殊”思想的繼承與轉化。
1917年至1918年間,毛澤東聽楊昌濟的修身課時精心研讀了德國哲學家泡爾生所著《倫理學原理》一書(楊昌濟指定的課程教材),並做了大量批註。其中,他寫下一條:“發顯者即本體,本體即發顯,合無量數發顯而為一大本體,由一大本體分為無量數發顯。”毛澤東使用的“本體”與“發顯”這一對範疇,都是來自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本體”是宋學範疇,亦即所謂“道體”。例如,朱熹在解説《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一句時指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朱熹還專門探討過“心之本體”問題。至於“發顯”,當源自《中庸》作者提出的“未發”“已發”這一對範疇。馮友蘭論及形上形下時曾指出:“在中國哲學中,相當於形上形下之分,又有未發與已發、微與顯、體與用之別。”可見,發、顯都屬於形而下、用的層次。
汪澍白曾指出,青年毛澤東此論“與朱熹的‘理一分殊’論若合符節”。然而,何以見得?我們知道,《論語·里仁》篇的“一貫”章對於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該章記載了孔子與曾參的一段對話:“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注曰: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這裏,朱子以“一本萬殊”來詮釋孔子的“一貫”之“道”。“一本”是為“道之體”,而“萬殊”則為“道之用”。汪澍白認為,這段話是朱熹“理一分殊”論的典型表述。這並不是十分確切的。實際上,朱熹亦曾以“理一分殊”來詮釋“一貫”:
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個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
這裏,朱熹通過“理一分殊”講的是“一理”與“萬理”“萬殊之理”(“萬事各有一理”)之間的關係。當然,在朱熹的言論中,“一本”與“一理”、“一本萬殊”與“理一分殊”常互換使用,而沒有做實質性區分。
楊昌濟曾在《論語類鈔》中長篇抄錄朱熹闡發夫子之道的言論,深以為然。他沿着朱子所闡明之義理進而發論道:“宇宙為一全體,有貫通其間之大原則,宇宙間所有一切之現象自此大原則而生。吾人當深思默會,洞曉此大原則,所謂貫通大原也。”這裏,楊昌濟把朱熹所謂“體”“一本”“一理”稱為“大原則”“大原”“大本大原”。他還就《論語》義理的發明,駁斥清代漢學家對宋學的詬污:“近世漢學家言,不以宋儒之談性道為然,謂其近於空虛,鄰於禪學,乃矯枉過正,於《論語》中道及大本大原處,均諱言而曲解之。”
作為楊昌濟的得意學生,毛澤東在求學時代深受業師的理學傾向的薰染,一度究心於“大本”“本源”“大本大源”的探尋。他曾認為:“聖人,既得大本者也。……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為此,他立志要“見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青年毛澤東主持新民學會會務期間,摯友蔡和森曾評價他“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應該説,青年毛澤東執着於“大本”“宇宙真理”,與宋儒對所謂“理”“道體”的領悟是相通的。
回到前引毛澤東讀《倫理學原理》時寫下的那句批語。他所謂“一大本體”,亦即朱熹所謂“一本”“一理”;而所謂“無量數發顯”,亦即朱熹所謂“萬殊”“萬理”。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本體與發顯這對範疇,與他後來採用的原則與表現這對列寧主義範疇恰相對應。由此,或可證得毛澤東對於馬列主義的接受、理解實有朱子理學——特別是“一本萬殊”(或“理一分殊”)思想——為其會通基礎。
汪澍白在其關於朱熹對青年毛澤東思想影響的研究中指出:“在新舊交替的轉變期中,他的哲學思想有兩條交叉的伏線。一條是繼承了顧炎武、王夫之以來的‘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並與西方傳入的近代唯物主義經驗論相結合,開後來轉向馬克思主義和提倡‘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先河。另一條是繼承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傳統,同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相融匯,究心於探求性理之大原,形成他終生極其重視哲學和改造世界觀的基本思想。”此論甚有見地,揭示出毛澤東思想的理學淵源。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一論斷卻也遮蔽了思想成熟時期的毛澤東在思考重心上從“本體”“普遍性”“基本原則”向“發顯”“特殊性”“表現形式”的轉移。本文的研究旨趣主要放在後者。以毛澤東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中的論述為例,他着重強調的是“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因不同的具體歷史條件而各有所不同,由此才得以開出中國經驗之主體性的政治空間來。這一點是本文立論的基本起點。
5
遺產與方法:
毛澤東對“理一分殊”的化用
如前所述,毛澤東的思考與論述是從中國革命戰爭經驗的特殊性(《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升到基本原則與表現形式的關係問題(《戰爭與戰略問題》)。**筆者認為,他的看法不僅是接續了列寧主義的國際共運路線,而且傳承了朱熹理學的“理一分殊”思想。**毛澤東非常強調中國革命的特點,而這與宋明儒者特重“分殊”的方法論思想是相通的。
下文中,我們首先來簡單瞭解朱熹的“理一分殊”論,並由此來觀照毛澤東的思想與其契合之處。然後,再從毛澤東使用過的幾個譬喻來把握其“理一分殊”思想。
“理一分殊”是朱子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在理學研究中受到高度重視。這一命題最初由程頤在回答楊時對張載《西銘》的疑問時提出,以辨明儒、墨之別:“《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程頤提出這一論題時,主要表現為一種倫理學的意義,即普遍道德原則與具體倫理規範的關係。朱熹則將這一命題的意義擴大,從而具有了更為普遍的哲學意義。他指出:“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對朱熹而言,“理一分殊”表達的是普遍的同一性、統一性與具體的差別性、多樣性。可以説,天下事物都存在“理一分殊”的關係。
朱熹和程頤
“理一分殊”命題,經朱熹加以闡發後,對後世學者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明代理學大家羅欽順嘗言:“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在天固然,在人亦然,在物亦然;在一身亦然,在一家亦然,在天下亦然;在一歲則然,在一日亦然,在萬古亦然。”清初江南大儒陸世儀亦言:“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亙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可見,“理一分殊”被後代理學家視為貫通天人古今的基本法則。
這一重要的中國思想遺產,在毛澤東那裏也得到了繼承、轉化與發揚。例如,朱熹説:“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爾。”在他看來,“理一”和“分殊”兩者是不即不離的體用關係。毛澤東曾批評黨內教條主義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此見識恰與朱熹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之主張猶合符節。又如,朱熹曾指出:“聖人未嘗言理一,多隻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他認為,人們的認識必須經由“分殊”而上升到“理一”。這一重要見識,為朱熹提供了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基礎。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則指出:“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説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他批評教條主義者“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他抨擊教條主義者是懶漢,因為“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澤東在認識論與思想方法上對矛盾特殊性的強調,與朱子對“分殊”的強調,實可謂一脈相承。
我們再從毛澤東使用過的幾個譬喻來進一步把握其“分殊”思想,不妨先重温毛澤東在1956年8月同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的談話。他在談話中曾使用了一個譬喻:“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專門講了思想方法問題,強調獨創精神。他在回顧了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經驗後指出:“基本路線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葉不同。”所謂“枝葉不同”,表達的正是“分殊”之理。
值得指出的是,類似的譬喻,朱熹在論“一本萬殊”時就曾使用過: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如今學者只是想像籠罩得是如此,也想像得個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如一源之水,流出為萬派;一根之木,生為許多枝葉。
1961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講話時再次使用了枝葉譬喻。針對蘇聯方面對中國的攻擊,毛澤東説:“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們也反對。我們無非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這是一個樹幹和枝葉的關係,有什麼好反對呢?”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他在樹幹枝葉喻後隨即又提出一個楊柳松柏喻。他説:
每一種樹都是不一樣的,楊柳和松柏就不一樣。同樣是楊柳,這一棵和那一棵是有差別的。同樣是松樹,這一棵和那一棵都是有不同的。各國具體的歷史、具體的傳統、具體的文化不同,應該區別對待,應該允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具體化,也就是説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樹幹與枝葉是本原與派生的關係。而且,兩者在意象上均為實體。樹與楊柳松柏則是一般與個別、抽象與具體的關係。“樹”是名、一般性範疇,而“楊柳松柏”則是實,各各不同的具體實在。松柏與楊柳之間不是派生關係。顯然,較之樹幹枝葉喻,楊柳松柏喻之“分殊”意味更勁。
毛澤東提出這個譬喻,恐與當時中蘇關係的惡化不無聯繫。1958年,毛澤東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就曾表達過對蘇聯人傲踞無禮的強烈不滿,指責“俄國人有的看不起中國人”。除斯大林外,他特別點了米高揚的名。他説:“我對米高揚在我們八大上的祝詞不滿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議。很多代表都不滿意,你們不知道。他擺出父親的樣子,講中國是俄國的兒子。中國有它自己的革命傳統,但中國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也不能勝利,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能勝利。”他還跟尤金説:“我們要學習蘇聯,但首先要考慮到我們自己的經驗,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為主。”看來,米高揚就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所做的父親兒子比喻,深深刺激了毛澤東。他提出的楊柳松柏喻則與之針鋒相對,強調中國自有其獨立的革命傳統,而反對把中國革命視為十月革命(本原)的派生物。
阿納斯塔斯·伊凡諾維奇·米高揚,蘇聯政治家,曾於1949年1月31日-2月7日秘密訪問中共機關所在地西柏坡。
無獨有偶。清初理學大家陸世儀不滿意於朱熹混淆了“理一分殊”(一般與個別的關係)與“一本萬殊”(本原與派生的關係)兩個不同性質的命題,曾對之做出區分。他説:“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説下;理一分殊,猶言理雖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説開。”陸世儀所謂“分別説開”,亦正是毛澤東強調中國有它自己的革命傳統的政治用意所在。朱熹在闡發理學義理時常使用水喻,如前文提及的“如一源之水,流出為萬派”。為了進一步説明“一本萬殊”與“理一分殊”的區別,陸世儀也針鋒相對採用了水喻。他説:“譬之於水,一本萬殊者,如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個水,而江河湖海各自不同也。”“一本”之水,講的是源與派的問題;“理一”之水,講的則是同一性(一般)與差別性(個別)的問題。陸世儀認為,“理一分殊”的要害在於“江河湖海各自不同”。我們不難看到他的江河湖海喻與毛澤東的楊柳松柏喻在神韻上的相似之處。
以上可見,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與宋學“理一分殊”論之間存在高度的同構性。它透露出兩者之間存在的某種思想傳承關係,而這也正應了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説的“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那句話。
當然,**必須看到,“理一分殊”的具體內涵在這一轉化中發生了實質改變:毛澤東用“矛盾”這一辯證法範疇取代了“理”這一理學範疇的位置;矛盾論又建立在實踐論的基礎之上。“實踐”這一唯物論範疇,其豐富內涵(包括“造反”)則是舊儒所謂“行”所無法涵蓋的。**就此而言,以辯證唯物論為本,毛澤東的“理一分殊”論已大大突破、超越了中國傳統哲學。因此,準確地説,所謂繼承指的是“批判繼承”,或馮友蘭所謂“抽象繼承”。
行文至此,我們仍面臨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毛澤東本人在他的著述中畢竟沒有直接使用過“理一分殊”這個表述。那麼,我們論證的所謂“承繼”,是否僅僅是一種邏輯上的暗合呢?筆者認為,毛澤東對朱子的“理一分殊”論或曾有所聞見,茲舉例為證。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壽辰大會上講過一句名言:“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有趣的是,論及世間道理,朱熹曾有一句名言:“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個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非常顯而易見,以上兩句話在修辭結構上存在高度同構性。難道這純屬巧合嗎?筆者以為,最可能的是毛澤東借用了朱子語錄的修辭形式來表達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理解。前文曾提及,毛澤東在青年求學時代就曾研讀朱子著述,對《朱子語類》中記載的言論不會陌生。而“千頭萬緒”這句略帶俏皮的話,則如雪泥鴻爪一般,為我們提供了毛澤東出入朱子理學並曾接觸到“理一分殊”這一説法的思想蹤跡。
如果我們的推斷合理,那麼毛澤東的思想方法所展示出的“理一分殊”意藴,就不是無心的暗合,而應是有心的化用。他在這句話中給宋儒的“理”賦予了全新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內涵——造反、革命。“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內容,民族形式——這正是毛澤東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之義。
6
結語:毛澤東的思想、中國文化
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生根,離不開中國的文化土壤。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就已經有了很深入的認識。1943年5月26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做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時指出: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削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同日,中共中央關於執行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的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發揚光大。”決定進而指出:“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今後更加深入地與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可見,毛澤東所謂“民族化”(或“中國化”),意味着馬列主義不僅要與中國實踐相結合,與中國歷史相結合,而且要與中國文化相結合。
那麼,中國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具體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歷史實踐中,馬列主義與中國思想文化是如何結合的?這就成為亟待探討的重大文明史問題。
早在1985年11月,毛澤東的前秘書胡喬木在一次關於中共黨史研究的討論中就曾指出:“中國文化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中國為什麼能接受馬克思主義?我們很需要認真研究,答覆這個問題。……中國歷史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有那些特色?究竟在哪些問題上結合了?還要研究。”1991年11月,胡喬木在與逄先知、金衝及討論如何編寫《毛澤東思想概論》時再次提出:“毛澤東思想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不講這個不好。只講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跟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還不完全。它有一個歷史背景,有一個文化背景。”1998年6月,費孝通在與台灣學者李亦園的談話中也提出:“馬克思主義進來後變成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後來又發展成了鄧小平理論,這背後有中國文化的特點在起作用。可是這些文化特點是什麼,怎麼在起作用,我們卻説不清楚。我覺得,研究文化的人應該注意這個問題,應該答覆這個問題。”無論是共產黨人還是如費孝通這樣的學界識者,都深切地意識到中國革命及毛澤東思想內在藴含的中國文化特點。然而,對於這些文化特點的認識,需要我們就其複雜的脈絡與隱微的機制做深入的梳理與發掘工作。
本文即沿此問題意識所做的一個初步的探究嘗試。筆者認為,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經驗上形成的指導性思想方法——原則與表現、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乃是對宋明理學“理一分殊”論的繼承。當然,我們還要看到,同是“理一分殊”之道理,毛澤東卻把宋儒的宇宙本體論轉化成了革命行動論。理論原則固然是一,但不應成為束縛行動的教條,而應是引導行動的指南。如此,他的思想方法達成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的主體性與創造性的張揚。綜上,“理一分殊”可謂毛澤東一以貫之的思想方法,而正是這一思想為珍視中國經驗、注重中國特點、探索中國道路提供了重要理據。
行文最後,筆者想指出的是:當年毛澤東大膽地採用“實事求是”這一“漢學”的思想綱領來會通馬克思主義,今天我們也不憚於揭示“理一分殊”這一“宋學”的精華義理,作為理解毛澤東如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另一把鑰匙。至於毛澤東的思想中“實事求是”與“理一分殊”這兩大中國化理路之間的內在聯繫,則是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重大理論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