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再也不會去動物園了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0545-2018-09-29 20:03
本文由公眾號單讀(ID:dandureading)授權轉載。
旅行,一件能讓很多人感到興奮的事情。但提到“旅行文學”,你又瞭解多少?
比起網絡上圖文豐富的遊記指南,文學聽起來總顯得嚴肅,旅行文學卻是一種自由、成熟、獨具個人風格的寫作。《正午 6 :舊山河,新故事》正基於此,進行了全新改版,首推“旅行文學”特刊。本期單讀選摘了其中的一篇文章,藉此換個角度看生活。
《正午 6 :舊山河,新故事》
台海出版社 出版
《這個冬天的動物園》
葉三
這個冬天快要過去的時候,我又去了一次動物園。想來上次去動物園應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拒絕去動物園,並且要求自己對它抱有中年朋克的憤怒。打倒兇殘的人類,打倒不自由!這當然是我將生活過於文學化的結果,某種自毀型的矯情。
在這個冬天快要過去的時候,我覺得我可以了。
遊歷一個動物園,線路很重要。我深深懷疑動物園的設計者工於心計——總是從爬蟲類開始。一些趴在玻璃後面,幾乎與假岩石混為一體的兩棲類動物。要站很久,才看到鱷魚的眼皮微弱地動了一下,或者尾巴。它們像一些白痴滿懷心事地瞪着空氣。它們在思考啥呢?我嘗試去感受玻璃另一面的氣氛,寧靜而厚重。我想起大部頭的俄羅斯小説,然後我又想起名牌手袋。
冷血動物實在讓我沒法移情,小時候去動物園,總以為它們是假的,動物園做來騙我的。村上春樹跑去悉尼寫奧運會,也去動物園,他饒有興趣地記下澳洲人叫鹹水鱷“小鹹”,淡水鱷“小淡”,思及至此,我覺得自己不配寫小説。
一條粗壯的蟒蛇被飼養員握着,另一個飼養員用粗棍子將一隻小白鼠捅入它嘴裏,再繼續捅下去。握着它的手不勝憐惜地輕輕揉搓脖子假設在的部位,讓白鼠順利通過。蟒大概不覺得自己有脖子。小白鼠的尾巴在蟒蛇嘴邊很不情願地消失掉。人們舉着手機,驚歎着拍攝這難得的一幕。
我從來沒在動物園裏見過白鼠、蒼蠅和蟑螂。從來沒有一本正經的牌子告訴我它們的來歷出身和習性。這不公平啊。
禽類令我愉快。不會遊的在地上啄啄走走,歪頭看看,再啄啄走走,嘮叨忙碌的樣子。會遊的優雅地浮在水面上。一羣火烈鳥聚在一起,一大團一大團的肉紅色,乍一看,像內臟被翻了出來。我遠遠地看了一會兒。不開屏的孔雀拖着大尾巴走過去。各種號碼的鸚鵡,顏色極鮮豔,分門別類站在枝條上,像幾羣不同黨派的議員集合開會。看起來很好吃的肥肥的珍珠雞。看起來不太好吃的倔強的野雉。
我覺得應該把禽們和兩棲爬蟲類放在一起,以某種當代藝術的設計思想隔離着混搭。也許鱷魚們會活潑一些,而禽們會深沉一些。
極大的一間露天籠子,外罩鐵絲網,裏面,本該生活在高原上的鷹和鷲,認命地與竄訪的麻雀飛在同一個高度。這就很折墮了。我很快地離開那裏。
據查,動物園裏的猛禽有罰沒的,有來自社會救助組織的,還有自己飛來留下的。“我們有苦衷啊。”我想它們會這樣告訴我。
一頭長頸鹿的生平。“ 1978 年生於日本橫濱, 1980 年被贈與上海動物園, 1993 年 7 月 12 日早晨突然腹部劇痛,犄角抵牆,慘不忍睹。雖經全力搶救,終告不治,於上午九時半而亡,留下出生僅 28 天的第六胎幼鹿,哀叫不已,令人唏噓……”這頭名叫“海濱”的長頸鹿被做成了標本,現在站在玻璃箱裏,警醒人類,它死於“誤食遊客拋擲之食品塑料袋”。
“海濱” 四足孤苦伶仃,毛已半褪。它還活着的同類們伸長脖子,去夠樹上的葉子。所有食草動物的眼睛都是毛茸茸水汪汪的。五歲那年我摸過一頭老牛的鼻子,它轉過頭來慈祥地看着我,我記得它的眼睛。
賈雷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寫,可馴化的動物都是可馴化的,不可馴化的動物各有各的不可馴化。“總之,在全世界作為馴化候補者的 148 種陸生食草類大型野生哺乳動物中,只有 14 種通過了試驗。” 他舉了斑馬的例子,來論述這條安娜卡列尼娜定律。不曾被馴化的動物,要麼拒絕在眾目睽睽下做愛, 要麼對人類而言利用價值太低。
[美] 賈雷德·戴蒙德 著
謝延光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
作為賈雷德的旁證,斑馬用屁股朝着我,大象用屁股朝着我,驢也是,野牛和犛牛也是。
六年前我第一次去青藏高原,也是冬天,看到枯黃的草原上一大羣一大羣悲壯的犛牛,驚呆了。同去的攝影師跑下車,對着吃草的犛牛拍了又拍,犛牛靜默着反芻,天長地久地站着。我鳴笛催攝影師上路,一大羣犛牛聽到,一同緩緩地莊嚴地抬起頭,幾百對犛牛角轉過來,嚇壞了攝影師。
不知不覺,我已置身於哺乳動物之中。大象臭得敦實,狐狸臭得陰險。土狼焦躁地在斗室裏一圈圈小跑,夾着一泡尿的樣子,也像丟了什麼東西在找。更像我有稿要交又寫不出的狀態。不禁百爪撓心。
獵豹冷漠地趴在樹根下,我看見它周身無懈可擊的線條。 1960 年,人類第一次成功在動物園中使一頭獵豹出生。這是人類特別有興趣馴化的物種之一,因為它們跑得比最快的獵犬還要快得多。但誰又見過獵豹在動物園裏奔跑。我猜我正看着的這頭豹從來不曾在草原上奔跑過。
當今動物園裏的動物,野外捕捉已經很少。小部分是友情交換(好多換來的動物因水土不服而死去),大部分靠人工繁育(所有動物園裏都有一大羣人專門忙這個)。賈雷德認為,在人工環境中繁育是被馴化的一條重要特徵——賈老師你看,動物園便是人類從動物馴化史上生生挖下來的一塊牆皮。
▲人工飼養的小獵豹
經過企鵝館,我沒進去。企鵝屬於特別難繁育的野生動物——“中國的動物園和動物保護研究所可以向中國國家海洋局極地考察辦公室以“用於極地科普教育”名義提出申請,獲得批准後由南極科考隊負責捕獲。”好好地在冰上走着,一不小心就被捉來,放在玻璃房裏供人看,再怎麼豁達,也會覺得自己命運多舛吧。我寧可所有企鵝都生活在好萊塢的動畫片裏,能歌又善舞。
孩子們站在老虎和獅子的雕像前供父母拍照。雕像比真的老虎獅子好看很多。動物園裏,這兩種動物永遠在它們的地盤上躺着,有沒有太陽都在曬太陽。老虎的肚皮一起一伏,一起一伏。一個男子大聲叫它:“老虎!過來!”老虎不為所動。這是對的。
黑熊站起來,對着高牆外的人們作揖,然後一偏頭,熟練地張口接住一個桔子。人們遂開心了。人們在遠遠的熊貓前自拍。成年大熊貓總讓我有打掃衞生的衝動,想用刷子在它身上使勁刷,刷出許多肥白的泡沫。它們髒死了。人們臉貼臉地看着猩猩。大猩猩的表情太像人類,猩猩館太像人類的精神病院,讓我害怕。我快速地走過這些地方。
我在狒狒山停留了很久。領頭大哥帶着夫人坐在高台上捉蝨子。母狒狒餵奶,公狒狒打架,幼崽們追逐打鬧。這裏又熱鬧又安詳,我可以看很久很久不膩。也許是因為狒狒山完整地呈現了一個多層次的種羣生活,而又生氣勃勃,我覺得整個動物園最合理的地方就是這兒。
一隻成年狒狒坐在離狒狒羣稍遠的地方,專心致志地玩弄自己的陰莖,它把它拉出半尺長,仔細地端詳。它的陰莖是鮮紅的。我看着它,覺得它很像我熟悉的某個人。到底是誰呢。
這個冬天的動物園不再讓我悲傷或憤怒。走出大門的時候,我思考着為什麼。也許是沒精力再矯情,也許是麻木。我覺得無趣,乾笑着凍到了牙牀的那種無趣。在那裏我沒有與任何一隻動物對視過,除了“海濱”。我不打算追問它們來自何方,死後又會到哪裏;更不打算追問動物園存在的意義,以及如果可以選擇,動物們會不會自願生活在動物園裏。
有人告訴我,應該在春天的夜晚去動物園,據説那時,大型猛獸會露出它們的原始面目,整夜整夜地奔突和咆哮。在想象中的一個春夜,我翻過高牆,面對一頭猛虎,而它面對一杆槍——這不是危險,而是卑劣。
我想我再也不會去動物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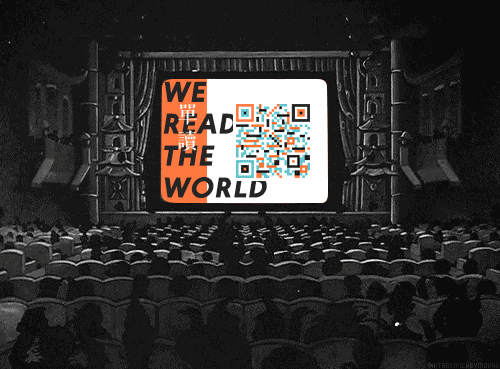
▵長按二維碼,關注單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