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如何書寫近代史?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8-10-08 13:00
【編者按】
在如何書寫近代史這一問題上,王鋭老師此文通過評述孫歌教授《歷史與人》一書中對1950年代日本學者關於“昭和史”論爭的研究,提供給了我們一個如何更好的書寫中國近代史的極佳參考視角。
通過對比孫歌的“昭和史”論爭研究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一些問題得以顯現,諸如,“複雜的國民情感”如何在結構性的分析當中刻畫出來?如何汲取更多的思想資源來作為研究歷史的重要參考?在“豐富的思想能量”於傳承過程中出現了問題的情形下,是否能夠通過重新回到文本本身,來探討其中藴含的“思想能量”?
在王鋭看來,這些問題實為思考如何更好的書寫近代史之時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本文原刊於《東方學刊》2018年第1期,感謝王鋭老師授權保馬!
如何書寫近代史?
王鋭
在20世紀中國,“中國近代史”這一寫作體裁的出現,與中國遭逢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迫使時人必須面對與思考中國的癥結何在、世界的景象為何、時勢的邏輯如何把握、未來的出路如何達到等關乎中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息息相關。因此,如何敍述、闡釋晚近的歷史流變,對於探索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至為重要。從梁啓超用“中國四十年大事記”作為李鴻章傳記的另一名稱開始,到1930年代蔣廷黻、陳恭祿為南京國民政府學以致用的近代史通論,以及范文瀾、胡繩、何干之、華崗等左派史家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原理分析近代中國的各種問題,可以説在現代中國,中國近代史雖然不斷被賦予一定的學科屬性,但卻從來不能只從學科的意義來理解其內涵(或“範式”)。這在冷戰之後中國多種意識形態共存、論爭、糾纏的語境裏,表現得尤為明顯。甚至刻意強調這一主題的歷史寫作的“學術性”、“規範性”本身,背後也帶有極強的現實訴求與文化、政治想象。
因此,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即如何在一種富有思想意涵的歷史觀之下,更為全面、細膩,甚至靈動的敍述近代史,在呈現歷史變革大勢的同時,將生活在這段歷史當中的個體的心理、情感、思慮儘可能生動地描繪出來。按照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屬辭比事”與“疏通知遠”至為重要,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歷史提供的正是抽象理論表達所不能窮盡的複雜面向,並在此基礎上提供探索思想遺產、是非判斷與行動空間的可能性。
正是在這一點上,孫歌教授對1950年代日本學者關於“昭和史”論爭的研究,在筆者看來,給予了我們一個反思如何更好的書寫中國近代史一個極佳的參考視角。這場論爭源於日本三位馬克思主義學者在1955年末出版了一本旨在反思近代日本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軍國主義的《昭和史》,隨後引起文藝評論家龜田勝一郎的批評,以及之後許多歷史學者與社會科學工作者紛紛就歷史研究與書寫問題展開討論。作者除了梳理這場論爭的“基本問題”,更着眼於“對於論爭中那些有可能引發結構性調整的‘轉化’的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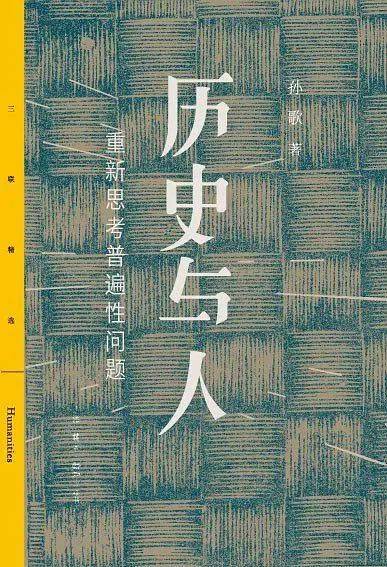
《歷史與人》 孫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標題: 重新思考普遍性問題;2018-1-1
作者指出,《昭和史》的作者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立場與方法,強調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階級鬥爭等結構性話語出發,論述昭和時期日本的政治、經濟、金融與國際關係等問題。而龜田則批評這一分析模式忽略了作為個體的人的情感與心理,難以呈現時代氛圍中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情感”與“國民的聲音”。龜井甚至認為,這種寫作特點乃日本左右翼所共存的弊病,“它使得社會高度同一化與機械化,它導致語言變成咒符,導致感覺與精神頹敗。”在作者看來,昭和史論爭建立在兩種對歷史不同的理解之上:一方強調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着眼於分析社會事件的性質,挖掘人民羣眾的抗爭力量;另一方則認為,歷史的核心要素應該是富於感情的人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羣體。
不過更引起筆者思考的是,作者如何透過龜田的批評,來評價《昭和史》的作者們所確實忽視的問題。作者認為:
《昭和史》所嘗試的科學性與客觀性,由於針對着是這種複雜的社會性感情記憶,它的“高高在上”在事實上就意味着一種政治姿態:它否定了充溢於日本社會的那種很難言説、很難找到形狀的“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否定了以對抗美國為背景被建構起來的從肯定被害體驗到肯定侵略戰爭歷史的動向。但是這種政治姿態也難免會帶來另一方面的缺陷,那就是它不僅使自己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日本社會最複雜的國民情感問題,而且由於把這種複雜的國民情感簡單地等同於右翼民族主義立場,就在事實上把日本戰後社會歷史記憶的形塑工作讓給了右翼,失掉了打造社會歷史記憶的其他可能性。同時,在歷史敍述層面,這樣一個超越了複雜感情糾葛的視角,固然可以使所有歷史事實都變得“一目瞭然”,但它卻必定要犧牲歷史過程中特有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
就中國史研究而言,按照梁啓超所設想的“新史學”,其中“史家之目的,在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之生活息息相關,而因以增加生活之興味,睹遺產之豐厚,則歡喜而自壯;念先民辛勤未竟之業,則擻然思所以繼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觀其失敗之跡與夫惡因惡果之遞嬗,則知恥知懼,察吾遺傳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矯之也。”以此為基礎,具體到如何認識人在歷史中的活動,梁氏聲稱:“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若暫且不論梁氏此處所受的德國哲學之影響,他針對中國史研究,同樣強調了在勾勒一條歷史敍事線索的同時,需注意到將人的豐富活動在歷史流變中呈現出來。通過不斷地展現這種活動的豐富性與多樣性,進而挖掘歷史中所藴含的思想遺產與實踐經驗,通過不斷回溯歷史、解釋歷史,為更好的理解當下與未來提供豐厚的理論資源。
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為了更好的實踐這一事業,就要思考作者所提出來的問題,即“複雜的國民情感”如何在結構性的分析當中刻畫出來,如何在敍述歷史的過程中充分重視歷史所特有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更為關鍵的是,如果説歷史記憶能具體而微的影響當代人的時代感覺與政治文化認同的話,那麼一旦嚴肅的歷史敍述忽略了人的情感與心理因素,那麼歷史記憶的“形態塑造”工作,很可能就拱手相讓給另一類人。後者借豐富歷史場景之名,訴諸大量的“私人記憶”、“個體經驗”、“隱秘回憶”,將本來或許只是某一及小羣體的歷史片段,刻意放大成為一個時代的集體風貌,並在其中注入本身並不“複雜”的另一種意識形態言説。這樣的結果之所以會大量出現,作為其對立面的正義的歷史與社會科學研究者,或許也應充分進行自我檢討與反思。同時還必須正視作者對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者進行的解析:“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日本的抽象化和絕對化,是與政治和社會現實生活中日本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各種摸索、挫折、失誤和創新並行不悖的。”
此外,作者還關注了由昭和史論爭所引起,但與其核心部分保持一段距離的另外一些討論。通過分析上原專祿與加藤週一在1957年進行的一場對談記錄,作者指出,上原強調“歷史學的邊界”,其意涵在於:
因為過強的危機意識,往往會衝破這種邊界意識,以非歷史的方式處理歷史,以便直接介入現實,這種貌似緊貼現實的“學術”,實際上與不具有緊張感的書齋學問一樣,既不會真正影響現實,也無法為思考現實問題提供幫助。
“以非歷史的方式處理歷史”,主要基於對現實的強烈關懷,但若因此而將歷史簡化成為一二教條或口號,那麼在犧牲歷史本身的複雜性同時,更不可能對現實有何參考。這一點,無疑提醒了許多歷史研究者,如何在以現實作為思考出發點的同時,能與現實保持適當的距離,並拓寬歷史的豐富可能性,是一個需要進行細膩處理的重要問題。
與之相關,作者指出,上原的談話另一個要義,是對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的知識分子論提出委婉的警惕。在上原那裏,知識分子應具有庶民性格的説辭,本身就已經知識分子化了。而關鍵在於,在具體的學術工作當中,“如何成為擺脱‘知識分子性’的知識分子,而不在於宣佈自己不是知識分子。”這一觀點是對《昭和史》的作者們那種戰鬥啓蒙心態的委婉質疑。如果説歷史的主體是生活在各個時間段裏的人,那麼歷史研究的主體便是歷史學家。後者如何在書寫歷史時保持良好、正確的心態、情感、立場,對於一項好的史學作品能否問世極為重要。上原的這番批評,可以説非常引人深思。
在作者的這項研究裏,另一引人注目的,應該是將丸山真男在同一時期的思考納入《昭和史》論爭的視野當中。作者深入解讀丸山的名篇《斯大林批判中的政治邏輯》,認為其政治學研究處理到了如何在複雜歷史場景中面對具有多個側面的人的問題。關於丸山這些思考的意義,作者指出:
關鍵並不在於歷史是否寫人,而在於歷史是否僅僅依靠宏觀的整體性把握就能夠呈現出它豐富和複雜的內涵,在於以明確的“法則性”是否可以有效地解釋不斷變動的歷史。歷史寫人,並非是以“與歷史人物邂逅”為目標,而是找到那些在無數因果關係中進行選擇的關鍵環節。恰恰是這些環節提供了理解歷史動態性與不確定性的媒介,而它們卻無法被整合進抽象原則中去。
在清末,當社會科學理論初入中國,對如何認識中國歷史逐漸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之時,章太炎卻認為:“夫因果者,兩端之論耳。無緣則因不能生;因雖一,其緣眾多。故有同因而異國者,有異因而同果者。”而“愚者執其兩端,忘其旁起,以斷成事。”他特別強調:“今世社會學者多此病”。可以説,與丸山一樣,章太炎也注意到了面對“不斷變動的歷史”時,如何準確尋找到無數因果關係中“關鍵環節”的重要性。並提醒若無這種自覺性,很可能會將複雜的史事簡化為充滿武斷的條例。長期以來,在近代史研究中,這一弊病其實並不少見。而這也是另一種表面豐富內裏乾癟的歷史敍事,能夠不斷被複制再生產的主要原因。
此外,作者注意到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關於個體意志與歷史結果的論述,在這場論爭中屢次被不同思想背景的學者所援引。在恩格斯看來,要把費爾巴哈學説裏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作為在歷史行動中的人去考察。”關於如何理解恩格斯的相關主張,並對之進行闡發,日本學者之間展開了頗有深度的論辯。與當時全球範圍內的冷戰氣氛不同,作者指出,恰恰是這一點,“昭和史論爭中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表現出的彈性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表現出的誠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乾燥性格,並在大於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推進了關於歷史學學科自覺的建設性思考。”不止是對恩格斯,毛澤東關於矛盾轉化的思想,也成為當時論爭中被重視的一項理論參考。如今冷戰結束20餘年,世界局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可是類似於日本學者的那種“誠意”,似乎依然難得一見。如何提高近代史討論的品格,如何共同探討近代史中的時代主題,挖掘作為思想資源的歷史遺產,恐怕仍舊荊棘遍地、任重道遠。
很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如是總結昭和史論爭:
或許昭和史論爭最大的價值也在這裏,它不僅引導我們重新回到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回到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發現唯物辯證法精神是如何在創始者那裏藴含了豐富的思想能量,反思對於這筆寶貴精神財富的傳承出現了什麼問題;而且引導我們重新思考,如何以真正的辯證唯物主義精神把握作為“過程”的世界,在這個疾速變動的歷史過程中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今天,在近代史領域的史料方面,其實已經有極大的擴充,甚至讓人有難窮盡之嘆以。但是在史觀方面,在敍述歷史之前所應具備的理論基礎與價值立場方面,到底是多元還是簡單,是豐富還是貧瘠,恐怕不是一個十分容易回答的問題。如何汲取更多的思想資源來作為研究歷史的重要參考,正如作者所言,在“豐富的思想能量”於傳承過程中出現了問題的情形下,是否能夠通過重新回到文本本身,來探討其中藴含的“思想能量”,實為思考如何更好的書寫近代史之時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