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在課堂上講什麼?——一位大學文科教師的工作記錄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18-10-14 11:16
有的網友看了我談教學的一些文字,問我上課是怎麼上的,有什麼經驗。
還有些也教大學思政課的網友説,自己感到上政治課很難講出什麼新意。
其實,別看我説了那麼多,但我上課並不好:
其一,下面學生不聽的、缺課的都是一大把,我經常得靠點名和不斷批評人來維持教學秩序;
其二,我也沒有去刻意講究什麼教學技巧,經常出現預定要講的部分講不完的情況。
不過,我上的課大概也不能説一無是處。那麼,這些許的“是處”在哪裏呢?
記得剛到這所高校來工作的時候, 系裏一位領導曾經問過我:
“你是學西方哲學專業的,可是在我們這裏你上西方哲學課恐怕不是主要任務,更多地是要承擔馬克思主義公共課的教學。你覺得這和你的專業不衝突嗎?你能協調好這中間的關係嗎?”
我回答時大概説了三點:
“首先,不管我學什麼專業,首先我是共產黨員,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是我的職責,這個我決沒有二話;
其次,我的馬列主義水平不高,這確是事實,但這不是因為學西方哲學導致的,只是我自己沒抓緊學習罷了;
第三,學西方哲學,並沒有讓我懷疑或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是讓我在對比之下更加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優越性:許多西方哲學史上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比如思維與存在的關係,事實與價值的關係,自由與必然的關係,等等,據我所知馬克思主義都予以瞭解決,或者説,提出了全新的解決思路。所以,我對於馬克思主義是衷心認同的,當初我學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想從思想史、哲學史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所以上政治公共課,我能不能上好,這不好説,但我一定會認真地去上。”
所以,如果説我的課還有一點可取的話,其實就只是這一點:
我認同馬克思主義,所以我覺得去教馬克思主義,並且以這個思想為指導去講授西方哲學,不但是在教育學生,而且也是在全方位地教育自己,昇華自己。
我很多次不能按預定計劃把那一次課要講的講完,有時候是因為,我會放下課件或教案裏下一步本來要説的內容,彷彿不由自主地講出這樣的事先根本沒有準備的話來:
”同學們,剛才我們講了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的辯證關係的幾個要點。但我還想強調一下:發揮主觀能動性來認識和實現客觀規律性,尤其在社會領域裏,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時候是要經得起非常嚴峻的考驗的。
我小時候讀過一本書,叫《真理的追求》,是講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入黨的故事。其中説到了毛主席在一師時的老師徐特立是怎樣入黨的。 徐特立本來已經是很有名望和地位的教育家了,國共合作大革命的時候他是國民黨員。那個時候革命進展很順利,有人要他加入共產黨,他説不急,他還沒看出共產主義比三民主義好在哪裏。
結果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背叛革命,共產黨到處被通緝,被抓捕,被屠殺。 這時候,徐特立覺得他看明白了:那些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到處在屠殺共產黨,這説明共產黨是好人哪,共產黨能救中國啊。
這個時候他就到處去找共產黨,終於讓他通過一個學生找到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一個負責人。
兩個人就在鄉下一個大院裏的一間房子裏見了面,隔壁就是當地的土豪在説殺了多少共黨,殺得多痛快。
就在這樣猙獰的聲音不絕於耳的時候,徐特立對那個負責人説,我想入共產黨。
那個負責人説,我們黨現在處境很危險、很困難,到處在被殺頭。
徐特立説:
我是來“投機”的,投的就是這個殺頭之“機”,就是奔着這個殺頭來的,就是要爭取這個被敵人殺頭的機會。我就是擔心自己五十多歲了,我這顆頭不知道敵人還要不要,要的話我就太光榮了。你們是不是也嫌我老不要我?
那個負責人很感動,説,我們怎麼會不要您呢?您在這個時候來入黨,會給同志們多大的鼓舞啊。
這就是徐特立入黨的故事。我當年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也很感動,可我那時候才小學三四年級,懂什麼馬克思主義?
但我就覺得這樣的人是好樣的,是英雄,從哪個角度看都是英雄:人家看到共產黨被那樣屠殺,覺得害怕;他看到共產黨被壞人殺,他不想別的,他教數學的,他邏輯推理,就認定共產黨真好,這一認定,就偏偏在血雨腥風最危險的時候去找黨,入黨。
所以毛主席非常敬重他的這位老師,在延安的時候為老師祝壽,寫信給徐老説:
你二十年前是我的先生,現在也仍然是我的先生,以後你必定還是我的先生。

(毛澤東與徐特立)
所以説,追求真理,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有時候要發揮的主觀能動性,就不是一般的主觀能動性,那需要多大的見識、決心和勇氣。但是,能讓千千萬萬的人這樣捨生忘死不顧一切去為之奮鬥,這也正好説明他們要去實現的那種客觀規律性實在是太強大了,太有力量了,太不可抗拒了……”
其實,在教西方哲學的時候,我有時也會插入申述自己的一些本來並沒有寫在講義裏的看法——有時僅僅是西方哲學範圍內的:
“我們剛才講了康德的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的區分。那麼綜合判斷分兩類,一類是經驗判斷或者叫後天綜合判斷,這類是以經驗為基礎聯結主謂詞,比如:一切物體都有重量;另一類就是先天綜合判斷,這一類就不能以經驗為依據來聯結主謂詞了,比如: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有其原因。為什麼這一類判斷不能以經驗為依據呢?康德認為,這是因為經驗提供不了這類判斷中所有的那種普遍必然性。
(按講義講到這裏,不知道為什麼,又開始突發奇想了)

(康德)
當然這裏就有問題了,有同學可能就會想:一切物體都有重量,這個命題不也有普遍必然性嗎?可它又是一個經驗判斷,後天綜合判斷,也就是以經驗為基礎聯結起來的,那為什麼經驗在這個判斷中又可以提供這種普遍必然性呢?這豈不是很矛盾嗎?我當年讀這個《純粹理性批判》的時候,就覺得這裏彷彿是有矛盾的呀。
那這個矛盾怎麼解決呢?以前我和一些老師討論這個問題,覺得大概有兩個思路:
一是什麼叫做先天綜合判斷,它恐怕不僅是看這句話本身,而是還得看你這話是怎麼得出來的。像一切物體都有重量這個話,如果你只是通過一個個觀察物體,發現你觀察到的物體都有重量,於是你像休謨説的那樣,進行習慣性聯想,猜測你沒觀察到的物體也會有重量,於是得出一切物體都有重量的結論。如果這樣的話,你的這個結論貌似有普遍必然性,但其實沒有,其實它是説,你觀察到的物體有重量,你猜測那些你沒觀察到的物體多半也會有——因為後天經驗加習慣性聯想,能提供的只是這些,所以這樣一來它就只是一個後天綜合判斷。但你如果不是這樣,而是運用康德所説的純粹知性範疇,比如實體性等範疇,去能動地綜合經驗材料,那你作出的結論,一切物體都有重量,就真的有普遍必然性了,雖然看起來好像還是那句話,但它的認識價值就不同了,它就不是後天綜合判斷,而是先天綜合判斷了,但這個普遍必然性不是來自後天經驗,而是來自先天的純粹知性範疇能動的綜合作用。這是其一。
其二呢,我們或許也可以這樣看,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認為一切物體都有重量只能是後天綜合判斷的話,而且即便如此,它也有一定的普遍必然性,那麼這裏面物體的概念、重量的概念都是來自經驗,它們的聯結也是經驗來提供基礎:你今天看到一個物體有重量,明天看到一個也有重量,所有你觀察到的物體都有重量,於是你就把這種經驗的相對普遍性擴展成完全的普遍性。在這種情況下,你的經驗其實還是部分地為你的這個判斷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了依據的,只不過不完全。所以在這裏,結論與根據的差別還只是一個量的差別——有些物體有重量你觀察到了,更多的物體以及這些物體有沒有重量你沒有觀察到,所以你的結論所斷言的範圍比你的經驗所提供的要大一些。那麼在先天綜合判斷裏,比如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有原因,這就不同了。如果説“物體”、“重量”這類概念總還是有經驗性的成分,那麼“原因”這個概念,是經驗性觀察完全不能提供的。你很多次看見物體有重量,但你一次都沒有看見發生的事情有原因,你只是看到甲事件之後有乙事件,或許你看了很多次,但你一次也沒有看見過甲是乙的原因,甲引起乙。換言之,你在經驗中看到物體與重量的那種伴隨關係,至少可以部分支持你對這一伴隨關係的普遍斷言;但這個“原因”是你在經驗裏一次也看不到的。那麼這種普遍必然性,它和後天經驗就不是一個量的差別,而是一個質的差別了。經驗性的東西不是能部分提供根據,而是完全提供不出這個普遍必然性的根據了。
總之,一切物體都有重量的這個普遍必然性,你要麼把它理解為一種真正的普遍必然性,和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有原因一樣,那麼經驗就完全不能提供,要麼理解為一種作為經驗的擴展的普遍必然性,那麼經驗可以部分地提供。但即使在後一種理解中,我們仍然可以説,這種普遍必然性是不嚴格的,比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有原因要低一個檔次。總之就是經驗可以部分地支持某種較低層次的普遍必然性,但永遠完全不能支持嚴格意義上的普遍必然性。 這個話插得太長了,而且只是我個人想法,不見得都恰當。只是不管怎麼説,康德的這兩個劃分是很值得琢磨的。好了,接下來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康德對純粹理性批判的總構想……”
有時,也會涉及到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現在我們看洛克的實在本質也好,後來康德的物自體也好,他們都認為是不可知的。因為我們只能知道客體在我們眼中的表現,知道客體刺激我們之後所呈現出的樣子,這不是客體自身的本來面貌,而只是我們認為客體是什麼樣子——而他們認為這兩者是有原則區別的。至於客體如果不刺激我們,它的本來面目是什麼樣子,這些現象後面是什麼樣子,那我們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這就是所謂不可知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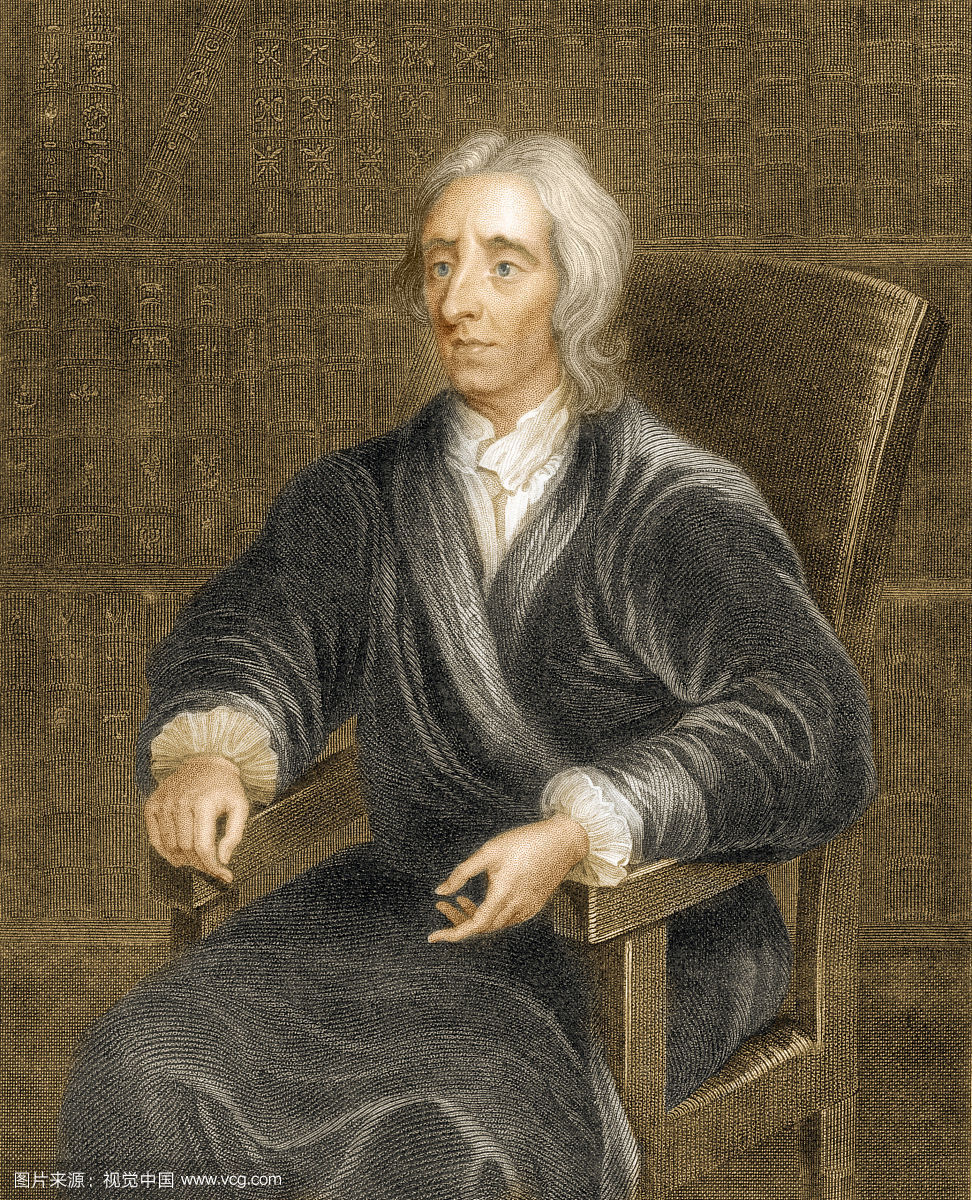
(洛克)
那我們就得指出,這種不可知論就是這些哲學家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在認識論上給他們造成的侷限。
我們知道,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
那麼按照這個實踐觀,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我們不能光等着物自體來刺激我們,更重要的是,我們得反過來刺激它,也就是通過實踐來能動地改造它。
如果你光等着客體來刺激你,那你當然就會困惑:它裏邊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是永遠不會來刺激我們的,是老躲着我們,不讓我們認識的?你會覺得這説不定啊,要真這樣的話,我們也拿它沒辦法啊,因為我們只能坐等它刺激嘛。所以洛克、康德他們的不可知論傾向,從根源上説,就是這麼來的。康德當然是發揮了認識的能動作用,認為客體是我們能動地構建的,所以對於這個我們自己構建的客體,我們當然是有把握徹底認識的。
但他這個能動性只是一種思想範圍內的能動性,是因為我那麼去感受,那麼去想。但物自體是在你思想範圍之外的自在客體,你對它還是無可奈何。而且你越是發揮能動性,越是把你主觀固有的一些感性形式、知性範疇一層層加進去構建客體,你所構建的這個客體似乎就越來越深地陷入你的主觀世界,離那個完全在你之外的物自體反倒是越來越遠了。你所謂對客體的認識,只不過是把自己加進客體的東西抽出來,發現這些東西總是用來整理物自體刺激你產生的那些感覺材料的,於是你覺得一方面這個客體雖然是我構建的,但總還有物自體給我的材料在裏頭,不是我臆造的;另一方面,我對它的構建本身也還是按一定規則進行的,不是亂來的。所以你覺得有理由認為,這個由思想構建出來的客體,也還算有客觀性(就它感性材料的出處是物自體而言),而我們對它的構建也是有序進行的,這樣我們算是把一種普遍必然性賦予了這個一定意義上也還算客體的東西。
但我們不難看出,這種普遍必然性,康德是不敢相信它屬於物自體(也就是本來意義上的客體)本身的。
這歸根到底是因為他只是在思想中構建客體,而沒有認識到人首先是在行動中,在實踐中構建客體。人僅僅在思想中構造的客體及其普遍必然的規律性,當然只能理解為是在物自體的外部,跟物自體的本來面貌有不可逾越的隔閡的,但人們用行動構建的客體,以及通過這種行動所實現的認識,則是逐步深入到物自體的內部去的。
在實踐中,我們刺激物自體本身,迫使它作出反應。這些反應,有些是我們如果不這樣刺激物自體就永遠看不到的,比如我們用某種高能射線轟開原子核,看到了噴射出的帶正電的質子流和不帶電的中子流。如果我們只是坐待刺激,那就永遠看不到這些。現在我們刺激了它,改變了它,並且繼續觀察它被我們改變之後的進一步反應,這就把物自體一步步變成了我們實踐活動的一個內在的環節。
如果你覺得對這個實踐活動的其它環節的把握(比如經驗現象)不成問題的話,那麼你也不應該認為對物自體的把握就存在什麼原則性的障礙。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對康德等哲學的超越,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就是對實踐把自在之物不斷轉變成為我之物,不斷打破所謂現象和本體的界限這一點的理解和闡發開始的。
所以,我們學習西方哲學,心態要端正。可千萬不要抱着一種覺得馬克思主義很樸實,説起來太平淡,不能引人注目,説一點康德黑格爾才顯得很高深,很酷的想法。這種心態我覺得是不太健康的,也是很難真的理解包括康德黑格爾在內的一切真正有價值的哲學思想的。
樸實往往是真理的標誌,深刻之中的樸實、平常,與生活渾然一體,才是最有價值的。”
—— 以上是我上課時説的有些話,有些是把我在幾個或幾次不同的課上講的關於同一個主題的話(比如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的關係),集中了一部分到這裏。 我的教學計劃、課件和教案、講義裏都沒有這些話,這些話也不見得就對,或者就有什麼水平或價值。但我確實就是這麼去上課的,而我這樣去做的唯一理由,就是我覺得,一位教思想政治和哲學這類課程的共產黨員,任何時候都不能停止思考,而且要激發和引導學生去思考。
遠方那位教思政課的同志説她講不出新意,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所講的那些話,算不算有點兒什麼新意。我只是覺得,我們這些教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得高度關注現在的時代特點,特別是我們的教育對象的特點和發展態勢:
我們現在要去教的九零後、九五後這一代人,對於我們國家的命運,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命運,有着特殊重要的意義。 他們從小生長在全球化時代、信息化(互聯網)時代、物質豐裕時代、市場經濟時代,以及中國逐漸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時代。 ——這一代大學生,將成為中國新一代工人階級的中堅。
而由於上述的時代特點,這一代工人階級其實是中國第一代完完全全經歷了市場經濟乃至全球資本主義洗禮的,同時又是文化水平較高,有條件對人生,對社會進行更理性、更深入的思考乃至上升到理論層面的人。 這樣的一代人,這樣的一代工人階級(當然他們大部分不是體力勞動者),以數以千萬計甚至數以億計的規模,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出現在世界的東方。這是一件大事——很大很大的大事(我上課經常這樣説廢話,海涵)。
我從自己的教學經驗中體會到:
第一,決不能輕視這一代人,那些歷史條件決定了他們在總體素質上要遠遠超過他們之前的那幾代人——比如我們這些七零後。所以,他們對老師的要求可不低;
第二,決不要以為他們天生就反感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他們所處的環境和所接受的信息,讓他們並不會在西方的東西面前就盲目自卑,他們見識更廣,對國家更有信心,對待各種社會思潮,事實上會有一種比他們以前的七零後、八零後更加客觀公正的態度。問題在於,老師們要注意到,他們會以他們特有的、他們覺得有趣的方式來表達這種態度,而往往不是以我們原來所期待的那種方式;
第三,要恰當認識他們對個人價值的追求。他們的確非常看重自己個人價值的實現,包括對高品質的生活享受的追求,並且會把這一切公開講出來(我參加過兩三次我校大學生職業生涯設計大賽的評判,對此深有體會:有的女孩甚至會説,找個好人嫁了,也是自己大學生涯的目標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很多人會主動尋求把這種個人價值的實現與某種集體的、國家的目標聯繫起來。在這方面,他們事實上非常需要並且期待老師的引導。 學生是不需要我去刻意迎合的,事實上他們能夠理解老師與他們的不同以及老師對自我的堅持,因為他們自己也不願意去違心地迎合別人。
但問題在於:我與他們的這種不同,是不是有價值呢?它到底是我自己以及人民羣眾生活實踐和智慧的結晶,是我對前人思想融會貫通的領悟,是我對某個課題認真的精神勞動的結果,抑或僅僅是一堆我背誦下來的教條,甚至是我的某些格調比學生還不如遠矣的庸俗想法呢?
早在五十多年前,毛主席就説過,從那時起,五十年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發生空前深刻變化的時代,是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這個歷史正在我們眼前展開,它將要考驗九零九五後這一代人,以及之後的好幾代人,但首先是考驗作為他們老師的我們:
能不能擺脱我們自己的某些習慣性的偏見,某些集體無意識的陰影,某些悲觀沮喪心理,某些自以為是的惰性和世故,去更加嚴肅認真地進行我們自己的精神生活?
我在這些方面做得並不好。 但我能夠肯定的是:每當我默默地用這些問題拷問自己的時候,不論是在看書學習,還是在備課上課,我的狀態就會稍好一點。前面列舉的我上課時講的那些話,就是在這種稍好的狀態下説出來的,它們或許能夠證明:
説着這些話的人,至少在那一刻還存着一點誠實和認真。 以上就算我的一點工作記錄和感想吧。
國慶節假期過去不久,最後説一點有關國慶的回憶:
高中時,有一年國慶前夕,學校請了一位姓陳的老紅軍給我們作革命傳統教育的報告。
陳老是四川人,當年是紅四方面軍的一名紅小鬼。他個子不高,但是精神矍鑠,目光炯炯,穿着一身綠軍裝,戴着勳章,作報告前先給我們行一個軍禮,我們回應以熱烈的掌聲。 陳老説他小時候家裏很窮,穿的是“皮鞋”,什麼皮呢?人皮——十冬臘月赤着腳走路,可不就是人皮鞋嘛。
參加了紅軍以後,陳老認識到:紅軍好。一是為窮苦人打天下,解放全中國,讓老百姓過好日子這個目標好,得人心;二是紅軍紀律嚴明,和羣眾的關係好;三是打仗的時候,幹部帶頭往前衝,撤退的時候,幹部在最後掩護,所以大家一條心,不像白軍當官的叫當兵的“給我頂住!”自己卻先跑了。
——説到這裏,老人倒是替敵人嘆了口氣,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説: “唉!怎麼頂得住喲?!這樣的部隊怎麼能打仗喲?!碰到我們還不只有繳槍當俘虜?!”
話鋒一轉,陳老説: “現在我們共產黨也有些人變成這樣囉:叫下面人幹活,他自己貪污好多萬。這是共產黨啊?這是烏龜王八蛋!和國民黨那些烏龜王八蛋一個樣子嘛!”
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陳老接下去説: “不過,有人問我:老爺子,是共產黨好還是國民黨好?我講:國民黨壞,不過國民黨裏也有好人,也有清官兒,也有抗日的英雄,但是它搞的那個社會黑暗啊;共產黨好,解放了全中國,老百姓日子好了,不過共產黨裏也有烏龜王八蛋!這是那些人壞,不是黨壞。這個還是要講清楚!”
此外,印象最深的,就是陳老講他當通訊員第一次執行任務的故事:
“那時候我還只十多歲人,連槍都沒得,就挎了幾個手榴彈。回來的路上,讓二十幾個敵人跟上了,一路追起我跑。我沒辦法就爬上一棵樹,敵人就圍起喊我小赤匪快投降。我心想,今天硬是要拼命嘍。我就朝下面喊:好,我投降,我把包扔下去!敵人就圍攏來抓我,我看到他們走近了,就是兩個手榴彈扔下去,轟,轟,報銷他幾個。”

(當年的紅小鬼))
這時陳老像當年一樣,很孩子氣地笑了:
“嘿嘿,格老子叫你狂!我就趁着敵人死的死,傷的傷,一片混亂,一溜煙兒下了樹,跑了。要是不跑啊,嘿嘿,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裏囉!”
全場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陳老又説:
“你們現在是趕上好時候嘍。我十多歲出來當兵,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幹革命,打了幾十年仗,負過好多次傷,要是哪一次犧牲了,也就沒了。哪像你們現在,有書讀,有這麼好的學校上。好日子要珍惜,學習不要偷懶,長大了還是要為國家做點事。要好好學習喲,不然,陳爺爺知道了,對你們不客氣喲……”
陳老講的話都很樸實,但是同學們雖然一開始個別的有點兒淘氣,也有點兒沒聽明白他的口音,後來大家還是聽得很專注,也還是非常愛聽的。
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就是無數這樣正直、勇敢、堅強、樂觀的英雄們建立起來的。所以我們的共和國,也同樣具有這正直、勇敢、堅強、樂觀的品質,巍然屹立,氣象莊嚴。
當年長征的紅軍都是陸軍,而今共和國的運載火箭與核潛艇都以長征命名,這就是偉人所的中國人民“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豪情壯志與英雄氣概,是在告訴我們:
新長征的目標,是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