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絕版譯製小説《外交家》,看今日美國的嘴臉_風聞
李禹东1988-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8-10-16 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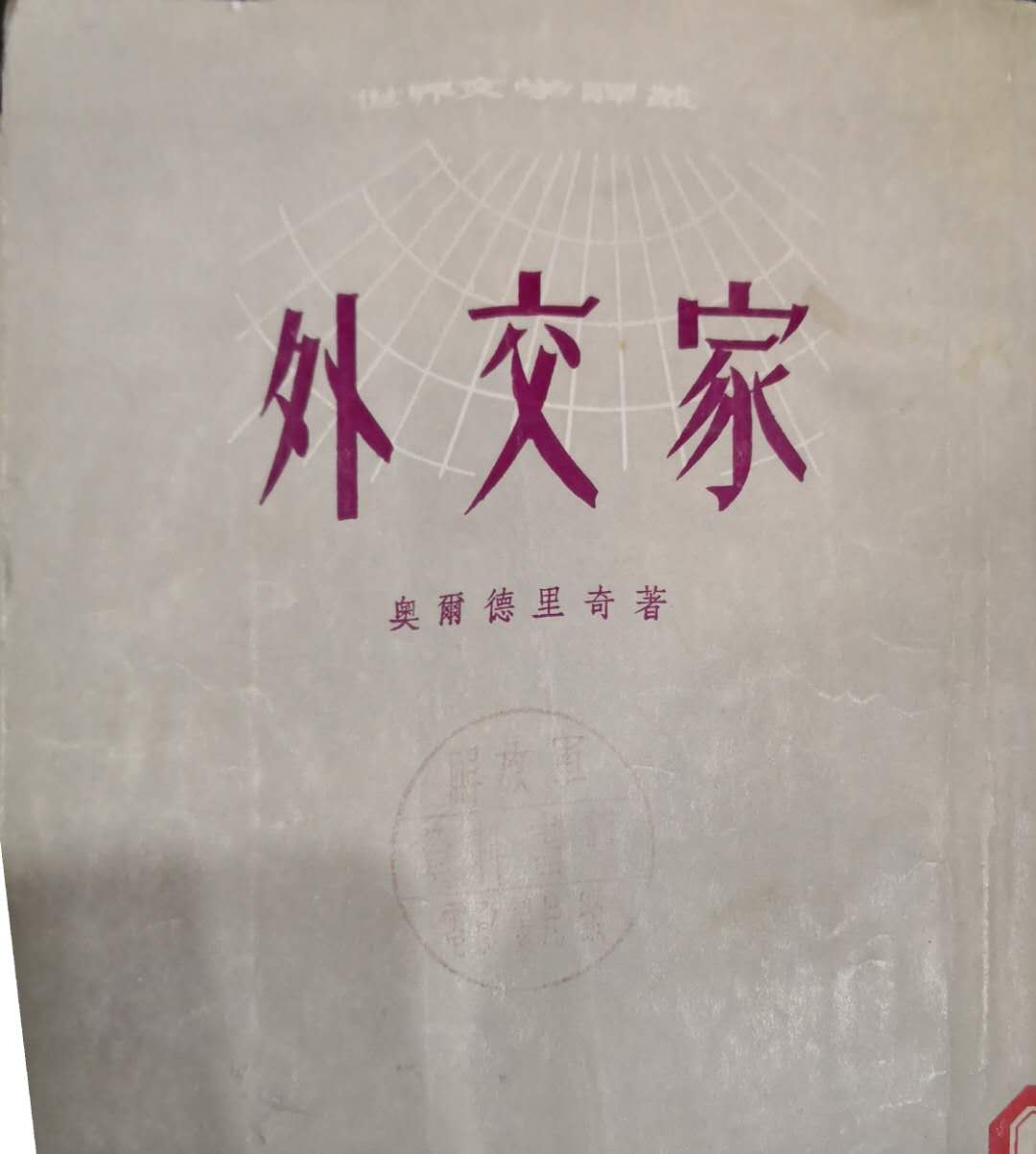
歷經了二戰的血雨腥風,愛好和平的人們,或許還未能在慶祝勝利的喧鬧中感到盡興——然而,我們這個焦躁的世界,卻並已並不打算繼續那麼歡鬧下去。對於世界未來秩序的構建,這個星球上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主流觀點。
一種叫做資本主義。另一種,便是社會主義。
兩種觀點在一段長時間的發展過後,逐漸形成了兩股強大的勢力。眾所周知,前者的代表,是西方世界的頭號強國——美國。而後者的代表,便是在“十月革命”後迅速崛起的超級大國——蘇聯。
兩股力量在戰後迅速做大,一個覆蓋着西方,另一個囊括了東方。
正如我們如今所理解的那樣,在對於財產分配、社會結構等問題上,兩種思想體系分歧嚴重,彼此對抗。正因如此,以此為紐帶所形成的兩個集團,從一開始,就顯得格格不入。
而在1946年3月5日,兩個相互對抗的集團,終於隨着老牌帝國主義列強——大英帝國的前任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城威斯敏斯特學院的一場演講,捅破了彼此之間最後的一層窗户紙。
在這場演講中,丘吉爾以極端的言語,號召全體“民主國家”,向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展開鬥爭。
整個世界一片譁然。
這場演講在後來被稱作《鐵幕演説》——它揭開了二十世紀那場曠日持久的、“冷戰”的序幕。
而這場東西方的全面對峙,正是小説《外交家》故事中的時代大背景。
和許多嚴肅歷史題材的小説類似,這本小説成功地將一個真實的邏輯、裝入一個虛構的故事中,從而用極盡藝術的手法,揭開了一段歷史的面紗。
而在這面紗之下,有些西方世界的思維邏輯,卻又與我們今日的世界一脈相承,實在無法不令人感同身受。
自1905年起,由英國人創立的英波石油公司,便牢牢地掌控着伊朗的石油資源。二戰以後,強勢崛起的美國,為了同樣的目的,亦將其勢力滲入其中。為更好的相互協調,兩個西方的巨人於是在彼此間達成了一種分贓的協議,不遺餘力地維持着其當地封建腐敗的政府,以保其長久控制這一重要的資源。
得到了美英兩座靠山,伊朗封建勢力於是愈加肆無忌憚地作威作福、壓榨人民。久而久之,這片在數千年前曾一度象徵着財富的國度,只剩一片荒涼。人民窮困潦倒、衣衫襤褸,整日整夜地在生死間徘徊,在痛苦中呻吟。
然而,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面對這每日每夜垂死掙扎的生活,當時尚屬於伊朗的一個地方,掀起了一場民主革命——這個地方就是阿塞拜疆。這場革命的目的,正是要推翻腐敗的德黑蘭政府,建立一個富有生氣的、嶄新的國家,只是,這場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化的。他們從一開始就要將諸多被私人資本家控制的國家資源,重新收歸國家。
這,足以引起西方勢力的恐慌。
於是,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故事的主人公——一位聰明絕頂且經驗豐富的英國外交家艾克賽斯隆重登場了。在英國方面看來,伊朗的革命,絕不可能依靠其自身的力量獨立完成。可如果不是靠其自身力量,那麼環顧四周,最有可能成為其“幫兇”的勢力,當然可能、也必須只有一個——那就是蘇聯。
艾克賽斯就是帶着這樣一副有色眼鏡空降到蘇聯的。他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通過談判,要求蘇聯撤出其二戰以後在伊朗的全部軍事力量,停止對伊朗的一切“干涉”。
只可惜,英國人的認知與事實完全不符。一個被壓榨到無法生存的民族,她的革命運動,本身就擁有着廣泛的羣眾基礎。事實上,對於阿塞拜疆的革命者來説,為了保持其自身獨立性,對於蘇聯勢力的介入,他們非但不願意接受,而且還帶有着某種微妙的牴觸心理。他們不願在未來趕走一羣豺狼的同時,又迎來另一條豺狼。也正因如此,艾克賽斯在蘇聯的外交活動,本質上,就成了一場無理取鬧。
經過幾輪談判,這位英國紳士最終見到了蘇聯領袖斯大林,可他的要求,最終一無所獲。那時候,在伊朗境內駐守的,不只有蘇聯勢力,美英勢力也同樣存在。斯大林認為,如若要求蘇聯撤走所有力量,美英也應該同時、對等撤走其勢力。而至於阿塞拜疆革命運動因蘇聯勢力而起,至於對蘇聯破壞戰後相關和平條約的指控——這一切都顯得毫無道理。蘇聯對阿塞拜疆的運動奉行“不干涉”原則,並同樣要求西方的勢力,也必須按照約定,對這一地區嚴格遵守這一原則。
不過為了自證清白,斯大林最終還是決定為這位英國外交官在邊界上開一道口子,請他深入阿塞拜疆,去那裏走走看看,親自調查一下當地革命運動的原委。
只可惜,所有人都被他騙了。這位資深的外交家從一開始,就壓根兒沒有想要深入過什麼阿塞拜疆。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英國政府都絕不可能允許阿塞拜疆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順利完成。被擺放在枱面上的理由全都是假的——他們唯一在乎的,依然不過還是那兩個字——“石油”罷了。
艾克賽斯深知,蘇聯必須是這一運動的幕後指使者——即使它不是,也必須在輿論宣傳和聯合國大會上,把它變成這樣的角色。因為,只有蘇聯的“干涉”,才能成為英美勢力對這一地區進行干涉的合法依據。真正想要干涉他國內政的,是他們自己。
與此同時,打着深入調查的幌子,艾克賽斯踏上了另一種旅程。
他開始四處扶植地方勢力,拉攏咯德(庫爾德)內部的一部分極端分子,賄賂之,以將其改造成一支親西方的隊伍,從而與阿塞拜疆革命政黨相互對抗,同時維護英國在伊朗的石油特權。
而至於伊朗普通百姓的疾苦,至於他們無從醫治的病患、無從安身的現狀,他絲毫不放在眼中。
等到所謂的調查最終結束時,在大英帝國整個上流社會的讚歎中,他回國了。接着,他開始通過媒體等各種渠道,全時段、多角度地將一個早已構思好的故事一點一點裝進人民的腦子裏。蘇聯干涉了伊朗內政、恐怖的共產主義正在全世界蔓延、共產主義政黨將要毀滅大英帝國。接着,對蘇聯的指控,便被提上了聯合國安理會的議事日程。
讀至此處,一個畫面忽然鑽進了筆者的腦中。就在今年(2018)早些時候,俄羅斯雙面間諜突然在英國遭到神經毒劑襲擊,接着沒過多久,甚至在調查還未展開之時,英國人便率先發難,一口咬定俄羅斯為“幕後真兇”。事情的結果,正如大家所知,俄羅斯以鐵證反擊,英國方面最終不得不尷尬收場。
在政治立場上,筆者並非一個十足的“親俄派”,但就這樣的事件而言,大英帝國這種運用於不同時代的、自導自演的手法,實在有點一脈相承的味道。
但在故事中,就在聯合國安理會即將召開之前,有一個人卻終於按捺不住。這個人叫做麥克格雷高爾,是個出生於伊朗的英國人,本是個地質學家,是英波石油公司的科學工作人員,二戰時進入軍隊,事後被分配到外交部印度事務部門,在小説中,由於看重他精通多國語言和伊朗出生的背景,艾克賽斯將他選為了自己前往蘇聯和伊朗時的特別助理。
但恰恰是因為出生於伊朗,這位麥克格雷高爾自幼就對那個苦難國度裏的人民有着深刻的瞭解,也恰恰是因為此次出行,在與艾克賽斯的交流中,他終於理解了伊朗人民苦難的真正根源。他本是一個科學家,他並不明白艾克賽斯這個政客理解事物的出發點,他只是深深地同情着那些可憐的人民,也隨着這一路政治陰謀的歷程,陷入了一場對道德的深邃思考。
最終,在身為一個人的良知下,他再也無法抑制內心的衝動。在政客的虛假輿論中,他站了出來,幾經周折、冒着生命的危險,以詳實的第一手資料,揭穿了英國勢力對伊朗罪惡的企圖,最終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暫緩提出其對蘇聯方面的指控。
而他的下場——在朋友的幫助下,通過政府內部重要人士的幫助,在自己的名譽遭到嚴重抹黑、甚至被全社會描述為“賣國賊”之後,勉強保住了性命,但卻失去了自己作為公民本應享用的一切福利待遇。
他回到了伊朗。回到了他的科研崗位上——但他決心繼續鬥爭。
就這樣,故事戛然而止。
故事的作者名叫詹姆斯·莫爾德里奇——看上去,像個蘇聯作家的名字。但事實上,他是個徹頭徹尾的英國人。
我所閲讀的版本,出版於1953年,出版單位為“文化出版社”。
我閲讀本書的時間,是距離那個年份遙遠的2018年。
然而,世界卻從來不曾改變。
蘇聯解體了。蘇聯的解體,自有其自身的嚴重問題,但一個對手的轟然倒下,卻並不能改變西方世界對於超額利潤的瘋狂追求。
如果你瞭解歷史,回首雅典的一場被西方世界捧為“希臘民主基礎”的梭倫改革,你就不難發現,為了平衡邦內階級矛盾,梭倫通過法律,強行將城邦內所有的奴隸變回了公民,並贖回了被賣至外邦的本邦奴隸,同樣賦予其公民權。
看上去,他確實是個偉大的政治家。
然而,他的改革卻並沒有真正促進生產力的變革,也並沒有將雅典帶入一個真正更加文明的高度。很多年以後,雅典城內的奴隸數量,竟然飆升到了總人口的50%——只不過,這些奴隸全都是從外邦得來的。
梭倫的改革,也不過只是通過對弱小的鄰邦轉嫁矛盾,從而用以維持其舊有制度罷了。
這樣的做法,羅馬繼承了。
中世紀繼承了。
現代的西方,也同樣繼承了。
小説《外交家》中,作者通過一位工黨覺醒人士的話,提到了這樣一個問題:
美國人雖然自稱是英國的盟友,他們不斷地給英國投資、幫助英國發展、為英國繼續力量——然而,這一切的核心,卻是美元經濟。想要得到大批量的援助,英國必須與蘇聯對抗,同時也在一點一點地幫助美元經濟,建立更加穩固的霸權地位。不止英國——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全都如此。
美國人憑藉其早期所積累的強大經濟力量,悄無聲息地、以這種手段滲入每一個國家,可有誰想過,它的經濟一旦發生了問題,金融危機的海嘯,則勢必將迅速擴散,作為金主美國,它本身可以通過其國際貨幣的優勢條件,將危機的風險轉嫁給它的盟友們。
但,它盟友的危機,又將有誰來承擔?
而至於那些美元經濟和美國政治無法徹底入侵的國家,它或者訴諸於武力,又或者將其塑造為一個長期的敵人。
蘇聯正是這樣的敵人。
2018年的世界,蘇聯早已不復存在。但擺在那西方主子面前的,卻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對手。
那便是中國。
正如故事中所講的那樣,今日倍感壓力的美國,和昔日走向衰落的英國有着異曲同工的微妙之處。
它會向世界編造各種各樣的謊言,製造各種各樣的話題,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去抹黑、污衊,給你扣帽子、給你製造謠言。它還會通過它們那位副總統的嘴對世界喊話,聲稱“共產主義給人民帶來苦難。”
但它的目的事實上只有一個——而這個事實,他們的總統特朗普先生,在自己那場看上去與其副總統彭斯完全相悖的講話中,已經説的非常清楚:
“中國人過得太好了!”
真是有點滑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