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母的文化》:美國社會是否已經到了陰盛陽衰的時刻?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3987-2018-10-17 09:40
《殺母的文化》:美國社會是否已經到了陰盛陽衰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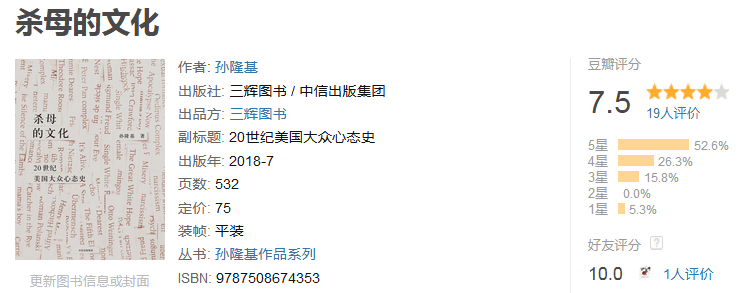
冷戰結束後,美國儼然是以世界霸主的席位自居,用一句不太恰當的話來講,就是雄風浩蕩,對世界上的看不順眼的刺頭,不由分説,動用武力與軟實力雙管齊下,讓其雌伏在美國的強大羽翼之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認為美國的大眾心態裏有一種陰盛陽衰的取向潛伏在各個社會層面,你能不能接受?
我想,在是否決定接受之前,首先會產生心理上的好奇。
現在這樣的看法,由華人學者孫隆基橫空出世的提出來了,而且用一本洋洋灑灑達47萬字的書來闡述這一主題,的確讓我們產生一種欲罷不能關注的強烈衝動。
這就是剛剛由三輝圖書策劃、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殺母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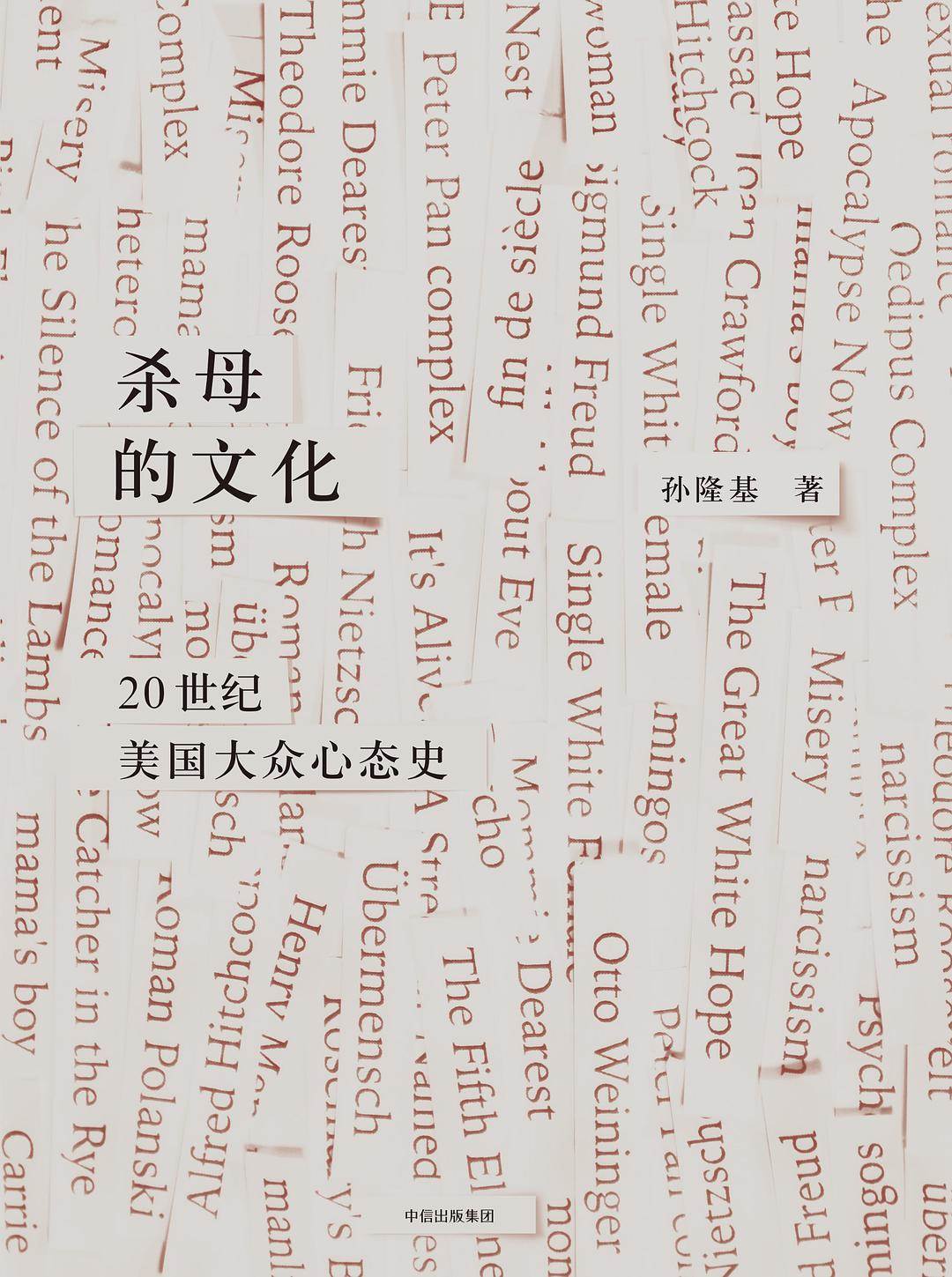
對於作者孫隆基,過去看過他所著的一本《新世界史》第一卷。當時對這本書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者用散文筆法來寫歷史,其中的一些句語帶有台灣學者寫學術論文的那種特有的散文化寫作傾向,讀起來很有新鮮感。
《殺母的文化》這本書,是孫隆基2009年出版的一本專論美國大眾文化的讀物,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給人一種文青的感覺,如果説《新世界史》裏,孫隆基忍不住欲對歷史的起承轉合,採取一種抒情筆墨與文學修辭來進行表達的話,那麼,在《殺母的文化》裏,我們看到了孫隆基繼續從文學藝術這個緯度來擷取美國大眾心態的素材,以此作為他立論的原始材料。
在這本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利用了大量的美國文學與電影作為他的資料提供者,從而使本書給人一種非常親切感,包括《星球大戰》《第一滴血》《阿甘正傳》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電影,都在作者的安排下,作為他透視美國大眾文化的一個切入點與觀察口。
作者認為美國大眾心態中有一種從“仇母”到“殺母”逐漸加深的心理軌跡,是不是這樣?作者是出於什麼動機,觀察到了美國社會的這樣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顯然,孫隆基所立足的中國文化背景,給了他觀察美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參照系與參考量。
他自己也毫不遮掩他之所以寫這本美國大眾心態的書的目的及觸發機制,正是“從美國人批判中國人‘母胎化’引申出來的一個論題”(見該書“新版序言”)。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母親是神聖的,不容侵犯的,怎麼到了美國,就有一種“殺母”的衝動呢?
這種疑惑可能是我們每一箇中國人都會產生的。而孫隆基也提到了在此書出版後,眾多身在美國的華人對他提出的這個觀點的質疑,很多人都説,並沒有遇到作者在書中提到的“殺母”現象啊。
孫隆基回答得也很巧妙,他説 ,長期在華的老美,也沒有看到中國人有“割股療親”與“郭巨埋兒”這類事啊。個人認為,這裏孫隆基實際上有一點犯了狡辯的毛病了,他所列舉的中國的“孝舉”都是古代的事情,與美國二十世紀的大眾心態傾向同時類比,這不是像關公戰秦瓊嗎?
但由此更加激發了我們對孫隆基如何闡述他的對美國大眾文化發現的好奇心。
孫隆基認為,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是美國“殺母”契機的開始,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是美國“男性殺母”的幻想高峯期,七八十年代,這種“殺母”傾向繼續流佈於社會,到了本世紀初,作者認為,即使女性“殺夫”與“殺夫”浪潮已退,但“殺母”依舊。
那麼,“殺母”這種集體意識為什麼會產生?作者從美國社會的變遷來尋找根由。
應該説,作者的脈線還是很清楚的。而美國發生的這種社會思潮的變化,也是世界上各個國家都有過的經歷。
作者認為,上世紀開端的時候,社會人文思潮中,“達爾文主義佔壓倒性優勢”,它的特點就是強化人的生物性,顯然達爾文拉近了人與動物之間的聯繫,但是一味地把人以動物的方式進行關聯性地探索,會讓人失去自我的獨特性。因此,達爾文主義很快走上了末路,今天,正如我們現在所感知到的一樣,達爾文主義在闡述社會大眾心理方面的確沒有什麼發言權。
而在這個時候,那個如雷貫耳的弗洛伊德大師開始大舉入侵美國的人文領域了,並一舉攻下了美國的思想界,至此,心理學成為美國思想界解析人心的一個重要的測試工具,並且在這一工具的操縱下,把“殺母”情結撥弄得如虎添翼,日漸紅火。
弗洛伊德有一個著名的性潛伏期説,書中在多處對此作了複述與詳解,我們隨便地從書的後半段的一個總結性闡述中,摘取對這個理論的簡易圖解:“弗洛伊德學説的‘性潛伏期’是指:男孩到了‘殺夫娶母’階段與爸爸衝突,遭到爸爸打擊,其後性慾的表現轉入收斂階段,待到成年以後重新恢復,在家庭以外另找對象。”(P379)
這就是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到的美國男性的“分離與個體化”,大意就是説,男性到了成年之後,就要脱離出父母,呈現出自身的“個體化”。摘錄一段書中對上述觀點的闡述:“美國的‘男性理想’其實就是‘個體的全面確立’,要求個人從環境中全面分化出來,並且還與之對立和保持一種支配關係。它勢必要求個體和人生早期徹底斷裂,而在人生早期具全面支配權的媽媽——那個自身個體化不徹底、一直在心理上混淆人我界限的兒童化女性——不可避免會構成對兒子人格成形的最大威脅。”(P110)
這時候,美國男人該怎麼做?作者分析道:“美國式的男性成長要求男人擺脱女人、擺脱媽媽、擺脱人我界限不明朗的狀態,才有足夠的、清晰的‘男兒性’去進行異性關係,換言之,才能真正地去搞異性戀羅曼史。”(P119)
也就是説,一個美國男性要健康成長,就必須通過母性這個水簾洞般的障礙,達到彼岸,如果在哪一個環節上未完成這一點,那麼,這個男性就會因為壓抑而導致心理異常,包括同性戀,都是這種異常的後果。
在這種心理學説的左右下,為男性成長必須通過“殺母”環節提供了合理性,而二戰到冷戰期間的全國徵兵,也凸顯出母親沒有讓兒子實質上斷奶,從而為“殺母”理論的成立有了社會環境的理由。五十年代的性革命,更為“殺母”火上澆油,因為性革命的主導者是女性,她們所欲推翻的是男性在性關係中的霸主傳統,“女性既然也能像男性那樣放心地享受性,勢必導致女性在心理與行為上的性解放,不是傳統式‘媽媽的兒子’型的男人能應付得了的。在‘被閹割’感日趨嚴重的情形下,美國男性‘殺母’的呼聲日趨尖鋭。”(P176)
當然,作者所説的“殺母”更是一種社會思潮,並不是一種直接可見的社會暴力,所以,質疑作者並沒有看到美國大面積地出現“殺母”的犯罪現象啊,其實,作者更多地立足於社會文化心理,來揭示出這個社會的隱性訴求,而文學乃至更為顯形的電影,更能潛在地反映大眾的心理傾向,這就是作者為什麼在分析美國大眾心態的時候,多是採用的是好萊塢電影來尋找證據。
這一方面顯示出作者畢竟是後期移居美國,對美國現實的社會面貌的感知時間畢竟不夠充足,特別是民間的社會心態,在還一時半會難以真正融入其中的情況下,更是難以真正地把握到核心關節,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從電影、文學這一社會思潮趨向的載體來透視整個社會的精神訴求,確實是一個非常的便捷的切入點。電影與文學中提供的信息非常博大,哪怕是一個字,一個用語,一個神態,都意味着作者對社會的明確定位,從電影與文學提供的立體圖景的一個側面,能夠很好地看清時代的特質,由此,我們會被作者的這一獨到的發現,去重新認識美國社會的隱性心態,同時,通過作者揭示出的社會大眾心態再去檢視電影與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也能夠觸碰到我們過去忽略掉的心理層面。
當然,對弗洛伊德那一套,中國人向來是不以為然,對把人心看成如此之複雜,幾乎難以理解,尤其是弗洛伊德那一套兒童時期的“口腔欲”“肛門欲”更是視着奇談怪論,嗤之以鼻,這也使得作者的書中羅列出的美國學者用弗洛伊德心理學原理去套用中國的現實時,會出現很荒唐的尷尬局面。但是由作者所牽引出的東西方文化的比較,卻是能夠看出美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巨大差異,作者選取了“殺母”文化這一個切入點,來透視中美文化的異同,可以給帶來我們一種觀察世界的新方法,至於它觀察到的結論是否是真實的存在,那麼,就有待於我們繼續深入地觀察並進而驗證真偽的進一步努力了。
(本文經作者葛維屏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