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老師:作為語言學家的啓功先生_風聞
章黄国学-2018-10-19 17:47
“葛郎瑪”重要還是語言現象重要?讓我們看看作為語言學家的啓功先生關於漢語語言學的新思路吧!
漢語現象和漢語語言學
——讀啓功先生《漢語現象論叢》
啓功先生《漢語現象論叢》(後文均簡稱《論叢》)1991年12月在香港出版,內地的讀者看到這本書的不多。後來有了大陸版,又收入了啓功先生的全集,才有了更多的讀者。能讀過本書,都感到新穎動人、妙趣橫生。書中涉及到的有關古代典籍文化、詩文音律的知識,年長者如逢故交,親切逼真;年輕者瞠目詫異,聞所未聞。這種書,只能是中國文化通家的大手筆所為。
在現代學科的分佈中,啓功先生的專業並不屬於語言學,他的專業被界定為“古典文學”或“文獻學”,啓先生對稱他的專業是“文獻學”很不以為然,所以我們成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時,啓功先生不願意用“文獻”來指稱他的學術,才改成了“典籍”。啓功先生的出身、早年經歷和自己的好學深思,造就了他睿智的學術眼光。青年時代得遇陳垣校長和其他幾位名師,又推動他學識的精進,他對中國古代文化獨到的體驗比比皆是。他在字畫碑帖鑑定上的精準、對傳統詩詞書畫的美學價值和內在規律的深入探究、對漢語漢字特點的獨到見解、對書法問題富有個性的態度……都可以用‘身懷絕技’來形容。尤其是他在表達上富有個性的言語方式,總讓我們想起一句話,叫做“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他的學養帶有綜合性,帶有經驗性,一旦把這些框到無論哪一個小格子裏——如古典文學、文獻學等等,原有的知識內涵就無法充分體現了,反而不如那些一開始就在小格子裏培養出來的人那麼適應。在漢語問題上,啓功先生並非不懂西方,但他對漢語的感覺是純正的、不含雜質的。《漢語現象論叢》是一位深刻體驗過古今漢語的通家對自己本國語言的真實體驗。

《漢語現象論叢》語言平易,如同閒聊;但是細觀本書,讀者自會發現,《論叢》絕不是為憶古拾趣而著的,而是針對着一個討論多年而不得解決、現時代又不能不解決的問題而發,這就是如何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漢語語言學問題。讀了啓功先生這本書,會引起我們對一些問題的深入思考。
一
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漢語語言學的顯學就慢慢變成語法,研究者們遵循《馬氏文通》來建立以語法為中心的研究體系和教學體系,希望通過對《文通》體系的修補,使古今漢語較為合轍地嵌入拉丁文總結的“葛郎瑪”中去,整整一個世紀不停地將二者磨合,甘苦説猶未盡,成敗論而難分。能不能另找一條路來建立一種完全從漢語事實出發的漢語語言學或文學語言學呢?《論叢》正是以這個宏大的論題作為全書的宗旨。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是從“小學”演化來的。“小學”研究的語言單位主要是書面語的詞,更偏重於其中的意義。漢字是表意文字,古漢字的形音義是統一在一起的,於是“小學”分成文字學(講形)、音韻學(講音)、訓詁學(講義)。《文心雕龍.章句》説: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為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淸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
古人的觀念很明白:要把漢語講懂、讀懂,把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所有的詞都弄懂了,句子、篇章當然也就懂了,挨個兒解釋對了所有的詞,就串成了句子;詞講錯了,連起來就不象漢語的句子,這叫“不辭”。他們不着重去把句子拆成多少塊兒來講結構,因為覺得沒有必要,既然詞義通了句子也就明白了,何必還要去從形式上分析句子呢?漢朝人作的章句,是以句為單位來解釋古書的,但也還是着眼在詞義。比如:
《孟子·梁惠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趙岐《孟子章句》:“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
這段話也就講了三個詞:一個“老吾老”的第一個“老”,一個“幼吾幼”的第一個“幼”,一個“運於掌”的“運”,意思全清楚了。所以中國傳統語言學最豐富的是講義訓、義理,並沒有一套成體系的句法。

《馬氏文通》把“葛郎瑪”引進了漢語,不論文言文還是白話文,可以把句子劃成“成分”分析它們的關係,這確乎是一個進步,但問題接着也就來了。啓功先生對這個問題有個十分形象的説法。他在《漢語現象論叢·前言》裏説,英語的詞有固定標誌,所以因性分類;但漢語的詞,用法太活,性質太滑,以英語套漢語,每有顧此失彼的情況,拿英語的辦法套漢語,如同用小圈套大熊貓,很難合轍。
此話不假。“老吾老”、“幼吾幼”第一個“老”、“幼”得講成動詞,而且是意動用法 ,第二個“老”“幼”得講成名詞。用這種格式一翻譯就成了“把我家的老人當成老人”,“把我家的小孩當成小孩”,意思並不跟古書的意思一樣。至於説“孟子將朝王”的“朝”是“受動”,“欲闢土地,朝秦楚”的“朝”是“使動”,得先把意思講出來才能判斷。《左傳》一個“門”字,可以當“城門”講,可以當“攻城門”講,也可以當“守城門”講,究竟如何區分三種講法,“葛郎瑪”實在無能為力,還得靠前後文把意思分析出來。最不好辦的是被“葛郎瑪”稱作“動賓短語”的那一堆詞語,“指示王”是“指給王看”,“爭杯酒”是“因一杯酒而爭鬥”,“頷之”是“向他微微點頭”,“攔道哭”是“在路上攔着哭”,“五月鳴蜩”,乾脆是“蜩鳴”……用一個“動+賓”格式一概括,原來讀文言文憑着語感已經弄懂了的句子,這一下反而不懂了。這並不是説,語法總結出的那些法則沒有用處或不正確,而是説,僅僅有“葛郎瑪”,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套不上是一個方面,即使套上了,也不能解決主要的問題。
這些還大半是散文,如果説起詩詞,那就更是套不上。不用説“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這樣的奇怪詩句用“葛郎瑪”分析不了,就是“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這種本來看得明白、想得出來、感受得到的句子,如果用“主謂賓定狀補”這麼一套,詩的意境也就煙消雲散了。
既然“小學”從根兒上被否定了,只認為語法才是“真正的語言科學”,近現代的語法學家,想了各種辦法,創出了許多體系,增加或改換了好多術語,想讓“葛郎瑪”和文言、白話合榫頭兒,實際上能合上的馬建忠早就合上了,合不上的----馬建忠就合不上的,他之後的語法學家也合不那麼準,或根本合不上。
從“葛郎瑪”延申出來的構詞法,想把雙音合成詞的兩個成分的關係用句法格式描述出來,不少詞是合上榫頭兒了,可也有些依然合不上。例如:“海拔”,“親戚”、“緘默”、“刻苦”……頭一個字(語素)和第二個字(語素)是什麼關係?要是不把每個字(語素)的意思弄清楚,再把來源出處弄明白,它們是“主謂式”、“動補式”還是“聯合式”?一下子還真説不出來。這些詞有的書面語味道濃一些,有的乾脆就是大白話,可是要追究組成它們的語素意義,大半還得找到文言裏去,這一下連白話、文言的界限都得打亂!總之,“葛郎瑪”提出的那些格式用到漢語裏既有多餘的,又有不夠用的、非另想辦法不可。
二
漢語語言學以語法為中心——而且走向單純從外部形式上搞“葛郎瑪”,也已有些年頭兒了。內容的貧乏和方法的不適應,已經引起了相當一部分人的關注。特別是文學界,因為“葛郎瑪”管不住豐富的文學語言事實,解釋不了五采斑爛的文學現象,便弄得文學家不買語言學的帳。按道理説語言規律應當能解釋語言的藝術,語言的藝術裏也應當能總結出語言的規律,可是好些語言的規律總是跟語言藝術的欣賞擰着。“葛郎瑪”説句子得有主語、謂語,而且主語多半應在謂語的前面,又説定語、狀語是附加在中心語上的,而且定語、狀語多半應在中心語的前面……可是到文學作品裏去查一查,不這麼擺的句子絕非一個兩個。於是語法學家管不符合“葛郎瑪”的那些句子、段落的安排都叫“修辭”,語法是正常,修辭是反常。這正和有些文藝美學、文學語言研究者的結論走到一條道兒上去了。美學家認為,要想文學豐滿、涵意深刻,必須“超越語言”。“超越”當然就是“反常”。這兩家的共同認識是:正常的語言準確而不美,沒有欣賞價值;非得反常才美,才經得起欣賞玩味。這不能不使人感到費解:為什麼正常的語言規律管不住文學作品的語言呢?是因為文學根本不是語言的藝術,而是超語言或反語言的藝術呢?還是那些被稱作“規律”的條條框框總結得有些問題呢?應當説,語言的變通是有的,但變通本身也應當符合一種規律。看來,要改造的不是那些能夠懂又能使人產生感受的語言材料,而是那些套不上漢語事實的“葛郎瑪”。
近年來,繼承漢語語言學的傳統,提倡“重視民族文化特點,建立切合漢語實際的漢語實際的漢語言學”的呼聲越來越高,很多人朝這方面努力,成效當然是日漸其大,但在有些領域裏,仍有兩種方法上的錯誤導向在起作用:一種是抓住幾條漢語的特例就奢談漢語特點,其實仍然沒有和漢語事實對上號;另一種則提倡考釋孤立的生語料,有的是一個一個考,也有的是一片一片考,但都是單個兒的語料堆砌,難以從中生出一種可稱作規律的條例。這兩種導向造成了兩種後果:前一種造成空泛,後一種造成煩瑣,應當説,都是研究方法的誤區。
怎樣走出空泛與煩瑣的誤區,儘快創建成熟的、切合漢語實際的漢語語言學?啓功先生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從漢語現象出發。一種法則切不切合漢語實際?看它能不能涵蓋漢語語言現象;還有沒有新的分析漢語的法則?也只有從漢語語言現象去觀察。
現象是事物在發展、變化中所表現出來的外部狀態和聯繫。通過外部現象來觀察內在規律,這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普遍方法,但是在語言學領域,還提倡得很不夠。語言學界強調的“第一手材料”,和“語言現象”並不是同義語。含有規律的現象並不是單個語言材料的堆砌,而是一種存在在許多語言材料之中共同的外部狀態。一種形之於外的狀況,如果不斷出現,想躲也躲不開,一不小心就“掉進去”了,這才可以稱作是一種有意義的現象,那裏面似有一種冥冥的力量在制約着它,這力量就來自語言的規律。把它捕捉到,概括出來,就是語言的法則。總結這種法則,才能適合漢語實際。
啓功先生在《論叢》裏説起他如何注意到漢語規律。他在《文言文中“句”、“詞”的一些現象》説:
歷年教古典文學作品,目的和方法不過是要讓學生了解古今文詞的不同。“五四”以後文言已不習用,講文言文必須説出個道理,説明那些話為什麼那樣説,變成另一樣為什麼意思就不同了……因此留心觀察那些文言文中有哪些現象,又從那些現象中探索它們的共同常態。
這就是從反覆出現的現象中觀察出的法則。《論叢》還指出,從正面觀察現象可以得到法則,從反面觀察現象也可以得到法則:
任何醫生,都要從‘病象’入手。看不懂古文,是病象;從不懂到懂,是治療過程;現在探索怎麼懂的,是總結治法。評選最有效的醫方。證明治百病的單方無效,也由此得到根據。(《前言》)
這一番話,把從現象出發來研究漢語的問題説得再透不過了:只有從現象出發,得到的法則才能解釋漢語的問題:只有從現象出發,才能講出符合漢語的規律;只有從現象出發,才能對付得了言語作品紛繁複雜的事實,而不致用“葛郎瑪”這個單一的藥方去治百病。這些説法都可以看出,啓功先生並不是認為語法絕對無用,只是認為,要真正符合漢語實際,套不上的不要硬套;而且,不要就用“葛郎瑪”一種辦法來研究、解釋、教學漢語,不要拿他來治百病。
三
從言語作品中出現的語言現象出發,宣告了語言學的研究領域必須擴大。這樣一來,僅僅從形式上歸納出的幾條公式和定律顯然不夠用了。僅僅以詞句為單位進行的語言本體研究着眼點顯得太窄了。把語言學限制在只管通不通、不管美不美的狹小領地裏當然更不符需要了。過去的漢語言學只能運用於散文,不能運用於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與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藴的典故之類,這自然顯示了當今語言學的一種貧血現象。
《論叢》從十分寬闊的領域裏,提出了探索漢語特點的新思路。我想,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1
從“僵死”的形式中追尋鮮活
《論叢》指出:
歷史上歷次的打倒,都只是‘我不理它’而已,它的存在‘依然如故’焉。我們作文章不用它的樣式,毫無問題;如探討漢語的種種特點,正視漢語的種種現象,就不能用‘我不理它’的辦法去對待了吧!(《前言》)
八股文是漢語語言作品中被否定得最徹底的一種文體,但它是吸取古代若干項文體陸續沉澱積累而成的。定型以後,又加以人為的擠壓,加上一些苛刻的條件,並且規定用來表述被統治者規定下來的僵化思想,因而導至這種文體的枯竭僵死。但是,這種文體中積累的那些文章技法、語言運用格式,仍然可以追溯到它鮮活的時期。
如果説得更透一些,一種世世代代被使用漢語的人接受、採用、推廣、生髮的形式,正是因為它藴藏着一種精華的東西,才能被人利用,利用得過分了,人為的限定多了,便容易僵死。對研究者來説,不應當因其僵死而忘掉追尋其中的精華。《論叢》舉出許多例子説明那些符合漢語特點的語言格式想扔也扔不掉,想躲也躲不開。比如唐宋古文家反對駢體,去偶求單,可是他們的散文一不小心就掉到對偶句裏去。又如,八股文的起、承、轉,合,接與比的格式,規定死了,限制人的創造性,可是沒有八股的限制,有些文章和語段,仍然跑不出這樣的格式。正是這種不自覺掉進去的地方,反映了一種民族語言的習慣甚至是一切語言的通則。

2
從變動的事實中尋求定則
語言在應用中是多變的,句法成分時常增減、顛倒,虛詞在語言中異常遊離,用法都不那麼固定。可是,漢語的表達並不如有些人所説的“缺乏準確性和完整性”。在前後語、上下文的制約和特定的語言環境中説話,從來都是明確的。因為變動,就使人抓不住定則,《論叢》指出:
所謂愈分愈細,常見有時把一個小虛詞翻來覆去,可列出若干個説法……如果將來規範化徹底完成,或説書面語十分固定之後,把這類遊離的小細胞畫出區域,不許亂動,那時才容易分析;否則它們常常把人搞得眼花繚亂,如在水裏抓泥鰍,稍松即跑了。(《文言中“句”“詞”的一些現象》)
又説:
從一個小虛詞到整個口裏説的話,都給它固定住。怎樣固定,固定成什麼樣子?無非是想使它們一一都符合‘葛郎瑪’而已。其實泥鰍也有它們的生活動態的規律,有待於細心觀察罷了。(同上)
這裏提出了研究語言完全不同的兩種思路:一種是按別人總結的法則來套漢語,希望把活語言框住;而另一種則是按活的語言現象來歸納法則,承認變動之中也有定則。
所謂從變動中歸納定則,首先要承認變動不居不等於隨意而為,變動是在一定的範圍內、受一定條件的限制、按自身變動的可能性來進行的。找到變動的範圍,提出變動的條件,把它們與語言自身的可變因素結合起來,便歸納出了定則。這種“則”,可以管住漢語中的各種現象,是屬於活的漢語的法則。如果不這麼做,看見一個變化套不上“葛郎瑪”,就列出一條“例外”,“例外”一多,就宣判漢語不具備準確性、規律性,豈不是倒行逆施!
3
從所謂的“超常”中發現正常
前面説過,因為用“葛郎瑪”來套漢語,“超常”的“變例”就出現得很多。可是“變例”又反而具有巨大的表現力,常常能構成優美的詩詞作品,耐人欣賞,激人遐想。從“葛郎瑪”出發研究語言形式的人看不起修辭,認為那不過是經驗之談,無理性可言,不能入語言學的主流。而研究修辭學的人,也有一部分自居於語言學之外,從一星半點的語料甚至三流作品生造出的語句中歸納格式,讓人們學着去寫作。結果正為《論叢》所説,按着修辭標準去做,常常寫出蹩扭的句子。
《論叢》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思路:
(古代文章和詩詞作品)句式真是五花八門,沒有主語的,沒有謂語的,沒有賓語的可謂觸目驚心。……我努力翻檢一些有關講古代漢語語法修辭的書,得知沒有的部分中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為什麼那麼多省略之後的那些老虎(王按:指詩句)還是那麼歡蹦亂跳地活着?(《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
在説到詩歌和駢體文時,《論叢》又尖鋭地提出:
我還沒有看到過對詩歌和駢體文語法修辭的探討,只看到過駢體文頭上一大堆帽子,什麼形式主義的,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不科學的,甚至更簡便地説是反動的。奇怪的是,既然那麼不合理,而竟然在二千多年來,有人寫得出,也有人看得懂,起過不少表達思想的交際工具作用。這是為什麼?……有無它們自已的法則?……有沒有生活上的基礎?還是隻由一些文人編造出來的?(同上)
《論叢》指出,存在在詩詞和駢體文中的一些語言格式和表現手法,都是有實際語言作基礎的,很多是口語中本來就存在而被文人提煉出來的,這些語言格式不應被判處為“反常”和“超常”,而應當承認為正常的法則,而且它們恰能反映出漢語不同於西方語言的特點。
口語中用字可以伸縮加減,重迭可以加強語氣,縮減也能加強語氣,在語言環境中説話,可以少説許多成分還能被聽懂,這就是漢語的特點。
口語中局部詞彙顛倒而大意不變;詩句和駢句中由於字數、聲調和為了增強效果而有所強調時,特別要倒着説;這是“倒裝”的基礎。漢語裏凡是正着、倒着都可以講通的句子,多半由於側重點不同。故意放在前面的是突出點,例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不等於“以政導之,以刑齊之”。故意放在後面的又是落腳點,例如“屢戰屢敗”是失利,而“屢敗屢戰”是勇敢。
口語中就有對句,雖然不一定整齊,但具備整齊的基礎。詩詞與駢文總結出各種對偶的詳細條款,無非是為了對得工,對得美,那是因為漢語具有這種條件。
至於“比喻”,《論叢》指出,“語言根本都從比喻而來”,比喻不但不超常,簡直就是詞彙發展的經常性規律 。
沿着這個思路走下去,通常所説的“修辭”本來就寓於語言的正常法則之中,有一大部分應當迴歸到漢語語法中去。文學家所説的超越語言的種種現象,其實正被語言的正常法則在冥冥之中控制着,所以《論叢》説:
有些詩歌、駢文的句、段、篇中的修辭作用佔絕大的比重,甚至可以説這些部分的修辭即是他們的語法。(《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
當然,這樣一考慮,對語言法則的歸納總結無論如何不能簡單化,更不能套現成,這不正給漢語語言學的研究拓寬了道路嗎?
4
從單純的形式結構研究中走向多維的探討
《論叢》並不是絕對反對“葛郎瑪”,只是反對不顧漢語的語言事實而對拉丁語法硬性套用。而且,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比如一句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其中僅有一句不通。要解釋這種現象,“葛郎瑪”無能為力。又如漢語裏動不動就出現四節拍,多於四拍的壓成四拍,少於四拍的加成四拍。這種現象也不是語法形式能解釋得了的。《論叢》提倡從多維的角度來觀察漢語現象。其中對語言學最具有啓發性的應當是“意義控制説”和“音律配合説”。
《論叢》指出,句中詞與詞的關係“總是上管下”,又延展説:“不但詞與詞之間是這樣,句與句之間也是這樣”。什麼叫“管”,《論叢》説,所謂的“管”,不只是管轄、限制,也包括貫注、影響、作用等意思和性質。很顯然,這裏所説的“管”,指的不是結構關係,而是意義關係。漢語的詞語組合和句子排列,很少有形式上的成分來銜接,大部分都是意合,而話又要一個詞一個詞、一個句一個句地説出來,形成一種線性,這就迫使説話的人先提出主要的話題,然後順着話題承接着往下説。一句話裏有許多詞,先説哪個後説哪個,全看説話的人如何組織那些詞的意義關係。句子更是如此了,把重要的意思説在前頭,相關而次要的意思説在後頭,讓前面已經説了的意思貫下去,影響後面的意思,才能讓人聽明白、聽懂。本來,任何民族的人説話都應該這麼説,只是拉丁語系的語言因為有語法形式的限制,任意組織意義的自由比較少;而漢語沒有語法形式的限制,反而得到了這種自由。用意義控制——前面的控制後面的,來解釋漢語的語序,的確是個非常深刻的想法。這就是“意義控制説”。
“音律配合”説就更符合漢語實際了。文言文以單音節為主,組合又是二合法,凡是三音節,大半是二合之後再與一個相合,凡是四音節,大半是兩個二合再往一塊兒合。這種兩層二合最勻稱,也最容易把韻律諧調得好聽,所以最容易出現。為什麼不接着往下合,到三合、四合、五合?《論叢》説,那是人的生理限制住了,一口氣吐三個字、四個字,已經到了需要喘氣的時候了,再往下説,就要停頓一下。所以許多虛詞經常用來把三個字或四個字之外的句子成份隔開。散文的句式已經看出了這種音律配合現象,詩詞的句式不過是把這種自然形成的格式再加以人為的規定罷了。漢語的陰陽頓挫、雙聲迭韻開始時只是人們説話時追求朗朗上口而自發形成,一旦被文人們發現了,規定出來,便成了格律。不信你去研究現代漢語雙音詞的語素配合,為什麼A非配B,而不配B的同義詞C?如果沒有意義的原因,那多半是有韻律在起作用。
《論叢》的意思很明白:對漢語來説光一個語法結構解釋不了那麼多現象,更應重視的是意義和音律的配合關係,三者合而觀之,多維度地觀察語言事實,這樣的語言學才能更加符合漢語的特點。
四
其實,語言形式與內涵之所以有民族性,是文化的多樣性形成的。從文化的積藴看語言的形式與內涵,才能明白漢語的特點。
《論叢》在談到八股文和典故的時候,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那就是,語言形式是從不同時代的語言運用經驗中陸續積藴而成的。許多典故,典面雖壓縮成兩三個字,可內涵卻是“一件複雜的故事、一項詳細的理論”,而且典故用過一回又增加了一些文化的積藴,越積越厚。能不能理解這些語言形式和詞語內涵,全取決於聽話的人文化素養高不高。現代符號學提出,要建立三個新的語言觀:第一是語言能夠規定思考的方式;第二是語言應對美學功能加以關注;第三是語言以最典型的形式表現文化。 這三個語言觀都涉及語言與民族歷史文化的關係。《論叢》從分析八股文、分析古代詩詞、駢體文和分析典故中所闡發的思想,比這些提法要深刻得多也具體得多。西歐語言學家把漢語稱作“孤立語”,後來覺得帶有貶義,改稱“詞根語”,這是針對漢語缺乏語法形式,因而也很少有結構的外部手段而言的。他們針對漢語詞彙缺乏詞形變化這一點,又稱漢語為“分析語”,認為這種語言的詞彙沒有綜合概括的外部條件。二十世紀初打倒文言文的時候,宣告漢語落後要改用世界語的呼聲早已有過,也無非是因為西方語言學家對漢語的這種判決。其實,只要認清那些從貶低東方的語言出發而判定東方民族落後的態度,認清那些要同化之、侵略之的惡劣動機(這當然不是多數語言學家的動機),西方語言學家從對比中總結出的漢語特點,倒是相當準確的。問題在於缺乏詞形變化和語法結構形式的語言,便隨之產生另一方面的優越條件,這一點普通語言學裏卻很少講到。
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鈎,一邊有環,一邊帶鈎。這個鈎鈎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鈎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鈎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鈎,詞的結合自由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乾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迴文詩,乾脆接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遊戲,可難道不啓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

漢語的詞沒有詞形變化,不給結構提供各類語法形式,但是,漢語詞的意義容量卻非常大。在文言文裏,一個單音詞的講法真是“煙雲舒捲,幻化無方”。虛實相生,動靜互易,正反相容,時空互轉,換一個地方有一個講頭兒,即使再高明的訓詁大家,也難窮盡性的表述描繪。如果有一個講頭就列一個義項,連工具書也沒法編了。所以啓功先生説漢語工具書得重編,一個“書”字概括起來只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書寫”,一個是“所寫”。別的詞也一樣,比如“間”字,概括起來也只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當中”,一個是“隔離”。“間雜”、“中間”、“間諜”、“間廁”都是夾在當中。“間隔”、“離間”、“房間”、“間居”都是隔離開。所以需要從特點上概括,就是因為每個特點下的容量太大,列得太煩瑣了根本沒法選用。
詞的意義容量極大,與別的詞發生關係時結合的能量自然也就很大,加上句子結構的形式限制極小,所以就產生了一個五言詩句可以改為十個句式而只有一個不通的現象。這當然都是漢語的特點。
詞的意義容量為什麼會那麼大?這不能不説是悠久的歷史文化積藴的結果。其實,典故的濃縮方式,在許多漢語的一般詞彙裏也都存在。周代的相見禮儀中,主方有上儐、承儐、紹儐管回話,賓方有上介、次介、下介管通報,紹儐與下介是主賓雙方的第一接交人員,於是凝成雙音詞“介紹”。“介紹”不是典故,但文化積藴不能説不深。“夜深前殿按歌聲”,“朱門沉沉按歌舞”,張相説,在唐宋詩詞裏“按”當“排練”講。其實,排練的意思是從擊鼓來的,《楚辭》已有“陳鍾按鼓”之説。如果中國的國樂沒有用鼓來司節奏而暗中充當指揮的習慣,“按”引申為排練也就不會有可能。“按”不是典故,同樣有文化積藴在其中。
影響詞的結合能量的,除了意義和文化的因素外,還有音律這個重要的因素。文言文的單音節詞直接進入到現代漢語裏充當語素,被漢字這種承負“音節——語素”的表意文字所書寫,字也好、詞也好,都離不開音節的聲、韻、調。聲、韻、調的配合加上節拍構成音律,也是控制詞的結合能量的。
啓功先生的這些獨到的見解,對漢語語言學的發展指出了一個方向,那就是應當建立一套切合漢語事實的理論和操作方法,從只重視語法結構,轉回到傳統語言學更加重視詞的音義的道路上去,對語文教學和社會應用有所指導,對文學創作和語言藝術有所貢獻。
這些見解對語文教學也是很有啓發的。前些年,有些老師提出在語文教學中要“淡化語法”,一開始不少人很難接受。其實所謂“淡化語法”,無非是針對把“葛郎瑪”當成幾乎是語文教學裏唯一語言知識的傾向説的;針對讓學生套語法、教學生背語法、出題考語法的這種片面應試的做法説的。面對那麼豐富而有特色的漢語,是不是還應當從意義、韻律和文化這些角度來認識他、鑑賞它、運用它?是不是應當重視漢字在漢語發展和運用中的作用?是不是應當給文言文閲讀應有的地位?——總之,是不是應當啓發學生從漢語的事實出發來學會運用自己祖國的語言文字,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在語文問題上,一味模仿西方、追隨西方會產生什麼後果?這些問題早已經提到日程上,讓我們不能不考慮了。在這種時候,讀一讀啓功先生的這本書,確實可以對我們多所啓迪。
本文初次發表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集刊1996年第4期,題目是“漢語語言學研究的新思路”,這次應約作為《漢語現象論叢》一書的導讀,為更好體會啓功先生的意思,作了多處修改。
文 章 作 者
王 寧
1936年生,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北師大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主任,章黃學術在當代中國的重要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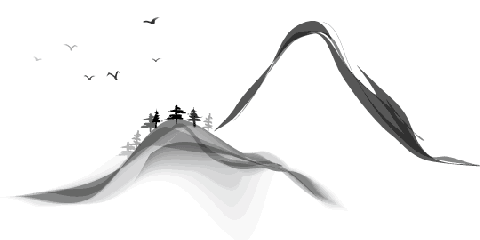
公眾號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美術編輯:張臻 孫雯 高佳玉
專欄畫家:黃亭穎
責任編輯:蔡若葵
部分圖片來自互聯網
特別鳴謝
敦和基金會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章黃國學
有深度的大眾國學
有趣味的青春國學
有擔當的時代國學
微信ID:zhanghuangguoxue
北京師範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漢字研究與現代應用實驗室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研究所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
文章原創|版權所有|轉發請注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