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四個收養的中國孩子這事,讓我想起在兒童福利院實習的那個夏天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15332-2018-10-19 15:47
10月16日,在美國女權運動最高漲的州之一的田納西州爆出一個重量級消息,一名領養了四個華裔兒童的全職母親,在當地時間15日晚間被發現與領養的孩子一起死在家中。根據警方初步調查,這名55歲的女子先開槍打死四個領養的孩子,之後開槍自殺。
四個孩子最大的17歲(也有一個説法最大的16歲),最小的14歲,三女一男,均死在母親的槍下。
這個基本上只有在驚悚小説中才能看到的故事情節,赤裸裸地在現實世界中上演了。平心而論,美國每年因為各種原因死於槍下的人數以萬計,對平時非常關注國際新聞的公眾來講,美國槍擊案帶來的新聞衝擊感差不多如同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發生汽車爆炸一般,哪怕並非廉價地奉上一句“死者安息”,也無法掩蓋某種司空見慣的麻木感。
但這次,此案或許對國人來説有一種別樣的感覺——被殺死的四個孩子原本都是中國人,是被自殺的兇手母親所領養的。
通篇新聞看下來,疑點仍然很多,比如四名孩子從幾歲開始被家庭收養,以及為何四名收養子女保留了原有的中國姓氏等,警方都暫時無法給出回應,只能初步判斷母親死於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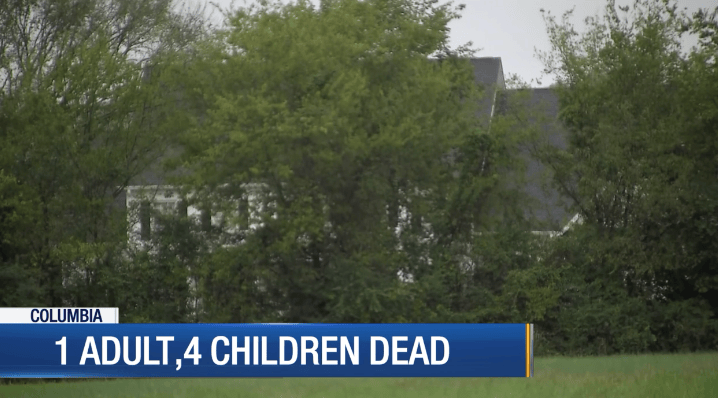
此事撩動中國公眾神經的,恐怕已經不是單單對死去孩子的同情,而是一個關鍵性的語詞:領養。
母親55歲的辛西婭·科利爾(Cynthia Collier)估計某年和丈夫一下子領養了四個華裔孩子,卻最終釀成了這場悲劇,再次激起了筆者對中國領養制度的一些“不必要”的感慨,為什麼説再次呢?因為首次引發俺想對領養制度討論慾望的是去年的體操世錦賽,一個戴着牙套和眼鏡的某體操運動員小姑娘是華裔,也是被一個美國單身媽媽領養,從小把她撫養長大,而且要力爭把她培養成世界冠軍。
這兩件事雖然一個是悲劇,一個是美談,這個奇異的反差卻能共同激起國內讀者的問題意識:他們到底是通過何種渠道領養到中國孩子的?為什麼中國的失獨家庭和不孕不育家庭領養一個孩子這麼難呢?
那個領養體操女孩的美國大媽不但單身,而且沒有穩定工作,但能很順利很迅速地領養到中國孩子,也是個問題。
再想單獨開個貼討論這個問題之前,筆者想首先分享一點自己的生活經歷。也許沒有這段經歷,俺這一輩子估計都不會和“領養”這個非常異己的詞聯繫在一起,但N年前的一段實習期,讓我有機會踏入到孩子領養的重要中轉站之一的兒童福利院,這兩個月的奇特生活體驗給自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去觀察這一類社會現象,窺探這類純事業單位的某些“日常操作”也讓自己領會到之前從未接觸過的一個職場江湖。
起筆之前俺倒是想玩一個類似科恩兄弟那種虛實相間的惡搞,他們喜歡把一個純粹虛構的劇本搬上熒幕,開場就打出字幕:這可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其實就是對“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的免責聲明的調侃,抑或是像曹雪芹那樣搞一個“甄士隱”,真事隱去,卻也擋不住紅學索隱派的順藤摸瓜和抽絲剝繭般的“探案”。
無論如何,本文的真實姓名都要隱去,因為就在昨天晚上手機聯繫一兩個那裏的舊友,他們都説當初你接觸到的幾乎所有人還在原地,蹲坑,普通員工基本只進不出,也許這也是兒童福利院這種單位的一大特色吧。
本文有點長,流水賬一般的紀錄,也不想再加什麼圖,湊合着看吧,湊成此文也是為了不想讓記憶中的某些邊邊角角失去一些參證。
那是N年前的春夏之交,本科馬上結束的俺就差實習就要修滿150學分(實習學分好像是15個)可以畢業了,已經準備讀研所以打算着15個學分也就混混算了,初始想法是在學校的圖書館當個臨時管理員,主要協調圖書館和系資料室的打通工作,順便可以讀點書。
不料想一個在北方某直轄市找到一份不錯工作的師姐(去了國有銀行)回來做找工作報告,私下聚會吃飯的時候説她三舅媽家的小侄女在該市認識兒童福利院的副院長,説要招三個實習生,點名了説要找外地的,因為之前的四年有三年的實習生都是本地的,而本地畢業的實習生乾貨很不利索,還頂撞了領導,前一年陰差陽錯找了某東南高校的即將畢業的實習生,領導反而比較滿意。
師姐説的這個事情在飯局上無人響應,主要是因為兒童福利院這個機構和專業毫無關係,而且對之後的就業也基本上沒啥幫助。她轉過身對我説了一句,“不鏽貓,你不是6月份還要在B市考雅思辦護照什麼的嗎,不如你去這家兒童福利院實習一下,就當是玩玩。”
我一想也是,我還從來沒去過B市,不如去開闊一下眼界。
五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三,去系裏開了證明辦了手續,買了一張北上的車票,提着半乾癟的行囊望着車窗外的時候,心理勾畫着對兒童福利院的種種想象,估計和幼兒園差不多吧,人畜無害,一個充滿童趣和有母愛的大姐姐的地方……
這家兒童福利院的全稱就是B市兒童福利院,是民政局直屬,兒童福利院的院長基本都是副處級幹部,再加上該院的員工數量和佔地面積,這幾乎就是我去之前homework所能做到的全部,比較詫異的是它並沒有官方網站,能用搜索引擎查找到的信息寥寥無幾。
大約此院(以下簡稱“兒福”)是民政局下屬所有單位的一個清流吧,下車後前來和我接頭的孫幹事加強了我對此單位的某些初步的好感,他中等身材微胖,戴着的眼鏡鏡片居然比我還厚,帶我去職工宿舍的時候,順手從北門的傳達室拿了一份自己訂閲的《北京青年報》。
“不鏽貓,今天你先住下,明天下午我再帶你去辦公室看看,認一認各路人。你現在被分在周副院長這一系統下,咱們主要是負責院內的保衞工作。”
按照以往我對同類型單位的瞭解,分管保衞工作的人相對來説都是比較“糙”的,但兒福保衞科的幹事居然都充滿了文氣,看來兒福確實非同一般。
“我這身板,能保衞什麼呢?防盜抓賊我肯定不行啊。”我打了一個諢。
“呵呵,防盜的工作主要靠保安,咱們現在這兩個月的主要工作一個是防汛,一個是消防。現在民政部門要搞一個消防大檢查,消防數據庫的活你要幫忙做一下。具體怎麼幹,祁副科長還要再給你開個小會。不鏽貓,這次來了一共倆實習生,把你分到這裏,相對來説是很幸運的,咱們平時沒什麼事,也就是每天喝喝茶讀讀報,另一個實習生被分到了護理部了,那裏就很髒很累了。”
孫幹事帶着我在居室樓周圍和辦公樓內轉了一圈,閒聊的時候他説老婆待產,接下來一個月基本上上三天兩頭就要請假,説有什麼事兒,祁副科長會給我再講解。
我安頓好了之後,在佔地萬平米的院子裏隨意閒逛,夏初,花草鬱鬱葱葱,該院有前後兩個門,南門外正對一條河,河邊遛狗的老人和河裏的野鴨子也許都能從側面訴説,也許此處並非塵囂狹陋之地。
誰也不曾料想,第二天剛準備踏進孫幹事指引我的那間辦公室,要會會領導的時候,卻遭遇了很尷尬的一幕。
整個辦公樓的二樓都能聽見一個唱京劇黑頭般男人的怒吼:“不願幹都雞巴給我滾蛋,兒福缺了誰都他媽不算缺!”
這時候從另一頭的洗手間出來一個很瘦的中年大叔,他留着平頭,步速和語速都很快,他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到一旁:“你是不鏽貓吧,昨天孫幹事和我説了,辦公室還沒收拾,你今天先別進去了。你現在去隔壁樓的中控室找高燊鋒,他現在做消防繪圖,明天咱們再開個小會。”
我正轉身要走,一個大姐披頭散髮地嚎哭着出來:“媽了個x,老孃我他媽還不回來了!”
我嚇了一跳,為了避免尷尬,沒等電梯,從右側樓梯口直接出去,繞了一個圈到了中控室。
後倆才知道,中控室是消防系統的總樞紐,福利院耗資巨大剛買的兩台消防主機就在這裏,而且這個還有全院94個攝像頭的總監控,門口寫着:保衞重地,閒人免進。
這八個字的分量,我從中控室的門就能體會出來,門特別重,打開極為費力,設計的時候主要考慮到了防噪防塵防輻射。
當時俺記得那天中控室有一男一女,除了高燊鋒,還有一個姓韓的大姐,半老徐娘,但香氣撲鼻,描眉畫眼,看到我進來笑嘻嘻地打招呼:“你就是那個來的大學生吧,剛才在辦公室門口把你嚇壞了吧?哈哈哈”。
原來,中控室通過這90多個攝像頭,能遍觀院裏發生的一舉一動,剛才保衞科辦公室門口的一切,當然逃不開在中控室值班人員的眼底。
韓大姐接着説:“你劉姐不能給你送見面禮了,你這段實習期估計見不到她了。”
高燊鋒身材壯碩,説話的本地口音很重:“韓姐,該給這小夥乾點正事兒啊。這張圖給你,你今天溜達溜達,看看圖上標註的消防栓的位置,看看有什麼遺漏的。”
説話間他給了我一張圖,還有出入護理大樓和居室樓的門卡。我心想實習期第一天最好別出什麼疏漏,剛要走的時候,韓姐走到我跟前耳語:“不鏽貓,天兒現在也熱了,你也不用瞎溜達,沒事兒就回宿舍休息,吃完午飯下午再來。”
我還糾結着要不要乾點“正事”,走到北門,保安隊的鄭隊長招呼我過去聊會天,才知道就在我到院的那天晚上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鄭隊長河北人,和我年紀相仿,人很機靈。後來才知道,他在所屬的外派的保安公司裏也是一個另類,眾多保安隊長只有他一個戴着金絲邊眼鏡。
鄭隊長説,昨天晚上,那個在科長門口大鬧的劉大姐和某姓高的保衞科幹事在值夜班的時候,因為打熱水和拖地等清潔工作發生了激烈爭吵。劉姐和高本來就不想搭伴上夜班,結果第二天早上劉和高一起去科長那裏鬧,最後都打了休假條,中控室值班的一下子少了倆。
“你是新來的實習生,有些話給你説也無妨。高是科長的人,劉姐是周副院長的人,有些事看起來是小事,其實不是。”
我也沒料到,那個中控室將會成為這倆月實習的主要工作場所,而並非辦公樓的那間羣體辦公室。因為這個突發事件打亂了保衞科的人事工作調配。
我記得下午三點多科長打了一個電話給韓大姐,説那個實習生小夥就在中控先幫忙幹起來。
後來才知道,中控室有一個專屬領導,就是祁副科長,春節後不小心摔斷了腿,一直休假,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但能“遙控”中控室。
由於當時是5月中旬,按照兒福慣常的傳統,已經進入“防汛期”了,防汛期期間,要院裏的每個大領導帶隊上大夜班,也就是正院長帶着三個副院長輪流值夜班。
中控室出於消防的需要,也24小時值班,白班早八點晚五點,晚班從五點直接上到第二天早上8點,但晚班做一休二上,分成三組。
排班表出來一看,我和一個姓關的大哥搭夥上夜班,心理一開始確實很怵,從晚五點到早八點,整整15個小時。按規定消防這一塊,至少要兩個人一起合作,一旦有火災,一個人去現場跑點,一個人守着消防主機。
初見到關哥,就感覺很親切。都説京油子衞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關哥的嘴特別貧,為什麼安排我和他搭檔,主要是除了我就沒別人了,通行的説法是,別人看不慣他佔單位的小便宜。
説實話,實習期的這倆月我猛增長了很多消防知識。
所謂的佔單位的小便宜,就是關每次上班,都拿着大包小包,裝着老婆孩子的衣服,還有牀單什麼的。
他的工作流程是,上班打卡後先去浴室把衣服洗完,然後去食堂吃飯,拿着洗完的衣服回到中控室,打開空調吹。到晚上八點開始,抽煙思考半個小時左右,然後我們倆開始聊天。
聊天聊到晚上10點左右,去辦公樓看看院長副院長的燈是否還開着,如果燈關了,説明領導已經睡了,這時候關哥把停在辦公大樓的標緻307開到居士樓前面,打開水龍頭接上膠皮管開始洗車。
“我知道很多人背後説我洗衣服洗車什麼的,去他們媽逼。我佔便宜?我佔的是最少的了。”第一天晚上上班,關哥在聊天中就打開了話匣子。
“雖然你只是個實習生,倆月後你也留不下,有些事兒讓你知道知道。祁副科長偷院裏的滅火器拿出去賣,而且和保衞科的另外一個合夥賣,院裏都知道。”
我詫異:“啊?這事就沒人管管?”
“我願意跟你這種剛畢業的大學生聊天,這裏的人太腌臢了,官大一級壓死人你聽説過沒有?這句話在這裏其實是不管用的。”
聊深了我才明白,這裏就是個小江湖,每個人都會選邊站隊,派系黨爭無處不在。
主管中控室的祁副科長和周副院長兩個人結盟,給科長到處使絆子讓他難堪,科長管不了副科長,但副院長又管不了科長,因為科長背後還有民政局的後台。
“沒有關係進不了這裏。你得摸清楚他背後有什麼人。”這裏形成了層層嵌套般的“整人”鬥爭,比如B是A的上級,C是B的上級,D是C的上級,A和C聯合起來鬥B,B又和D聯合鬥C,不亦樂乎……
坦率地講,離開這個地方之後,唯一讓我惦念的就是這個關大哥,因為他是讓我覺得接觸過的所有人裏幾乎唯一一個沒有混日子感覺的。因為他每次上班都帶着一本日語二級。
“哇,關哥你還學日語啊。”
“是啊,總不能讓自己廢了,我老婆是旅遊單位的,跑日韓這趟線,日語什麼的也要學學。”
幾天下來,工作流程稍一熟悉,就發現通常機關單位的人浮於事和各種的效率低下,以前只是傳説,這次是親眼見到了。
高燊鋒、關哥還有接我的孫幹事都是消防兵退役之後轉業,據關哥説,高本來在上海當消防兵,後來成了逃兵,回來後走了關係進到這裏。
那麼保衞科的女眷也有一派,韓大姐和劉大姐都是軍嫂,丈夫都是副團級幹部。不單單是在保衞科,護理部,理療部等等很多女員工都有軍隊背景,這批人被稱為軍嫂派。
我也漸漸明白,軍人——福利院——民政口確實是有內在關聯的。
關哥有一次在轉業之前的滅火行動中,被高壓消防水槍打斷過臂骨,有傷殘軍人證,坐公交車可以免費。
第一天上班,到了晚上10點半,關哥踱步又去觀察了領導辦公室的燈光,洗完車之後,坐下來點上煙思考。11點半左右,説了句:“去宿舍拿你的被子,咱倆再把大廳的兩把大長椅抬進來。”
“啊?”
“啊什麼?睡覺啊,早上八點才下班啊,不睡覺你熬的過去嗎?上晚班就是睡覺。”
我本來還覺得熬夜太辛苦,這下心裏踏實了。回宿舍拿了被子,“組裝”上大長椅躺下,關哥從包裏拿出鋪蓋,躺在了寬大的窗台上。
這時耳邊只有消防主機滋滋的聲音。
我好奇地問了一句:“關哥,你那個……抽煙思考的時候看你很專注,都在思考什麼呢?”
“我啊?我思考每天怎麼肏人,我要不思考這個,人就要肏我了。這個單位就是這樣。”
我無語。
由於關哥洗了衣服要晾乾,大夏天的他空調開了熱風。“我知道別人都不願和我上晚班,就是煩我晾衣服,你忍受一下,衣服幹了我就把空調關了。”
我嗯了一句,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從來沒這麼睡過覺,再加上實在是太熱,早上六點多醒來,嘴上起了一個大泡。
早上六點半就要起牀,把被子再抱回宿舍,整理好長椅恢復原樣。
正要準備去洗臉刷牙的時候,保衞科的鄭隊長慌慌張張跑了進來:“十五分鐘後派出所的人要來,你們準備好調取監控。”
我還以為院子裏進了賊。關哥呷了一口茶:“又有人扔孩子咯。”
果不其然,片兒警來了之後調取監控,説昨晚上有人往院子裏扔孩子,是從河邊的西牆扔進來的,孩子現在被保安發現後通知了護理科,正送醫院搶救。
片兒警拷貝了監控之後,關哥告訴我:“你這回長見識了,這時候恰好是扔孩子的高發季節。春天結束之後,咱們院經常會在早上撿到各種孩子,一早起來,草地上甚至樹上都會有孩子。”
原來比如早孕的,孩子身有殘疾的,未婚父母或者嫌棄孩子的不想養活,就偷偷在後半夜把孩子扔到福利院。但對於孩子的監護人來説,扔孩子屬於遺棄罪,警察是要管的。
孩子扔進來之後,如果身體檢查有毛病,就會馬上被抱走被人領養。有殘疾的就留在福利院。
通過一個星期的觀察,我才發現,留在福利院的孩子主要不是身體殘疾,絕大部分智力都有問題,包括很多唐氏綜合徵患者。
在前半個月裏,和調監控有關的還發生過三件事情:
1 一對夫婦在90年代末把孩子扔進了福利院,幾年後又回家接走了,結果養到20歲不想養了,想再送回福利院,每天在門口大鬧,有一次還衝進了院長辦公室打砸;
2 護理部的某個在編的護工,早晨六點半在院前的花叢中毆打孩子,結果被旁邊高層建築的居民看到後直接舉報給了保衞科,釀成那個月院裏最轟動的新聞,至於到底怎麼處理這個護工的就不清楚了。
3,某內蒙古千里迢迢來的一個50多歲的大媽,帶着各種證件,包括抗美援朝的烈士家屬證,來到院門口想領養孩子,結果遭到寄養辦的嘲諷:你想什麼呢?跑這裏領孩子,懂規矩嗎?結果在門口台階上坐了一會,痛苦地暈倒在地,被幾個護工抬上了救護車……
關哥告訴我,目前院裏的臨時工和在編員工比是6:4,在編人員哪怕是護理部的基本都不在一線,喝茶看報,真正幹活的都是臨時工。這一次是臨時工辭職回家,暫時讓一個在編的頂上,也許是久疏戰陣,沒有了關愛孩子的心,才對那個殘疾兒童又踢又打。
“她這回被抓了個現行,但開除不了。兒童福利院開除不了在編的。”
“那……關哥我很好奇,如果有人想領養孩子,比如有人扔進來一個特別健康的嬰兒,要走什麼程序才能領養呢?”
“這不好説,若是走正常程序,你排隊等個五年八年都不行,你得有路子。”
“什麼路子?”
“什麼路子?整個民政口,下面兩個大的油水單位,一個是殯葬處,一個是福彩中心,這倆單位撈了多少錢?人家家大業大有的是騾馬。咱兒福是個清水衙門沒錯,但是上面想搞點外快,從哪裏下手呢?説實話,這個院就是吃孩子的,全院全靠這450個殘疾孩子養活呢。但是有一節,你要有美國護照啥的就好辦了,沒護照有綠卡也行。外國人從咱這裏領孩子,就是快,而且都不用怎麼審查。”
“那就不怕被哪個反華人士領了去?至少該有個政審啥的吧。”
“你想太多了,外國人領的多了,説明國際化程度高,領導也願意這麼幹,而且孩子被帶到國外,協議只要一簽,比國內領養的人要省心多了。”
我心裏五味雜陳,琢磨着這事也不好再細問,不過沒想到這個“國際化”很快就來了。
過了一個星期,院裏要迎來一場“大考”——六一國際兒童節。
而且這次的兒童節非同尋常,聯合國兒童發展基金會的某特派員要來訪問兒福,全院如臨大敵。各種設施不但裝飾一新,而且院裏的孩子們衣服都換了,每天被護工們帶着去綠化區透氣,見了我變得很有禮貌了:“哥哥好,叔叔好。”
我回來把這事一説,關哥笑着説,這羣孩子看起來智力上有殘疾,其實未必那麼不懂事,是能好好教育的:“咱們這個院,只有0-5歲的孩子,孩子長到五歲後就會被送到第二福利院和第三福利院,那裏的孩子其實更不省心。”
“為啥呢?孩子長大之後至少不用很辛苦的再換尿布什麼的,這裏的孩子看起來生活都不能自理。”
“孩子也是人,長大一定程度就打架,也拉幫結派欺負弱者,而且從小無父無母,心理都有缺陷,二福和三福的孩子們,待遇很多還不如少管所。”
六一國際兒童節前兩天,科長給大家開了一個大會,説加強安保,不能出什麼紕漏。
本來作為一個實習生,心想也就是看個熱鬧,5月28晚上,劉哥抽完煙告訴了我一件事,引發了我長久的感慨和思索。
“不鏽貓,給你説個事,艹,哎,這個世道啊。”
“咋啦?關哥。”
“昨天科長找我談話了,副院長也在邊上,説兒童節讓我暫時把我的孩子貢獻出來。”
我心裏一驚:“什麼叫貢獻出來?”
“有個老外要來參觀,還是什麼jb聯合國的,院裏組織孩子們表演節目,搞一個晚會,可是咱們院大部分孩子有殘疾,唱歌排練實在是太累,不行。院裏領導的意思是,能不能找正式職工和臨時工,讓我們的孩子暫時充冒充一下,頂過去再説。”
我苦笑了一下:“這種弄虛作假,穿幫的概率不小啊。”
“你覺得這是弄虛作假,人家不這麼認為,對民政局寫的文件可是院職工孩子和兒福收養孩子的聯歡,哪怕沒有殘疾孩子演出,這種事就是糊弄老外,真追查下來也查不到什麼,院裏的孩子搬搬椅子抬抬桌子也算演出了。再説了,出孩子院子裏的職工的都給特殊補助。”“那你答應了嗎?”
“我答應他mlgb,我説我們家閨女發燒重感冒,姓葉的副院長在旁邊還説,你可是個黨員啊,要有模範先鋒作用。他還有臉談黨員。”
關哥好像是保衞科除了科長之外僅有的兩個黨員之一,98年湖北洪災,他初入部隊也跟着上了前線,而且是火線入黨的一批。
六一兒童節那天,除了居士樓之外人聲鼎沸,院內其他地方卻奇異般地安靜……
幾天之後,B市迎來入夏後的首次大範圍降雨。
瓢潑大雨中,我看到科長鼻青臉腫打着傘進了辦公室。
南北門站崗的保安都在談論着科長和祁副科長打架的事情。我才知道,要文鬥不要武鬥,在這樣的單位爺只是個傳説。
原來,周副院長為了整治科長,前一天突查夜班,發現門上了鎖,從後門砸開之後進去一看空無一人。打電話沒人接,直到早上7點,倆上夜班的才開車回到院裏,沒想到,等待他們的是副院長猙獰的臉,據説臉部肌肉扭曲讓厚厚的粉底都掉了。
按照兒福不成文的規定,院長和副院長都是女的,黨委書記是男的,在傳達處理指示的會上,很可能祁副科長當場嘲諷了“管理不力”的科長,下屬擅自離崗云云,由於某些歷史原因早就不睦的二人當場打了起來,一地雞毛,斯文掃地。
鬧劇發生了之後,周副院長這時候顯示出了領導的才能,為了再次防止上夜班的員工脱崗,他發明了一個辦法。
晚上10點之後,讓南門——北門——中控室連線。兒福的南門北門都有保安站崗,配有電話,這樣,三方在晚上10點半之後,每隔半個小時打一次電話,互相監督,串在一起。
先是南門給中控打,中控再給北門打,北門給南門打,半小時之後再反過來打一次。這樣,假如有一方沒接電話,就按離崗處理,要罰錢。
第二天該輪到我上夜班了,關大哥把這個規則告訴了我。我一聽頓時極為鬱悶,這意味着上夜班真的要熬夜了。
説實話,消防這一塊,除了早晨起來食堂蒸饅頭的大姐,會因為蒸汽導致火警誤報之外,其他時候沒什麼事情。夜班兩人一起熬夜,確實極為乏味。
不料首先找上門來的是保安隊的鄭隊長。
“我也煩啊,上班淨打電話誰他媽受得了?我把保安隊這個月的排班表給你一份,咱們通個氣,對對口供。”這樣北門南門和中控三方約好了,建立一個攻守同盟,大家都不打電話,但彙報的時候怎麼説都通好氣,大家皆大歡喜。
其實保安隊的鄭隊長也是個人精,平時做事看起來很利索,這次敢對副院長的新政對着幹,是因為他通過內部消息知道這個副院長馬上就要調走了,要調到一個民政局搞的一個第三產業部門,好像是個玩具廠當廠長。
上班睡覺依舊,這個時候我的實習期還剩下不到半個月。晚上快到11點,關大哥又去觀察了領導的辦公室的燈光,然後我回宿舍依舊抱了被子,依舊抬進來大長椅。
睡覺前關哥倒掉煙灰,説:“不鏽貓,你知道那天值夜班的倆去幹嘛了嗎?”
“不知道,我也有些奇怪。”
“他們倆去嫖娼了。”
“啊?!”我激靈靈打個冷戰。“還有這事兒?這簡直……”
“是不是覺得很新奇?其實也不是什麼秘密。這不過這次倆人玩的有點大,他們開車去T市(臨近的另一個直轄市)嫖。”
“愛嫖娼也不一定道德上一定有問題。為啥跑這麼遠呢?”
“周圍都嫖了一遍,沒啥意思了。而且最近查的嚴,那邊比較松,再説了,就怕遇到熟人。在T市同樣的價格能嫖到外國妞,黑的白的都有。”
我沉思了一下:“那倆大哥平時看起來很正經啊。”
關哥:“呵呵……那天帶進來的小孫你還記得吧?這段時間老婆待產,沒怎麼上班。”
“我記得,孫大哥斯斯文文的。”
“一年前孫直接把妓女帶到南門保安室的內室,和保安隊隊長一起幹的,當時還不是這個鄭隊長,那個姓呂。”
我頓時陷入了沉默,而且瞬間覺得,我好像只看到了某些現象的木榫和釘卯,不過話説回來,能一窺勾欄管廊,又能如何呢?
10天之後,我收拾行囊即將南下,這兩個月的寶貴實習期要結束了。
臨走的時候,平時喜歡集郵的關哥送我一套中國科技史的郵票。昨天又從抽屜裏拿出來又看了一下,沈括那張的邊角小缺了一塊。
我拿着實習證明找科長蓋章簽字。科長配上了非常有套路的表情:“回去之後多聯繫,你再來B市一定要再來看看。最高分多少?100分?我給你打95吧。”
我:“科長,這段時間我確實學習了不少,感覺自己做得很不夠,我們按ABCD打分,您就給我B-吧。”
拖着行李箱走出北門的時候,正好碰上一個護工帶着一羣孩子出來散步,孩子們的口中也沒有了“哥哥好,叔叔好。”我回頭看了一眼大門,心想,也許用不了幾個月,這裏的所有人都不會記起我曾經來過。
多年之後,中央巡視組多次進駐民政部門。
老虎和蒼蠅們紛紛現行。
2016年年底,民政部專門管殯葬處的副部長因通姦與受賄落馬;緊接着,福彩中心原正副主任均被雙開,而且之前的三個主任一連串的落馬,再次讓我聯想到關大哥口中的民政口的油水單位。
上個月和關大哥聯繫,他告訴我,兒童福利院正在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福利院分區大改革,以後院裏的孩子會越來越少,而且之前的第三產業玩具廠也封門歇業了,院長已經多次開會,讓大家做好自謀生路的打算……心泛漣漪,驟願滌眼耳之塵,心舌之垢,復錄舊遊這暮煙四合之地。
(版權所有,轉載請聯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