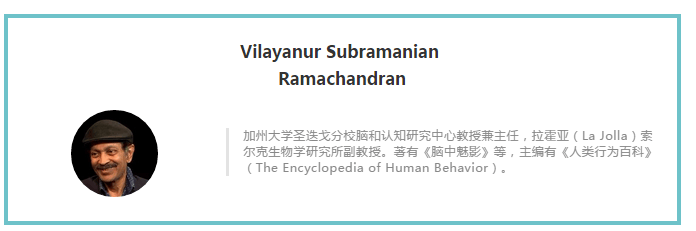追蹤幻影:幻肢為什麼會痛?_風聞
神经现实-公益的科学传播组织2018-10-29 1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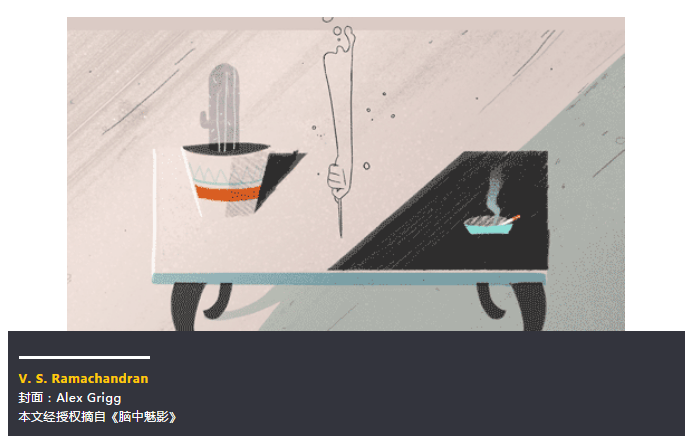
來源:神經現實
您永遠也不可能從您身體投出的影子中認清您自己,或者從其影像,或您在夢中所看到的身體,或從您的想象中認清自己。因此您也不能從這個活着的身體中認清您自己。
尚卡拉(Shankara)(788 — 820年),《吠陀經》
當有一位記者問著名的生物學家霍爾丹一個問題:他的生物學研究對他認識上帝有什麼幫助時,霍爾丹答道:“如果確有造物主的話,那麼他一定特別喜歡甲蟲。 ”
這是因為甲蟲的種數比任何其他生物羣的種數都要多。按照同樣的理由,神經病學家也可以斷言上帝是製圖員。他必定特別喜歡圖,因為隨便您看腦的哪個部位,都有大量的映射圖。例如單就視覺而言就有超過30個不同的映射圖。對觸覺或是體感來説,也就是觸覺、關節和肌肉感覺之類,它們都有許多映射圖,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彭菲爾德侏儒,這是腦兩側縱向皮層條上的映射圖。
這些圖在整個一生中是相當穩定的,從而有助於保證知覺通常是精確而可靠的。但是也正如我們看到過的那樣,作為對異常的感覺輸入的反應,這些圖也經常會進行更新和細化。請回想一下,當湯姆的手臂斷掉以後,對應於其已失去了的手的一塊很大的皮層就會被從他臉上來的感覺輸入所“接管”。如果我摸湯姆的臉,這時感覺信息就到達兩個區域 ——原來的臉區(本該如此),同時也到達原來的“手區”。腦映射圖的這種變化可能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手斷掉以後不久湯姆就會產生幻肢現象。每當他微笑或是當面神經上有某種自發活動時,這些活動就會刺激他的“手區”,由此使他誤以為他的手還在那兒。
但是這還不是全部故事。首先,這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許多幻肢病人聲稱他們能夠隨意地動他們“想象中”的肢體。這種運動錯覺的根源是什麼?其次,也沒有解釋這些病人為什麼有時會在已經失去了的肢體上感到劇痛,這種現象被稱為幻肢痛。再次,如果一個人生來就沒有一隻手臂,那又會怎麼樣呢?在他的腦中也會發生映射圖重組嗎?還是在他的皮層中根本就沒有發育過手區,因為他從來也沒有過手。他會有幻肢的體驗嗎?會有人生來就有幻肢嗎?
這些想法聽上去似乎很離奇,但是如果説我在這些年裏懂得了一件事,那就是神經病學中充滿了驚奇。就在我們發表了第一篇有關幻肢的文章幾個月後,我見到了一位25歲的印度研究生米拉貝爾·庫馬爾(Mirabelle Kumar),她是由森(Sathyajit Sen)醫生讓她轉診過來的,因為這位醫生知道我對幻肢感興趣。米拉貝爾生來就沒有雙臂。她只有兩條短短的殘肢從肩部垂下。X射線檢查發現這些殘肢內有肱骨(上臂骨)頭,但是沒有橈骨或尺骨的任何痕跡。她也沒有手上的小骨頭,雖然在她殘肢中確實有原始的指甲。
在一個炎熱的夏日,米拉貝爾走進了我的辦公室,她的臉由於爬了三段樓梯而發紅。這是一位迷人的、高高興興的年輕女士。她的臉上極明顯地顯現出“請別可憐我”的神氣。
當米拉貝爾坐好之後,我開始問一些簡單的問題:她是什麼地方人?她在哪兒上的學?她對什麼感興趣?如此等等。她很快就不耐煩了,並説道:“請説吧,您到底想知道什麼?您是想知道我是否有幻肢,對嗎?我們不要説廢話了。 ”
我説道:“好吧!是的,事實上我們在對幻肢做實驗。我們感興趣的是……”
她打斷我説:“沒錯。絕對如此。我從來就沒有手臂。我所有的就是這一些。 ”她敏捷而熟練地用下巴幫着脱下假臂,假臂掉在我的桌子上砰然作響,並且舉起她的殘肢。“從我童年能記事時開始我就有非常生動的幻肢感。”
我有些懷疑。是否有可能這只是米拉貝爾出於希望才這樣想?也許她有潛藏的慾望想要變得正常。我開始有點像起弗洛伊德來了。我怎麼能確定她不是在編造呢?
我問她:“您是怎麼知道您有幻肢的呢?
“是這樣的,因為就在現在我和您談話時,它們正在做手勢呢。正像您的臂和手那樣,當我指點東西的時候,它們也在指點這些目標。 ”
我向前靠了靠,完全給迷住了。
“醫生,關於它們還有件有趣的事,這就是它們並沒有它們該有的長度,它們短到只有6到8英寸。 ”
“您是怎麼知道的?”
米拉貝爾直視着我説道:“這是因為當我帶上我的假臂時,我的幻肢要比它應有的長度短得多。我的幻手指本應和假手的手指相配,就像戴手套一樣,但是我的幻臂短到只有6英寸長。我對此感到非常沮喪,因為這種感覺很不自然。通常我最後會要求假肢匠減短我假臂的長度,但是他説這看起來太短了而顯得滑稽可笑。所以我們最後採取了折衷方案。他給我的假肢比絕大多數假肢都要短,但是沒有短到異乎尋常而使它們看起來十分奇怪的程度。 ”她指了指落在桌面上的一隻假臂以使我明白。“它們比正常臂要短,但是絕大多數人不會注意到這一點。”
對我來説,這證明米拉貝爾的幻肢並非是她希望要而想出來的。如果她想要像別人一樣,那麼她為什麼會要一隻比正常的要短的手臂呢?在她的腦中一定發生了些什麼,使她產生了生動的幻肢體驗。
米拉貝爾還有另一個論點。“醫生,當我走的時候,我的幻臂並不像正常臂那樣晃動,就像您的手臂那樣。它們僵在身旁,就像這樣。 ”她站了起來,讓她的殘肢筆直地垂在身體兩邊。她説道:“但是當我講話的時候,我的幻肢會做手勢。事實上,現在我講話時,它們就正在活動。”
這並沒有聽上去那麼神秘莫測。當我們走路時負責流暢而協調地晃動手臂的腦區和控制做手勢的腦區是不同的。如果沒有後天從肢體上連續不斷地發來的反饋的話,或許負責手臂晃動的神經迴路就不能存在很久。當失去手臂以後,這種迴路就廢棄掉了或者不再發育。但是負責在講話時激發起來做手勢的神經迴路可能是在發育過程中由基因決定的。(有關回路可能先於口頭語言之前就有了。)值得注意的是,米拉貝爾腦中產生這些命令的神經迴路似乎一直是完整起作用的,儘管在她生活的任何時候她都沒有從這些“手臂”上接收到過視覺或運動感覺的反饋。她的身體一直在告訴她:“沒有手臂,沒有手臂。 ”然而她依然一直體驗到在做手勢。
這説明負責米拉貝爾身體影像的神經迴路一定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基因決定的,而不是嚴格地依賴於運動和觸覺經驗。有些早期的醫學報道聲稱出生時就沒有肢體的病人不會有幻肢體驗。然而我從米拉貝爾那兒所看到的卻表明我們所有人在出生時就有內在硬件布好線的有關身體和四肢的影像,這種影像可以一直起作用,甚至在遇到感覺上有矛盾的信息時也是如此。除了自發地做這些手勢之外,米拉貝爾也能用她的幻肢做隨意運動,成年後失去雙臂的病人也是如此。和米拉貝爾類似,大多數這種病人也能“伸”幻肢出去“拿”物體、指點、揮手告別、握手或是做一些精巧的動作。他們明白這聽上去像是瘋了,因為他們理解到他們沒有手臂,但是對他們來説,這種感覺體驗卻是非常真實的。
····
**在我遇到約翰·麥格拉思(John Mc Grath)之前,**我一直未能領會這種感覺上的運動有多麼逼真。這是一位手臂被截的病人,他是在看了一部有關幻肢的電視新聞故事之後打電話給我的。約翰是一位頗有造詣的業餘運動員,他在三年以前失去了肘以下的左臂。他笑着説道:“當我打網球時,我的幻手就會做它本來應該做的動作。當我發球時,它就要把球扔出去,而在我打一個高難度的球時,它就想幫我保持平衡。它總是想去接電話。它甚至在餐館中招手要賬單。
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我要求約翰伸手去拿杯子,但是在他的幻肢碰到杯子之前,從他那裏把杯子拿開又會怎樣呢?
約翰有一種稱之為望遠鏡式的幻手(telescoped phantom hand)。感覺上這隻手好像就直接連在殘肢上,中間並沒有手臂。但是如果某樣物體,比如説一隻茶杯放在離殘肢一兩英尺之外,他可以試着伸手去拿它。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的幻手就不再留在殘肢處,感覺上好像被拉伸了出去去拿茶杯。
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我要求約翰伸手去拿杯子,但是在他的幻肢碰到杯子之前,從他那裏把杯子拿開又會怎樣呢?幻肢會不會就像卡通人物的橡皮手臂那樣被拉長了呢?或是它就停在自然手臂的長度處?在約翰説他夠不着之前,我能把杯子移多遠呢?他能去拿月亮嗎?對真實手臂適用的物理約束是不是對幻肢也同樣適用呢?
我放了一隻咖啡杯在約翰前面,並要求他去拿它。就在他説他正伸出手去拿的時候,我突然把杯子搶走。
他高叫起來:“喔,不要這樣! ”
“怎麼回事呀?”
他重複説:“不要這樣,您搶走杯子時我的手指剛握住杯子的把手。這真的很疼。 ”
請停一下。我突然從幻手指中搶走一隻真的杯子,而病人叫喊起來,哇!當然囉,這些手指只不過是些錯覺,但是疼痛卻是真的,而且還那麼痛,因此我再也不敢重複這個實驗。
通過和約翰打交道,我開始考慮視覺在保持幻肢體驗中的作用。為什麼僅僅“看到”杯子被奪走就會造成疼痛?但是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考慮為什麼人會體驗到幻肢運動的問題。如果您閉上眼睛而動您的手臂,您當然能很生動地感覺到手臂的位置和運動,這部分地是由於有關節和肌肉中的感受器。但是不管是約翰還是米拉貝爾都沒有這種感受器。事實上他們連手臂都沒有。那麼他們的這些感覺又是打哪兒來的呢?
説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關於這一謎團我最初得到的線索來自我理解到有許多幻肢病人(或許佔到總數的三分之一)並不能動他們的幻肢。當要他們動他們的幻肢時,他們説:“醫生,我的手臂灌了水泥。 ”或是“它凍在一塊冰塊中了。 ”我們的一位病人艾琳(Irene)説道:“我想動我的幻肢,但就是動不了。它不服從我的意志,它不聽我的命令。 ”艾琳用她的好手臂模仿給我看她的幻臂的位置,給我看它是如何僵成一種古怪而扭曲的姿勢。它那樣已經有一整年了。當她進門時,她總擔心會撞到她的幻肢,這會使它痛上加痛。
幻肢(並不存在的肢體)怎麼會癱瘓呢?這聽上去好像是自相矛盾的。
我查了病歷,發現有許多這類病人從脊髓進到手臂的神經原來就有病變。他們的手臂以前就是癱瘓的,用吊帶懸起來或是固定了好幾個月,後來因為它們經常礙事而被截掉了。有些病人是被勸説截肢的,或許誤以為這樣就可以消除臂痛,或是糾正由這些癱瘓的手臂或腿所造成的姿勢異常。在手術之後這些病人常常生動地感到有幻肢,這是無足為怪的,但是使他們極端失望的是他們的幻肢還是像在截肢之前一樣僵在老地方,就好像對癱瘓的記憶繼續傳到了幻肢上去。
這樣我們就碰到了似乎荒誕而實有其事的情況:米拉貝爾在她的整個一生中從來就沒有過手臂,但是她卻能動她的幻肢。艾琳只是在一年前才失去了她的手臂,但是她的幻肢甚至一動也不能動。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仔細地看一下人腦中運動和感覺系統的解剖學和生理學。請想一下當您或我閉上眼睛做手勢時會怎麼樣。關於我們的身體、四肢的位置及其運動,我們都有生動的感覺。有兩位傑出的英國神經病學家布雷恩(Russell Brain)爵士和黑德(Henry Head)(沒錯,這些都是他們的真名)造了一個術語“身體影像(bodyimage) ”,以此來表示這種和身體對應的(vibrant)內心構造出來的體驗集合,也就是有關隨時空變化的自己身體的內心影像和記憶。為了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產生和維持這種身體影像,您的頂葉皮層就必須把來自許多來源(肌肉、關節、眼睛和運動命令中樞)的信息結合在一起。
當您決定要移動您的手的時候,首先是在額葉皮層上,特別是在稱為運動皮層的一縱條皮層組織上發生一連串事件,最終導致運動。這條皮層正好在把額葉皮層和頂葉皮層分隔開來的溝裂前面。就像感覺侏儒正好就在這條溝裂後面佔了一條皮層區域一樣,運動皮層也有整個身體的一個倒立的“映射圖”,不過這一映射圖是發信號到肌肉去,而不是從皮膚接收信號。
實驗表明初級運動皮層主要是和一些簡單的運動有關,例如動動手指或是咂咂嘴唇。就在其前面有一個稱為輔助運動區(supplementary motor area)的腦區,它似乎負責揮手告別、抓住扶手等比較複雜的技巧。這個輔助運動區就像是某種儀式的主持人,它向運動皮層發出一連串要加以執行的運動的特定指令。驅使這些運動的神經脈衝就從運動皮層傳送到脊髓,再到對側身體的肌肉,這樣就使您得以揮手告別或是塗口紅。
每當有“命令”從輔助運動區送到運動皮層時,它進一步到達肌肉並使它運動。與此同時還有兩份同樣的命令信號也傳送到另外兩個主要的“加工”區,也就是小腦和頂葉皮層,告訴它們想做的是什麼運動。
一旦這些命令信號送到肌肉之後,就有一條反饋環路起作用。肌肉在收到運動命令之後就運動起來。接着從肌梭和關節發出的信號又通過脊髓送回到腦,並通知小腦和頂葉皮層:“是!命令已經執行無誤。 ”這兩個結構幫助您對您的意向和實際執行結果進行比較,這就像伺服環路中的温變自動啓閉裝置那樣起作用,根據需要而修正運動命令(如果太快了,就制動;如果太慢了,就增大運動輸出)。這樣意圖就轉換成了流暢的協調動作。
····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病人,**看這一切和幻肢體驗究竟是如何關聯起來的。當約翰要動他的幻臂時,他腦中的額部依舊在發命令信息,因為約翰腦的這一特定部分並不“知道”他的臂已經丟掉了,儘管約翰“本人”無疑知道這一事實。頂葉也在繼續監視這一命令,並感到是在運動。但是這種運動是幻想出來的幻臂運動。
因此幻肢的體驗看來至少依賴於來自兩個來源的信號。首先是映射圖重組,請您回想一下從臉和上臂來的感覺信號激活了對應於“手”的腦區。其次,每當運動命令中樞發送信號到已經沒有了的手上時,有關命令信息也送到了包含有我們身體影像的頂葉。從這兩個來源來的信息會聚在一起,這就產生了在任一給定時刻和有關幻臂動態相對應的內心影像,當臂在“運動”時,這種影像也在不斷更新。
對於一條真實的手臂來説,還有第三個信息來源,那就是從該手臂的關節、韌帶和肌梭來的脈衝。幻臂當然沒有這些組織,因此也沒有來自它們的信號,但是奇怪的是這一事實似乎並未使腦免於受到愚弄,它還是以為肢體在動,至少在截肢的頭幾個月或頭幾年裏是如此。
不管從生理學上怎樣來解釋,當以後手臂被截去後,病人還依舊保持着這種更改過的影像:有一隻癱瘓了的幻肢。
這使我們回到了前一個問題。幻肢怎麼還會癱瘓呢?為什麼在截肢之後幻肢還會繼續“僵”在那兒?有一種可能性是當真的肢體癱瘓時,它用吊帶或支架固定起來,腦還在發送其通常發的命令,要手臂和腿動起來。頂葉監視這些命令,但是現在它收不到適當的視覺反饋。視覺系統告訴病人:“不!手臂沒有動。 ”這一命令又重複了一次:“手臂,動起來! ”視覺系統再次回覆告訴腦手臂沒有動。最後腦終於知道手臂不會動,而在腦的線路里留下了某種“習得性癱瘓(learnedparalysis) ”的印記。這一切究竟發生在什麼地方還不得而知,但是這可能有一部分是在運動中樞,也有一部分是在和身體影像有關的頂葉區域。不管從生理學上怎樣來解釋,當以後手臂被截去後,病人還依舊保持着這種更改過的影像:有一隻癱瘓了的幻肢。
如果您能習得癱瘓,那麼是不是也有可能使您不這樣呢?如果給艾琳送去她的幻臂“現在動起來了”的消息,那又會怎樣呢?而每當如此時,如果她都收到幻肢在動的視覺信號,不錯,幻肢聽從了她的命令,那又怎樣呢?但是如果她連手臂都沒有,那麼她又怎麼能得到視覺反饋呢?我們是不是有什麼辦法欺騙她的眼睛,使她以為真的看到了她的幻肢呢?
我考慮起虛擬現實來。或許我們可以造成一種視錯覺,使病人以為又有了手臂,而且還能服從她的命令。但是這種技術的價格要在50萬美元以上,一下子就會把我的整個研究經費都用光。幸而我想出了用一面從廉價商店裏買來的普通鏡子做實驗的方法。
為了使像艾琳那樣的病人能知覺到她們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手臂真的在運動,我們做了一個虛擬現實箱。這個箱子是把一個紙板箱的頂部去掉,然後在它裏面垂直地插一面鏡子。在箱子的前面開兩個洞,病人可以把她的“好手”(譬如説,右手)和她的幻手(左手)從這兩個洞中伸進箱子。因為鏡子插在箱子的中央,所以右手在鏡子的右側,而幻肢則在鏡子的左側。然後要求病人看她的正常手在鏡子中的像,並讓她把右手稍微動一下直到這個像就好像疊加在她所感到的幻肢的所在處。這樣她產生好像看到了兩隻手的錯覺,其實她只是看到了好手在鏡子中的像而已。如果現在她向兩臂都發命令,要它們做鏡面對稱的運動,就像在指揮交響樂或拍手那樣,當然這時她也“看到”了她的幻肢也在動。她的腦接收到了視覺反饋,證實幻肢正在按她的命令正確地動起來了。這樣是否對她能隨意地控制她的癱瘓了的幻肢有所幫助呢?
····
**菲力浦·馬丁內斯(Philip Martinez)是探索這一新世界的第一人。**1984年菲力浦從他的摩托車上被拋了出去,當時他正以45英里/時的速度沿聖迭戈高速公路疾駛。他飛過中線,掉在一座混凝土橋的橋腳,他暈頭暈腦地站立起來,但還有神志檢查了一下是否受傷。頭盔和皮夾克使他倖免於難,但是菲力浦的左臂在近肩處給劇烈地擰壞了。就像龐斯博士的猴子那樣,他受到了臂撕裂(brachial avulsion),支配手臂的神經給從脊柱上撕了下來。他的左臂完全癱瘓了,了無生氣地吊在吊帶上有一年。最後醫生勸告他做截肢手術。這條手臂只會礙事,而再也不會恢復功能了。十年之後,菲力浦走進了我的辦公室。當時他已經三十好幾了,他的殘疾反而使他作為一名落袋枱球戲玩家而名聲大震,朋友們稱他 為“獨臂大盜(one-armed bandit) ”。
菲力浦從當地新聞中聽説了我對幻肢所做的實驗。當時他很絕望:“拉馬錢德蘭醫生,我希望您能幫助我。 ”他往下看他失去了的手臂。“我在十年以前沒有了手臂。但是打那以後,我的幻肘、腕和手指一直劇痛不止。 ”以後又做了進一步的面談,我發現在過去十年中,菲力浦一直未能動他的幻臂。它總是固定在一個古怪的位置上。菲力浦是不是得了習得性癱瘓?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能不能用我們的虛擬現實箱子通過視覺讓他的幻肢“復活”並恢復運動?
我要求菲力浦把他的右手放到箱子裏鏡子的右邊,並想象他的左手(幻肢)在鏡子的左邊。我命令他説:“我要您同時動您的左右兩臂。”
菲力浦叫道:“喔,我做不了呀,我能動我的右臂,但是我的左臂僵住了。每天早上當我起身時,我總是想動動我的幻肢,因為它位置不當,我想動動它也許能緩解一點疼痛。但是, ”他向下看了下他那無法看到的手臂,繼續説道:“我從來也未能動這隻手臂,哪怕就那麼一丁點兒。”
“好吧,菲力浦,無論如何試一試吧。 ”
菲力浦轉動身軀,移動肩膀,把他那沒有生命的幻肢“塞進”箱子裏。然後他把他的右手伸到鏡子的另一邊,並試圖讓它們同步運動起來。當他看鏡子的時候,他喘了口氣驚叫起來:“啊呀,天哪!啊呀,天哪,醫生!真不敢相信,真是想不通! ”他就像個孩子那樣跳上跳下。
“我的左臂又接通了。我就好像回到了過去。多少年以前的所有這些記憶又都湧回到我的頭腦裏。我可以再動我的手臂了。我能感覺到我的肘在動,我的腕在動,又都動起來了。 ”
等他冷靜下來一點以後,我説:“好吧!菲力浦,現在請閉上您的眼睛。”
他很明顯失望地説道:“啊呀,天哪,它又僵住不動了。我能感覺到我的右手在動,但是幻肢不動了。 ”
“睜開您的眼睛。”
“喔,是的,現在它又動起來了。 ”
這就好像是菲力浦暫時抑制或阻斷了通常使幻肢運動的神經迴路,而視覺反饋則去除了這種阻斷。而尤其令人吃驚的是,這種手臂運動的體感一下子就恢復了,儘管這在前十年中從來也沒有感覺到過。
儘管菲力浦的反應令人振奮,並對我有關習得性癱瘓的假設是某種支持,那晚我回家自問:“這又怎麼啦?我們讓這個人又能動他的幻肢了。但是如果您仔細想想,這種能力完全沒有什麼用處,這正是那種我們醫學研究人員中許多人所責備的對一些神秘現象的研究。 ”我完全明白是決不會因為使一個人移動一隻幻肢而獲獎的。
但是習得性癱瘓可能是一種更為普遍的現象。真實肢體癱瘓的人(比如説,由於中風造成的)也可能會發生這種情形。為什麼人在中風之後會用不了一隻手臂了呢?當供腦的血管堵住之後,從腦的額部到脊髓去的神經纖維缺氧而受到損傷,結果就使手臂癱瘓了。在中風早期,腦發生腫脹,使有些纖維死去了,但是還有些纖維只是暫時性地失去作用,打個比喻説就是“離線(off-line) ”了。此時,手臂喪失了功能,腦接收到視覺反饋:“不行呀,手臂動不了了。 ”在腫脹消退以後,病人的腦還可能繼續有某種形式的習得性癱瘓。那麼是否可以用鏡子那樣的小玩意至少部分地消除由於習得這部分因素所造成的癱瘓?(當然了,對於由於纖維受到真正毀壞所引起的癱瘓,想用鏡子恢復其功能就無能為力了。)
但是在我們能對中風病人進行這類新的治療之前,我們需要確定這種效果並非像幻肢運動那樣只是一種臨時性的錯覺。(請回想一下,當菲力浦閉上雙眼之後,幻肢運動的感覺就消失了。)如果讓病人用這種箱子練習好幾天,以不斷地接受視覺反饋,那會怎麼樣呢?有沒49 有這樣的可能,腦可以消除習得的損傷了的知覺,而使運動得以永久性地恢復?
第二天我回到辦公室,並問菲力浦:“您是否願意把這個裝置帶回家去練習?”
菲力浦答道:“當然囉,我很願意帶它回家。我對我能再動我的手臂感到非常興奮,即使只是一會兒。 ”
因此菲力浦就把鏡子帶回家了。一星期後,我打電話給他。“情況怎樣?”
“喔,很好玩。醫生。我每天都用它十分鐘。我把手伸進去,到處揮動,看看到底有什麼感覺。我的女朋友和我一起用它來玩。非常好玩。但是當我閉上雙眼,還是不行。如果我不用鏡子,那麼也不行。我明白您想要我的幻肢能再次運動,但是如果不用鏡子就是不行。 ”
又過了三個星期,直到有一天菲力浦來看我,既激動又興奮。他説道:“醫生,沒有了。 ”
“什麼東西沒有了?”(我還以為或許是他丟失了鏡箱呢。)
“我的幻臂沒有了。”
“您説的是什麼呀?”
“您要知道,是我的幻臂呀,我都有了十年了。再也沒有了。我現在只有幻手指和幻掌就懸在肩下。”
我當時的反應是,喔,不會吧!我好像已經用一面鏡子就永久性地改變了一個人的身體影像。這會對他的精神狀態和心情產生怎樣的影響呢?“菲力浦,這可使您感到煩惱嗎?”
他説道:“不!不!不!不!不!不!正相反,您知道我肘部一直以來的劇痛吧?每個星期它總要折磨我好幾次。好了,現在我沒有了肘部,我再也不痛了。但是我還是有手指,它們就垂在肩下,還是發痛。他停頓了下來,顯然是要讓我理解這一點。他接着説:“不幸的是,您的鏡箱不再能起作用了,因為我的手指位置太高了。您能不能把設計改變一下,好消除我的手指?”看來菲力浦把我當成某種魔術師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幫助菲力浦解決他的問題,但是我認識到這大概在醫學史上還是首次得以成功地“切除”了一隻幻肢!這個實驗表明,當菲力浦的右頂葉同時得到兩種相互衝突的信號時(視覺反饋告訴他手臂又能動了,而肌肉告訴他根本就沒有手臂),他的心智就採取了50 不承認的態度。他那受到困擾的腦對付這種離奇的感覺衝突的唯一途徑就是説:“真見鬼,根本就沒有手臂! ”作為鉅獎,菲力浦也連帶不再感到幻肘部的疼痛了,因為大概不大可能再在一隻不再存在的幻肢上感受到無所附着的疼痛。還不清楚為什麼他的手指還在,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手指在體感皮層上受到了過度的表徵,就像嘴唇在彭菲爾德的映射圖上很大一樣,因此可能更難於否認。
····
**關於幻肢運動和癱瘓的問題就夠難於解釋的了,**許多病人在截肢後不久所感到的劇痛就更令人不解了,而菲力浦則使我直面這個問題。有哪些生物學上的條件合在一起才會引起在一隻根本就不存在的肢體上的疼痛?這有好幾種可能性。
這種疼痛可能是由疤組織或是神經瘤(神經組織在斷面上所形成的捲曲小團)引起的。腦可能把對這些團塊和受到磨損的神經末端的刺激解釋為已經不復存在的肢體的疼痛。用外科手術切除神經瘤有時也能消除幻肢痛,至少暫時如此,但是它們往往在不知不覺間又去而復回。
疼痛也可能部分來自映射圖重組。請記住映射圖重組通常是有模態特異性的:這就是説,觸覺通路管觸覺,温覺通路管温覺,如此等等。(正如我指出過的那樣,當我用棉球籤輕觸湯姆的臉時,他感到我在碰他的幻肢。當我滴冰水在他的臉頰上時,他就感到他的幻手上有冷的感覺,而當我滴熱水時,他的臉部和幻肢上都感到熱。)這大概意味着映射圖重組並非是隨機的。和每種感覺有關的纖維一定“知道”到哪兒去找適當的靶體。因此在絕大多數人中,其中包括您、我和截肢病人都沒有交叉佈線(cross-wiring)。
但是如果在映射圖重組過程中發生了些許錯誤(在藍圖中有些小錯),因此使得有些觸覺輸入碰巧輸入到了痛覺中樞,那又會怎樣呢?每當擦到病人臉部或上臂的一些區域(而非神經瘤)時,甚至只是輕輕地擦到,病人都有可能感到劇痛。輕輕一觸就可能產生劇痛,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由於有一些纖維到了不該去的地方,做了不該做的事。
坦白説,我們真的還不知道腦是如何把神經活動模式翻譯成有意識的體驗的,不管是疼痛、愉快還是顏色都是如此。
映射圖的異常重組還可能通過另外兩種方式引起疼痛。當我們感到疼痛時,根據需要激活了一些不但傳導而且還同時加強或減弱這種感覺的特殊通路。這種“音量控制(volume control) ”[有時也稱為門控(gate control)]正是使我們在有不同需求時得以有效地調整我們對疼痛的反應的原因所在(這也許可以解釋針麻為什麼能起作用,也可能解釋為什麼有某些文化背景的婦女在分娩時並不感到疼痛)。在截肢病人中完全有可能由於映射圖重組而失去了這種音量控制機制,結果產生了一種像回聲那樣的“哇哇(wha wha) ”迴響,並對疼痛加以放大。其次,映射圖重組從本質上來講就是一種病理過程或者説是一 種不正常的過程,至少在失去肢體之後發生大規模重組時是如此。很可能觸覺突觸並沒有得到正確的重布,它們的活動很可能是混沌的。腦的高級中樞於是把這些不正常的輸入模式當成了垃圾,並知覺為疼痛。坦白説,我們真的還不知道腦是如何把神經活動模式翻譯成有意識的體驗的,不管是疼痛、愉快還是顏色都是如此。
最後,有些病人説就在他們截肢之前所感到的肢體疼痛成為一種疼痛記憶而保存了下來。例如,手榴彈就在自己手中爆炸的士兵常常報告説他們的幻手總是在某個固定的位置,緊握着手榴彈,正準備扔出去。這種手痛是鑽心刺骨的,和手榴彈爆炸時的感覺一模一樣,永久地烙在他們的腦中了。有一次,我在倫敦遇見一位婦女,她告訴我説,在她童年時她曾經有好幾個月老是感到她的拇指有一種像冷天時凍瘡那樣的疼痛。這個拇指後來變成壞疽而被截掉。現在她有一個幻拇指,而且每當天轉冷時總感到是生了凍瘡。另一位婦女則説在她的幻關節上感到有關節炎痛。她在截去手臂之前就有這個問題,但是在不再有真的關節之後問題依然如故,當天氣變得潮濕和寒冷時疼痛就會加劇,這就和關節在被截去之前一模一樣。
我所在的醫學院中有一位教授告訴我一個故事,他發誓説這是件真事,這是一件關於另一位醫生 ——一位卓越的心臟病學家的故事,他由於血栓閉塞性血管炎(Buerger’s disease)而在腿部發生陣發性的痛性痙攣(pulsating cramp),這種病使動脈收縮,並在腓腸肌中產生強烈的陣發性疼痛。
儘管經過多方治療,始終未能止痛。這位醫生完全絕望了,因此決定截去他的腿。他再也不能忍痛活下去了。他找了位外科醫生同事並安排了手術,但是令外科醫生驚異的是,病人説他有一個特別的要求:“在截掉我的腿之後,您是否可以把它泡在一瓶甲醛裏面給我?”
説得最輕,這一要求也是離奇古怪的,但是這位外科醫生還是同意了,截掉了腿,把它放在一瓶防腐液中並給了這位醫生。他把瓶子放到了自己的辦公室裏面,並且説道:“哈!我最終還是得以看着這條腿並嘲笑它説:‘我最終還是擺脱了你!’”不過笑到最後的卻是那條腿!陣發性疼痛又回到了幻腿上以資報復。我們那位好醫生無法相信地瞪着漂浮在瓶中的肢體,它也反過來瞪着他呢,就好像在嘲笑他想擺脱它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了。
流傳有許多此類故事,這類故事説明疼痛記憶的驚人特性,當肢體被截掉後它還會表現出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可以想象如果在手術之前就對要截去的肢體進行局部麻醉的話,這樣就有可能降低截肢以後疼痛的發生率。(確實也試過這種方法,並取得了某些效果。)
····
**在所有的感覺中,**痛覺是瞭解得最少的感覺之一。疼痛常常使病人深為沮喪,連醫生也是如此,疼痛還常常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從病人那兒經常能聽到的特別令人不解的一種抱怨是,他們的幻手不時地 變得緊握成拳,手指深掐進手掌,其力量就像一位職業拳擊手在準備揮出決定性的一擊時那樣。
羅伯特·湯森(Robert Townsend)是一位聰明的工程師,55歲時,由於癌症而使他截去了肘上6英寸的左臂。我遇到他是在他截肢7個月之後,他非常生動地感到有一條幻肢,這條幻肢經常不由自主地緊握到痙攣。羅伯特説道:“就好像我的指甲要掐進到我的幻手裏面去一樣。痛得無法忍受。 ”即使他全神貫注想鬆開這隻看不到的手,還是一籌莫展,無法緩解它的痙攣。
我們想知道是否也可以用鏡箱幫助羅伯特消除痙攣。就像菲力浦一樣,羅伯特朝箱子裏看,把他好手的位置擺得使其鏡像正好和幻手相重,先用好手握拳,然後試着同時鬆開兩手。羅伯特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就宣稱他的幻拳隨着好拳一起鬆開了,這完全是由於視覺反饋53 的作用。更好的是疼痛也隨之而去。有好幾個小時幻手就一直張開着,直到後來又自發地產生新一輪的痙攣。要是沒有鏡子的話,他的幻手會抽痛40分鐘或更長時間。羅伯特把箱子帶回了家,每當他又握拳而痙攣的時候,他就故技重施。如果不用這個箱子的話,即使竭盡全力,他也無法鬆開拳頭。如果他用了這面鏡子,手一下子就鬆開了。
我們對十幾名病人試過用這種方法進行治療,大概對一半病人有效。他們把鏡箱帶回家,每當發生痙攣時,他們就把好手伸進箱子鬆開手,痙攣也就隨之而去。這真是一種治療嗎?很難搞清楚這一點。痛覺極易受安慰劑效應的影響(説服的力量)。或許只要有精巧的實驗室設備或是一位治療幻肢的名醫在場就足以消除疼痛了,可能這根本就和鏡子沒有關係。我們對一位病人檢驗了這種可能性,我們給了他一隻沒有什麼害處的電池盒,它可以產生一點電流。我們要他在產生痙攣和姿勢不當時,就轉動他那個“皮膚電刺激器(transcutaneouselectrical stimulator) ”上的轉盤,直到他開始感到在他的左臂(他的好臂)有刺痛感。我們告訴他這會立刻恢復他幻肢的隨意運動,並解除痙攣。我們還告訴他這種方法對一些和他有同樣問題的病人很有效。
他説道:“真的嗎?哇,我恨不得立刻就試。 ”
兩天以後他回來了,顯然非常惱怒。他叫道:“一點用也沒有,我試了5次,就是沒有用。我把它轉到了頭,雖然你們告訴過我不要這樣做。”
同一天下午我給他鏡子試試,他立刻就能張開他的幻手了。痙攣也沒有了,指甲深掐到手掌裏的這種感覺也消失了。如果您仔細想一下,這是一種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這裏講的是一個既沒有手,也沒有指甲的人。這個人怎麼會把並不存在的指甲掐進也不存在的手掌裏面去,還由此產生鑽心刺骨的疼痛呢?為什麼一面鏡子就能消除這種虛幻的痙攣呢?
當有運動命令從前運動皮層傳送到運動皮層去握拳時,請想想看您腦中發生了些什麼呢?一旦當您把手握成了拳,從您手中的肌肉和關節發出的反饋信號通過脊髓回送到腦,並告訴腦:“慢一點,夠了。進一步握緊就要握疼了。 ”這一本體反饋以驚人的速度和精度自動起制動作用。 然而如果肢體沒有了,也就不會再有這種制動反饋了。因此腦繼續發送命令,再握緊點,握緊點。運動輸出甚至得到進一步的放大(直到遠遠超過你我所曾經達到過的最大水平),這種過度的運動輸出或者“竭力感(sense of effort) ”本身可能在感覺上就成了疼痛。鏡子的作用可能是提供視覺反饋使手鬆開,因此也就消除了緊握產生的痙攣。
但是為什麼有指甲深掐的感覺呢?只要想一下當您握起拳頭而感覺到您的指甲掐入手掌的無數次經歷。在您的腦中,這些經歷一定在握拳的運動命令和明確無誤的“指甲掐入”感之間建立起某種記憶聯繫[心理學家把這稱為赫布聯繫(Hebbian link)],因此您很容易就在您的心智中喚起這種景象。但是儘管您可以把這種景象想象得非常生動,但是您並不會真正有這種感覺,並且説道:“啊,痛呀。 ”為什麼呢?我相信其原因就在於您有一個真的手掌,而這個手掌的皮膚告訴您並不痛。您可以這樣想象,但是您不會這樣感覺,這是因為您有一隻正常的手在發送真實的反饋,在現實和虛幻發生衝突時通常總是現實勝出
但是截肢病人並沒有手掌。從他手掌上並沒有發出取消信號以禁止產生原來存儲着的疼痛記憶。當羅伯特想象到他的指甲正掐入手掌時,他得不到來自皮膚表面的相反信號告訴他:“羅伯特,你這個傻瓜,這裏並不痛呀。 ”事情確實如此,如果運動命令本身和指甲掐入感聯繫到了一起,那麼可以想象如果把這些信號加以放大,就會使和這些信號連在一起的疼痛信號也被相應地放大了。這可能可以解釋為什麼這種疼痛會如此難以忍受。其中的含義非常深刻。即使是短暫的感覺聯繫,就像握拳和指甲掐入手掌之間的那種聯繫都會在腦中留下永恆的痕跡,並且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才會表露出來,在這個例子中就是感覺到幻肢痛。此外,這些理解還意味着疼痛是對機體健康狀態的某種評價,而不只是對損傷的一種反射性反應。在腦中並沒有從痛覺感受器到“痛覺中樞”的直達熱線。與此相反,在不同的腦區之間有許許多多相互作用,例如那些和視覺與刺激有關的腦區就是如此,只要在視覺上看到拳頭鬆開了,這種信息就會回過來一路饋送到病人的運動通路和觸覺通路,並使病人感到拳頭鬆開了,因此消除了在一隻並不存在的手上的疼痛錯覺。
····
**如果疼痛是一種錯覺,**那麼像視覺之類的感覺對我們的主觀體驗有多大影響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對我的兩個病人做了些多少有點不那麼正規的實驗。
當瑪麗(Mary)走進我的實驗室時,我要求她把她的幻肢右手巴掌向下伸到鏡箱裏面。然後我要求她在她好的左手上帶上一隻灰色的手套,並伸到箱子的另一邊的鏡像處。在確定她感到舒服之後,我要我的一名研究生藏身在一隻用幕布遮蔽起來的桌子底下,並把他戴有手套的左手伸進箱子中瑪麗的好手所在的同一邊,放在她手上面的另一個枱面上。當瑪麗向箱子裏看時,她不僅可以看到研究生戴手套的左手(這隻手看上去和她自己的左手一模一樣),此外還可看到這隻手在鏡子中的像,就好像她正在看她自己戴手套的幻肢右手。當這名學生握拳或是用他的食指墊(pad)去摸他的拇指球(ball)時,瑪麗生動地感到她的幻肢也在動。和我們的前兩個病人一樣,單靠視覺就能騙她的腦感到她的幻肢在運動
如果我們愚弄瑪麗,讓她以為她的手指處在一個解剖學上不可能的位置,那又會發生些什麼呢?用鏡箱就可以試試這種錯覺。還是讓瑪麗把她的幻肢右手手掌向下伸進箱子裏面。但是這次學生做的動作和上次不一樣。他不是把他的左手伸到箱子的另一邊和幻肢成鏡面對稱的地方,而是把右手手掌向上伸了進去。因為手上帶有手套,它看上去和她的“手掌向下”的幻肢右手一模一樣。然後學生屈曲他的食指去觸摸他的手掌。瑪麗向箱子裏看時,就好像她的幻肢食指向後翻轉去觸摸她手腕的背部,方向完全錯了!她的反應會怎麼樣呢?
當瑪麗看到她的手指向後彎時,她説道:“醫生,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感覺應該很奇怪,但是並非如此。感覺上手指好像就是向後翻轉,而不像人們認為它應該彎的方向。但是感覺上既不古怪,也不痛,或是諸如此類的感覺。”
卡倫(Karen)是另一位受試者,她苦着臉説道彎轉的幻肢手指很疼。她説道:“感覺上就像是有人在抓住我的手指拉,我感到劇痛。 ”
這些實驗很重要,因為它們和下列理論完全不相容:這種理論認為腦就像是為了應急而臨時組織起來的一隊人那樣由許多自主模塊組成。由於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的大力宣傳,人們普遍相信腦就像是一台計算機,它的每一個模塊都執行高度特異化的工作,然後把它們的輸出傳送給下一個模塊。在這種觀點看來,感覺信息處理只有從皮膚上的感受器和其他感覺器官到腦高級中樞的一條串行的信息單行道。
但是我對這些病人所做的實驗使我懂得腦並不是這樣工作的,其中的聯結異常多變並隨時間發生變化。知覺是從感覺多層次結構中不同層次之間信號的迴響中湧現出來的,這種迴響甚至可能跨越不同的感覺。視覺輸入可以消除一隻並不存在的手臂中的痙攣,並且消除了連帶產生的疼痛記憶,這一事實生動地説明了這些相互作用可以有多麼廣泛和多麼深刻。
····
**對幻肢病人的研究使我對腦的工作機制有了深刻的瞭解,**這遠遠超越了4年前當湯姆第一次走進我的辦公室時我開始問的那些簡單問題。我們確實見證到了(直接或間接地)在成人的腦中如何產生出新的聯結,不同的感覺信息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感覺映射圖的活動是如何關係到感覺體驗的,而更具普遍性的問題是:腦怎樣不斷地更新它內部對現實世界的模型,從而對新遇到的感覺輸入作出反應。
最後的這一觀察對所謂的先天—後天之爭給出了新見解,它使我們問下列問題:幻肢現象主要是來源於像映射圖重組或斷面神經瘤這樣的非遺傳因素呢,還是它們只是在精神上要求維持某種生而有之的、由遺傳決定的“身體影像”的一種表現?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能是:幻肢是從這兩者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中湧現出來的。我要講5個例子給您聽,來説明這一問題。
當截肢病人截去的是肘下部分時,醫生有時候會把斷面劈成像龍蝦螯那樣的兩半,用以代替安裝標準的金屬爪。病人在手術之後學着用他們斷面處的“螯”去抓東西,使它們轉向,並以新的方式操控物質世界。有趣的是,他們的幻手(離殘肢幾英寸處)在感覺上也分成 了兩個,在殘肢的每半片上都有一或幾個幻肢手指,它們都能逼真地模仿所在那片的運動。我知道有一個病例,醫生截去了病人的螯形殘肢,結果卻永久性地留下了分裂的幻肢,這是一個驚人的證據説明外科醫生的手術刀可以對幻肢進行解剖。在最初把斷面劈開的手術之後,病人的腦一定重塑了他的身體影像,其中包括了兩片螯狀物,否則他怎麼會感到幻螯狀物呢?
還有兩個故事既有趣又有教益。有一個女孩生來就沒有前臂,她感到在她的殘肢下6英寸處有幻手,還常常用她的幻手指進行計算和解算術問題。有一位16歲的女孩,生來她的右腿就要比左腿短2英寸,她在6歲時接受了一次膝下的截肢手術,結果使她產生了有4只腳的奇怪感覺。除了那隻好腳和另一隻預料之中的幻腳之外,她還有兩隻額外的幻腳,一隻正好就在截斷處,而第二隻腳則連着腿肚一直向下延伸到地板,要是這條腿不是先天就長得短的話,它就本該是這個樣子。雖然研究人員曾經用這個例子來説明遺傳因素在決定身體影像方面的作用,但是人們也可以同樣用這個例子來強調非遺傳的影響,因為人們可以問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您的基因對一條腿要指定三個分開的影像呢?
説明基因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第四個例子要回到我們對許多截肢病人體驗到有生動的幻肢運動的觀察,這些運動既有隨意的,也有非隨意的,但是這些運動最後大多數都消失了。最初感到這些運動是因為腦在繼續向截肢之後已經不再存在的肢體發送運動命令(同時也在對它們進行監視)。但是或遲或早由於缺乏視覺上的確認(呀,手臂沒有了)就會使病人的腦否決這些信號,因此也就不再感覺到有 運動。但是如果這個假設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又怎樣來理解像米拉貝爾這樣生而無臂的人會一直有生動的肢體運動錯覺的現象呢?我只能作這樣的猜測:正常成年人都在一段時間內保有視覺和運動感覺反饋,這使得腦甚至在截肢以後依然期待着有這種反饋。如果這種期望落空,腦感到“失望”,最終就不再有隨意運動的錯覺,甚或完全失去了幻肢本身。但是米拉貝爾腦的感覺區從來就沒有接收到過這種反饋,其結果是根本就沒有習得的對感覺反饋的依存性,這可能可以解釋為什麼她的運動感覺可以持續25年之久而毫無變化。
最後一個例子來自我的祖國印度,每年我都要回去一次。在那裏可怕的麻風病依然相當普遍,這種病常常使病人不斷致殘以致失去四肢。在韋洛爾(Vellore)的麻風病院裏,人們告訴我這些失去手臂的病人並沒有幻肢的感覺,我也目睹了一些病例,並證實了這些説法。對此的標準解釋是這些病人逐漸“學會”了利用視覺反饋把殘肢融入他的身體影像中,但是如果這種説法成立的話,那又如何解釋截肢病人一直感到有幻肢呢?或許這是由於逐漸喪失四肢,或者是由於麻風菌也同時逐漸損傷神經,它們以某種方式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這或許讓他們的腦有更多時間去重新調節他們的身體影像以適應現實情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當這種病人的殘肢是由於壞疽而切除了有病的組織之後,他們確實也有幻肢現象。但是這個幻肢並非是原來的那個殘肢,而是整個幻肢手!這就好像腦有雙重表徵:一個是由遺傳決定的原來的身體影像,另一個則是與時俱進的不斷更新的影像使之能把以後的變化也吸收進來。由於某些還不知道的原因,切除手術打亂了這種平衡,而使原來的身體影像又復甦了,這種身體影像一直在想贏得注意。
我之所以要提起這些離奇古怪的例子,是因為它們意味着幻肢是由遺傳因素和經驗因素的複雜相互作用湧現出來的,關於這兩種因素貢獻的相對大小隻有通過系統的經驗研究才能得以闡明。正如許多先天—後天之爭一樣,要想追究哪個因素最重要是沒有意義的,儘管在文獻中一些極端的説法與此正好相反。(説實在的,問這樣的問題並不比問下列問題更有意義:水的潮濕性主要是由構成水分子的氫原子呢,還是氧原子?)但是好消息是通過做恰當的實驗,您可以把這兩者分開,研究它們如何相互作用並最終研究出治療幻肢痛的新方法。即使僅僅只是思考您有可能用視錯覺來鎮痛都似乎是天方夜譚,但是請記住疼痛本身也是一種幻覺,它和其他任何感覺一樣都完全是在您的腦內構成的。用一種幻覺去消除另一種幻覺看來畢竟不那麼令人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