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存在“東亞文化共同體”嗎?從朝鮮看大清_風聞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教授2018-10-30 15:56
發現“東亞漢文文獻”:驚異的豐富
我從2000年起開始關注這些漢文文獻。在這裏,我想先説明一下,這十幾年來,我為什麼要從中國思想史研究轉向東亞文化史領域,為什麼會如此關注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的這些有關中國的漢文文獻。
第一個原因,是近年來關於“東亞”的話題逐漸升温。但是,究竟“東亞”(或者東北亞)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就像“歐洲”一樣)在政治、歷史和文化上彼此認同的“共同空間(或共同體)”?
什麼要素能夠使它成為一個彼此關聯的“歷史世界”?要成為這樣一個“共同空間(或共同體)”,是否需要檢討和反省各自的歷史和文化?現在的中國、日本和朝鮮,是否文化與觀念上還那麼接近,就像漢唐時代所謂“漢字文化圈”一樣?要形成一個歷史視野中的“文化圈”,它是否要在歷史文獻中尋找“關係”?這些學術界和思想界不能迴避的話題,卻沒有很深入的討論。
為了回應現在流行於韓國、日本和中國大陸及台灣學術界的這一話題,近年來,我越來越關注這個被叫作“東亞”的、原本並不是我所擅長的歷史世界,並且漸漸進入了這個研究領域(5)。
第二個原因,是由於近年來,受到後殖民、後現代等歷史學新理論的影響,一些學者對於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描述歷史的方法,有很多質疑和批評,這引起了一系列新話題,究竟什麼是“中國”?如何重新理解和釋“中國”?是否可以像某些人説的那樣可以“以中國解釋中國”?是否必須超越“國家”而進行“區域”研究?這又刺激了我重新理解和解釋“東亞”和“中國”的興趣。因為我覺得,不能不改變長期以來習慣地以“西方”(尤其是歐洲)為尺度和背景來觀察中國、以及用現代的政治國家來討論歷史的文化中國的方法,可能需要通過“周邊”(或者像日本人説的那樣叫“周緣”),來重新審視中國這個特別的民族、國家與文化的歷史存在和現實意義(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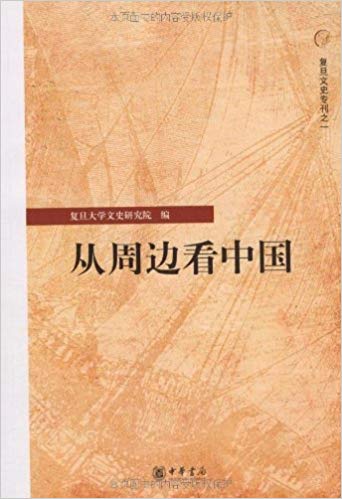
因此,我一直很注意在日本、韓國、越南和港台地區閲讀和收集這類資料,不僅組織了一些有關的文獻整理出版工作,也請了一些朋友和學生為我收集這些資料(7)。當我仔細地看這些文獻的時候,覺得相當有趣,也覺得十分震驚,因為留存在那裏的資料,數量太多,內容太豐富;也覺得相當詫異和不解,過去為何我們視而不見這些可以重新理解“中國”的東西?前面提到過《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吳晗所輯十二大冊,就已經給我們留下很多課題,而日本的《華夷變態》、《唐通事會所日錄》以及漂流船的詢問記錄等等,數量龐大,也有着相當多的珍貴史料,而李朝朝鮮的《同文匯考》、《承政院日記》、《備邊司謄錄》中有這麼多有關朝鮮與中國的資料,也相當讓人吃驚(8)。
這裏有太多中國早已不存,或者隱而不彰的歷史。例如明代政治的黑暗與官場的腐敗,例如明清易代之際流亡中國人對於明亡清興的歷史反思,例如清王朝穩定之後,仍然有相當激烈的滿漢衝突等等。這裏我隨意舉一個例子,像康熙十三年(1674)吳三桂起兵反清時,聲討滿清“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衣冠”的《檄文》,不管他是不是真心,這一檄文都不被清朝官方文獻所保留,卻收錄在朝鮮的《李朝實錄》和日本的《華夷變態》中,在東亞(包括中國沿海)曾經廣泛流傳(9)。
其實有價值的史料,遠不止是龐大的官方史料和整齊的歷史書籍,那些散見的個人記錄,比如日記、文集、筆談,甚至詩歌,有時比官方檔案和歷史著作更深刻地呈現着當時朝鮮、日本人對於中國的見聞、記憶和想象。
我之所以用“見聞”這個詞,是因為這裏有很多是實地考察的實錄。到中國來旅行的日本和朝鮮文化人,特別是到明清帝國出使的朝鮮使臣,留下了像《朝天錄》、《燕行錄》這樣數百種詳細的中國記錄,這些記錄大體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當然,它是有朝鮮立場的官員和文人的觀察,是用“異域之眼”對中國,特別是從鳳凰城到北京這一路北中國的政治、社會、風俗、人情的觀察。這些觀察相當有價值,就像一個初到異域處處好奇的人,常常能夠發現本地人習以為常而忽略的細節一樣。比如朝鮮人觀察到的,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大清帝國風俗的變化,就相當深刻地呈現了中國社會的內在變遷(10)。
其中,朝鮮人特別關注的一些風俗轉變,諸如“喪禮用樂”、“男女無別”、“崇祀佛陀與公”、“官員文人經商”之類,就呈現出恪守傳統的朝鮮人眼中,大清帝國的深刻社會變化。以喪禮用樂為例,他們看到北京“喪制敗壞……作樂娛屍”(11),批評漢族士人“送葬之際,廣設齋會,緇徒填空,佛樂盈
路”(12),特別不滿漢族中國人在喪禮中間吹竹彈絲,而且喪車前有樂隊(13),這些見聞和評價,可以和清代祁爾薩條奏所説的“風俗日下,至有多豬羊,大設盛饌送飯者,競相效法,過於奢靡,無所止極……近漢人居父母喪,才□□即變易服色,以更宴會”的記載互相印證,也可以和福格《聽雨叢談》卷六里記載的北京城裏的喪禮新俗用鼓樂彼此對照(14)。
上面提到的這些變化中的習俗,按照今天的觀念來説,對死者的娛樂性紀念(理性地看待生命現象)、男女平權(對於性別的平等觀念)、宗教信仰的多元(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和經商不再是賤業(重商觀念)等等現象,或者被認為是社會觀念“進步”的表徵,或者被解釋為“現代性”的自發產生,但是,在朝鮮記錄者的心目中,卻是一個曾經輝煌的中華文明的衰落。
不過,無論如何看,這些朝鮮文人的記錄,都呈現了十七世紀以後,由於政權嬗變引發的中國傳統轉向的內在潛流。當然,有些不是“見聞”而是“記憶”。這是因為朝鮮官員和文化人也常常把對於傳統中華尤其是大明王朝的嚮往和羨慕,轉化為“歷史記憶”,通過與清帝國的對比,變成對於過去“華”的讚美和對於現實“夷”的鄙夷,這使得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分裂的“中國”。其實,過去的中華帝國尤其是大明帝國,也未必是理想的天堂,像早先的洪翼漢(1586—1637)在天啓四年(1624)出使
明帝國,就曾經看到過明帝國魏忠賢和客氏弄權,天子昏憒而忠良被逐,朝政上下一團糟(15);而第二年的《承政院日記》(仁祖三年,1625)也記載明朝使團在朝鮮的無盡索賄,從明朝大臣對滿洲崛起的疏忽輕慢,以及朝鮮君臣對明朝大臣楊鎬的處境探尋中,我們可以瞭解後來明王朝迅速敗亡的一些端倪(16)。

到了崇禎九年(1636)出使北京的金堉(1580—1658),也同樣一次次地被看守朝陽門的宦者、守東長安門的火者敲詐,讓他覺得“朝廷大官只是愛錢,天朝之事亦可憂也”,有着很不愉快的經驗(17)。但是,一旦時光流逝,大明灰飛煙滅,當昔日仇敵清帝國成為巨大陰影,朝鮮使者卻不得不面對的時候,當年江華島被迫簽訂城下之盟的恥辱烙印,和對於已成往事的大明帝國的美好追憶,便使他們產生
了一些情感上的偏執。
所以,在朝鮮文獻裏面尤其是朝鮮文集裏面,我們看到那些比中國的程朱學者更加捍衞程朱的朝鮮學者,在不斷表達他們對中華文化的惋惜和對自身文化的自豪,其實,説到底這是在不斷地藉助消失的明帝國,貶斥這個現實的清帝國。這種愛憎分明的記述,當然説的,未必是真實的歷史,但是在他們心目中,卻是歷史的真實。在韓國曆代文集中,有很多詩歌、序跋、遊記和書信等等,在裏面都可以看到對於漢唐宋明中國不無誇張的想象回憶,也看到他們對大清帝國多少有些固執偏見和無端蔑視。
我反覆用“想象”這樣的詞語。這是因為我在這些文獻中也看到一些一廂情願的想象,比如,德川時期日本人對漂流船和貿易船的中國商人和船員的訊問交談中,他們曾經想象清朝皇帝的祖上出身於日本,應當是日本源氏後人,這顯然是把日本的傳説當成了真實的歷史,並且通過這種傳説來貶低清代中國(18),而我在《燕行錄》和當時人的文集中,更常常看到一些懷有對大清帝國強烈鄙夷的朝鮮文化人,對於他們聽到的和看到的各種現象,在做滿懷批判的聯想和帶有偏見的想象。
如果讀者耐心讀下去,那麼,就像我在本書中講的那些故事一樣,比如他們固執地相信正月初一清晨清朝皇帝祭堂子,不是傳統的祭天,而是祭祀明代鄧將軍,以此乞求前朝漢族將軍鬼魂的寬恕;又比如他們懷着鄙夷的態度,對薊州城外祭祀楊貴妃和安祿山的現象,作出種種奇怪議論,認為這是大清滿人帶來的蠻夷之俗;再比如,他們居然會把一個原本是降清的吳三桂部下的遺孀季文蘭,硬是想象成明清易代時的明朝江南秀才之妻,被野蠻的異族擄走的悽慘故事,他還寫了好多詩歌來詠歎,以表達對於“蠻夷入主中原”的批判(19),這些就不是歷史而是想象,只是在這些想象背後,又攜帶了太多的歷史,隱含了太多的情感。
二 異域之眼:朝鮮、日本史料的價值
當然,最值得中國學者注意的,還是有關歷史的豐富史料。過去,在樸趾源《熱河日記》中記載的關於
清代中國思想文化世界的一些資料,就常常被人們引用(20),比如其中的《太學留館錄》,它記載
的樸氏與中國讀書人王鵠汀、郝志亭的對話,就戳穿了大清帝國倫理風景的底線。表面上,當時的主流社會似乎都遵行《朱子家禮》,但是,王氏卻説並不盡然;在公開場合人們都説“失節事大”,可是,私下裏王氏卻在議論這種陋習的不合理;官方政治意識形態仍然堅持説“百行孝為先”,可是,當樸氏諷刺所謂孝道“斷指嘗糞,盡是疏節,冰筍凍魚,乃為笨伯”的時候,王鵠汀居然也同意這個似乎很叛逆的説法;而郝志亭甚至對維護政權秩序的“忠”也提出了疑問,説“陸秀夫之負帝赴海,張世傑之瓣香覆舟,方孝孺之甘湛十族,鐵鉉之翻油爛,人不如是不足以快,後世之為忠臣烈士,其亦矣”(21),這幾乎是對傳統道德底線的全面質疑。
生活在大清王朝的中國文化人筆下,這類記載並不多見,但在朝鮮士大夫的記載中,這類資料卻頻頻呈現。同樣,在各種《燕行錄》中,有很多滿漢之間種種矛盾、怨懟、傾軋的記錄,過去,通常學者會認為,清帝國的滿漢衝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於清政權的強力壓抑、加上歷史漸漸遠去後,明清易代的記憶消失,以及政治、軍事和經濟的繁榮,清帝國已經成為一個多民族共同體,或者清皇帝已經成為多民族大帝國的統一領袖,“人間歲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22),似乎這種族羣之間的恩怨已經淡化。
但是,我們在朝鮮人的記錄中,卻看到處處時時都呈現漢族激烈的民族情緒,究竟這是真實的歷史,還是朝鮮人的特意渲染?因為那些恥於滿族蠻夷衣冠的話,不止是“思漢之心”,幾乎是對滿族統治的公然反抗。這些當時人所説近乎叛逆的話,在中國文獻記載並不多,但在朝鮮文獻中留存卻不少,從朝鮮漢文文獻中,也許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被歷史“減去”或被“淡化”的內容。
這是來自異域的觀察。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完全可以從日本的《華夷變態》中日本人對於來到日本的中國商人和船員反覆詢問的那一兩百個問題,諸如明清差異、滿漢關係、重臣為誰、有無災荒、風俗變化等等,看到日本官方對中國的關注,究竟聚焦在什麼地方(23);也可以從《唐通事會所日錄》的記載中,看到中國船員和商人的觀念舉止行為,與日本當地人的風俗差異和衝突,這呈現了日本與中國文化和習俗上的不同(24);還可以從當時教日本通事學漢語的《官話問答便語》中,看到對於一般日本人來説,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有關中國的知識,也可以看到他們如何理解中國(25)。
很多歷史資料是相當珍貴的,歷史研究是後之視前,由於總是有“後見之明”,所以一方面常常有忽略的“死角”,一方面常常有越俎代庖的“脈絡”,可是借用當時的、異域的資料,卻可以看到很多被遮蔽的和被淡化的東西。像清代文學史由於後設的文學價值判斷影響,對於道光年間的文壇,常常不會提及孫玉庭、汪廷珍的名字,可是,在總愛問誰是文壇領袖的朝鮮文人的記錄裏,我們卻知道這兩個“位至卿相,主當世之文柄”的人實在影響文學潮流很大,而當時文人所崇拜景仰,“皆為翰林之官,號為翹楚”的“廣西陳繼昌、湖北陳沆、四川王炳瀛、安徽凌泰封”,似乎在文學史上也同樣是被遺忘的角色(26)。
同樣,研究近代史的人,也可以在這裏找到有關晚清中國、日本、朝鮮以及西洋之間外交角逐的新資料,比如朝鮮的《燕行錄全集》收錄的鄭健朝《北楂談草》,在其中記錄同治十二年(1873)清國與朝鮮官員的對話、筆談中,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同樣面對“東之倭,北之俄”,並在西洋和東洋夾縫中,兩國士大夫的很多心情和委屈(27);像金允植《天津談草》記載的光緒七年(1881)與李鴻章、許其光、周玉山、劉薌林、馬建忠、徐建寅、羅豐祿的多次談話、李鴻章致信給朝鮮大臣勸其“聯美親中國二者為最要”以牽制日本、擬舉薦德國人穆麟德(Paul Gerog vonMollendorff,1847—1901)幫助朝鮮對付日本等等,都是很有現場感的史料(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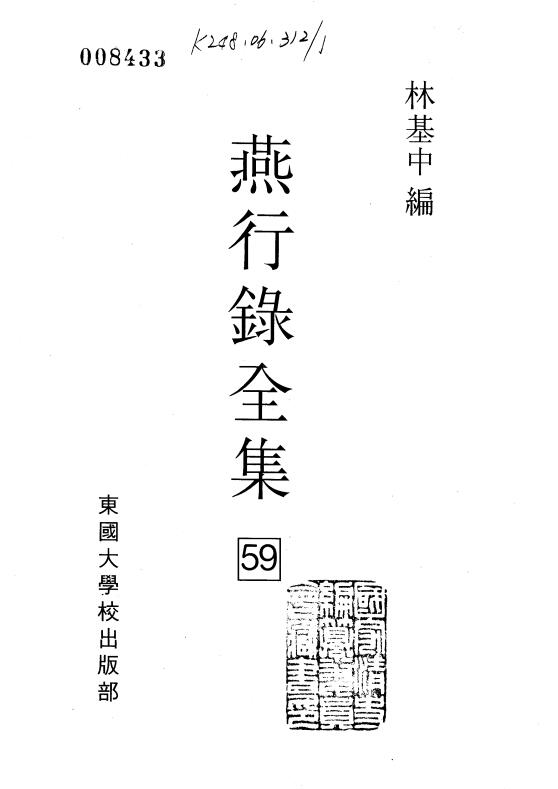
當然,在日本、朝鮮文獻中還可以看到很多本國人忽略,而異域人所關心的歷史細節,這些細節是本國文獻所不載的。這很正常,大凡到了外國,人們注意到的常常是與本國相異的東西,那些一眼看去覺得不同的事物、人物和現象,會自然地凸現在視野中,而生活在其中的本國人,卻常常會因為熟悉而視而不見,因此被淡忘和忽略。
以朝鮮燕行文獻為例,如果要研究清代北京戲曲演出、票價、座位、劇目和觀眾,要研究明清北京東嶽廟的香火狀況,要研究北京琉璃廠的書肆以及當時流行的圖書,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詳細的資料。特別有趣的,還有關於清代皇帝的相貌資料,通常,清朝治下的漢族中國人不會細細描述皇帝的“天顏”,即使記載下來,也因為避諱而多是“龍鳳之姿”一類冠冕堂皇的記述,但朝鮮人卻不然。康熙八年(1669),閔鼎重(1628—1692)在北京看到年輕的康熙,就説他“身長不過中人,兩眼浮胞,深睛,細小無彩,顴骨微露,頰瘠頤尖”(29);雍正七年(1729),金舜協(1693—1732)見到雍正,則説他“顏貌豐碩,而極其端雅,但聲音強亮異常”(30);接下去是乾隆,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李德懋説,他“面白皙,甚肥澤,無皺紋,鬚髯亦不甚白”(31),兩年後,樸趾源也説“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帶黃氣,鬚髯半白,貌若六十歲,藹然有春風和氣”(32),但又説他春秋已高,很是容易躁怒。而
對於道光皇帝的記載更有趣,道光三年(1823)的徐有素(1785—?)《燕行錄》記載,剛剛登基兩三年的皇帝:“貌甚傾,上豐下殺,顙廣準高,齒盡脱,兩眼多精彩,耳大身長,蓋其狀貌,古所謂天日之表,龍鳳之姿,恐不近似。猶有英邁氣象,此其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歟?”(33)
但五年後(1828)出使北京的一個官員卻記載,他“黃面,上廣下狹,短鬚無髯,臉長細眉,大口齒落,身長背僂”(34),這兩份互相不同的記載,倒是記載了同一個皇帝形象,這恐怕不是中國資料中會有的。只是對於咸豐,咸豐二年(1852)權時亨的記載倒還不錯,他在正月十五見到咸豐皇帝,説他“坐下一匹烏騮大宛馬,左手持洋畫竹藤鞭,右手執純黃革,頭戴紅紅的帽子,身穿貂皮長襖,毛在外,生得六尺餘身才,年可二十內外,面方白淨,微帶鐵色,臉上沒了一根髭鬚,貌瘦體剛,眉目英邁,其光射人,真有君天下之像”(35)。
對於研究思想史和學術史的人來説,特別有興趣的,是從這裏還可以看到清代學術與思想的風氣嬗變。舉一個例子,像柳得恭(1749—?)《燕台再遊錄》就記載嘉慶六年(1801)四月,柳氏赴北京購朱子書,曾與紀昀交談,他所求購王懋竑的《白田雜著》,北方沒有,紀昀因此説,“邇來風氣趨《爾雅》、《説文》一派,此等書(指《朱子語類》等)遂為坊間所無”(36)。
這顯然可以作為昭槤《嘯亭雜錄》卷十中,關於“(北京)遂將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坊間二十年沒有理學的書,可為“恐其無人市易”這一著名記載的佐證(37),説明一代學術風氣正在悄悄轉移。
三 跳出中國:為的是反觀中國
過去,也許由於曾經作為朝鮮的佔領者和殖民者的緣故,日本學界對於朝鮮文獻有較多的關注,不僅林泰輔(1854—1922)、白鳥庫吉(1865—1942)等東洋學的開創者對朝鮮有相當深入的研究(38),還出現了像今西龍(1875—1932)、藤冢鄰(1879—1948)等這樣的專家,他們對這些朝鮮漢文文獻有很多收集和研究。後來,日本仍然有很多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也有像天理出版的《朝鮮學報》這樣高水準的學術刊物,就連我們常用的樸趾源《熱河日記》,也有今村與志雄的詳細註釋。
但是,在中國只出版過《李朝實錄》等少量朝鮮漢文史料,像《同文匯考》、《承政院日記》、《備邊司謄錄》、《通文館志》等相當多的文獻,都很少被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學者關注。還好,現在我們比較容易看到韓國文獻了,因為這些文獻很多已經由韓國整理影印出版,對於研究者來説是相當方便了。不僅是過去已經出版過的《李朝實錄》,現在還有韓國景仁文化社影印的《韓國曆代文集叢刊》
三千冊,以及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的《韓國文集叢刊》三百五十冊(39),這些文集絕大多數是漢文書寫,大致相當於明清時代的史料(40);而韓國東國大學校林基中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分別編輯的《燕行錄全集》和《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一百零六冊,幾乎五萬頁的資料,基本上是明清兩代朝鮮人對於中國的觀察和記錄(41)。
當然,還有日本的史料,我以為,研究中國的人完全可以把視野放寬,有些未必直接涉及中國,或者不一定直接記載中國的資料,其實也有“中國”在。因為無論在漫長的歷史中,還是在現實的空間裏,對於朝鮮和日本來説,“中國”都是一個巨大的“來源”或“他者”,使得那個時代的日本和朝鮮人在互相交往禮聘的時候,在彼此贈酬唱和的時候,在互相觀察和評價的時候,在引經據典的時候,都會出現“中國”。
因此,像成大中編《海行總載》就收錄了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多種日記和詩文,這裏記錄了大量日本和朝鮮人對於中國的觀察、想象和評價(42)。舉一個小小的例子,被誤收在《燕行錄全集》裏的洪景海《隨槎日錄》(43),就是一份很有趣的文獻,它是乾隆十二年也就是日本延享四年(1747)朝鮮通信使隨員洪景海的日記,記載的是他在日本的見聞,其中我們從他和日本各界文化人的互相唱酬、筆談中,就可以看出很多當時日、朝人對中國的想象和評價,因為在使用漢文互相溝通、漢詩互相唱酬、漢典加以裝飾的時候,無論是評價、讚譽還是質疑的標準,竟然常常來自它是否符合傳統中華的風格與樣式(44)。
而同樣重要的是,日本江户時代在長崎和其他地方接待清帝國貿易船隻的各種官私文書,以及所謂唐通事的資料,也已經被大量整理和出版,除了像前面提到的著名的《華夷變態》以及《唐通事會所日錄》、《古今華夷通商考》之外,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出版的《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江户時代漂着唐船資料集》(45),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的有關資料,以及大量有待發掘的史料,也都呈現着已經分道揚鑣的日本對中國的細心瞭解和冷眼旁觀(46)。
俗話説,“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也許,這些資料能夠讓我們“跳出中國,又反觀中國”,瞭解中國的真正特性。
通過對方,看到了彼此細微卻深刻的不同。透過原本混沌的“同”和看似細微的“異”,也許更能使
彼此看清各自文化,也體會到這些細微的文化差異,是如何經由歷史和時間的放大,漸漸演變成現在東亞諸國深刻分離而難以彌合的文化鴻溝。
————————————————————
(1) 《胡適致傅斯年》(1938年9月2日),王汎森輯《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載《大陸雜
志》第九十三卷第三期,11頁,1996年9月。
(2) 金毓黻編《遼海叢書》(大連:右文閣,1934—1936)第一集、第八集。
(3) 吳晗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自1354年起,至1894年,共十二冊。
(4) 近年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在陸續整理和出版朝鮮漢文史料中的中國資料,如有杜宏剛等編《朝鮮文集中的明代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影印十三冊。又如趙興元等編《〈同
文匯考〉中朝史料》(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也已經出版三集。參看本書【附錄3】的
介紹。
(5) 關於這一問題,請參看葛兆光《想象的和實際報》第30期,2003年12月),收入葛兆光《宅茲中
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二編第五章,169—195頁。
(6) 關於這一問題,請參看葛兆光《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原載《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
總第90期。收入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1—38
頁。
(7) 我參與整理出版的,如《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25冊和《韓國所藏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30冊。又,這裏特別感謝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劉國忠教授,他在2003年赴韓國訪問期間,為我收集了很多與《燕行錄》有關的資料。
(8) 《同文匯考》(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鄭昌順等編。據吳晗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十一《李朝實錄·正祖實錄》卷二(正祖十二年、乾隆五十三年)記載,當年(1748)九月編成《同文匯考》,“舊法,事大交鄰文字,承受分屬皆由承文院,其貳本三年一印,藏於掌故,著在
經國大典……上之八年,命承文院提調李崇佑等裒輯各年詔諮表奏及使臣別單、譯官手本,匯為一書。原編二十五目,別編十四目,補編五目,附編十四目”(4798頁)。但是,後來陸續又有多次補充,一共成為十編,記事下訖1881年;《承政院日記》是朝鮮承政院每日事務的記錄,原有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所編本,校點本由韓國古典翻譯院標點,正在陸續出版中;《備邊司謄錄》(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2)為十六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之間,李朝朝鮮備邊司的官方日誌彙編,為記錄當時朝鮮國內國際各種事務的材料。
(9) 朝鮮金錫胄(1634—1684,曾擔任燕行使團的官員)曾經在《以馬島來問中國事情事移禮部諮》説
到前一年夏秋之間,東萊倭館的翻譯曾經得到日本人從商人那裏傳抄的《吳三桂檄文》,但是金錫胄似乎很不相信,説“決是卉服伎倆,不類漢人文字,既已譭棄勿留,亦不敢煩聞大朝”,這一年,對馬藩主平義真又派人送來檄文,他仍然覺得這是“賣弄哄人”的東西。這一段記載相當有趣,可以考見中國禁止不傳的《吳三桂檄文》在東亞之間的流傳情況,見《息庵先生遺稿》卷十九(《韓國曆代文集叢書》第605冊,首爾:景仁文化社影印本,1999),323—324頁;其實,清代初期這樣的文獻在中國被禁絕,但在日本、朝鮮保留不少,比如自稱明遺民的何倩甫的《大明論》、林上珍的《清國有國論》,均撰於康熙十四年(1675),見《華夷變態》(東京:東方書店,《東洋文庫叢刊》第十五種上,1975)上冊,111—114頁。
(10) 參看本書第二章《時代背景》。
(11) 李 《燕途紀行》下,《松溪集》卷七,《燕行錄選集》(首爾:成均館大學校,1962)下冊240頁。以下所引《燕行錄選集》均同,不一一註明。
(12) 韓泰東《兩世燕行錄》,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1981)第二十九卷,252頁。以下所引《燕行錄全集》均同,不一一註明。
(13) 金正中《燕行錄》,《燕行錄選集》上冊,574頁。
(14) 蕭奭《永憲錄》卷二下雍正元年冬十一月《祁爾薩條奏喜喪儀制以杜奢侈》,福格《聽雨叢談》卷六、卷七,轉引自余英時《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載《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240—242頁。
(15) 參看洪翼漢《花浦朝天航海錄》,《燕行錄選集》上冊,126—129頁。
(16) 《承政院日記》(韓國古典翻譯院,2009)仁祖三年(明天啓五年,1625)六月十一日,283頁。
(17) 金堉(1580—1658)《潛谷朝天日記》,《燕行錄選集》上冊,記載使者到東長安門等待開
門,“火者在門內索賄不納,給白貼扇五柄、油扇六柄、刀子十柄,然後許入”(215頁)。又載“以桃花紙五十七張、雪花紙七卷,應提督之求,還給其錢,提督不受,錢不滿其意,恚恨而去”(218頁);又記載朝廷大官只是愛錢(220頁);並且記載中國雖然也有監督官員,但是“有科道兩衙門,但其人自己亦貪,何暇糾他人”(221頁)。
(18) 參看葛兆光《西方與東方,或者是東方與東方—清代中葉朝鮮與日本對中國的觀感》,載《九州
學林》(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第三卷第2期。收入《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
歷史論述》第二編第四章,151—168頁。
(19) 分別參見以下第八章《堂子或祀鄧將軍》、第六章《明燭無端為誰燒—朝鮮朝貢使眼中的薊州
安、楊廟》、第五章《想象異域悲情》等等。(20) 樸趾源《熱河日記》(朱瑞平標點本,上海:上
海書店出版社,1997)以及日本今村與志雄的日文譯註(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本,1978)。
我在這裏用的是上海書店出版社標點本的頁碼。
(21) 樸趾源《熱河日記》卷二《太學留館錄》,131頁。
(22) 李頤命《次副使見新曆有感韻》,載其《燕行詩》中,《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四卷,92頁。
(23) 比如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變態》(東京:東方書店,1975)卷十二(康熙二十六年,
1687),654—719頁,記錄了康熙皇帝巡遊蘇杭、湯斌如何教導東宮太子、山東浙江的洪水、
滿漢風俗差異、《聖諭》宣講規則、佛教信仰情況等等,便可以看到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注意焦
點。
(24) 例如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唐通事會所日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5)第一冊寬文七
年丁未正月五日,日本官員頒佈的案文便申斥唐船上的中國人,警告他們不得恣意放肆嫖賭喧譁
與鬥毆,87頁。
(25) 參看赤木文庫所藏《官話問答便語》,這裏用的是京都大學木津祐子教授《赤木文庫所藏出〈官
話問答便語〉校》,載《沖繩文化研究》(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2004)三十一號,543—
657頁。
(26) 陳繼昌(1791—1846)是嘉慶二十五年(1820)狀元;陳沆(1785—1826)是嘉慶二十四年
(1819)狀元;凌泰封(1783—1856)是嘉慶二十二年(1817)一甲第二名及第;王炳瀛,是嘉
慶十九年(1814)進士。
(27) 鄭健朝《北楂談草》,《燕行錄全集》第七十八卷,321頁以下。
(28) 金允植《天津談草》,《燕行錄全集》第九十三卷,208、370頁。
(29) 閔鼎重《老峯燕行記》,《燕行錄全集》第二十二卷,347頁。
(30) 金舜協《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八卷,409頁。
(31) 李德懋《入燕記》卷下,《燕行錄全集》第五十七卷,297頁。
(32) 樸趾源《熱河日記》卷二《太學留館錄》,138頁。
(33) 徐有素《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八十一冊,104頁。
(34) 佚名《赴燕日記》,《燕行錄選集》下冊,847頁。
(35) 權時亨《石湍燕記》,《燕行錄全集》第九十一冊,204頁。
(36) 他説,“此行為購朱子書,書肆中既未見善本,紀公曾求諸江南,雲亦無所得。紀公所云邇來風氣
趨《爾雅》、《説文》一派者,似指時流,而其實漢學宋學考古家講學家等標目,未必非自曉嵐倡之也,見《簡明書目》論斷可知也。多見南方諸子所究心者六書,所尊慕者鄭康成,相譽必曰通儒,曰通人,程朱之學不講,似已久矣。中國學術之如此,良可嘆也”。此外,還有一些很有趣的資料,像柳氏與紀昀曾談到李鼎元、李雨村、翁覃溪、孫星衍等,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資料,比如談到孫星衍之子孫衡“聲名藉甚”,為京師四凶,被紀氏捕回原籍。見《燕行錄全集》第六十卷,265—270頁。
(37) 《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十《書賈語》,317—318頁。
(38) 自林泰輔的《朝鮮史》(1892,有陳清泉的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朝鮮近代史》
(1901)之後,還有坪井九馬三、白鳥庫吉、池內宏、今西龍、原田淑人等的大量研究。其中,白鳥氏的朝鮮史研究如《檀君考》等,有相當的影響。參看和田清《我が國に於ける滿蒙史研究の發達》,在《東亞史論藪》(東京:生活社,1942),241—268頁。
(39) 這部分文集,有相當好的提要介紹,見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便覽》(首爾:韓國古
典翻譯院,2010年12月)。
(40) 其中,當然也有少量較早期的資料,如崔致遠(857—?)《桂苑筆耕集》、李奎報(1168—
1241)《東國李相國集》等等,但是,絕大多數文集作者的時代,相當於中國的明清。
(41) 在《燕行錄全集》出版之後,林基中教授又出版了《燕行錄全集續編》(首爾:尚書院,2008),共五十冊。
(42) 參看成大中編《海行總載》(朝鮮古書刊行會)四輯,此書收錄了1420年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
錄》到1764年趙曦的《海槎日記》二十二種;近來,又出版了《海行總載》的續編,續編為我們增加了幾乎與原來數量相等的有關朝鮮通信使與日本往來的新文獻材料。又,日本方面出版了相當完備的辛基秀、仲尾宏編《大系朝鮮通信使》(東京:明石書店,2003),共八冊,但是,它的時代限於日本德川時代,德川時代之前與之後的朝鮮使行記錄則不在其內。在各種朝鮮通信使文獻中,整理最好的一種是姜在彥譯註、申維翰撰《海遊錄—朝鮮通信使の日本紀行》(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本,1975)。
(43) 洪景海《隨槎日錄》(乾隆十二年、日本延享四年,1747),見《燕行錄全集》第五十九卷。其
中提到的日本林信篤與新井白石“分黨各立,戈戟相向”、提到日本朱子學如伊藤仁齋、淺見絅齋、
貝原篤信的情況,提到林恕三代與朝鮮通信使的交往等等,均是很可貴的資料。
(44) 例如,申維翰《海遊錄》(平凡社“東洋文庫”姜在彥譯註本,63頁,1975)記載,1719年(日本享保四年)朝鮮人申維翰(1681—?)與對馬藩的記室橘雨森(1668—1755)、松浦儀(1676—
1728)唱酬筆談時,曾有對話:“餘問曰:白石公無恙乎?(松浦)儀……問餘曰:公以為其詩如何?餘答曰:婉朗有中華人風調。儀舉手加額謝曰:昔木下先生門下,與白石為同門友,幸蒙君子嘉賞,何幸如之。”
(45) 《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第一至第五冊中,有《中華之儀ニ付申上候覺》、《和漢寄文》、《朱氏三兄弟集》、《荻生北溪集》、《蘭園雞肋集》等等,關西大學出版部出版,1986—1996。而《江户時代漂着唐船資料集》則已經出到第七種,即松浦章編《文政十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蔣元利資料》(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6)。感謝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松浦章教授饋贈此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