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在鎖國與開國之間的東亞三國_風聞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教授2018-10-31 15:45
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九世紀的開頭,日本國、李朝朝鮮和大清國對西洋傳教士終於先後關閉了大門,既包括外在的國土之門,也包括內在的思想之門。
面對那個遙遠的、看不清的西洋,東亞三國對來自那裏的懷有某種意圖的天主教傳教活動,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拒斥。此後一百年間,經歷了鴉片戰爭的大清國、經歷了黑船事件的日本國,和經歷了江華島事件的李朝朝鮮,似乎才陸續重新“從鎖國到開國”。本文並不是在追溯這一歷史,只是想通過十九世紀初東亞三國面對西洋天主教時的不同策略中,看看這同屬於所謂“東亞”的三國,在政治、社會與宗教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也許不僅會導致面對西洋宗教時策略的差異,多多少少也會影響到此後三國面對西洋“堅船利炮”時態度的不同,甚至從中可以體察到,何以東亞三國會有各自不同的“近代道路”。
為什麼東亞三國應對西洋宗教的態度與策略有差異?導致這些差異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需要詳盡的歷史研究,這裏不能細説,但是,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卻想從這一歷史現象來討論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謂“衝擊—反應”模式。
眾所周知,自從1954年鄧嗣禹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中提出這一近代中國歷史的解釋模式,而1965年費正清、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克雷格(Albert M. Craig)的《東亞文明史》及次年克萊德(Paul H. Clyde)和比爾斯(Burton F.Beers)的《遠東:西方衝擊與東方回應之歷史(1830—1965)》把這一模式的運用從中國拓展到整個東亞歷史敍述以來,這種西方主動的“衝擊”與東方被動的“回應”的解釋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幾乎成為一種“典範”或者“定勢”。

朝鮮李朝所繪製的《天下圖》
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在他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中曾經尖鋭批評這一模式,試圖“在中國內部發現歷史”,也就是在中國或東亞文明的內部,尋找現代起源的內在因素和社會變遷的自我資源。這當然是在推動一種典範或模式的轉移,也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但是,儘管歷史學的研究並不等於酒廠釀酒越陳越好,但是歷史學的理論也絕非時裝,總是越新越好,現在看來,舊的“衝擊—反應”模式雖然簡單卻也簡明,它仍然可以容納中國和東亞相當多的史料,可以解釋東亞近代相當普遍的歷史現象。
問題是,我們如何對這個看上去有些簡單的模式進行修正和補充?本文所討論的十九世紀初葉面對西洋宗教(衝擊)時的日本、中國和朝鮮的不同策略(反應),也許可以説明,在面對同樣“衝擊”時,由於各國政治、社會、宗教之差異,“反應”仍有相當的不同,這説明“亞洲”或者“東亞”並不是一個,不僅政治、社會、宗教和環境不同,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和態度也不同,因而近代化路途與進程也不同。是否應當重視,在回應外來文明時,“各有各的反應”?本文通過敍述十九世紀初在朝鮮、日本和中國面對西洋宗教的不同策略和態度,就是試圖討論這一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我們認為東亞諸國確實“各有各的反應”,那麼,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是,影響朝鮮、日本和中國面對西洋宗教(以及後來的近代西洋文明)的不同策略和態度的背後,究竟是什麼因素在起作用?這也是一個極大的話題,但是,如果允許我簡單概括,應當説其中既有政治、社會,也有宗教信仰各方面的差異。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日本、朝鮮和中國各自國家政治結構的不同。在西洋傳教士到來的十六世紀中後期,由於日本並不中國那樣早就有一個強有力的皇權,而且整個社會一直處於大體同一政治意識形態和儒家思想學説籠罩之下。
在日本,不僅各區域的實際控制者出於各種原因,可以成為外來宗教的庇護者,而且各個階層的人士出於各種興趣,也可以成為新信仰的支持者,正因為如此,日本才會出現熱情的“受容”。然而,由於天主教傳入日本時,正好是日本民族國家漸漸從紛亂到統一,意識形態由鬆散到強化的時代,織田信長之後,在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時代,日本國家的統一訴求愈趨強烈,所以,又會因為對於異己觀念和信仰的警惕與戒備,導致很嚴酷的“排斥”。
其次,相對中國而言,在社會結構上,日本從來就沒有形成通過科舉制度和文化知識掌握權力的知識人階層,也沒有形成以“儒學的理性原則”為制度和思想基礎的國家意識形態,儘管接受中國的律令制度,卻總是以“宗教”與“武力”為中心,建立國家意識形態,因此,會出現對西洋宗教“受容”與“排斥”的兩極搖擺,終於在德川時代初期日本逐漸強化國家意識和本土觀念的時候,鐘擺從“受容”轉向了“排斥”。
在本文討論的十八、十九世紀之際,日本在東洋(中國)和西洋(歐洲)之間,逐漸培植自己“日本型華夷思想”,並且通過重建神道和推崇天皇建構民族國家,這時,對西洋宗教就仍然持有十分的警惕,禁絕措施也格外嚴厲。
反觀中國,由於一直處於“天朝帝國”的自我想象之中,過度的自信和自大,以及知識階層對儒家文明的過度自信與自我調整,使得朝廷與士人兩方面,都對西洋宗教既沒有那麼警惕,也沒有那麼熱情,即使是在本文論及的十九世紀初,嘉慶帝嚴厲禁止天主教之時,其實,朝廷也並沒有像日本和朝鮮那樣緊張與焦慮,當然,知識人也沒有那麼認真地看待來自異域的這些新信仰和新知識。
而在兩班士人壟斷着知識與思想的朝鮮,由於傳統相對穩定,思想也相對保守,他們始終延續着明代以來以儒學特別是朱子學為中心的政治觀念和哲理信仰,之所以如此回應西洋宗教,主要是由於外來宗教與國內士人的結合,並且成為黨派角逐和宮廷政治的政治因素,這才引起了軒然大波。
再次,當然也要注意各國宗教信仰的狀況。
對於天主教的警惕和禁絕,在大清國主要由皇權即政治權力主導,它的主要動因是來自對皇權或者國家主權的維護,而本來應當直接發生衝突的宗教即佛教、道教,在這一對異教的禁絕過程中,卻幾乎沒有任何作用。換句話説,這種與外來信仰的衝突,是政治的而不是宗教的。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大清國政治權力的強大和宗教信仰的微弱。然而,在李朝朝鮮對天主教的禁絕中,除了國家權力的主導與黨派力量的介入外,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起了一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使得對於天主教的批判多少帶有一些思想和信仰衝突的意味。
而在日本禁絕天主教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較多顯現着佛教、神道教的影子,在影響豐臣秀吉等人從歡迎到排斥天主教的轉變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在當局頒佈的禁令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維護佛教、神道的話語,如“伴天連追放令”中第一、二條中就有“日本是神國,從天主教國傳授邪法,其事甚怪異”、“天主教徒破棄神社佛閣,前代未聞”等等涉及宗教信仰的意思。而在羣臣議論中,也常常可以看見“昔日我國三教盛行,信仰之事已充分,至邪正不明之新宗門始,令日本無從可辨邪正”。正如我們前面所説的,德川時代的天皇、幕府以及神佛均對外來宗教有恐懼和焦慮,因此,導致“禁教”的原因既有國家的意志,也有宗教的排斥,這才使得日本對於天主教的禁絕相對比較徹底。
**第三個問題是,是否應當注意重新審視和研究“東海”即中國、日本和朝鮮這一區域的歷史,這種重新審視和研究,會有什麼樣的典範意義?**近年來,張廣達先生在新出版的著作序文中,曾提起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一譯布勞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對地中海的研究,1949年出版的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討論的是1551年至1589年時期的地中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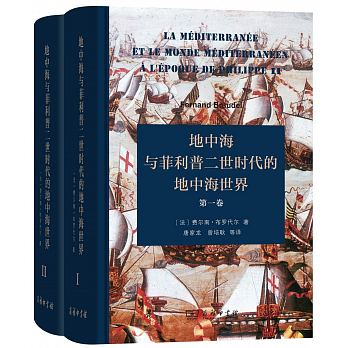
地中海本來就是一個種族、宗教、政治異常複雜的地域,埃及人、亞速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的交織,猶太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的衝突,很長的歷史時間裏海路作為交通渠道,都使得環地中海形成了有關聯的“歷史世界”或者“文化空間”,在布羅代爾研究的那段時間裏,包括土耳其和西班牙兩大帝國以及其他國家,就是在這個舞台上互相交流與互相影響。張廣達先生覺得,他所研究的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亞一帶,也是當時世界上一個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點,僅以宗教而言,漢族中國的儒家與道教、南亞印度的佛教、西亞甚至歐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這裏留下痕跡,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地中海”。
不過,我始終覺得,如果站在中國的立場和角度觀看交錯的文化史,“西域”這個區域即元朝以前中國的左翼,確實是一個宗教、語言、歷史交匯的“地中海”,漢族文明在那裏與其他文明激盪,形成一個極其錯綜的文化空間。然而,如果在元朝之後,那麼“東海”即中國的右翼,也許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地中海”,在這個交錯的文化空間中,不僅和本來就存在文化差異,逐漸“由異而同”的地中海和西域不同,朝鮮、日本與中國逐漸“由同而異”,從共享漢唐傳統轉向彼此文化分離,而且更隨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又加入了西方世界的因素,使得這個本來就和地中海、西域不同的文化區域,變得更加風雲莫測。或許,這個文化區域交錯的歷史圖像,不僅可以讓我們超越國境發現更多的故事,而且它進入“近代”的差異性和特殊性,也可以給全球文明史增添一個新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