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困局:當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生死的時候,權力該交給誰?_風聞
晴晏-认识人类-探寻事物的边界及其可能2018-11-06 10:22
前言:近來台灣名嘴傅達仁去荷蘭赴死的新聞又將安樂死話題提上了風口浪尖。對於中國人而言,死亡本就是一個禁忌話題,何況安樂死還牽涉到倫理問題,大家自是眾説紛紜。而在安樂死早已合法的荷蘭,這仍舊是一個牽動民眾情緒的議題。我日前翻譯過一篇荷蘭作家Henk Blanken的文章,詳細記述了他數十年來在等待死亡臨近過程中對於安樂死的思考,希望能給予你啓發。

我已是個半死之人了。身體的一半會抽搐,小便時會流口水,在雪地裏見到細小的樺樹殘枝就會流淚。有時候我的左手會突然舉起,將握着的一杯水打翻在自己肩頭上,就像喜劇橋段那樣。2011年,我51歲,被診斷出帕金森症。醫生説我或許將在10年或15年後需要護理,但也有可能會和這個病一起變老。“死不了人的,”他説。
但那樣的結局可不體面啊,我想。
典型的帕金森病人將在8-10年間喪失自理能力,但這樣的典型病人並不存在,每個人的情況都有所不同。在確診六年後,我還在網球場上奔跑。然後一切都開始不對勁了。幾個月內我就成了一個搖搖晃晃的病人,連走路也時常會絆倒,我不得不依靠助行架來慢慢挪動自己。
我的神經科醫生説做腦部手術的時候到了,他們准許我前往荷蘭北部的一家診所去“觀察觀察”。我花了好幾天時間才適應了那裏的病人們。他們一共有七位:三位男性,四位女性。我觀察他們不自覺的震顫,以及他們如何行走:非常小心地一步一步地移動着,拼命地想要把助行架的輪子轉到正確的方向上來。他們吃東西的時候很安靜。一個從村裏來的壞脾氣農民坐在破舊的活動躺椅上,無聲無息地尿了出來。
晚餐時,另一個七十來歲的男人坐在我正對面,壯碩的腦袋上兩隻無神凝視的雙眼。他像一隻受驚的鳥兒一樣蜷縮在座位上吃着他的酸菜絲,挨着盤子的嘴緊閉着,流着口水。食物不時地從他的叉子或紅腫破裂的嘴唇上滑落。當盤子空了一半的時候,一個護士過來仁慈地又餵了他幾口。他的下巴垂到盤子上,灰色的鬍鬚泡在了已經涼掉的酸菜絲裏。
天啊。我以為我已經都想好了。我知道帕金森病人有更大的可能會痴呆。我接受了有一天我的妻子將不得不幫我切碎食物,繫好鞋帶。我甚至都在網上看好了價格合理的電動代步車。我已經幾乎快要可以接受這一切了,但經過這次診所之行,神經科醫生那句“死不了人的”意義完全變了。當所有事情都不對了(而且這就是我註定的前景),而我竟然還死不了。
痴呆症所帶來的若隱若現的遺忘和帕金森症導致的殘酷的身體失能之間,哪一種更糟糕?是困在一個糊里糊塗的大腦裏好,還是在一具不受控制的軀殼裏尚存一個清醒的意識比較好?
這幾年來,我一直在和我的朋友約普討論這樣的問題。我們不定期見見面,討論下死亡,就跟討論一個長期的天氣預報一樣。約普有阿爾茨海默症,已經開始忘記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識。但他還十分清楚的是,他不想像他的父親一樣在護理院裏死去。他説:“我不想在追逐護士中離開。”
即使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替換臀部、膝蓋或其他器官,即使人類的平均預期壽命一直在增加,我們的大腦仍舊在衰老。在否認存在是有限的這一點上,人類有着極強的驅動力,而神經退行性疾病則是我們為之付出的代價。我們的大腦遲早會開始搖搖欲墜,神經元會損壞,我們將在護理院裏四處尋找護士,尋找影子,尋找我們自己。
我太瞭解約普最深的恐懼了。我的老丈人尼科,在他91歲的一個深夜裏,將他妻子當做入侵者,用菜刀攻擊了她。這次事件後不久,他被送進了一家老人院的監視病房。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個畫面:當玻璃門緩緩關閉,那個被我們留在身後的男人,困惑又無助。他盯着我們的眼睛裏,透着不可阻擋的孤獨。幾周過後,當我們再去探訪尼科時,他正在埋怨他的妻子不管他。他嘟囔着説,她從來都不來看我。儘管一小時前,她剛哭着喂他吃了幾片面包。
回家的路上,我意識到我寧願死也不要變成這樣。我第一次開始嚴肅地考慮自願結束生命的可能性。畢竟,荷蘭可有着全世界最規範的安樂死制度呢。
歷史學家詹姆斯·肯尼迪説,直到上世紀50年代,荷蘭還是個比其他歐洲國家更保守、更具宗教性、也沒那麼繁榮的國家。然後一切都變了,這個可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先驅者。我們成為了一個在倫理問題上起帶頭作用的開放自由社會。我們容忍毒品,允許墮胎,還向妓女收税。
我們曾經是虔誠的加爾文教徒,上世紀60年代起我們進入了一個墮落時代。教堂變成了商店和公寓。上世紀末,基督教政黨喪失了對權力的掌控,他們的教條不再能主宰生死。舉國上下討論了很久協助死亡在某些情況下是否可以合法化。2001年,荷蘭議會的投票將荷蘭變成了全世界第一個安樂死合法的國度,支持者的主要論據是自決權。“我的死亡是我自己的,”荷蘭人説。
安樂死法案於2002年4月開始生效,如今,它得到了百分之九十的荷蘭公民的支持。這項法案允許醫生在病人的請求下協助其結束生命,前提是病人有着“無法忍受和絕望的痛苦”,並且毫無緩解的可能。比如説,這意味着醫生可以預防一位肺癌病人因為嗆到自己的血而窒息身亡。
人們對於安樂死的討論並沒有因為法案的通過而停止。更多病種的病人想要申請加入,對這個法案也有了更加自由主義的解釋。而在每次放寬安樂死標準的裁決之後,就會有另一羣人為了更進一步的立法而運動。每一個新的請求都會給安樂死之辯再填上一把火。支持者將法案的範圍擴大視作道德進步,反對者則預言我們正在朝着一個德國納粹般的社會前進,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可以擺脱那些“無用”之人,比如那些高齡的或有着嚴重精神疾病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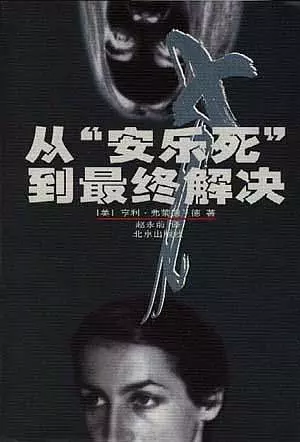
(1930年代納粹分子曾以安樂死為藉口,實行種族滅絕政策)
然而,安樂死之辯貌似進入到了一個尷尬的階段。一件非常“不荷蘭”的事情發生了。我們的舌頭好像被綁住了。荷蘭,這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相信每個人都有自願死亡的權利的國家,這個將無痛死亡輕描淡寫得就像個退款保證的國家,正在痴呆和死亡之間的困境中掙扎。
2012年9月的一個冷雨天,我第一次遇到約普,他已經七十幾歲了。一年後當他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的時候,他看起來還十分健康。但當他在二十分鐘裏第三次跟我講起他們老人院的唱詩班及其表演的故事時,我意識到,痴呆已經侵入了他的短期記憶。
儘管約普當時還沒有意識到他的病已經開始蠶食他的心智,但他知道那一天總會來的。他無法忘記自己在護理院裏看到的那些景象。他已經決定了如果有一天他不能再和自己心愛的妻子燕妮生活在一起的話,他寧可去死。
“你認為那一天會如何到來呢?”我問他。在他的想象中,那將會是很平常的一天,他的孩子和孫子們將會過來説再見,“然後醫生會進來給我打一針。”
這聽起來有點兒天真。這樣一個當約普不能再住在家裏時可以幫助他死亡的醫生,燕妮和約普已經找了有一段時間了。他們交流過的醫生都告訴他們,除非約普的痛苦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否則無法執行安樂死。但是當約普問到:“如果我的痴呆惡化到了無法做決定的時候你們會怎麼辦?”醫生們説,在那樣的情況下,他們無法執行安樂死。
我想約普從來都沒有完全理解過這第二十二條軍規。痴呆症為安樂死拋出了難題。在荷蘭法律下,如果病人在意識清楚時已經準備好了安樂死指示的話,醫生可以協助患有嚴重痴呆的病人死亡。約普已經準備過了,他以為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然而並沒有。
荷蘭每年有一萬名痴呆症患者死亡,其中大約一半都預留過安樂死指示。他們以為醫生將會“幫助”他們。畢竟,這是法律允許的,並且是他們明確的願望。百分之四十的荷蘭成年人對安樂死也擁有着同樣天真的自信,他們以為一張預留的指示就會給他們委派一位醫生。但事實上,醫生並沒有義務做任何事情。安樂死是合法的,但它並不是一項權利。
鑑於醫生對於這樣仁慈的殺人有着壟斷權,他們的倫理標準,而非法律,從根本上決定了像約普這樣的人能否死亡。預留指示只是影響醫生決定是否執行安樂死的眾多因素中的一個。即使法律説這是合法的,也幾乎沒有醫生願意為嚴重痴呆病人執行安樂死,因為這些病人已經喪失了做出一個“深思熟慮後的請求”的能力。

(醫生需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因為安樂死在荷蘭仍然是犯罪。但如果能夠證明滿足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報告已經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將不會受到起訴)
這就是第二十二條軍規。如果你的痴呆症尚處早期,你還清醒到能夠決定你是否想死,這時候去死似乎還“太早了”,你還有好些年可活呢。然而,等到痴呆症已經惡化到你真的想死的時候(如果你的思想還未受損的話),你已經不被允許去死了,因為你的心智狀況已經沒有資格做出這樣的決定。此時想死就“太遲了”。
這真是個悲哀的故事。死亡的權力在荷蘭已經被討論了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已經相信每個人都有想死就能死的權力。但到了最緊要的關頭,病人卻不是能夠決定自己死亡的人。除了醫生,沒有人能決定。對於上萬個以為他們可以逃脱最悲慘結局的痴呆症患者而言,荷蘭的安樂死法案就是徹頭徹尾的失敗。2017年,荷蘭共執行了6586例安樂死,絕大部分都是癌症病人。作為對比,自2012年以來,只有7位嚴重痴呆病人被執行了安樂死。幾乎沒有痴呆病人可以“按時”死亡:所謂按時,就是當他們真正想死的時候。
2008年,當他無法再寫作了的時候,曾數次名列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名單的比利時弗拉芒作家雨果•克勞斯選擇了安樂死。克勞斯深受阿爾茨海默症的痛苦,但心智上還有能力決定死亡。他的決定被很多人視為“勇敢”,但也招致強烈的批評,尤其是在比利時,這個緊隨荷蘭將安樂死合法化的鄰國,天主教仍然將安樂死視為嚴重的罪惡。
但克勞斯之死帶來了一些改變。社會學家雨果•範•德威登説,痴呆症患者因此獲得了史無前例的關注。法律本身並未改變,但有些醫生改變了他們對於“不可忍受的痛苦”的解釋,對未來痛苦的恐懼也被醫生們納入其中。其結果是,有些醫生現在更願意為痴呆早期的病人提供安樂死了。
但第二十二條軍規仍然存在。病人仍舊需要被視為心智清楚到足以確認他們是否想要死亡。如果他們苟延殘喘得太久,如果他們還想要看到下一個蘋果樹開花的春天,不知不覺間進入了更嚴重的痴呆階段,他們就會錯過一個早點離世的機會,只剩下一條直通往墳墓的漫長迂迴的道路。
從2002年起,大約有15萬患有痴呆症的荷蘭人死去,他們中成千上萬的人都曾預留過安樂死指示。但他們大部分都死得“太遲了”,因為“太早”選擇死亡這件事過於困難。在安樂死法案執行的早些年間,沒有一位嚴重痴呆病人以他們希望的有尊嚴的方式死去。近年來,大約有百分之一的痴呆病人以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死去,即,“過早”死亡。這也是約普的選擇,去年5月8日,他在醫生的協助下離開了。
2016年2月一個週一傍晚,一百五十萬荷蘭人在電視上共同觀看了哈妮•胡德里安的死亡。在這個記錄片裏,我們看到了即將進行安樂死的哈妮。在某個片刻,有人問她是否真的清楚即將發生什麼。
“你什麼意思?”她回答説。
她知道醫生為什麼會過來嗎?
“噢,我不知道,”她説。
“你想離開,對嗎?”她的丈夫赫裏特問道。
“我想,嗯,準備,好了,快點兒。”
“你確定嗎?”她的丈夫問。
“是的。”
透過屏幕看,哈妮•胡德里安是位高齡老人,稀疏的灰色短髮,略帶驚訝的面孔,薄嘴唇緊閉着。
“你對我不感到抱歉嗎?”當安樂死醫生過來坐到她對面的時候,她丈夫問道。
“我很抱歉,”哈妮説,“所以,快點吧。”
“時間到了,寶貝兒,” 赫裏特説,“現在勇敢點,你都勇敢了那麼長時間了。”
他用雙臂環抱住她,把頭靠在她肩膀上,彷彿在尋求她的安慰。哈妮讓醫生開始進行。她的丈夫就這樣抱着她。插在她左手上的滴管,通過一根透明的管子連接到醫生手上的注射器。醫生的另一隻手握着哈妮左手的兩根手指。然後醫生將藥物注射進了血管。哈妮,68歲,她臨死前説:“太可怕了。”

(哈妮被執行安樂死的畫面)
哈妮•胡德里安非常清楚將會發生什麼。她患有語義性痴呆,這種罕見病將緩慢又不可避免地奪走一個人的語言。數年前她就寫好了遺囑,聲明一旦她喪失了適當溝通的能力,她希望儘快死去。她的私人醫生考慮良久,認為自己無法確定她是否真的想死,於是將她推薦給了“生命終結診所”(End of Life Clinic),一家由NVVE(荷蘭死亡權)於2012年成立的機構,一個當人們想要尋求死亡又被自己的醫生拒絕時可以尋求幫助的地方。然而,這家診所也無法保證自己能夠授權死亡。它的醫生們面臨同樣的問題:這能夠在法律範圍內解決嗎?
哈妮的安樂死實際發生在公開播放一年前的2015年,當時協助她死亡的醫生是雷姆科•韋爾維爾。他仔細閲讀了哈妮的遺囑,諮詢了經手此事的項目經理,然後再跟哈妮本人談了七次。哈妮在一個清醒的時刻説:“已經沒有什麼留下了,裏面空空如也,我什麼也不能做了,我喪失了一切,我想離開了。” 韋爾維爾説:“她變成了自己最不想成為的樣子。”在她去世後,安樂死監督委員會判決説韋爾維爾將這起死亡處理得很“慎重”(with caution)。
但還是有很多觀眾被驚呆了。認知神經科學教授維克多•拉美在看完紀錄片後發推特説:“這是一起有一百五十萬目擊者的謀殺。”第二天,在荷蘭收視率最高的黃金時段節目De Wereld Draait Door上,他再次重複了這一未經判決的指控,直指坐在他正對面的韋爾維爾醫生,而韋爾維爾則試圖解釋説拉美教授只看到了他自己願意看的那一面。
公眾被震驚的一個原因是,他們確實地看到了一個醫生如何終結了一位女性的生命。對一個模糊的、理論性的安樂死法案發表意見是一回事,在起居室裏喝着咖啡看着真真切切的死亡又是另一種不同的體驗了。
這部紀錄片原本是想要展示“生命終結診所”的狀況,但它還揭露了另一個現實。我們談論自己的死亡時沒覺得有什麼,但當涉及到他人的死亡時,感覺就變了。儘管我們都不希望在護理院裏孤獨終老,變成自己曾經的影子,但我們卻都聲稱護理院裏的祖父“看起來還挺開心”,即使他只穿着條內褲在走廊裏晃來晃去。
同樣地,我們非常重視對於自己生命盡頭的掌控,但當心愛的人説她的生命已經“玩完”的時候,我們卻異常痛苦。我們會問:“這是不是太快了?”當我們是被留下的那個人,死亡變得更加難以接受。顯然,所愛之人的死亡遠比我們自身的死亡更加可怕。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所言:“死亡是活人的問題。”
去年的一個週日,我請我的妻子到花園裏來,在那顆大蘋果樹下,我們終於開始討論那件等待着我們的事情。“一起變老不應該是這個樣子,”我説,“我知道我將會變得半死不活。但你將不得不幫我係鞋帶,推輪椅,甚至還可能需要餵我吃酸菜絲……”
“別傻了,”我的妻子説,“我一直都知道這將會發生。但也可能反過來,是我需要你來幫我做這些事。”
我就是在那時遞給她我的信封的,裏面裝着我的安樂死指示。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件原本屬於哲學和政治領域的事情,當你不得不對那個將會被你留下來的人解釋的時候,它就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我一直都知道你對這件事的感受,”她説。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那就告訴我吧。”她説。
我説:“日常的不便我可以忍受,那些愚蠢的痛苦根本就無法逃避。我會慢慢變得生活不能自理,但我想我應該可以就那樣活着。我可能會習慣頭部的搖晃,夜晚的疼痛,老想往另一邊走的腿,以及不停敲打的手指……或許還會有個護士將不得不幫我擦澡……天啊……只要我還能閲讀,我甚至願意穿尿布。”
我可以看到她的想法:你在故作冷靜。難道你忘了護理院什麼樣子了嗎?
“我根本不關心尊嚴啊端莊這些事情,我在第一次尿失禁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這些。但是如果我不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如果真正的我開始消失而變成了另一個人,如果我再也認不出我們的孩子,那就是時候合上這本書了。”
起風了,有夏日香甜的味道。她問我想怎麼辦。
“我以為我知道。我以為我想先走一步,在痴呆早期就結束生命。我只是缺了開口的勇氣。”
“但是……?”
“但是我改變了主意。而這與我的勇氣無關。”
她盯着我,懷疑着,猶豫着。
我試圖解釋説我終於意識到,我的死亡對我而言並不重要。我們對死亡知道些什麼呢?死亡什麼也不是,我們將永遠無法瞭解它。既然如此,我怎麼可能害怕它呢?沒有任何理由去害怕啊。我們為什麼如此執着於要保持對自己的控制?為了誰?
“這與我無關,”我深呼吸了一口氣,“我的死亡不是我自己的。我的死亡只有對被我留下的那些人才有意義。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我甚至都不會知道嚴重痴呆所導致的半死不活會是什麼樣子。就讓我慢慢地離開吧,越過那個虛無的、再也不能回頭的點。”
“沒有一個醫生會來幫你,”她説。
“是的。醫生不會來幫助我。”
我告訴我的愛人我心意已決。“我不希望會這樣,但如果那一天到來,我喪失了我的意識和能力去説服醫生讓我死,另一個人將不得不來幫我做這個決定。”
“但醫生不會這樣做的。”
“是的,醫生不會。”
“那誰來做?”
“其他人。那些被我留下的人……”
我在腦海裏搜尋着準確的詞彙,試圖跟她解釋我仍然認為人應該有自決權。我們並沒有要求變老,不是嗎?但是在我們試圖控制生命的慾望中——一個悲劇而孤獨的慾望——我們有時候忘記了別人。現在我明白了,沒有人是孤獨離世的,永遠都會有人被留下來,不得不去處理這些死亡。而這,賦予了我們繼續活下去的道德義務。
我説:“死亡的權利應該是這樣一種權利,它授權他人——不是醫生,而是一個所愛之人——去決定是否結束你的生命。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只不過這現在是被法律所禁止的。這樣的法律應該改變,而這或許需要很多年的時間。”
我繼續説着:“但是如果你能看到我的痛苦,如果你能感受到我的恐懼,如果你認為我已經變成了人類的一個悲哀的棄兒……那你就可以把那片藥放進我的粥裏了。”
她覺得這個想法荒謬極了。怎麼會有人請求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拒絕。”
“然後呢?”
“那我將不得不去尋求其他人的幫助。這是我唯一的願望:由我自己來決定那個可以決定我的死亡的人。”
儘管這個想法跟以前那個一樣的痛苦,一樣的不可能。
我試圖讓她冷靜下來。“我什麼時候死由你説了算,不論你做出怎樣的決定。”
“好吧,如果這是你的選擇的話……”花瓣輕輕地飄到她的膝蓋上。
她會幫助我,就像她一直以來所做的那樣。“不管怎樣,我都會照顧你直到最後一口氣。”
原文閲讀:‘My death is not my own’: the limits of legal euthanasia. The Guardian. 2018/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