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認知的革命_風聞
神经现实-公益的科学传播组织2018-11-07 2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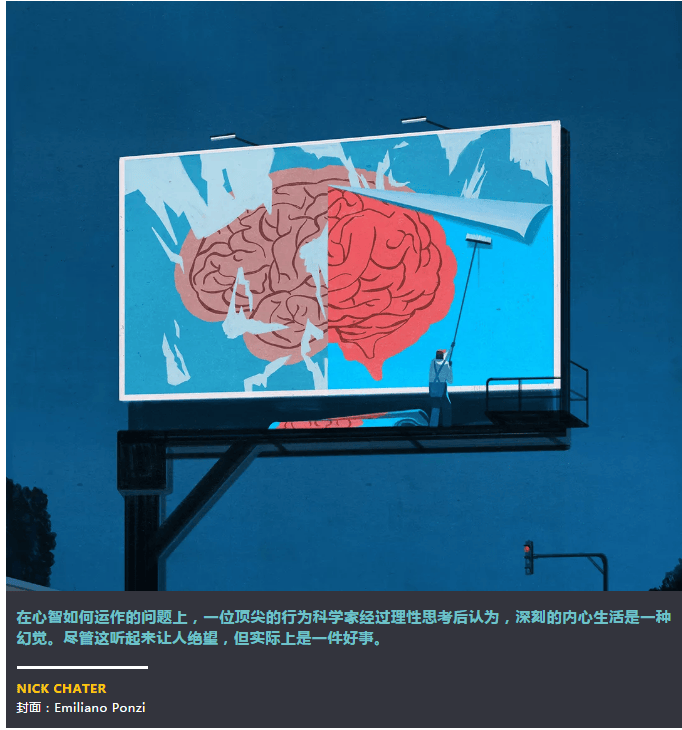
《安娜·卡列尼娜》裏有一幕場景驚心動魄。一輛火車從莫斯科邊境某車站駛出站台,女主角直接跳進火車軌道。但她真的是想死嗎?她是對俄羅斯貴族生活感到倦怠?還是因為失去愛人渥倫斯基而被恐懼束縛?她真的已經到了難以承受,只求一死的地步嗎?還是説,這次自盡行為只是一時衝動?會不會是她因為絕望才產生這種戲劇性的行為?在這麼做之前甚至都沒認真想過?顯然,我們問這些問題,是無法得到答案的。如果托爾斯泰説,安娜頭髮是黑的,那就是黑的;但如果托爾斯泰沒有交代安娜為什麼要自殺,那她的動機就是個謎。我們也許可以嘗試以個人的角度解讀她的行為,並討論背後的可能性。但至於安娜真正想要什麼,沒有人知道。因為她是個虛構人物。假如説,安娜是個歷史人物,而托爾斯泰的著作是新聞式的再創作作品,那安娜的動機就不再是文學解讀,而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我們探究這個問題的方式還是一樣的:從同樣的文本信息中找出一絲線索(有可能不靠譜),看看這個真實人物的心理狀態。這時,有不同解讀的人就是歷史學家,而不是文人。想象一下,現在我們可以採訪安娜本人。假設那列火車能及時剎車,然後受了重傷的安娜被匿名送到莫斯科一家醫院,並神奇地熬過了鬼門關,我們在瑞士一家療養院找到康復中的她。但安娜很可能和其他人一樣不確定自己的真實動機,畢竟她試圖解釋自己行為時也必須進行闡釋。誠然,她可能有他人無法獲得的信息,比如,她可能記得自己靠近站台邊緣時腦中閃過絕望的話,“渥倫斯基(Vronsky)永遠離開了我”。然而,這類信息也可能是安娜自己以為的,與真實情況存在偏差。畢竟,自傳的真實性總要打個問號。
Keira Knightley出演的《安娜·卡列尼娜》(由Joe Wright執導)
圖片來源:Leon Chew
**從這一情節可得出兩個截然相反的結論。**一是我們的思想存在晦暗不可知的部分。我們不能指望人們能進行可靠的自我觀察,或完整準確地表述個人信仰、動機。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和神經科學家長期以來都在討論如何更好探索人類更深層次的動機,目前多采用字詞聯想,夢境解析、數小時深度心理治療,行為實驗、生理記錄和大腦成像這些方法。
沒有任何治療、夢境分析、字詞聯想、實驗或腦部掃描能揭示一個人的“真實動機”,不是因為難找,而是找不到。
但我認為,我們的思考應導向另一個完全不同結論:解讀真實人物,和解讀虛構人物之間沒有差異。如果托爾斯泰的小説是報道文學,而安娜是一個活生生的19世紀俄國貴族,那麼自然存在安娜是否在禮拜二出生的歷史事實,但我認為安娜的真實動機仍無定論。沒有任何治療、夢境分析、字詞聯想、實驗或腦部掃描能揭示一個人的“真實動機”,不是因為難找,而是找不到。
騙局的證據
得到這個結論並不容易。 作為一個心理學家,我想要了解人們如何思考、做決定。如果説,每個人在講述自己想法或故事時有一定條理的話,那瞭解思考、做決定的過程就非常簡單。只要把人們的表述稍加整理、精簡,就可以推出人們真實的想法和意圖。理論上是這樣,但實際上完全做不到。因為太多證據顯示,現實中的思想深度超出我們想象。精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這些年來,我一直不肯承認這一點,現在終於意識到問題出在哪裏。
12點錯覺
Jacques Ninio
**感知會經常矇蔽我們。**比方説,由Jacques Ninio設計的“12點錯覺”作品。圖裏有十二個黑點,每行四個,一共三行。在純白背景下,人可以同時看到這些黑點。**但一旦黑點嵌在網格里之後,就只有你盯着看的時候才會出現。**那些注意力範圍外的黑點就神奇地消失了,彷彿被灰色對角線“吞噬”了一樣。有趣的是,當我們盯着看的黑點的時候,都能看到周圍那些相鄰的一對點,或點線,或三角形、甚至正方形。雖然這些相鄰的黑點能被看到,但也因為注意力沒法永遠集中的原因,就會常常消失不****見。同理,日常生活裏我們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我們每次只能關注一個物體,其他東西就直接忽略掉了。**我們能觀察到的“注意力窗口”非常窄,每次只抓取一個對象、詞語或臉。所以,如果有人説他可以做到記住視線範圍內所有的細節還有色彩,那麼他肯定在吹牛。之所以吃瓜羣眾信,那是因為當那個人被問起來視域裏的特定細節時,比方説某花瓶的顏色或某個單詞的含義,他/她可以做到馬上調度注意力轉動眼睛搜索信息,鎖定“目標”後、馬上回答問題。給的答案太順暢,以至於吃瓜羣眾以為那個人早就把一切信息裝在了腦子裏。再説遠一點,連我們內心深處那些滿到要溢出來的感受和想法,也都可以打個問號。要知道,大腦會自己添油加醋。不相信?來給大家講個故事吧。認知神經科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有一個很經典的研究,研究對象是左右半腦被手術切斷的“裂腦”人。解剖學層面來講,我們大腦是對側控制身體的。比方説,右半邊的視域信息是傳輸到左半球視覺皮層處理的,然後左半球運動皮層控制右手,反之亦然。 所以對於裂腦患者來説,左右半腦能獨立響應完全不同的刺激源。有一個著名的論證是,加扎尼加給右半腦看一幅雪景,給左半腦看一隻雞爪。接下來,右腦的任務是要找到與雪景相關的圖片,並用左手選出鏟子(下雪天剷雪用)。按説,左腦看不到雪景,只能看到雞爪,所以是無法解釋左手選鏟子的原因。然而,左腦自己找到了個能説得通的解釋:雞爪與雞有關,你需要鐵鍬來清理雞棚。這聽起來很高明,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語言系統對我們行為背後原因一直尋求合理解釋。不過,在不瞭解真實情況時,語言系統依然照以往的習慣去強行解釋,這就不合適了。
**我們的內心世界,可以説是想象力產物。**在和他人交換能量的時候,會形成自己對事物的理解,就如同我們從文字裏裏感受到小説裏虛構人物的性格一樣。説回安娜,我們可以猜她的絕望也許更多是因為自己社會地位的急劇衰落、或是擔憂她兒子的未來、或是無意義的貴族生活,而不是為情所困。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正確的解釋,哪怕有些解釋是基於托爾斯泰的小説稿,比其他更具説服力、更好證實。作為小説作者,托爾斯泰頂多能按自己的意願去解釋“真實”的安娜的行為,而安娜本人也只能再提供多一種解釋。生活情節的發展和小説沒那麼不同,我們每一刻都會形成信念,價值觀和行為。**和虛構作品一樣,思想產生那一刻之前並不存在。**換句話説,以往我們認為行為只是冰山一角,而底層還有深不可見的動機、信仰和慾望,但這只不過是思想欺騙了我們。事實上,無所謂深無所謂淺,心智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切。對於所有事物,我們的心智都會有對應的解釋。每次選擇、偏好、或者信念受到挑戰時,都會嘗試尋找一系列合理的解釋。為什麼選這個沙發?為什麼是巴赫,不是勃拉姆斯?為什麼選擇這個職業?為什麼要孩子,或為什麼不要?為什麼是進化論而不是創造論?如何使用自行車,小提琴或貨幣?**每次合理化都能得到更多的論據支撐,然後提煉論點再闡述清楚,這個過程可以無限循環下去。**我們有如此強大的創造力,以至於解釋什麼都易如反掌,我們甚至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心智先知”,能為每個問題找到現成的答案。
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心智先知只是一種幻覺。因為它提供的解釋漏洞百出。如今大家的共識是,我們的想法經不住推敲也自相矛盾**。**我無法準確告訴你冰箱如何運作,或電怎麼在屋裏走線。每當我努力想解釋英語語法規則、量化寬鬆工作原理或水果蔬菜的區別時,我總會陷入矛盾混亂。
“我們經常把自己的認知強加到事物上(亂投射一通)。
難道這些漏洞就補不上了麼?矛盾就解決不了?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試。我們也嘗試了。兩千年來的哲學都在致力於“釐清”諸多常識:因果、善美、空間、時間、知識、思想等;不用説大家也知道,“釐清”這些常識的任務尚未實現。同時,科學、數學也始於常識,但結果卻被完全曲解:這些常識被改頭換面,包裝成了全新的複雜難懂的概念——比如討論點落到了具體的熱量、重量、力量、能量等角度上,然後只能得到和直覺相反的推論。這就是為什麼探索了幾世紀後才發現“真正的”物理學規律,這也是每一代學生需要面臨的挑戰。哲學家和科學家發現,信仰、慾望和類似的日常心理概念尤其令人困惑。**我們經常把自己的認知強加到事物上(亂投射一通):**比如説,我們認為螞蟻是“知道”食物在哪裏的,並且是“想”將把事物帶回巢的;電子寵物Tamagotchis是“想”被投餵的;本來我打算輸入“穀物”(grist)時,搜索框“猜”我想輸入的是“軟骨”(gristle)。我們隨意將信念、慾望投射到自己和他人。自弗洛伊德以來,我們甚至創造了多個內在自我(如本我、自我,超我),每個自我都有他們的動機和行為方式。但這種合理化只不過是一種省事的虛構,精神分析也只是一種最高級合理化的投射:故事情節的錯綜複雜源自行為的細節和夢的片斷。
一個人工智能實驗
我們的思想行為受“常識理論”指引,儘管不同於科學上的理論,但仍能邏輯自洽。這種想法佔據主流地位。從20世紀50年代起,很多科學家花了好幾十年時間,研究怎麼創造能和人一樣思考的機器,其終極目標是系統化有序地批量製造出這種機器。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發沿用這種思路,大家都對這種思路寄予厚望。在過往的幾十年裏,頂尖的科研人員預測可在二十到三十年之內實現和人類同等水平的人工智能。**不過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懷疑這個思路。**到80年代時,系統化挖掘知識的計劃陷入僵局。其實,從內心那兒尋求某種理論是不成功的,完全沒有指導意義。這也説明找出人類行為背後的知識、信仰、動機是非常困難的。國際象棋頂級大師也無法解釋他們如何下棋,這如同醫生無法解釋他們如何診斷患者病情。**我們誰也完全無法解釋自己如何理解人和事物的日常世界。**我們的説法聽着像解釋,但實際上只是勉強合理。也許人工智能前幾十年研究的最重要發現就是,這問題本身如此艱深難解。
不需要高級智能的工作:由捷豹路虎機器人組裝的汽車。
—
Matt Crossick / Empics
模擬人類智能的計劃從此被逐漸遺忘。相反,AI研究學者打造的機器開始不向人類學習經驗,它們直接通過大數據(圖像、語音波、語料庫和國際象棋棋局等)學習,相關研究在最近幾十年取得了重大突破。大部分的人工智能研究重心已經轉到完全不同但有所關聯的領域:機器學習。很多前沿突破讓機器學習的出現成為可能,例如運算更快的電腦、更大的數據量和更智能的學習方法。**但機器學習無法讓我們挖掘人類信念或重建常識理論。**我認為,驚人的應變能力就是人類智能的核心。這賦予我們能力,讓我們能成功應對複雜、開放的自然、社會環境的挑戰。舉個例子,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已經可以在不需要應變能力的領域準確完成工作,如國際象棋、AlphaGo和汽車裝配工廠。但“機器人的崛起”不過是自動化的加強精進,至於我們的隨機應變能力,大腦驚人的創造力,短期內芯片做不到,也可能永遠都做不到。
自己創造未來
**別絕望,**這不代表不存在“自我”。我們大腦喜歡即興創作,還不知疲倦、充滿熱情,還每時每刻都在產生思想。但就像舞蹈、音樂或故事講述之類所有即興創作一樣,每個新想法都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基於過去的片段。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段有着奇妙創造機制的獨特歷史,這機制能重組過往,形成新的感知、想法、情感和故事。而經歷的肌理使我們對一些思維模式感到自然而然,對其他則尷尬不適。每次回顧過往,我們都在不斷重建自我。通過影響重建過程,我們塑造出當下、以及未來的自己。 所以我們的驅動力,並非來自於幽暗、深沉的內心世界。**相反,我們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過去思想行為的變形。**至於更看重哪些原則、允許哪些轉變,我們都有選擇的自由,以及判斷力。既然今天的想法行為,會是未來的經歷,那我們就時刻都在重塑自我。這個觀點,與弗洛伊德的心理極其矛盾,但與認知行為療法(CBT)完美契合。臨牀案例非常好地印證了CBT的效果。**重塑思維行為十分困難,需要建立新模式,以覆蓋掉舊習慣。**也就是建立一條路徑,能讓思維流動更順暢及高效。**CBT旨在準確建立新行為和思維模式,通過接近恐懼對象,來轉變“躲開”這種消極思維方式。**新路徑能慢慢影響、控制舊習慣。諸多治療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改寫過往經歷,產生對未來更有建設性的思維行為習慣。不過無法揭示隱藏在我們心靈最深處的病症——不是因為深不可測,而是它們不存在。你也許會説,這解釋蠻好。**但我們也需要信念動機,來解釋想法行為是有意義的,而不是徹底無序的混亂。**毫無疑問,的確存在諸多重要心理事實,影響我們行動方式:我們所重視的事、所信仰的理念,以及驅動我們的熱情。但如果思想是平的,即便存在所謂的故事,關於自己和他人的,信念、動機仍不足以驅動行為——因為它們只是一種投射,而不是事實。
作為個體,我們的“自我”有限、破碎、驚人脆弱,我們只是某種最粗糙的文學畫像;但作為集體,我們構建的日常、組織和社會則十分穩定自洽。
但很多之前的例子可以為思維的有序(有時是無序)本質提供全然不同、更具説服力的解釋——為創造新模式,而對之前的思維、行為的連續適應、轉變。尤其是我們的文化,可以被當作以往歷史的共享規則:我們所做的、所要的、所説的、所思考的——產生了社會和每個個體的秩序。通過定下新規先例,我們共同逐步打造我們的文化,但新規也基於共享的舊先例,所以文化也在塑造我們。作為個體,我們的“自我”有限、破碎、驚人脆弱,我們只是某種最粗糙的文學畫像;但作為集體,我們構建的日常、組織和社會則十分穩定自洽。我相信這是個解放性的觀點。我們不是被隱藏的動機驅使,並非被潛意識束縛,也沒有無望地被過去困住,每個新想法、行為都是重塑自我的機會,哪怕只是輕微地。當然,自由也有侷限。業餘薩克斯演奏者不能“自由地”像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一樣演奏,英語初學者不能隨心模仿西爾維亞·普拉特(Sylvia Plath),物理學生也無法天然像愛因斯坦一樣思考。
自由有其侷限性:我們無法選擇像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一樣演奏。
—
Hulton Getty
新的行為、技能和想法需要豐富深刻的思維習慣,養成有專業基礎的習慣需要的幾千個小時,這個過程沒有捷徑。**在新思維、行動的產生中,我們每個人都自成一派,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會以各自的方式演奏音樂,寫作和思考。**然而,有些東西在日常生活中是相同的,如我們的恐懼和焦慮,我們與他人交流有時存在困難。我們的自由,不是自我神奇地一步躍變,而是一次一步“重塑”思想行為。即使緩慢,我們當下的想法和行為也在不斷重構思維。難道這説明我們是一塊白板?可以往上書寫任何心理模式?完全沒有的事。比方説音樂。我們對音樂的感知建立有好幾個方面:神經系統的節奏生成區域、大腦分類聲音的方式等等。再比方説語言。語言的塑造取決於我們的發聲器官、大腦形成和識別複雜句的方式等等。人類的音樂和語言有許多形式——但不是任何形式。思想也不例外,會受到大腦的偏見偏好,以及基因的影響。**所以我們的思想行為是會受到生物學影響,但不是完全由生物學決定。**而我們也並不會被神秘心理力量困住。任何思維困境都是我們自己建造的,也都可以像建造時一樣拆除。如果思想是平的——當我們設想自己的思想,生活和文化時——我們有能力想象並實現一個鼓舞人心的未來。
本賬號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簽約賬號
翻譯:五月
校對:Root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apr/01/revolution-in-our-sense-of-self-sunday-essay
Nick Chater
華威商學院行為科學教授,Decision Technology Ltd.聯合創始人,著有《思想是平的》(The Mind Is Fl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