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恰特:思想是平的,無意識是不存在的_風聞
神经现实-公益的科学传播组织2018-11-12 16:17
來源:神經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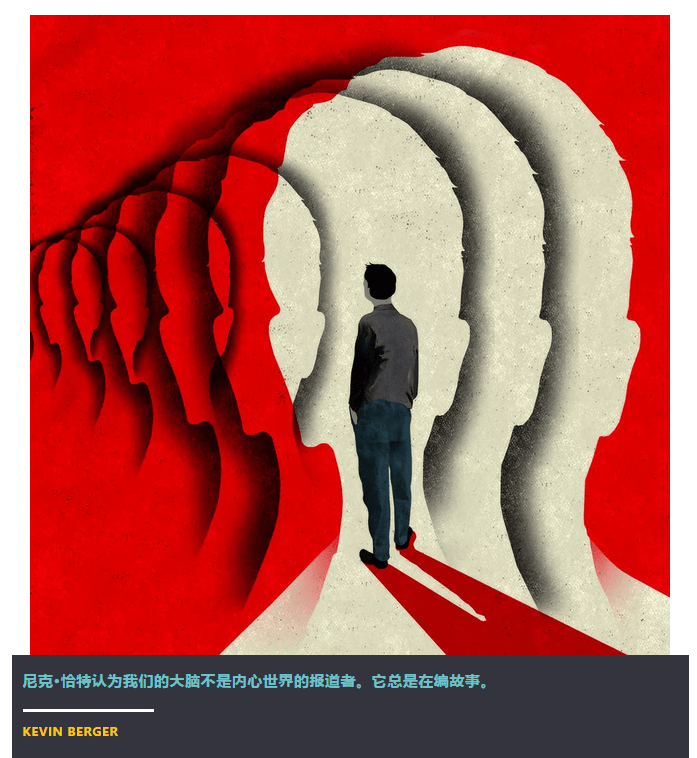
最近出版了一大批關於大腦的書。如果你想把這些各執一詞的文本都弄懂,大概會讀到昏迷。所以,當我打開英國行為科學家尼克·恰特(Nick Chater)的《思想是平的》(The Mind Is Flat)這本書時,也沒什麼特別的興致。雖然説書名還挺有趣的。但我一開始閲讀,瞬間就精神抖擻了。也許是因為開篇濃墨重彩地探討了安娜·卡列尼娜,還讓讀者試着揣測她自殺的動機。我們該怎麼解釋呢?要是蒸汽火車在最後關頭急剎,安娜活了下來,然後被送到一家瑞士療養院接受康復治療——她會如何向心理醫生解釋試圖自殺的原因呢?
不用在意安娜只是個虛構角色,恰特寫道。對於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們會以同樣的方式拷問他漫長精神旅程的來蹤去跡。可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倖存下來的人,不管怎麼努力釐清內心的千頭萬緒,當心理醫生問他為什麼自殺,他只能説出一個“故事”。恰特的論點簡直狂妄:不存在所謂動機背後的深層真相。“任何治療手段,無論是夢境分析、詞彙聯想,還是實驗、腦部掃描,都不可能揭示人們的‘真實動機’,不是因為它們藏得太深,而是因為它們根本不存在,”他寫道,“所謂內在的精神世界,以及被認為容納於其中的信念、動機和恐懼,這些東西本身都是想象出來的。”
自我認知的革命
在心智如何運作的問題上,行為科學家尼克·恰特經過理性思考後認為,深刻的內心生活是一種幻覺。
好吧,我心想,如果恰特繼續這樣大放厥詞,《思想是平的》這本書也就是平的了。然而,他接下來對現代認知研究與實驗的版圖展開了一番巡禮,並精準地抨擊了一個又一個在我們的文化中備受推崇的、所謂混沌大腦中的潛在真相,而它們在我們的文化中被奉為真諦。恰特寫道,情感不是預先形成的感受,只等我們表露出來;它們其實是暫時的即興樂段,為身體反應伴奏。我們的大腦就像爵士樂手,盡力在每一個瞬間編造出最好的思想和行為。探尋更高階的意識也許是個誘人的想法,恰特寫道,但這無異於“踩着高蹺胡説八道”。你是否也認為,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探索了心靈活動最深處的奧秘?“正相反。”恰特寫道,喬伊斯和弗吉尼亞·伍爾夫著名的意識流風格是“成功的思維過程的最終輸出”。(好吧,這説法有點傻。)
不管怎樣,我被《思想是平的》迷住了,一口氣讀完。我在其他幾本最近出版的書裏也讀到過類似的觀點,尤其是神經科學家麗薩·菲爾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的《情緒從何而來》(How Emotions Are Made),這本書細緻地展示了為什麼“情緒是大腦為身體感知創造的意義”。然而,恰特那些無所顧忌的論斷攫住了我——比如“我們都一直活在一個騙局裏,罪犯是我們自己的大腦”——雖然我不敢肯定他説的是對的。所以我等不及和恰特本人談談,看看我是否誤解了他筆下的無意識(unconscious),並解開我滿腦子的疑惑。他的答覆充滿了歡快的情緒和深刻的洞見,與我從他書中感受到的捷才相映成趣,尤其是他把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稱作“心理學的占星術”,真是精妙。我拋出的第一個話題是精神療法,因為“在無意識領域漫遊能夠解放心靈”這一金科玉律,正是恰特最渴望顛覆的。
— Nick Chater
你是不是認為,試圖通過讓無意識的動機浮出水面來緩解痛苦,這種精神療法……
註定失敗?
嗯,註定失敗。那為什麼這麼説呢?
因為事實上,不存在什麼隱藏的、深層次的內心故事。反之,是你有了一本小説最初的草稿,或者一些不連貫的筆記。你只有一片不連貫的混沌。可以説,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的混沌。一旦這些不連貫的東西種有什麼造成了麻煩,比如我們很想做某件事卻又恐懼它,包括害怕蜘蛛等微不足道的小事,這就構成了我們想法與行動之間的衝突。
你認為精神療法有價值嗎?
有啊。並且我認為,一個實際的治療目標可以幫助人們以更連貫、整體的方式認識世界。對於病人來説,這樣做大有裨益。
如果我們以為有意識的思考是由隱藏的心靈深處生成的,就會開始折磨自己。
如果像説起來這麼簡單就好了。
嗯,其實很難。不是治療師説一句“我看到你這裏有個心結,我們把它解開就一切都好了”就能搞定的。它需要一個創造性的飛躍。就像寫小説一樣難。如果你以為只要把劇情安排成連貫的整體,不要讓角色太突兀就萬事大吉了,那當然覺得寫小説很簡單啊。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為了理解生活煞費苦心,這至少不比寫小説簡單。
事實上,我們的思想不是基於連貫性的,而是基於先例,基於對過往經驗的一種變體或延展。過去的種種經驗相互依存, 創造了我們的思維習慣。有些過往是糟糕的土壤,會孕育出我們深惡痛絕卻難以擺脱的行為模式、思維模式。
有些人會説,“既然不存在隱藏的思想深處,精神療法不就易如反掌了嗎?”可是這個事實反倒讓精神療法難上加難。因為這樣一來,也就不存在只要稍加修改就能變得連貫完整的故事。我們面臨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從零開始創造對生活的理解,還得把故事説圓了。
我還是覺得,這聽起來好像在説,我們只需要即興應對就能擺脱困境?假如親人亡故了,悲傷吞噬了你,你該怎麼在精神上走出來呢?
我覺得無論什麼生活困境,都沒有立竿見影的萬靈藥。但是,喪親的打擊可能會摧毀一個人的人生觀。想象一下孩子或愛人離世這種最糟糕的情況,你可能拒絕接受現實,而糾結於這種想法正是你走不出來的原因。這和劇本里寫的不一樣啊。生活不該對我下此狠手。我的生命,我愛人、孩子的生命都有既定的路線和方向。可是現在,我該怎麼接受這一切?簡直是在開玩笑,整個世界都失去了意義。曾經有個面臨離婚的朋友對我説,他感覺有人剛剛搶走了劇本,還揉成了廢紙。你眼中的未來只剩下一片虛無。
然而,當悲劇從天而降,我們需要做的是重新寫故事。我認為當人們試圖改變,比如跨越喪親這道坎時,所做出的努力大多是創造性的再想象(re-imagining)。既然那麼糟糕的事情都能發生,我們得找到一種詮釋世界意義的新語言。也許我可以把逝者的一生看作非常美好的一生。雖然比我設想中的短暫,但我可以放大那些積極的部分。
假如你是精神治療師,你會怎麼對他們説呢?
我想我會首先告訴他們,我們理解身邊人的方式,以及那些塑造我們的行為和心理習慣,都能深刻影響我們對生活的感覺,決定我們能否應對生活的挑戰。因此,治療的目的之一是引導人們構建新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從而幫助他們繼續前行。治療不是為了,比如説,揭露、糾正無意識的動機、信念之類的,而是為了幫助有意識的大腦向前看。
深刻理解我們的思考本質上是淺薄、即興的,會帶來不少好處——試圖挖掘自己的內心深處通常會製造一些麻煩的幻想。如果我們以為有意識的思考是由隱藏的心靈深處生成的,就會開始自我折磨,拷問心靈深處到底有什麼東西。在那個喪親的例子中,人們可能會思忖:“我是不是不夠難過?我這麼快恢復是對的嗎?這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夠愛我的伴侶(孩子)?”於是你在找尋所謂內心深處的真相的過程中備受煎熬,我認為,正是這種感覺讓我們阻滯不前。
人們也會出於同樣的謬誤毀掉戀情。假如我們勘探自己的內心,尋找我“應該”對伴侶感覺到的那種愛,然而,可能找了半天沒找到,我會不會根本不愛她?可能找到了,但太少了,或者太多了。如果一直沉浸在這種想法中,你可能會達到一種病態的狀態。一切的禍根就在於,我們誤認為內心有深層次的真實,而外在的現實不符合它。更進一步説,一切關於真實感的想法都很危險,因為這預設了存在真實的和虛假的兩種感受,而且真實感受藏在我的內心。於是我們整天惴惴不安,就怕搞混了真實和虛假。對於這種感受的區分,我們應該持懷疑態度。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大腦為了回答這些對內心世界的拷問,會在問題被提出的時刻,立馬創造性地編造一個答案——而不是從內心世界儲存的那些既有的想法、感受和動機中尋找。這很容易發現。如果你用稍有差異的方式問自己同一個問題,得到的答案可能是徹底矛盾的。我們的大腦總是在編故事,雖然不一定很連貫,但它絕不是內心世界的報道者。然而,大腦編織的故事太流暢、太吸引人了,我們輕信它報道了事實,很難發現這都是它虛構的。
我懂你的意思,但我還不太明白你為什麼對無意識不屑一顧;過去的回憶和根深蒂固的習慣時刻影響着我們有意識的思考和行為,怎麼能説無意識是一種危險的幻覺呢?
我認為無意識這個比喻很危險,是因為它暗示了無意識心靈內容可以變得有意識。林林總總“揭開無意識的真面目,並轉變為有意識的東西”的理論,背後的預設都一樣,那就是無意識和有意識其實是一類。也就是心靈的冰山比喻:冰山露出水面的尖,和水底下不可見的絕大部分一樣,都是冰做的。我認為這種説法錯得離譜。實際上,我們有意識的體驗、思想、交流的片段,和那些我們無法意識到的東西——所有那些神秘的大腦過程,包括安放和讀取記憶,整合碎片化的信息等等——在類型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每一個層級上,流過大腦的東西都是思想,比如圖像、疼痛的感覺、語言的片段。但是生成這些思想的無意識大腦活動屬於另一類型。就算我們明白了數十億的神經元如何協作,藉助這些理論辨認出一張臉或者理解一段演講,也會發現這個過程與意識流好像沒什麼聯繫,就像肝臟如何運作和意識流毫不相干一樣。
假如我們勘探自己的內心,尋找我“應該”感覺到的那種愛,那麼它在哪兒呢?
你可以為大家澄清一下“思想”(thought)的定義嗎?
這個很難説清楚啊!大致來講,思想就是意識體驗的內容:流過你有意識的大腦的那些疼痛、刺痛、形狀、運動、聲音、語言的碎片等等。在弗洛伊德之前,人們會認為存在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思想是很怪異的事情。大腦被看似有意識但其實無意識的思想活動充斥着,這確實是極具顛覆性的想法——但這是個誤判,我認為。
你是覺得“無意識”的錯誤在於語義嗎?或許你認為我們平常對這個詞的使用有問題?
我認為這不是語義層面上的問題,而是個實質性問題。無意識思想這種看待大腦工作的方式,是極其偏狹的——它假設了,佔據着我有意識的大腦的思想很好地表徵了大腦如何運作,然而這些運作的對象又是我意識不到的。大腦的真實運作方式其實更加奇怪:大腦的感知、語言處理、運動控制、記憶等機制都幫助生成有意識的思想,但它們一點也不像有意識思想的隱藏“副本”。
大腦的活動是無意識的——這句話可以是對的,但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那個意思。我們容易掉到一個思維陷阱裏:“好吧,你説大腦活動不是有意識的,那麼大腦一定在做無意識的事情,那肯定是無意識思考了。”思考是什麼東西?是信念、推理、動機、計劃、疼痛等等流經有意識的大腦的東西。然後我們頓悟了:“原來如此,大腦有兩種思想,被某條神秘的意識邊界分開。”我認為這是個很大的錯誤。存在一些我們意識不到的大腦活動,這沒錯。但這些大腦活動不等於無意識的思考。
但它們的確影響了我們有意識的思考。
那當然。它們完全決定了有意識的思考。它們是不斷生成有意識的體驗與思想的機件。
我舉個例子來説明這種影響吧。我每次聽到大衞·鮑伊的老歌,情緒化的記憶就立刻湧上心頭。我的反應好像不是有意識的。
嗯,我能確定不是。但是思考一下,光是意識到這首歌是我熟悉的,而且歌手是大衞·鮑依,就牽涉到多少大腦活動啊。我們沒辦法內省地通曉這些大腦過程。我們永遠是這樣的,我們只能意識到大腦過程的最終輸出——“啊,那是鮑依”——而對過程本身一無所知。大腦中無意識的操作對思想至關重要,但它不等於思想。
我認為這兩者沒辦法分開啊。比如,你寫到“隱喻在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例證了人類大腦的創造性。可組成隱喻的那些東西,語言和符號,是通過演化、遺傳和文化環境獲得的。我不明白那些無意識的影響怎麼能和思想區分開來。你難道不認為,“無意識只是個傳説”這種説法也很危險,甚至有誤導性嗎?
沒錯,無意識影響着思想的東西無處不在,遺傳、個人經歷、思維習慣、我們使用的語言和隱喻等等,無法窮舉。但是這些無意識的影響,包括支撐着思想的大腦活動,本身並不是思想。我們太容易犯這種錯誤了。還有一個思維誤區是,我們以為通過自我審視,或者心理治療、腦成像之類的手段,就能把這些所謂的無意識思想挖掘出來,把它們帶到意識的陽光下。然而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大腦運作和其他生物機能一樣,都沒辦法變得更有意識了。我們可以像講故事一樣描述肝臟的工作任務,説免疫系統混淆了自體組織,或者自私的基因之類。我們也可以講講大腦的故事——假設它可能壓抑了信念,懷着隱藏的動機,潛入集體無意識,隨便什麼東西。但這些都是比喻,不符合事實。大腦對無意識思想的參與並不比肝臟、免疫系統和基因更多。
那你對情緒的定義是什麼?
我認為情緒是一種詮釋。理解你自己或他人的情緒,與理解小説中角色的情緒多有類似。你置身於某個情境中,產生了某個生理反應,於是你需要對它加以理解。如果你看到一個人站在高樓的窗台上,汗如雨下,神情緊張,你就會想,“這可不妙啊,他害怕掉下來,他正感受恐懼。”如果窗台上的人換作你自己,你也會想,“天哪,我的心快要跳出來了,我腎上腺素飆升,不停冒汗。”還有,“救命啊,我要掉下去了。”可是當你在百米賽跑的起跑線上時,也可能產生同樣的生理症狀。所以説,生理狀態極其模糊。關鍵在於,感覺不是從心靈深處的什麼地方迸發出來的。感覺不是預先存在的。它們是大腦對身體狀態進行即時詮釋得到的最佳反饋,而且受當前情境的影響。
能把你關於大腦如何運作的理論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一些重要方面嗎?比如宗教?
宗教倒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它很好地例證了我的觀點。
嗯,請展開講講。
如果你問那些信徒是否相信他們的教義,答案是百分百肯定的。可是,要闡明他們的信仰與教義是怎麼契合的,卻很難做到。我沒有説探究我們何以相信科學就是小菜一碟了。我們關於一切事物的思考幾乎都是不連貫的。也許這個世界對我們來説過於複雜了。話説回來,拿聖餐化質説(transubstantiation)舉個例子吧。信奉這條教義的人認為,耶穌基督的聖體和聖血真實地存在於麪餅和葡萄酒裏。但你試着剖析一下,深入理解這句話——你根本做不到,信徒也做不到。這根本就不可行。我認為這個例子説明,人們以為自己對某件事深信不疑,其實只是攥住了它的表象。鑑於我的粗淺之見、生活經歷等等,我選擇相信你説的話。我甚至甘願為此死在火刑柱上。
是什麼讓我們皈依於某一信仰,並認為其他都是無稽之談呢?
在我看來,問題的核心在於大腦是個順序處理機器(sequential processor),每個時刻只能思考一個想法。每一次思考,你都得吸收巨量的碎片化信息並加以整合。這些信息可以是感官的、語言的,或記憶碎片。而宗教最擅長的事情,也許就是讓我們感覺到所有的信息環環相扣。你會感覺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都豁然開朗。就好像你看着一張很難懂的圖片,突然想到,“噢,我明白了!原來是張牛臉啊”,或者“這是條狗”。
這時候,也許這些信息碎片其實並沒有整合起來,但它給你一種連貫一致的感覺。一旦你開始攪亂這種連貫性,生活的意義也就被減損了。有些人心甘情願維護某種世界觀,拒絕任何偏離。這樣一來,他們損失了創造性地理解生活的能力,眼中的世界變得狹隘,並且不再有新的人生目標。人們或許可以換一種方式思考生活,而且新方式並不比原有的方式無聊。然而,質疑是痛苦的過程,至少短期來看。質疑我們相信的任何東西,包括宗教,都不會令人愉快。
最後一個問題,把我們的大腦看作扁平的有什麼好處呢?
它讓我們着眼於理解自己生活這項創造性工作,而不是執拗地想解開什麼心靈密碼。我們如何才能提升生活的質量?如何才能更連貫、深刻地思考?如何解決問題,繼續前行?為了解決問題,有時候我們必須往回走,就像寫小説或者證明數學題那樣。有時候你得退後幾步思考:等等,我在這兒犯錯了,我不應該讓人物這樣發展,我計算出錯了。但更重要的是,你得把這項工作看成向前進展的,不要覺得自己甚至所有人都在某種神秘力量的控制之下,只有向內心探尋才能找到這種力量。向內看是沒有建設性的,我們應該向外看,看對方向。生活中我們應該時刻向前展望,才會有積極的收穫。
本賬號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簽約賬號
翻譯:有耳
校對:瑪雅藍
http://nautil.us/issue/62/systems/this-man-says-the-mind-has-no-dept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