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長輩講過去的事情——家族回憶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18-11-13 22:28
聽兩位常坐直達我們學校公交車的老人説:“你們學校的大學生不願意讓座,看到老人上車沒有座位,簡直視而不見。”
我説:“這不怪學生,怪我們這些當老師的沒教好”。
但想了想,又爭辯道:“可是我覺得我們學校大多數同學看到老人還是會讓座的,您看到的那些年輕人就一定是師院的嗎?”
“他們一直坐到你們學校門口下車,還能是哪兒的?”
我只好打趣説:“可能您二位看起來年輕,不像是上了年紀的人。學生們覺得讓您站站也無妨吧。”
兩位老人笑了。但我心裏可沒這麼輕鬆。記得有一回給某系的同學們上課,講到“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有相對的獨立性”,我就説:
“比如説,道德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就往往並不是一種直線的正比關係。例如某特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比我們這裏高很多,可是我的很多當地同學説,那兒的公交車上,經常就有年輕人看到老弱婦孺不讓座,他們自己都看不慣——這種情況我在那兒上學時也看到過。不過在我們這裏,尤其我們學校的同學就不會這樣,見到老人呀,抱小孩的啊,都會主動讓座,對不對?”
可是,同學們並不認同我的話,在下面議論紛紛的。幾個膽子大的同學還嚷嚷起來:
“沒有啊,咱們學校也有好多不讓座的呢!”
我覺得有些尷尬。因為我在本市也確實碰到過一回這樣的情形:
幾位老人上了公交車,往後擠了很久也沒有人讓個座。幾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不知道是不是咱們學校的)坐在座位上,老人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而我也是站着的,沒辦法。
所幸司機人挺好的,他在喊:“幾個老人家坐到座位沒有哇?”
我聽了,急忙配合,也朝着司機的方向大喊道:“沒有哇!”
這時終於有兩個年輕人(不是那幾個學生模樣的)不好意思地站了起來。這事我印象深刻,但是我總想,那幾個人應該不是咱麼學校的學生,因為我看到過很多次我們同學讓座。誰料…..
也許,聽我那次課的同學都會想:我們現在這是怎麼了?我們究竟應不應該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別人?
但是我覺得,更深層、更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去做一個怎樣的人?我們究竟應該向怎樣的人學習?我們究竟要到哪裏去尋找力量?
我不好説別人一定得如何如何,就説説自己的感想,自己對自己家裏人的一點感想吧。 而眼前兩位老人的話,讓我不禁記起了一個星期之前大舅和我談的一番話——我的長輩,他們豐富的人生經歷和感悟,常常會在做人這方面給我以深刻的啓迪。
到這學校來工作之前,離大舅家比較近,我一家經常到他家去玩。他退休在家,有時也會和大舅媽來我家坐一坐。那天吃完晚飯,我送他們回去,就聊了一路。大舅對我談起了他的爺爺,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我們叫“老外公”):
你的老外公去世後很久,我才理解了他那個人。你知道嗎?六、七年以前,就是外公去世後,而你小舅舅還沒有出國去的時候,我和你小舅舅有事回老家。在老家那幾天,我們曾經路過一個小廟。這個小廟離我們村子已經有幾十裏地了,我們在那裏休息,管廟的那個老人家聽見我們講話的內容,就問:
“你們是南村宋家屋裏的啊?”
我們説是啊。然後他問我們爸爸是誰,爺爺是誰,我們都一一告訴了他。誰知道他就激動起來了,對我説:“你們家是我的大恩人哪!你爺爺救了我的命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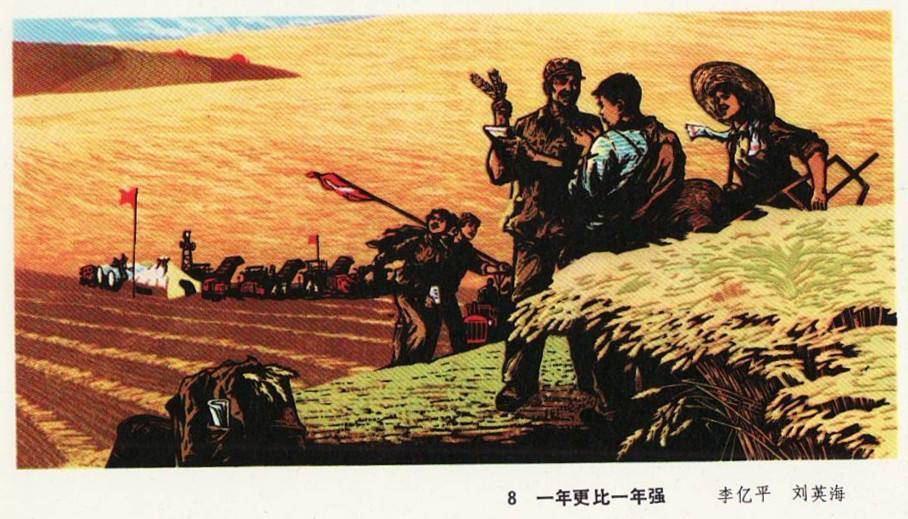
原來,大概五、六十年以前,他又病又餓,倒在路邊裏奄奄一息。你的老外公剛好路過,把他揹回家裏,給他推拿,搞草藥治病,又給他做了東西吃,終於把他救活,還送了些錢給他,讓他回家。他説他這條命就是你的老外公救的,所以他一輩子都記得南村的宋師傅。離開那座小廟,我和你小舅都有很多感觸:這件事情我們以前根本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你老外公是那樣的人。鄉親們都講,他做過不知道多少這樣扶危濟困的事情,説他其實自己有沒有多少錢,但是看不得別人受苦,是那種只要身上有一件衣服,都寧可脱給別人穿,或者起碼也剪下來一半給別人穿的人。不過他有些像《水滸傳》裏那些好漢:高大魁梧,性格豪爽,對別人好,對自己家裏的老婆孩子倒不怎麼樣,又好喝酒,還在舊社會里沾染上賭博的惡習。所以,他雖然很勤勞,很能幹,地裏的活也好,搞其它手工業也好,樣樣都做得比別人強,可就是發不了家,因為都讓他喝掉賭掉,或者散錢出去幫助了別人了——他曾經把家裏房子賣掉接濟朋友,不久又砌一座新房,然後把新房裏的好傢俱都賣掉還賭債。他一輩子就是這樣活着,我們小時候都不理解他。因為他勤勞苦幹,我們並不是説沒吃沒穿,但他這樣一弄,往往家裏剛有點起色,立刻就折騰光了,所以包括你外公都很有些怨他。但是現在我理解他了。他是有一些缺點,可他天性就是這樣急公好義,古道熱腸的人,一輩子仗義疏財,做了無數好事,十里八鄉有口皆碑,我們每次回老家,鄉親鄰里對我們這些人都要高看一眼,不是看你有錢或者什麼,是你這一家的名聲好,大家心裏佩服。——你看就連這麼遠的地方,都有人記得他。我們這些人誰能做到這樣?
大舅見我靜聽入神,又説:
別看你外公有點怨你老外公,可他自己一輩子也是赤膽忠心,勤奮工作,樂於助人,光明磊落,只有他幫別人,從來沒有損人利己,損公肥私。他先後辦了三個工廠,搞得紅紅火火,但是文革的時候,怎麼查都查不出他一點經濟問題。只是他吸取你老外公的教訓,並且受黨的教育,沒有你老外公的有些惡習,而且他更加精明、嚴謹,是個為國家搞企業,搞建設的實幹家。你還記得在你們家院子裏為外公辦喪事的時候嗎?我們請來主持喪禮的老先生,一看孝家的名單,再看看我們家這些人,就説:
“你們家真是很難得啊。我搞過這麼多年的喪禮,像你們這麼大家族,難免有一兩個早逝的,但是你們兄弟姊妹個個齊全,沒有一個兇短夭亡。家裏幾輩人一看都是健健康康,端端正正,儀表堂堂,這是福,是祖上積德,做了好事啊。”
雖然我是共產黨員,不信迷信,但我覺得他説的也有道理:因為他們兩位確實都是一輩子走正道,做好事,所以子子孫孫也走正道,雖然沒有誰發了大財,當了大官,但是你坦坦蕩蕩的人,確實身心更加健康,生活更加平安。
和大舅道別後,我還在回味着他剛才的話。家裏的長輩,尤其是前幾代長輩的很多事情,我過去都不很清楚,直到七年前外公去世的時候,我要代表孫輩致辭,這才從舅舅阿姨他們那裏瞭解到了一些情況——這真已經是太晚太晚了。但僅就瞭解的這些而言,我無法不對家裏的這些長輩生出一種崇敬之情。
其實,不只是外公和老外公讓我敬佩,父親也給我講過他的父親的一個故事:
那是建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都吃不飽飯,你爺爺擔任大隊長。大隊裏有幾個幹部喜歡搞些小偷小拿,但就怕過不了你爺爺這關。有一次,我路過生產隊放花生的地方,有個幹部叫住我,往我的兩個兜裏塞滿了花生,還很關心地跟我説:“你拿回去吃,給你的爸爸一起吃!”
我當時年紀小,不懂事,就兜着花生回到家裏。結果你爺爺劈頭蓋臉就把我訓了一頓:
“這個你也拿啊?這個你拿了,我還怎麼管他們?現在這樣困難,幾個幹部還把集體的東西,你拿一點,我拿一點,大家怎麼辦?!社員怎麼辦?!你拿了多少?給我當着他們面放回去!”硬領着我當着他們的面,把花生一粒不少地放了回去。
那幾個幹部看着,簡直就像被耳光打臉一樣!
他們見你爺爺這樣硬,再也不敢亂拿集體的東西了。
父親從此把這件事記在了心裏:公家的東西,不管是財物還是職權,都要為大家服務,要珍惜、愛護,不能破壞、貪佔、濫用。
後來無論在農村、在部隊,在企業,無論是當大隊幹部,當部隊司機,搞保衞工作,還是後來擔任工會主席,他始終牢記自己是來為人民服務,為大家辦事的,而不是來多吃多佔的。他從來沒有利用手中各種便利、職權,來為自己謀取過一分錢的不正當利益。

在部隊當戰士的時候,父親曾在嘉陵江裏救起過一位溺水的戰友;
當司機出外的時候,他會耐心説服那些想拿石頭打卡車車燈的農村孩子:“小朋友,這是國家財產,好孩子就不能破壞,對不對?”
當工會主席的時候,他為很多困難職工解決了實際問題,別人要提着東西上門來感謝,他和母親一概拒絕。實在推不過的一些煙酒之類的饋贈,他都會告訴母親選擇適當的時機,用價格相當的東西送回去——既不傷別人的臉面,又不佔這些困難同志的便宜。
在父親的敍述中的爺爺,和舅舅敍述中的我的老外公並不完全相同。老外公簡直是任俠使氣,不顧一切地去幫助別人,而爺爺則對父親説:“君子固本,量力而為”,意思是説,君子並不是不要個人利益,君子也得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再去幫別人,而且要掂量好自己的斤兩,不要頭腦發熱,輕易許諾,不要勉強自己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另外,在父親他們看來,世上還有個“救急不救窮,幫弱不幫懶”的道理,你幫助別人,你扶危濟困,雪中送炭,是很應該的,但是包辦代替,胡幫亂幫,則往往事與願違,害了自己又幫不了別人,所以出錢出力是幫忙,對那些懶惰的、不思進取的人進行批評教育,促其猛醒、上進,這也是幫忙,有時還是更有意義的幫忙。
長輩們的這些敍述和教誨,對我的意義真是不可估量的。——很多時候,我甚至願意放下那些頂盔貫甲的大師鉅著,專心去聽他們講話,去吸收這些樸實而高尚的心靈所賜予我的這些寶貴財富。
大舅還曾經對我説:
我為什麼喜歡毛澤東時代?你的這些長輩為什麼哪怕捱過餓,也都喜歡毛澤東時代?其實最終也沒有什麼大道理,就是因為我們都感到:人光為自己而活着,其實是很空虛、很貧乏的。內心裏只有自己的人,是一個精神上的窮光蛋。而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思想則告訴了我們:人除了為自己活着,還可以為什麼而活着?一個有道德的人,除了愛自己,愛親人,還會愛這個世界;而一個自私的人,到最後就會連自己的親人都不愛——我就親眼看到過很多這樣的例子,有些家庭就是為了錢,分崩離析,哪有什麼親情?有的雖然沒有鬧得這麼厲害,但是其實也很畸形,歸根到底就是大家太冷漠、太自私:對別人如此,對家人同樣如此!我也反對毛澤東時代的一些極“左”的東西,我也知道那個時代的人,並不是個個都大公無私,個個都那麼先進,也有落後的,懶惰的、阿諛奉承的,貪污浪費的,搞破壞的,但起碼我知道大多數人即使沒有雷鋒焦裕祿那麼先進,至少內心是光明的,是感到很充實,很有希望的。現在,你覺得大多數人是這樣嗎?你覺得你的學生大多數是這樣嗎?

三舅則向我講過一段他下放農村時候的經歷:
我當知青的時候還不到17歲,負責給生產隊放牛,有一次放着放着我就睡着了,牛就不見了。我一覺醒來,已經太陽快落山了。這回去怎麼交代呀?我這個急呀,連忙順着牛蹄子印,翻過山去找。找到晚上,發現這牛是跑到人家農民種菜的自留地裏,把人家的菜是啃得一塌糊塗。我敲開農民家的門,人家説:“牛我們已經繫好關着了,今天天色已經晚了,山路不好走,你一個人帶着牛回去不方便,搞不好又會丟。你先在我們家吃晚飯,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把牛帶回你們知青點就是了。”人家可是一句沒有提要我賠他們損失的菜呀,而且還留我吃了一頓很客氣的晚飯,等於我的牛在人家家裏吃一頓,完了我又吃一頓。
吃完飯,我説我還是得回去,牛先放你們這兒,因為我如果一晚上不回去,知青點還有大隊裏頭都會着急的。他們見留不住我,就打着手電送我回去。
走到半路上,就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火把和手電,在喊我的名字——原來,大隊書記一發現我晚上沒回知青點,着急了:“這是人家父母的小孩,交給我們,在荒山野嶺裏不見了。萬一出了事,我們怎麼向人家父母交代?”立刻動員了上百個知青和社員上山找我…..
這個事情以後,我也沒受什麼處分,也沒叫我們賠什麼——其實損壞的菜是人家農民自留地的,是他的直接損失——農民和幹部都是叫我以後注意點就是了。
這就是我經歷的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真的是很淳樸。人與人之間,就是那樣願意互相信任和幫
助。

我記下他們説的這些,不是為了懷舊,而是在分析他們的品格和力量是從哪兒來的:
一個時代培養了一個時代的人,而一個時代的人也可以改變一個時代。不盡如人意的現實,不盡如人意的自己,都是可以改變的。但是,怎麼改變呢?這就需要我們從前輩,從歷史那裏吸取必要的智慧和力量。
記得黃克誠老將軍——他也是我們湖南的,是郴州永興人——在有人大肆否定毛澤東的時候講過:
我記得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赫魯曉夫那個秘密報告送到我們中央,中央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毛主席給我們唸了一首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王、楊、盧、駱是指唐初文壇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當時盛行駢體文,王勃《滕王閣序》、駱賓王的《討武氏檄》部是有名的駢體文。到唐朝中葉杜甫那個時代,反對駢體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寫文章罵王、楊、盧、駱。杜甫是有點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他這首詩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體裁,現在一些人輕薄地批判恥笑他們,將來你們這些人身死名滅之後,王、楊、盧、駱的文章,卻會象萬古不廢的江河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念這首詩,是針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問題。我想,這首詩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鑑,使人們注意不要以輕薄的態度來評論毛主席。
…… 毛主席逝世了,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極因素。他的消極因素是暫時起作用的東西,經過我們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們正在很有成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寶貴的財富即毛澤東思想,卻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甚至把毛主席的正確的思想、言論也拿來批判。我認為這樣做是要把中國引上危險的道路,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的詩寫得好,黃將軍的話説得更好。
其實,不光是對毛澤東那樣的巨人、偉人是如此,對經歷過歷史的每個普通人也是如此。
當我們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長輩們——不管是偉人、巨人,還是我們的父母、親人——的這些精神財富,往往會給我們以巨大的鼓舞和啓發,但是,這得我們自己去認真地傾聽、辨析,弄清楚什麼是黃老將軍説的“暫時起作用的消極的東西”,什麼是能夠“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的積極的東西。
我的長輩們是經歷過很多困難甚至苦難的,但是他們教給我的東西,或許有對有錯,卻沒有悲觀、絕望,更沒有一絲一毫的消沉怠惰、玩世不恭——這本身就是一種會永遠發光的最寶貴的品格。
特別是,我總能在這種對話與交流中,找到一條幫助我弄清“依靠誰?為了誰?我是誰?”“我應該想什麼?做什麼?”這些問題的的越來越明確的線索。
這條線索,既屬於歷史,也屬於現實,而且我相信,它決不僅僅只對我一個人有意義。
不是嗎?
已經寫得太多了,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