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天才的最後15年,全獻給這部片_風聞
第十放映室-微信公众号:dsfysweixin2018-11-19 18:10
如果“考古學”也存在於電影領域,那麼發掘電影史上的幽靈傳説,正是它的主要任務。
2014年,三位製片人,在巴黎遠郊的一處封閉倉庫中,找到了1083卷膠片。
這些保存三十多年,包含8毫米、16毫米、與35毫米不同規格底片,正是電影大師奧遜·威爾斯未完成遺作——**《風的另一邊》**的原始素材。
就如《公民凱恩》剪輯師,執導過《音樂之聲》與《西區故事》的大導演羅伯特·懷斯所言,“奧遜·威爾斯,是他遇見過最接近上帝的人。”
光用傳奇一生,早已無法概括威爾斯偉大。
他不僅改變了電影史,也是美國乃至世界文化歷史上璀璨豐碑,三座終身成就獎完全無法涵蓋他的貢獻,是空前絕後的真正巨人。
將莎士比亞視作心中聖地的奧遜·威爾斯,曾站在41街舞台上,如了不起的蓋茲比一般,渲染了自我的神話。
他向世人發問,“當我可以一人千面時,你們為何是千人一面呢?”
的確,一生都在求索與否定的聖徒,創作了42部劇本,參演了一百多部影片,而最為人熟識的導演身份下,涵蓋了近40部作品,完美主義壓力,只有12部作品為他認可,其餘未竟與遺憾之作,不勝枚舉。
1985年,70歲的威爾斯,突發心臟病猝死在打字機前。
心中念茲在茲,還是那部耗盡了他最後15年生命,卻囿於資金缺口等各種問題,只留下兩段短片,與長達一百多小時素材的《風的另一邊》。
而相比猜測這部作品是否有望重見天日,總有勇士身體力行,試圖完成大師遺願。
天才總是多災多難,《風的另一邊》從創作中途夭折,到如今修復重組,都遍嘗磨難與辛酸。
2004年,彼得·博格丹諾維奇,本片主演之一,曾透露威爾斯在臨終前要他發誓,不管自己出了什麼事,都要完成這部作品。
2012年,位於洛杉磯的Red Road Entertainment公司,試圖接手這一**“不可能的任務”**,多方協力將本片版權從其女碧翠絲·威爾斯,主演奧雅·柯達,以及伊朗與法國的兩家公司那裏協商過來。
“《風的另一邊》作為威爾斯生前最後一部電影,如果不能讓它重見天日,便永遠無法完整地理解威爾斯的電影生涯和藝術遺產。”
三年後,彼得·博格丹諾維奇再次出山,他聯合《奪寶奇兵》與《諜影重重》製片人弗蘭克·馬歇爾,開始網絡眾籌。這次本打算在威爾斯百年誕辰之際,修復本片的計劃,依然尷尬收場。
200萬美元,最終只有2859名支持者,募集到的40萬美元,還不到目標一半。
一波三折,舉步維艱,《風的另一邊》似乎身纏詛咒一般,註定無法與影迷見面。
但假若如此,王老實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裏敲敲打打。
2017年,誰都沒有想到,流媒體巨頭網飛,突然發佈一則公告——他們買下了這部遺作的版權,且將包攬一切後期剪輯修復工作。
如此高風亮節與財大氣粗,值得大大點贊。
網飛在這一關鍵節點上,承擔了巨頭應有的責任。
首席內容官的一番話,也點出一二,“像許多看威爾斯作品長大的影迷一樣,這對我們來説也是夢想成真的瞬間。能夠將奧遜·威爾斯遺作帶給世界,是Netflix的驕傲。”
於是乎,2018年11月2日,遲到近四十年的這部**《風的另一邊》**,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與之同期發行,還有一部紀錄片**《獻給奧遜的最終剪輯:40年製作歷程 》**,點點滴滴包羅整部電影修復過程。
就如奧遜·威爾斯曾借《贗品》一片,試圖打破自己的光環與自嘲一樣,《風的另一邊》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算作是一部自傳。
故事源起自威爾斯與海明威,在1937年的一次“交手”。
是的,就是交手。那時年輕的威爾斯,在酒吧與海明威偶遇,海明威則嘲笑他是個娘娘腔。於是兩人大打出手,但終又舉杯暢飲,開始了一段長達二十餘年的友誼。
之後1961年,海明威吞槍自盡,威爾斯大受觸動,毅然決然開始帶有紀念性質的電影創作——關於一位偉人之死的真相。回到好萊塢之後,故事又融入了其本人與好萊塢及新浪潮的各種恩恩怨怨。
其演員班底,如今看來似乎不可置信。
《馬耳他之鷹》導演約翰·休斯頓,飾演男一;《最後一場電影》導演彼得·博格丹諾維奇,飾演男二;其餘莉莉·帕爾默、蘇珊·斯塔絲伯格等,隨便拿出一個都是震耳欲聾般的全明星譜系。
就如處女作《公民凱恩》,歷史兜了一個圈,又回到原點。
這部電影更像是包含多重維度的個人自述:
曾經光環加身的老導演,被好萊塢冷落多年後,試圖東山再起,他誠邀數位電影新秀,包括導演、影評人與演員一同商議創作,但就在創意即將成形之時,他猝死在桌前。
就威爾斯本人來説,任何試圖對他電影進行簡單的歸納,本身就是一種妄念。這位令人難分虛實的電影魔術師,傾注最後人生都無法完成的絕響,後人想要復原,近乎痴人説夢。
要從這一千多卷膠片,以及大量的手稿筆記中,梳理出威爾斯的原意,首先就是令人焦頭爛額的分類歸檔。
所有原始素材,都要先進行4K掃描,然後重新剪輯,再完成配樂。這本身就是鉅額的工作量。
光是面對這整面牆的底片,就算最資深的電影人,也會頭皮發麻。
就像於深海打撈沉船,工作人員並不知道自己會在這座素材山中發現什麼。
每打開一盒底片,就像啓封一隻寶箱,而他們的參照物,除了盒上的潦草編號,就是手寫於40年前的一份古老清單。
他們還得回到古老的工作方式中去,像不存在數字電影時一樣,在放大鏡下,一格一格觀察膠片。
剪輯師莫亨利,承擔了這一重任,她是少數還在從事膠片剪輯工作的人之一,第一部作品,就是《大白鯊》。
這些膠片,無一例外要按照數字標號順序組合,再一一粘貼在導片上,進入數字掃描前,所有工作都只能在這些老式設備上完成。
不幸中萬幸,原始素材保存完好,掃描工作進展也較為順利。
但萬里長征這隻算第一步,團隊還得依靠當事人的回憶與字條來重塑故事。
工作組,不僅要從這無數遺物中發現威爾斯的真實目的,還要深刻理解他看待剪輯的態度,才能最大程度上接近原有意圖。
這不僅要求他們閲讀所有關於威爾斯的書籍,甚至連書信筆記乃至便籤都不能遺落,如此才能深入他的腦海。
甚至在便覽數次素材之餘,生髮出更多困惑,“它是一部電影嗎?”
威爾斯曾説,《風的另一邊》像是一幅帶邊框的畫,它是電影中的電影,從不同的角度距離欣賞,將呈現不同的多元維度。
這一令人難以捉摸的描述,暗示了威爾斯本人對真實與虛構的曖昧態度。
銀幕中那些混雜紀錄片,電視節目與現場學生攝像機中的片段而組合成的聚會,如一場戲中戲,干擾着觀眾的判斷。多種類型膠片的混雜運用,還間接譏諷了安東尼奧尼的新浪潮風格。
在劃時代的《公民凱恩》中,一條尋找玫瑰花蕊的主線貫穿了主人公人生始終。
而本片開始就以老導演的神秘死亡進入高潮,各色圈中人等,來來回回出現,如同一場舞會,拼湊出破碎與瘋狂的幻夢,在諷刺好萊塢式敍事之餘,一場狂歡隨之上演。
人工智能的參與,出乎意料解決了很多麻煩,能夠識別人眼興趣點的AI介入,在比較了兩萬億幀的畫面後,在三天之內,就完成了人類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而合成語音的技術,也讓大多數已經去世的演員,得以在片中原聲重現。同時,奧斯卡作曲家,米切爾·萊格蘭德主導了編曲創作,他曾經也是威爾斯紀錄片《贗品》的御用配樂。
那是威爾斯所生活年代並不具有的便利,也是這部電影最終得以完成的關鍵助力。
在原片中,我們也能從老導演的資金困境,窺見威爾斯纏繞一生的掣肘。
電影的拍攝過程中,製片被指控私吞預算,作為投資人的伊朗國王的妹夫,中途撤資還捲走底片,成就電影發展的工業制,也在時刻傾軋着創作者本身。
使至於此,我們的確無法斷定,這部終於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水落石出”的遺作,到底能夠重現多少奧遜·威爾斯的偉大。
我們也難以找到一個所謂真兇,把對天才的種種磨難,歸咎於其上。就如特呂弗説,“那些‘導’他的,都是一些才華還不及他十分之一的導演”。
但這些由凌亂破碎的過往,所拼湊而成的支離歷史,似乎更可能接近威爾斯在往日傑作中一以貫之的預言——
一個被拋棄被捧殺又被拾起的悲情天才,也許並不需要一個足夠完美的終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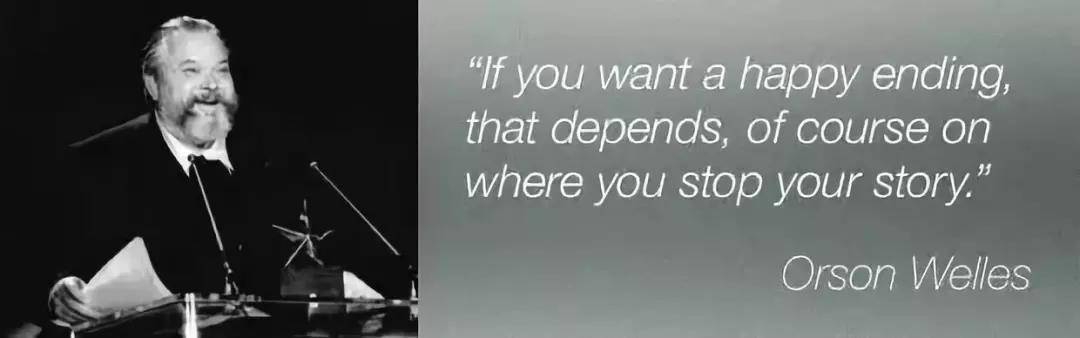
該原創文章首發於微信公眾號: 第十放映室(ID:dsfysweixin)
如需轉載請聯繫微信ID:dsfysweixin,微信搜索關注:第十放映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