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遊戲進化史:金庸的武俠世界在遊戲中重現了嗎?_風聞
一颗土逗-tootopia.me2018-11-19 15:56

遊戲《天龍八部》壁紙
摘要:“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説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這是金庸對武俠小説的期許,但在如今以金庸小説為題材的武俠遊戲中,卻少見對現實的批判。武俠遊戲隨着時代不斷“進化”,鋤強扶俠客精神淡出視野,取而代之的是競爭性邏輯。
十月三十日,一代宗師金庸先生駕鶴西歸,永遠離開了他創造的那個波瀾壯闊的武俠世界。
所謂“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説在上世紀的經久不衰,促成一大批武俠小説家走入了讀者的視野,卻唯有金庸的作品寓意深刻且蕩氣迴腸,透露出大師獨備的史識、政見、學養與大氣象。難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説卷)重釋中國文學史時,將金庸排定於第四的座次,只是“大師”謙遜,忙稱“萬萬不敢當”。如今,金庸先生“悄然離去”,或許武俠世界從此再無照亮前行的燈塔,萬千俠客就要迷失在茫茫永夜中。
金庸與遊戲
在讀圖時代,金庸的作品如僅限於文字,就未免太可惜。所幸在文學之外,金庸的小説還廣泛地吸納了戲劇、電影等新文藝媒體的長處,不僅有益於影視劇的翻拍,更被譽為“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有鑑於此,金庸的小説成為歷史上最熱銷的IP,並被不斷改編成電影、電視,甚至是青年人最喜愛的遊戲,就不足為奇了。
一般説來,大家應是對金庸題材的影視劇比較熟悉,而關於金庸題材的遊戲則少有見聞。事實上,金庸遊戲早已蔚為大觀,除去端遊、頁遊、手遊等較難清楚統計數目的遊戲,單論那些曾發售實體的PC及主機遊戲,直接改編自金庸小説的遊戲已不下30部。如再算上其他暗中截取金庸故事橋段的遊戲,道斷金庸小説可佔武俠遊戲的半壁江山,也不為過。

《笑傲江湖》系列遊戲
其中又數《笑傲江湖》最受青睞,已改編不下七次:既有智冠在93年的開山之作,亦有昱泉在00年代初發行《笑傲江湖》三部曲的繼興之舉,甚至不乏外星科技與南晶科技這兩家“著名”遊戲公司的“迷之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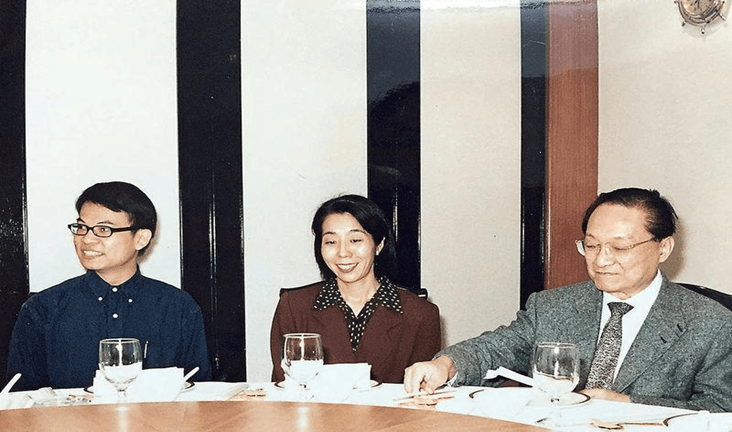
中為岡崎由美老師
當然,金庸的影響力絕不限於華語地區,“遊戲宗主國”日本也曾發行金庸題材的遊戲。1996年,日本早稻田大學岡崎由美教授翻譯《書劍恩仇錄》,同時着手在日本系統譯介金庸及中國的武俠小説。在此脈絡下,索尼娛樂為了打開中國遊戲市場,也曾於2000年推出《射鵰英雄傳》,是為金庸遊戲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開端。
金庸遊戲≠金庸小説
金庸遊戲受熱捧,自是美事一樁。可是,看金庸的小説與玩金庸的遊戲是一回事嗎?
顯然不是。
金庸小説最突出的特點即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説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所以相較其他作為純粹“娛樂性讀物”的武俠小説,金庸不少的作品皆有影射與反諷現實之意——他白天辦報寫政論,夜晚就把政見丟進武俠世界裏。
但金庸遊戲似乎難見這樣的現實介入性。這一方面與遊戲只是掛名金庸,並非真由金庸主導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遊戲媒介緩慢的成熟與被認識過程也限制了現實介入與介入現實的可能。
這是因為遊戲中的現實不同於小説,在小説中,現實被提煉成文字,寄居在文本里,讀者通過閲讀即可生成體驗,由此感悟現實。而在遊戲中則要複雜一些。雖然遊戲文本也指涉了遊戲外的意義系統——例如,遊戲《倚天屠龍記》中的道具“鐵叉”,它表面含義是遊戲程序裏的“鐵叉”DOS圖,深層含義則是現實經驗系統裏的“鐵叉”——但遊戲獨特的現實(感)卻不主要建構在圖形(“鐵叉”)之上,而在於圖形(“鐵叉”)的功能及其運用,即玩家操控鼠鍵完成目標設定(捕到遊戲中的“魚”)的過程裏。
換言之,遊戲中的現實(感)寄居於連接遊戲程序與現實經驗的遊戲行為中(這就可以解釋,何以我們玩過一款金庸遊戲後,糾纏我們的往往不是壯烈宏大的金庸故事,而是那些瑣碎的戰鬥/操作系統,比如遊戲中不勝其煩的迷宮)。

遊戲《倚天屠龍記》
如此看來,遊戲現實主義的方法論當然就不同於傳統文化媒介,除非現實關懷可以進入微觀的交互層(預設的遊戲行為),否則就無法真正形成介入。在這樣的認識脈絡中,金庸遊戲自然無法與金庸小説相提並論,它不過是“娛樂性的玩物”,與普通的武俠遊戲拉不開本應有的距離。
抵抗的媒介:武俠遊戲的意義
自《俠客英雄傳》首開遊戲世界武俠之風以來,PC平台公開商業發行的武俠遊戲少説也有86部。雖然大部分無法稱為精品,但也不乏《金庸羣俠傳》、《劍俠情緣》、《雨血》系列、《太吾繪卷》這樣的佳作問世。

那麼,何以武俠遊戲經久不衰?其內在邏輯仍是“讀者”熱愛那個英雄輩出的武俠世界嗎?
顯然不是。
遊戲的時代已不同於小説的時代,**玩家非是要藉助武俠遊戲來做心理按摩,武俠遊戲似也無意繼承武俠小説可以表達對現實不滿的功能。**事實上,現代化的生活現實及其理念也早已改寫遊戲一代的想象力,大概少有人幻想現實中的制度性壓迫須藉由手持冷兵器的俠客來推翻吧?
與其説遊戲一代痴迷的是俠肝義膽、快意恩仇的武俠傳説,毋寧説是他們對被現代化經驗打斷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發出的本能式好奇(當然悖論是,滿足這種好奇的遊戲程序正是現代化的最佳代表)。於是大部分喜愛武俠遊戲的玩家,往往也對奇幻、魔幻、玄幻、仙俠等古裝類遊戲保持着同樣的好奇心,甚至未有意識到分清它們之間差異的必要性。
可即便如此,仍應對武俠遊戲予以特別褒揚。因為在這一眾古裝遊戲裏,唯有武俠遊戲還稱得上是中國傳統文藝思想的“自留地”,它們在日美青年亞文化崛起並深度整合在地文藝思想資源的語境下,至少還能從形式上堅守與傳統的聯繫,努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同時,令無數中國玩家接觸到傳承千年的本國通俗文藝思想,並對它們保持好奇。而反觀其他古裝遊戲,已多是混淆視聽的中西日文化混成物,模糊了玩家本來的文化感覺。
正是在如此文化脈絡下,無論武俠遊戲質量如何,它的實踐都值得肯定。當然,這種肯定不單針對文藝思想本身,還指向實踐的策略與方法論。
熟悉早期武俠遊戲的玩家一定知道,在中華遊戲起步期裏,不少武俠遊戲巧妙地利用了遊戲獨特的媒介性,以“畫皮”的方式,將原本表現異國情調的遊戲設計徵為己用,這不失為對內置霸權結構的遊戲文化全球化的反諷,也構成了中華遊戲的鬥爭策略。
例如,1991年台灣精訊公司發售的全球首款武俠遊戲《俠客英雄傳》,它即徵用了日本國民遊戲《勇者鬥惡龍》的遊戲系統,將日西結合的奇幻冒險改編為懲惡鋤奸、拯救蒼生的中式俠義傳説,在日式RPG(JPRG)壟斷東亞市場的90年代,艱難地發出了中國俠客的聲音。

遊戲《俠客英雄傳》
這就構成了數字時代的文藝鬥爭策略,雖然鬥爭的初心多源於市場動機,並非主要是文藝目的,但經濟鬥爭附帶的文藝效果仍是顯而易見的——遊戲市場裏至少還能找出中國式的“通俗遊戲”,而非全然由日美“文化殖民”,中國的通俗文藝思想因而在形式上可以在遊戲這樣的最新文藝媒介中得以保存與延續。
換言之,我們在窘況中留住了通俗文藝的根。
時代文化結構:從“俠”到“爭”
“畫皮”策略雖然奏效,但其缺陷亦很明顯——即使遊戲元素是中國風、遊戲故事是“俠客行”,但在文化意義更為深遠卻極隱蔽的交互層,早期武俠遊戲只能仿製日美經驗(主要是日本),“借用”它們的界面、排版、系統架構、關卡設定等設計,長此以往,難免潛移默化地“污染”本是希望親近中國傳統的遊戲玩家之審美趣味、思維方式、想象力結構等等主體性要素。
幸好在華語地區近30年的努力下,上述弊端隨着一批優秀武俠作品的問世而得以一定程度的克服,但似乎又掉入另一自設的陷阱中。即隨着多人遊戲在2000年代以來成為主流遊戲模式,以及這些遊戲在2010年代全面朝向“爭”的“文藝”結構轉型,武俠遊戲也不可避免地在市場原理的牽制與鼓動下,將“爭”作為核心結構,朝向多人遊戲方向發展的同時,失掉了自身的特點。
這裏所謂“爭”,它有別於武,是一種時代無意識,或者説當下中國社會共通的感覺結構。但在解釋“爭”之前,有必要先點破“武俠”中原本的“武”與“俠”。
一般説來,“武”即武俠小説中的武技,它構成了武俠小説的外形。按理説,既然是武俠小説,作者須要精通武理。然正如梁羽生(化名佟碩之)所言,真正懂得武技的作家,恐怕是鳳毛麟角,所以包括金庸在內的“新派武俠小説家”後來才不自覺地走向描寫有些“神怪”的武功招式,比如段譽的六脈神劍可以劍氣制人。
既然武俠小説沒有建立授受武學的傳統,那麼自然就沒有理由責難武俠遊戲為何亂打一氣。不過,武俠小説還是起頭了一些好的傳統,比如“俠”。在梁羽生看來,“‘俠’是靈魂,‘武’是軀殼”,武俠小説裏,“俠”應比“武”重要,因而得到大力渲染。
可伴隨武俠遊戲從文學文本(單機遊戲)向算學文本[1](多人遊戲)“升級”,武俠遊戲也因之走入有“武”無“俠”的悖論。這是由於算學文本使用的是數字語言,而非傳統媒介慣用的文字或圖形語言,其基本敍事規則是利用遊戲裝備的數字(秩序)引起算學敍事。

某金庸題材手遊
而所謂算學敍事,其內容也很簡單——遊戲者為了爭取更高的(裝備)數字而發生爭鬥。比如,手持100點攻擊力倚天劍的遊戲者A,自然勝過掌握90點攻擊力屠龍刀的遊戲者B,而B為了改變自己在這數字秩序中的不利位置,必然試圖獲得攻擊力超過100點的破天一劍。如此循環往復,遊戲體驗因為這些數字而被調動起來,玩家因此引捲入“自然”流動的數字文法中,相互爭鬥。

某金庸題材網遊的裝備評分排行榜
由此可見,算學文本類型的武俠遊戲並不指向農業文明裏誕生的遊俠精神,不真正提倡鋤強扶弱、救助底層的文藝思想(有趣的是,一般遊戲設定其實是拒絕遊戲者協助陌生人的。比如在遊戲中幫助陌生人打怪的嘗試,反而會變成與陌生人爭搶獵物,引發鬥毆),而是配合資本增殖的需要,生產適合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爭鬥邏輯:競爭意識、工具理性、市場化的叢林法則、數字身份壓迫,等等。
這就意味着,如今的武俠遊戲已蜕變為反對“武俠”的武俠遊戲。它們在取消“俠”的精神同時,還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生產關於“爭”的認識論與新主體,遊戲者因此被改寫成配合0/1代碼結構的只關心自我的成功者/失敗者。
當然,我並不認為“爭”就是武俠遊戲或者遊戲獨有的文化結構,它更是時代無意識的縮影——大衞・哈維所謂“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的大眾文娛,正朝着“競爭性娛樂”的方向深刻轉型,例如當下最能動員年輕人情感的娛樂方式或多或少都呈現出“爭”的氣質與結構——搶紅包、宮鬥劇、《中國好聲音》、電子競技與觀看電子競技,等等。
那麼,正在盛行的“爭”文化,究竟會把我們引向何處?這或許將會成為未來遊戲批評,乃至文化批評必須持續反思的問題。
註釋:
[1]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詳細闡釋算學文本理論,部分論述可參見鄧劍:
「遊戲勞動及其主體詢喚——以《王者榮耀》為線索」、『중어중문학』、2017년、제70집。
鄧劍,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生,研究興趣為遊戲批評、東亞青年文化
本文及封面圖首發於一顆土逗,轉載請聯繫土逗獲得內容授權。
作者:鄧劍
編輯:Targaryen
美編:太子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