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高布蘭的驚豔畢設:五分鐘動畫版「黑鏡」反思虛擬與真實_風聞
动画学术趴-动画学术趴官方账号-2018-11-29 11:01
公眾號:動畫學術趴/babblers
文/沈毅

這部作品的創作靈感,來源於作者在國外的一次被搶劫的經歷。
隨着社交媒體的興起,手機幾乎成為所有人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我們沉溺於網絡中的虛擬世界,與手機朝夕相處,從虛擬中收穫“滿足”,但這樣的我們真的是幸福嗎?
今天,小趴要給大家推薦一部來自法國高布蘭的畢設動畫——《Best Friend》。
這部動畫短片在YouTube上線剛剛兩週,就已經獲得120萬的點擊量,《水形物語》導演吉爾莫·德爾·託羅(Guillermo del Toro)還在推特上轉發了這部作品。
動畫中對科技的思考,反烏托邦式的世界觀,與著名的英劇《黑鏡》殊途同歸。
在這個由“Best Friend”創造的虛假世界裏,人們得到的到底是幸福還是寂寞呢?一起在這部動畫短片中尋找答案吧!
温馨提示!觀看時請一定要戴上耳機!
雖然各大網站上已經有很多搬運工發佈的視頻,但此次沈毅導演在學術趴公佈的這一版本是團隊成員精心製作的Binaural Mix版,使用耳機****,****會給你帶來不一樣的體驗哦!!
— 導演介紹 —
沈毅
微博@DA-SHEN
2008-2012 中央美術學院附中
2012-2016 北京電影學院動畫藝術
2016-2018 法國高布蘭影像學院動畫研究生
2017-2018 法國高布蘭影像學院暑期班動畫老師
2017 倫敦Nexus工作室實習,藝術導演/分鏡師
現為旅法自由職業者
實際上,沈毅在此之前已經參與制作過多部動畫短片作品。
他曾聯合導演了2016法國昂西動畫片頭**《紅磨坊》和2017高布蘭短片《Morning Coffee》,同時也是英國BBC2018冬奧會開幕動畫《The Frealess Are Here》**的藝術導演與分鏡師。
英國BBC2018冬奧會開幕動畫《The Frealess Are Here》
這次,《Best Friend》的創作歷程又給他帶來哪些突破與成長呢?一起了跟隨導演的創作自述以及學術趴的專訪瞭解一下吧!
— 創作自述 —
多數人很難接受自己的生活秩序只是虛構的想象,但事實是我們從出生就已經置身於這種想象之中,而且連我們的慾望也深受其影響。於是,個人慾望也就成為虛構秩序最強大的守護者。 ——尤瓦爾·赫拉利 《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
記得幾年還在讀本科的時候我在網上看過這樣一部短片,記錄了一位服刑44年剛出獄的美國老人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反應,與他對現在世界的看法。
這種跳脱的錯置感讓我特別着迷——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當下世界,對硬生生地被拽進其中的他來説,已然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未來。
2016年,機緣巧合之下我有幸來到高布蘭參與那年為期6個月的昂西動畫節的片頭動畫製作。當時剛到巴黎的我英語法語都不會,手機理所應當成了我當時應對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久而久之,通過手機我逐漸適應了新的環境,半年的生活也即將告一段落。
一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3個黑人上來搭話。雖然聽不懂法語,但我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麼。當時我腦子一頓翻滾,隨身的包裏除了錢包和一些零碎的東西,最重要的是有本兩年來記錄我各種想法和畫稿的本子。我拔腿就往反方向跑,卻還是被他們摁在了地上。他們一人壓着我試圖搶我懷裏的包,另外兩人在旁一個勁往我口袋裏掏。凌晨3點的街上一個人也沒有。
我雙手緊緊揪着包,不停在地上拉扯掙扎着踹他們。中間的那人給了我臉上一拳,我那時才看清他的樣子——不同於電影裏惡人慣有的神情,在我眼前的竟是一張跟我年齡相仿,恐懼而慌張的臉。
他拽着我的衣領,用蹩腳的英語不停地喊:“你的手機!!拜託了!拜託了!你的手機!拜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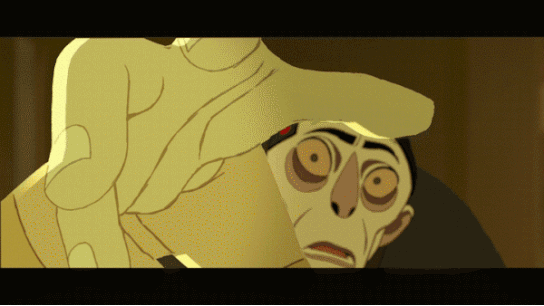
恐嚇,也好像是哀求,我現在還説不清那到底是一種什麼眼神。我楞了一下,但任然不停掙扎。不一會兒,3人搶走了我的手機和包,隨即起身向不同方向跑去。我爬起來狂追搶我包的那個人,從來沒有跑的那麼快過。可是一個拐角,那人便不見了蹤影。
一切發生得太快了,整條街一片死寂,只聽得見自己站在原地的喘氣聲。我看着因在地上掙扎磨破了皮而流血的雙手,無法抑制心中的暴怒。十分慶幸的是,我記得回家的路,鑰匙護照也都在。
無論是衣食住行,國內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與微信為首的app綁定在一塊,只要是有手機的人都能享受全天24小時的聯網服務。兩天之後照計劃回國的我,突然發現身邊的世界在我手機沒了之後變得不怎麼友好。我感受到了另外一種錯置感——只是丟了個手機,我的生活節奏竟像是被扯回到了好幾年前。
後來左手無名指破皮的地方結了一道疤,每次看到這個疤的時候眼前總時不時浮現那張驚恐而無奈的臉。而這道疤後來也成了片中Arthur的印記。
手機,在當今幾乎快成為一個為人的基本前提。
與我們朝夕相處的不是我們的親人,朋友或愛人,而是手機。當遇到任何問題時,我們下意識的動作也總是拿起手機。我們對他人永遠無法做到絕對的坦誠與信任,對手機卻可以。我們無時無刻都在用提供個人信息的方式來換得更多的便利。手機早已比任何人都瞭解我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手機比我們自己都瞭解自己。我們把自己的一部分儲存在手機裏,也讓手機成為了自己的一部分。
而手機也僅僅只是當今最普遍的一種載體,由互聯網數據餵養的AI及更多種種的高科技正進一步與我們發生關係。這種關係對上一輩的人們來説,可能是需要花更多時間來去適應的挑戰,或根本是可有可無玩物喪志的擺設;單對下一輩人來説,可能就像是空氣和水電一樣的天經地義。**而作為在20世紀末出生的我們,將會是最後一輩在沒有手機和WIFI的童年裏成長起來的人。**我們生活的當下特別像是各種科幻小説和電影中的前史階段,任何一種未來的可能性都近在咫尺。
Best Friend最開始的雛形(中文水平極度退化請大家見諒)
近未來,“Best Friend” 取代了電腦、手機和各種穿戴式設備,成為了新生代人類生活中的必需品。除了整合了之前產品的所有功能之外,還能創造只為你服務並且只有你能看見的“最佳好友”。有社交恐懼的主人公沉浸在自己創造的完美世界裏,開心成癮。
2017年7月初,班裏同學在昂西動畫節開始之前自發組織了一場畢設開題會,以討論初步的分組問題。我拿着這個最初的概念找上了Julianna和Nicholas,他們剛好也想做科幻,我們一拍即合。開學後,隨着Varun的加入我們終於開始了頭腦風暴。
大家討論劇本的過程
一説到科幻,大家滿腦子充斥的全是經典小説、電影和劇集,特別容易先入為主。我們想要避開雷同而在構建世界觀上有所創新,卻陷入了為不同而不同的怪圈。標新立異確實很吸引人,但是如果連我們自己都打動不了的話一切都毫無意義。而且科幻題材對於一部動畫短片來講,無論從體量和製作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與其花5分鐘做一個滿是字幕的動態PPT來解釋一個自以為恢弘獨特的編年史,我們更希望創造一個代入感強的世界,來講述一個小人物在其中的煩惱。
前期我對於世界觀的想法
我們在片中想關注的是在特定情境中人如何與自己相處的問題。而這個“特定情境”取決於Best Friend是怎樣的一款產品。多次討論後,我們決定在世界觀構建上一切從簡,以進一步完善Best Friend的產品概念來展開劇本創作。在反覆交流的過程中我們得到很多啓發,結合同時進行的素材收集,我們不斷推進故事。一切似乎進行得很順利。
直到10月《銀翼殺手2049》在法國上映,我們4個從電影院出來後互相對視。Best Friend的概念與片中的Joy高度重合,****而我們第一版劇本的結局更是與片中的一場戲幾乎一模一樣。(空無一人的街上,一個巨大的Cami從全息的廣告牌裏走出來,對着剛被搶去Best Friend的Arthur不斷重複着:“Best Friend,永不孤單。”)
組員們有點動搖Best Friend的整體設定,不想讓片子因此而背上“抄襲”的誤解。我卻不這麼認為——首先Best Friend作為產品並不完美,所有的角色是根據不同用户的喜好和上傳的個人數據而設定。其實質只是高級可視化的聊天機器人罷了,並沒有自我意識。與現在的手機一樣,Best Friend對有些人來説只是應對生活的工具,對有些人來説則是實現自我逃避的完美毒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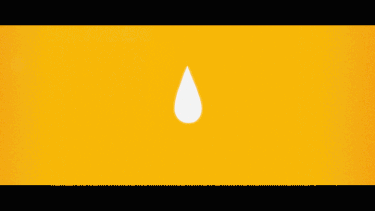
還在尋找更好的朋友麼?
現在,我們可以給你最好的
一款只有你能看見的朋友
Best Friend,永不孤單
這是在劇本成型之前就一直迴盪在我耳邊的廣告語。
帶着這個想法,我幾乎問了遍全班同學:如果現在有Best Friend,你會創造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班21個人,來自世界上17個不同國家和地區,從21歲到28歲不等。對我來説,這是一個完美的調查對象人羣。我得到的答案除了有自己、母親、不説話的豬、會飛的貓、噴火的金色獅子、漂浮的圓圈之外,還有很多不能播的東西(自行腦補)。
只對自己可見,Best Friend自然成了人內心世界的反映。所有片中出現的虛擬朋友其實是我們手機上各類app的外化表現:郵箱、遊戲、相機、音樂、天氣、社交媒體與各種來自電影遊戲虛擬世界的角色。這是第一層。
我做的前期設定
而作為Arthur內心深層所缺失的核心,我們從來都不想把Cami做成像《銀翼殺手》裏的Joy一樣,只是直男心中物化女性的性幻想工具。因為Arthur真正需要的,只是希望身邊能有一個聽他傾訴抱怨,並時刻給他鼓勵的朋友罷了。所以Cami不能性感,而必須是活潑開朗特別討人喜歡的那種可愛形象。Best Friend並不完美,是Arthur選擇相信自己創造的CAMI是完美的。
但沒人會關心你所有的這些過程和原因,**儘管我們保留了原有的設定,但還是必須改結尾。**這讓我們一下變得十分被動,想出好多不同版本結局卻誰都沒法説服誰。在一次次的相互推翻、質疑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自身對文本認知的侷限性。這時,David的加入讓我們有了新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也更加堅定了我們原本的方向。我們並不是要提倡反科技——造成任何一種反烏托邦未來的原因永遠不會是科技的問題,而只會是人自身的問題。我們試圖拿掉所有能讓Arthur開脱的藉口,讓他自己一步步深陷進去,最終選擇繼續快樂地活在自己編織的謊言裏。
我自知這個結局從類型片劇作角度看可能漏洞百出又不夠有張力,但我們想要塑造的Arthur從來都不是舉旗反抗體制的虛構英雄,而是像我們一樣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孤獨的普通人。對於大多數人來説在今天要是丟了智能手機,除了再補一個我們還有其他選擇麼?Arthur會有其他的選擇麼?在前期構想的時候深受尤瓦爾·赫拉利的“毒害”,索性就再引用他書裏的一句話作為結尾吧。
人們之所以不願改變,是因為害怕未知。但歷史唯一不變的事實,就是一切都會改變。
— 個人專訪 —
**學術趴:**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團隊分工是怎樣的?
**沈毅:**首先鄭重介紹一下我的組員。
來自巴西的Juliana經驗豐富,是我們班最好的動畫師;來自意大利的Nicholas跟我志趣相投,無論角色設計還是場景設計他都能獨當一面;來自印度的Varun是我們班特別搶手的概念設計師,擁有人肉打印機般的效率和質量,之前在美國Blue Sky動畫工作室實習過;來自西班牙的David是之前跟我一起做《Morning Coffee》的同學,互相對彼此的工作節奏很熟悉。
組員的個人網站,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我們
前期我主管故事版與動態分鏡,Juliana幫忙輔助。Layout階段是Juliana和我做Posing Layout,Varun、Nicholas和David做BG Layout。
Juliana是動畫指導,她將工作量平分成3份(她,David和我)。除了每人近30個鏡頭要完成之外,Juliana把握全片動畫節奏,我負責修改每個鏡頭的人物動作與形態,David負責所有屏幕裏的Motion
Graphic,片頭片尾字幕。與此同時Varun和Nicholas在全速畫背景,之後提前完成任務的他們被我們拽來清線與上色。當然了,除了我們5個人還少不了20個志願軍在動畫上的支持。其中包括高布蘭一年級的4個同學,幾乎一半3年級國際班的同學,再加上一個愛爾蘭交換生,兩個往屆學姐和之前在倫敦實習認識的朋友。這裏真的要特別特別感謝他們的幫助,沒有他們的話我們是絕對完成不了所有鏡頭的。
後期特效與調色由Varun主導,David輔助。我與Juliana幾乎是不斷地在收拾動畫一直到最後,Nicholas機動性比較強基本就是到處救火。
學術趴:團隊成員來自不同的國家,在合作過程中有沒有因為不同文化背景而在創作理念上產生分歧?不同文化的碰撞又給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沈毅:**先説融合吧。想要5個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瞭解是第一步。剛開始的前兩週我們大多是在咖啡廳,學校樓梯的轉角里聊天度過的。談話間,我們找到了很多的共通點——大家在各自國家生活時竟然都有跟我一樣被搶的經歷,每個人都在Arthur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不同文化融合最直接在片中體現的兩個例子:Cami的名字來源於意大利文的Amica,是女性朋友的意思;Arthur一人在家陶醉地站在沙發上唱歌嘶吼自然來源於中國源遠流長的KTV文化,也包含了我兩年沒機會回國唱K的怨念。
高布蘭的團隊合作是每個人都是導演,同時也就意味着你每做一個決定都要經過大家的同意。分歧肯定是常態,但這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我最大的心得是交流一定要直接,有什麼想法最好在當下説出來。在這個典型的歐洲低效率民主的規則下,這樣的溝通方式讓我們省去了大量的時間成本。特別是進了中期製作後,巨大的工作量和deadline的壓力下我們連出錯調整的時間都沒有,只能不斷推進。所以每週我們至少會有2次全體會議,每次只有一個小時。
這招對於我們組非常管用。每個人先展示這幾天的成果,然後大家輪流提意見: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為什麼。如果我想推翻一個點子而不給出替代方案的話,是説服不了另外4個人的。**直接是出於對組員的相互信任,理性是則最基本的尊重。**我們經常會爭執,但不是試圖證明我的感性的審美比其他人好,而是逼着自己、逼着對方理性地去找怎樣才是對片子最好的選擇。不是你想要通過這個片子自我實現什麼,而是你願意為這部片子犧牲什麼。
學術趴:《best friend》的美術風格是如何確定的?
**沈毅:**美術主要是Nicholas、Varun和我3人確定下來的。整體的大方向上我們一開始就達成了共識——我們都特別喜歡60年代的科幻風格,深受意大利設計師Joe Colombo的啓發。最花時間的是研究如何將信息點有效的分佈與擺放,其實是不斷反問自己對於我們創造的這個世界究竟瞭解多少的過程。雖然我們三個人的風格迥異,但好在片子裏需要設計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所以我們每人在不斷地磨合中都必須主要負責一方面的設計。
Varun主要負責場景設定與色指定:
黃色是一個看似十分温暖的顏色,但同時也能給你一種病態的壓抑。
這是Best Friend產品的顏色,同時也是本片的主要基調
我主要負責男主Arthur和劫犯的角色設計:
想要在影片一開頭就體現Arthur長期過度使用Best Friend,眼袋的設計是重點。另外溜肩駝背也是想讓他看起來就是那種弱不禁風不討人喜歡的樣子。結果畫着畫着,班裏同學都問我為什麼要天天畫自己……
Best Friend的世界裏可能只存在兩種人,沉浸在其中的和想要沉浸在其中的。片中搶去男主Best Friend的人就是後者。我不想把他簡單地歸類為搶劫犯,下面就稱他為R吧。
作為社會底層,深陷Best
Friend世界中無法自拔的R必須以不擇手段的方式來維持短暫的夢境。額頭兩邊的疤就是證據,也是他與Arthur的聯繫——他們其實都是孤獨的受害者。換句話説,Arthur可能是R墮落前的過去,而R也可能是Arthur未來將會變成的樣子。所以R人設上我是對照着Arthur來做的。
Nicholas主要負責Cami、所有虛擬朋友與在片中出現的路人設定:
後來加入的David負責片中的廣告與最終LOGO與產品界面的設計:
學術趴:畢設製作過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經歷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沈毅:**雖然是個門外漢,但聲音和音樂對影片敍事的重要性讓我一直特別着迷。在高布蘭做的這幾個片子中我都有幸參與了這方面的製作過程,這次印象尤為深刻。
本片的編曲和音樂製作是由朋友Arthur Dairaine Andrianaivo完成的。他是剛從巴黎Jean-Michel Bernard音樂學院畢業的大神。影片的整體配樂我們決定避開那些高辨識度的樂器並降低旋律性來與聲音設計揉在一塊。這正是他最拿手的地方。
Best Friend的主題曲方面,我在故事版剛開始的時候發給他一首皇后樂隊的歌《Friends will be friends》來作為參考樣本。可每次他給的小樣都很高大上,但怎麼都不對。後來我們索性決定做一首九十年代風格的KTV必點洗腦神曲,並在出片名的時候同時能聽到“Best
Friend”。所以歌詞要夠直接,編曲要夠簡單。我們前後碰了不下10次,一共做了6版旋律,每次我們都絞盡腦汁想怎麼樣能做得再矯情一點,整個過程特別有意思。最終的歌詞是我和他一起寫的,我蹩腳的英語一下讓這首歌明顯變得惡俗起來,直到現在每次聽我都不禁起雞皮疙瘩。
聲音設計方面則是我們老師Nadege Feyrit負責的。每年昂西開幕短片的聲音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她掌控,也參與過很多科幻片的聲音製作。
聲音設計對於本片來説尤為重要——Best
Friend作為芯片植入太陽穴以連接大腦,只有你能看到,其實也只有你能聽到。滿電時,聽覺像是包裹了層濾鏡一樣,降低了對正常世界的感知,在耳邊縈繞的是歡快的音樂和虛擬朋友的卡通音效,而且聲音來源是從Arthur內部發出來的。當程序暫停時,我們才能感受到現實世界的聲音從外部傳來。而到了最後Arthur在失去Best Friend的情況下,鬧市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向無序地他撲來。
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從擬音、做動效到最後混音都至少比其他組多花了一倍的時間。我和Nicholas負責最後的把關,一遍一遍地檢查,不斷提要求,最後都快把混音師逼瘋了。
記得最後我和Nicholas從混音棚裏出來是凌晨4點,而我們在棚裏足足待了12個小時
《Best Friend》在11月4日就在YouTube和Vimeo上線,所以國內網上早就能看到很多搬運工版本。**但這次我發在動畫學術趴的版本在音效上有質的不同,是Nadege這段時間專門針對移動端平台自願做的一版Binaural Mix。目的是為了給全片的聲音製造一些空間變化——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不妨試試找個安靜的地方戴上耳機再看一遍《Best Friend》,**你會感覺到Cami的聲源其實是從你後腦勺的位置發出的。這種感官效果只作用於耳機,公放或接影響是感受不到的。
需要注意的是,Binaural
Mix通常在高音調中聲音效果更好,而Cami的聲音屬於中高音,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環繞效果不是非常顯着。雖然不完美,但這是整個聲音團隊日夜創作的結晶,也是在影院之外我們能給大家在聽覺感官上最接近Best Friend的體驗了。
學術趴:本科畢業之後選擇去高布蘭留學,到如今留在巴黎從事自由職業,法國的動畫環境,包括學校教育、行業發展等給你帶來哪些不一樣的感受?
**沈毅:**我才來不過3年又只會説英語,沒辦法客觀地從行業大環境等等的角度回答,只能特別片面地説説主觀的感受。
最大的感受就是對於多元的認同。我這幾年接觸的朋友中,並不是每個人天天想着當導演攬項目掙大錢進軍奧斯卡。這裏沒有一個單一的成功標準,也沒有人高談闊論狼性。身邊很多在行業裏已經很有成就的法國朋友也是天天坐地鐵,好像只要做着自己喜歡的事還能夠因此掙點錢,他們就很開心了。這對於很多人來説是不求上進沒出息,但對於多元認同的背後,我看到了法國人對自己文化與行業的驕傲和底氣——有時甚至是過於有底氣,但這種不建立在外在社會認同的安全感對我個人而言很受啓發。
學術趴:現在有沒有正在準備的動畫項目?可否透露一下呢?
**沈毅:**現在在做自由職業的間隙同時準備一個4年前就開始的項目,因為16年來高布蘭被迫中止了,現在正在重寫劇本的階段。具體內容還是等着看成片吧,唯一可以透露的是一部關於我的家鄉福建漳州的短片。
- END | 動畫學術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