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主筆謝夢遙:我如何寫特稿的開頭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4046-2018-12-04 21:11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騰訊傳媒全媒派。)
“特稿的每一個段落,都很重要。但總有一些段落比另一些段落更重要。我會花更多的時間在開頭和結尾上。因為這個時代的閲讀習慣,開頭比結尾可能還要重要。能讀到(拉到)結尾的是少數人,但至少大家都會掃一眼開頭。就像站在《非誠勿擾》的台上,人們的耐心是那麼少,你要確保出口就得到喝彩,你要確保頭幾句話就調動起他人的期待,否則就你就被按燈下場了。”
本期全媒派(ID: quanmeipai)獨家發佈《人物》雜誌主筆謝夢遙的文章,與大家分享他如何寫特稿的開頭。
(一)
我寫稿時,經常卡在開頭很久,不是毫無頭緒,一般而言我早就想好了開頭大概的樣子,我會反覆打磨語詞,調換句子順序,找到一種最佳的節奏感。
特稿是講故事的報道,但寫一個故事的開頭,和用嘴講一個故事的開頭其實是不一樣的。當我們把故事説給別人聽的時候,一般而言,首先要為對方建立一個框架,確立時間座標,讓對方得以進入。“我來給大家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呢,發生在清朝乾隆年間”——這是評書式開場。“你們有沒有發現,地鐵安檢特別蠢,就拿我上週的經歷來説”——這是脱口秀的開場。寫一個故事,則可以拋棄這些暖場墊話,直接從最精彩的部分開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不用一開始就交代時間。在我2011年剛入行的時候,我記得在一次評刊會上,李虎軍老師提醒大家,那期雜誌有三篇報道都用了時間作為開頭的第一句話,一定要注意避免。從那時起,我就意識到,交代時間作為開頭,是特別平庸的做法。我從來沒這樣做過。一看到這種開頭,我就想起《新聞聯播》。
如果你真的覺得在開篇交代某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很重要,你至少可以頭兩句進行一段描寫那件事,抓住讀者,再引出時間。之前我寫過一篇談論自己如何入行的小文(那篇文章用了第二人稱的寫法),開篇是這麼寫的:
“剛一開口沒説幾句話,你就感到臉在發燙。你很羞怯,你羞於他人發現你的羞怯。你心裏罵着自己,祈禱臉上的血液能流得慢一點。但越是如此,你就越窘迫。你感到你的舌頭纏到一起。你想即刻消失。
現在是2011年12月……”
不止是特稿,任何類型的文章——大概會議紀要除外,我建議都不要把時間寫在第一句。
在我寫特稿的時候,我習慣把自己理解成一個電影導演。受訪者就像演員,採訪完成就等於拍攝完成,誰的鏡頭先上,人物怎麼出場,就看導演的調度安排了。這是開玩笑,我的意思是,特稿就像電影一樣,為讀者建立畫面感非常重要,這種畫面感從一開始就要出現。我會想,如果將這個人或者這個故事拍成電影,那第一幕應該是什麼,先是空鏡頭,插入低沉的畫外音,還是從一個局部特寫定格,鏡頭慢慢拉遠……
我去寫港版羅拉(一個意外成為網紅的香港女搬運工),我構想開頭的時候,腦中畫面是先於文字出現的。我覺得開頭就應該是一雙手的特寫,鏡頭從手拍到人。
那是雙剛健有力的手。那雙手能夠輕鬆抓起40公斤的重物。由於常年摩擦,掌心長出了厚繭,不止如此,從指尖到虎口,手掌的每一寸肌膚,都有硬塑料般的觸感。一隻拇指外翻,無法彎曲,那歸咎於一場工傷事故。如果忽略這一點,在搬運工人羣體中,那是一雙平凡無奇的手。
不同之處,在於那雙手的主人。一個年輕的女人。
局部特寫開篇的另一個例子,寫俞灝明。
那不是一張完美的臉。儘管有粉底遮掩,你仍能看到其中的瑕疵。現在,面對手機直播鏡頭,那張臉盪漾着微笑。是的,容顏縱然有變,友善、得體、温文爾雅,這些特質從未離開過俞灝明。
寫相聲演員岳雲鵬報道的開頭時,我想的那場景應該是,色調暗黑,煙霧瀰漫,我要在文字裏體現出那種混沌的感覺。
諸事不順。
劇場停電,音響故障,沒帶大褂,鞋穿錯了。他像是被困在了那個場景裏。所有可能的糟糕狀態都經歷了一遍。直到站上台的那一刻,他發現身邊搭檔不見了。只剩下自己。
他在半夜驚醒,確定那是一個夢。
那是2011年4月,岳雲鵬在民族文化宮大劇場的專場演出前夕——作為一個相聲藝人的首場大劇場商演。他告訴搭檔孫越,類似的噩夢一直困擾着他。
多説一句,這個開頭是一個短句,然後另起一段,這種用法比較冒險,因為頗有裝腔作勢的感覺,容易引發讀者反感。除非你覺得這個停頓的節奏感,是恰到好處的。光是這幾個字擺在這裏,就能讓人想繼續看下一段。
我喜歡看商業大片,是因為很多商業大片的鏡頭設計、故事線鋪展非常精緻,能夠給我很多啓發。文藝片就差點意思了,通常很悶,導演好像故意不好好講故事。而且文藝片按照時間發展的常規線性敍事居多,這些敍事方式太老派了。特稿不需要把故事脈絡處理得過於複雜,但相信我,故事從中間精彩段落講起,往回倒敍,再接回開頭,讀者體驗會好得多。
説到讀者體驗,我不喜歡《紐約客》的大多數報道,開頭結尾、整體架構都很任性。有時候真的要忍受無聊讀下去。我和一些同行交流過,他們有同感,但公開把這種感受説出來是另一回事了。我還是喜歡外刊《體育畫報》或者《GQ》的特稿,非常注重讀者體驗。
我通常都是寫人物報道,寫的強故事型題材極少,《猶在虎口》算是一篇(對不起,其實很不忍用強故事來描述一場事故,畢竟那是一個人的一生啊。講故事是一種方式,報道能帶來的真相、訴求或人與人之間的認知、理解才是目的)。
按照“故事從中間講起”的原則,我思考過放在開頭的故事轉折點應該是什麼。猛虎進攻的那一刻,是個太容易想到的轉折點了。如果換別人會這麼寫,我就應該避開。(後來成文時,我乾脆跳過這一部分情節,我覺得留白的效果更好。)我想到採用另一種平靜、柔和的方式,描寫主人公在醫院醒來的時刻,丈夫告訴她,母親沒有生命危險。一開始就展現一個假像,假像直到後半程才揭曉。回過頭來看,最震撼人心的情節,未必是衝突最激烈的那一幕,它可以是安靜地發生的。大慟無聲。
黑暗中,她聽見丈夫在輕輕地呼喚她的名字。她從那個沉睡的世界中甦醒過來了,卻發現什麼也看不見。她意識到,整個腦袋被繃帶纏繞着,眼睛腫得無法睜開。她感覺不到身體的疼痛,麻藥起了作用。
「你被老虎咬了。」丈夫説。「你下車以後,後面來了一個老虎,把你叼走了。」
老虎。這個詞跳進她的腦子裏,發出「轟」地一聲。但這個詞在記憶裏卻是沒有形象、聲音與氣味的。她努力回想,碎片慢慢拼湊,她記得了,她從副駕下車,走到了丈夫所在的駕駛位的車門旁,這時斜後方的車喇叭響起來。那是她能夠記起的最後一個細節了,但她不知道那意味着什麼。再往後,就是一片空白了,像兔子消失於魔術師的禮帽裏,連疼痛的記憶都是缺失的。
「媽媽也受傷了。」丈夫聲音低沉而平靜。
她激動起來,體徵監測儀器抖動地厲害,護士趕緊過來安撫她。她想説話,但因為呼吸機插在她的嘴裏,只能發出含糊的聲音:「媽媽……媽媽……」
「媽媽太着急了,衝下山坡扭到腳了。」
她想象着那個畫面。於是場景與人物漸漸清晰了,她似乎看到了母親從車中追出,直到摔倒時的樣子。倒下那一瞬,她甚至看清了母親腳上的那雙鞋。那是一雙綴着蝴蝶結的奶白色純羊皮的涼鞋,母親很喜歡它。母親腳拇指外翻,穿太瘦的鞋會磨腳。女兒根據母親腳型特意選的。
據她自己説,手術後甦醒過來的那個夜晚,在一種迷幻的狀態下,她夢見那隻老虎,關在一個鐵籠裏,就懸在她的頭頂。她能聽到老虎的喘息聲,能聞到尿騷味。與她一樣,那隻老虎正在醒來。
我在寫這段的時候,想着的畫面一開始是黑屏,丈夫的聲音先出現。然後變成主人公視角,眼睛慢慢打開,世界還一片模糊,就像好萊塢電影常演一樣。當然,文中所有出現的細節不能想象,全是靠一個個提問驗證得來的。
所以這就引到了我的一個重要工作習慣,不能坐下來寫稿的那一刻才想到着如何開頭,這個思索應該從接到報道任務的一刻開始,貫穿整個採寫過程。我一直想着通篇如何佈局,哪個場景是需要的,而我將如何獲得它。如果需要提問,就要周密設計好問題,如果需要現場信息,那就要讓自己出現在那裏。因為一旦採訪中錯過,可能再拿不到那些素材了。
以下是我對香港佔中事件第一夜的報道開頭:
“那枚催淚彈伴着火光落入人羣之中,白色的煙霧四散出來,瞬加將周圍的幾個人淹沒了。帶來的那種刺激感是全方位的,類似吃了一大口芥末,眼睛被滴入辣椒油,皮膚髮麻或者有灼燒感,頭會突然嗡得響一聲,伴隨着暈眩。這種個體感受,據説因人而異。”
那夜事發,我在人羣中觀察,當第一枚催淚彈發射,恰好落在我腿邊。那並不是戰地,催淚彈也不是炸彈,但那一瞬間我感受到了戰地記者是多麼需要勇氣的職業,我應該永遠也成為不了。當時我嚇得半死,馬上屏住呼吸跑開了。但後來我想到,如果我要寫這個開頭,必須要真正地感受那個催淚彈是什麼味道。誠然,網上可以查到催淚彈的相關信息,但永遠不如自己的感受來得直接。我知道這玩意兒對身體不會造成什麼永久傷害。於是,催淚彈再次發射時,我停在煙霧中,吞進一大口。我告訴自己,就是現在,充分感受一下。
最終我不僅收穫了一個我想要的開頭,我還收穫了未來可以用在**“我有你沒有”**遊戲中打敗所有人的殺手鐧。哈哈。
(二)
很多寫作者都是從模仿前人開始的。我覺得通篇結構、邏輯或許可以套用(如果你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你就不會這樣做,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故事都是特別的,但初學者可以被諒解),一些橋段可以借鑑,開頭絕對不要仿寫。因為太明顯了,業內人一眼看穿,可能你後面寫的很精彩,但這個開頭就降低了通篇觀感,不值得。而且開頭的方法有那麼多,幹嗎要把自己限制在別人塑造的入口裏。《百年孤獨》的開頭可謂經典:許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下午。這些年我至少看見六七篇報道仿寫了。清一色的,許多年後,某某會想起過去的某個時間點。其實你應該學習的,**是時間軸上跳動的寫法,**融不同時態於一體的環形敍事,而不是照搬這個句式。
開頭要避免落入俗套。有些稿子習慣開頭寫主角很忙(我承認我剛入行想不到好開頭也這麼湊合過),把日程流水賬似的羅列一堆。誰不忙啊,隔壁老太太還忙着買菜、做家務、照顧孫子呢。我總懷疑這種寫法不過是把談話習慣代入了寫稿,因為和人打招呼一般都會從“最近忙不忙”開始,這是脱口而出的第一個問題,特稿就別來這套了。
一般而言,編輯會鼓勵記者,用細節作為開頭。這類型有個經典套路,第一段細節,第二段背景,第三段直接引語。對於第一段的細節,建議別上來就寫,有經驗的老手,會讓第一句處理成一種上帝視角的評述,會增強文章質感。紐約時報的報道很喜歡這樣寫,舉個例子:
伴隨着厭惡而來的,還有一種挫敗感。今年早些時候,在自己位於燦爛奪目的上海金融區的辦公室裏,徐財源無助地看着電腦屏幕上閃動的數字。
中國股市再次出現自由落體式的下跌。就在幾個月前,股市暴跌,吞噬了像他這樣的職業投資者相當數量的資產和很多普通人一生的積蓄。這種不穩定蔓延到了全球市場。
“股市暴跌期間,很多中產階級投資者虧損,卻不知道為什麼,”38歲的徐財源在上海前法租界一家能夠俯瞰一處公園的東南亞餐廳吃午飯時説道。“市場暴跌是因為這是一場人為的災難。”
需要注意,傳統而言,不要讓開頭的這個有名字的人物出現一下就沒了,後面最好還有關於這人的敍述。像上面這個例子,徐財源並不需要是文章主角,但應該在後文裏至少再出現一次。
細節開頭,其實有多種,但很多人都選擇了動作細節開頭。即某某正在幹什麼事情。確實,這種開頭肯定比“某某最近很忙”的開頭好。這樣一開始就有了畫面感,人物也出場了。但我感到,一些報道的動作細節開頭太過常規,有點偷懶,傾向於寫受訪者在訪談、雜誌拍攝中的一些舉止。他走進攝影棚的樣子,他抽了根煙,她抿了一口茶——如果這個舉動在生活中發生都不會吸引你太多注意力,也是很難提升閲讀體驗的。這些動作確實可能體現主人公的某些個人特質,但天啊,這是開頭啊,難道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嗎?
就我自己而言,一直對用細節開頭保持謹慎。我會優先考慮綜述型的開頭。我入行所在的財經天下的主編商思林是個綜述型開頭的高手,他對我影響很大。他告訴我他的經驗是,宏觀綜述開頭,最晚第三個段落要有人物出場或者直接引語,否則就顯得沉悶了。
另一個原因是,我總覺得,細節是你採訪中看到的,遇見的,你只需要回憶、描寫就好了。某種程度上,它像是採訪對象雙手奉上給你的,而不是你努力得來的。綜述型開頭則需要你的創造力。你不僅僅是去寫出信息,你還是感受那些信息。你甚至要跳脱出來,用不同視角看待那些信息。
開頭一下進入故事,寫名人、新聞熱點人物恐怕還稍好,寫普通人對讀者吸引力恐怕不夠。“天矇矇亮,王建國起了個大早,他洗了把臉”,有時候我讀到這種開頭的報道,我心裏就會念叨,為什麼要讀這個故事,到底想説什麼?這人和我有什麼關係?綜述型開頭多少能解決這個焦慮。
我之前寫過二人轉羣像,沒有一個名角兒。這也是一篇比較靜態的稿子,並沒有什麼新聞由頭。怎麼抓住讀者呢?我換了幾個開頭,最後用了以下這個:
你永遠不會在二人轉演員姓名裏找到拗口生僻字,藝名多是師父改的。最簡單的才是最易記的,但這也導致名字會撞到一起。你一定知道誰是宋小寶,然後是名氣小一些的孫小寶,長春和平大戲院最近在力推的“轉星”叫陳小寶,除此之外這家戲院還有兩個演員叫“小寶”和“阿寶”。
事實上,真正好玩的遊戲叫做在“演員名字裏找對子與同花順”,而最終你的感覺會像迷失在一場複雜的德州撲克牌局裏:小瀋陽,小沈龍,小飛龍,小龍飛,小黃飛,於小飛,趙小飛,蓋小飛,關小飛…….以上都是有一定名氣的“轉星”。只要你願意,你大概可以無限接龍下去。
但孫海洋一直叫他的本名孫海洋,他是野路子出身。2007年,他15歲,拎着一個小皮箱坐上汽車,闖進葫蘆島這座城……
也許這不是一種特稿常規敍事,交稿後,頭兩段被刪節了,但最後主編張捷全加了回來,她覺得“這兩段話很有勁兒啊”。我當然也可以直接講故事,從孫海洋進城寫,但我覺得這樣很容易流失讀者。那麼我先給你呈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有趣的東西。它和這個人的故事沒有直接關係,但又並非和主題脱節,如何起藝名,也是二人轉文化的一部分。
其實這裏寫的是一種我的個體感受,是偶爾所得。當時我在長春的採訪完成,剩下半天我到處閒逛,走進一間二人轉劇場,看到公告欄的演員名單。我發現演員的名字很有意思,怎麼同一個劇場裏都這麼多叫小寶的。我便試着找出規律。所以,並沒有一個遊戲叫做“演員名字裏找對子與同花順”,是我憑着一個靈感,總結出來的。
綜述性的稿子就是這樣,**它是屬於你的創作,可以融入你的思考。**我寫過橫店創始人徐文榮的稿子開頭是這樣的:
這裏被稱作橫國是有原因的。紅色的城門打開,是開闊的廣場,穿過中庭,巍峨恢弘的秦王宮出現。護衞、宮女穿梭其間,如果運氣好,你可以見到公主。
古代與現代,刀槍劍戟與自拍神器,王侯將相與遊客,銅板與人民幣,衙門與快捷酒店,所有矛盾對立物混為一體。依靠步行(或者出租車)而不是時光機器,你可以完成一場又一場的穿越。橫國是魔幻的,最多的「皇帝」在此登基,無數「史詩級戰爭」在此發生。
你看這些句子,不是別人告訴我的,是我看到,感受過,思考過,重新組裝的信息。別的記者採訪徐文榮,如果他講述了一模一樣的故事,我們寫的時候可能在這部分撞車。但這個綜述開頭,是隻屬於我的。
再比如我寫歐陽靖説脱口秀的報道:
看起來是兩件毫不相干的事,脱口秀和 freestyle 説唱,但對歐陽靖先生來説,本質是一樣的。
都不會一字一句落於紙面,而是按照想好的概念要點,臨場發揮。都是自我表達,「需要把你自己的感覺放出來」,越真實——他用的是英文單詞「real」,就越能引發觀眾共鳴,如果同時又能找到切入問題的新穎角度,就更好了。
都需要 punchline(炸點)。
歐陽靖站起身來,做了一個 rapper 慣用的 dap 動作,拖着站立式有線麥克風——那是脱口秀傳統的一部分——走向舞台正中……
舉個極端假設,如果有100個特稿記者都坐在那個現場,看歐陽靖的演出,採訪也都全程參與,稿子裏用的細節、引語是不是很容易相同?但開頭的那段綜述不同,因為是你自己對自己説的話,藏在你的腦子裏,它讓你的稿子和其他人不一樣。
你越用心,你寫得越多,你的感受就會越敏鋭。你只要首先突破自己,試試去寫綜述開頭。
(三)
不要抗拒技巧。
我一直是這麼認為的,我們對素材保持誠實,遵守採寫傳統,但我們也要負責提升讀者體驗,就像餐館裏買正規食材、好好炒菜,跟擺盤漂亮、服務周到,並不矛盾。很有趣的是,我經常聽到的讀者對我特稿的一種評價是平實無華,其實我並非沒有使用技巧。這和炫技是不一樣的。有次我讀到一篇稿子,用了三個比喻句去描述一個事實,而這三個比喻句彼此沒有遞進,指向相同,這大概就是炫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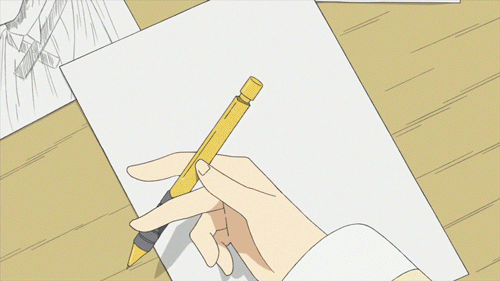
關於開頭的技巧,我試着總結若干則,這不是學術上的分類,只是我個人的實踐經驗。
(1)讓本來無關的信息、語詞彼此產生聯繫,虛實交織
“金秋送爽,丹桂飄香,全校師生們迎來2017年秋季運動會”,還記得這個句式嗎?開頭提天氣是老掉牙的操作了,《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上一篇文章的開頭是這樣的,能夠讓人會心一笑:
天空沒有被煙霧所遮蔽,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張維迎心情樂觀,同時具備這兩點的下午在中國首都北京並不多見。
拿我自己的稿子舉例,寫狗仔之王卓偉:
總有一些事情在你意料之外:充滿情懷的文藝片導演半夜在小衚衕裏玩車震;形象清純的女神激吻其貌不揚的三線男演員;而指揮拍攝下這一切的“內地第一狗仔”卓偉,長着一張顯得格外憨厚老實的臉。
“我們算娛樂記者裏的特種部隊。”卓偉四十多歲,他説起話來慢條斯理,語氣平靜。“狗仔隊有貶義,但只有用這個詞形容我們才夠準確。”不同於一般娛記,他和他的工作室的同事不跑新聞發佈會,他們瞄準的是名人八卦。
寫2015年的股災:
腎上腺素大量分泌的時候,人體的新陳代謝率隨之提升,耗氧量增加,會有一種心慌乏力的虛脱感。最能感知到這種身體變化的人,包括股民、賭徒、過山車與蹦極體驗者。有時候,這三種人其實是同一種。
生物學上的描述再精準,也永遠無法替代真實的感知。“你在場外看,和在場內玩,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90後股民顧峯對我説。北京工作的銀行職員王永超則説,“真是一天天堂,一天地獄。”
股市有風險,入行需謹慎,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通行的警示名言(當然有不同的版本)。但中國的股市近期所經歷的起伏,格外凸顯了這句話的告誡意義。隨着今年上半年的股市大熱,人們像是坐進了轟隆作響的上行的過山車,但熊市與牛市的無縫轉換,許多人也嚐到了瞬間墜落的滋味。
……
6月26日之後的暴跌,讓人們真正有機會開始審視股市與自身。但直到這個時候,他們才發現,許多關於股市故事都是相同的,並且沿着歷史時間軸,重複出現。
2012年底寫的音樂產業稿:
在咫尺可及的日子裏,兩個預言將很快驗證真偽:世界末日,和網絡音樂明年收費。不管瑪雅人口中的末日是不是靠譜,唱片的末日已經到來,在大勢所趨下,數字音樂產業成了音樂的出路。
(2)首尾呼應
脱口秀裏有個技巧叫call back,同樣的句子,最後再翻出來講一遍,能產生強烈喜劇效果。同樣,行文的首尾呼應也能起到奇效。我不鼓勵濫用,但用得合適,就像説唱歌曲裏的洗腦hook,是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寫新世相創始人張偉,開頭是:
中國有超過40萬個叫張偉的人。頂着怪異髮型的歌手張偉製造了不少流行但頗具爭議的口水歌,身高1米83的女籃運動員張偉獲得了5次WCBA總冠軍,還有一個長相英俊的張偉,是熱門喜劇《愛情公寓》的主角。但我們即將要談論的這個張偉,身高普通,長相普通,他更接近張偉這名字所暗示的意義,一個普通人。
張偉最近——也可能是生平僅有一次的出現在鎂光燈下,是《魯豫有約》的節目裏,作為擁有超過40萬粉絲的微信公號“世相”的運營者,他與十數位“大號”一同受邀,輪流請上嘉賓席分享心得。
結尾是:
“我內心的安全感比較強,”張偉説,“而儀式感與戲劇性是給人安全的東西。”
中國有40萬個張偉,頂着怪異髮型的歌手張偉,身高1米83的女籃運動員張偉,熱門喜劇《愛情公寓》裏的主角張偉。
但他是獨一無二的那個。
再比如寫林書豪,開頭是:
所有的故事都一樣,有着起因,經過,結局。對於很多人來説,林書豪的故事開始於2012年2月,坐在紐約尼克斯隊板凳末端的那位華裔球員突然爆發。
……
但對於29歲的林書豪自己來説,故事並不是看起來那樣。
“我覺得林瘋狂是the ending of one chapter。”在4月中旬的一個下午,開着純黑色的瑪莎拉蒂在紐約布魯克林的街區上,林書豪扭過頭來,對後座上的《人物》記者説。“第二個chapter可能是2012年,希望到我從NBA退休。如果我寫我的故事會是這樣寫的,分成這兩部分。”
結尾是:
所有的故事都一樣,有着起因,經過,結局。“我知道剩下的故事還沒有講完。”林書豪説,“There is more,there is better,我真的相信我退休的時候,他們當然會講林瘋狂,可是後來的故事更精彩。”
他説,最近他每個星期都會夢見籃球,那明亮又美好的夢啊,他是健康的,打球是快樂的。他還在等待上場的那一刻,他為那一刻的到來,已經準備太久。
(3)製造錯覺
之前説過,我喜歡用電影開頭去想象特稿開頭。但文字比圖像畢竟少了一層直觀視覺效果,這可能是劣勢,但你也可以將其轉換成優勢,正是因為讀者看不到,你可以引導這種錯覺,然後讓他恍然大悟。我試過兩次。
一次是寫馬東:
都是“奇葩”。
頭髮遮住半邊臉的非主流高中退學生;在網上更新“死亡日記”的胃癌晚期患者;敢給總理寫信的前鄉黨委書記;號稱願掏千萬元徵婚的富翁…….他們都來了。
節目尺度很大。與此對應的,是馬東的温情。他經常在節目中感動得掉眼淚。當然現在回顧起來,他是不會承認請那些“奇葩”來,是為了突破尺度。“這個東西怎麼沒人聊過,”他對《人物》回憶,他就是好奇,想聊聊而已。上綱上線,賦予價值,不是他的話語風格。
那位高中退學生首次登上電視訪談,因為他的某些驚世駭俗的觀點,他正在成為整個主流社會的眾矢之的。節目不求批判也無意褒揚,只求呈現,但馬東承認,他內心是有立場的。“喜歡他那個勁兒,我肯定是鼓勵他的。”他對《人物》回憶。
他設計了一段開場白,拿來一個裝滿水的玻璃杯子,揉一個紙團丟進去。“大家看到這個會想到什麼?這是一個年輕人,他想到的,是《杯中窺人》。”接下來,17歲的韓寒出場了。
等一等,你不會以為這是《奇葩説》的現場吧?
那是1999年,馬東電視生涯的起點,在湖南衞視做《有話好説》的主持人。他和那個10個編導的微型欄目組的絕大多數人一樣,只是個編外人員,但選題大多依着他的興趣來。韓寒、陸幼青、李昌平等登上節目的嘉賓都是他欣賞的人。與佈景華麗、字幕花哨的《奇葩説》不同,那是一個嚴肅對話節目。近20年前,“奇葩”這個詞尚未成為流行語,但不可否認,換一種包裝形式,當年的某些受訪者,也是《奇葩説》的候選人。
一次是寫綜藝節目《吐槽大會》:
開火吧,朋友。
肥胖;大齡未嫁;吝嗇;長得醜。他們不會放過彼此身上的任何一個槽點。頭大;個矮;不搞笑;“活兒”不行。那個舞台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互相傷害。
中國脱口秀界的第一場吐槽大會,尺度之大讓人觸目驚心。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至少表面上如此。美中不足是,配套設施實在簡陋,臨時搭起來的不足兩米寬的紅幕布前,放着一個立杆麥克風,音響效果非常差。等等,你不會還以為這裏説的是去年7月首播的那期網絡綜藝吧?
這是2013年6月,深圳的一羣脱口秀愛好者自發舉辦了這場活動……這一場的主角是一對80後夫妻檔,程璐和王思文,倆人正是因説脱口秀相識。幾個月前他們結婚了,朋友們商量如何慶祝,程璐提議,不如搞場吐槽大會吧。
就我個人而言,我很怕看到那種開篇就寫陳年舊事的稿子,有距離感,很難進入。特稿畢竟是新聞的一種,還講究一個新字,我更想知道最近發生的。一開始就寫舊事,那麼剩下的部分有多少是新鮮的,讀者可能會心裏犯疑。但過去和現在是有關聯的,那段故事如果對於下文是重要的,我至少可以換一種引入的方式,讓讀者有一種新奇體驗。
(4)主角稍後出場
我一直對《笑傲江湖》這部小説念念不忘,除了情節本身,讓我覺得很奇妙的是,金庸把主人公令狐沖出場時間安排得也太晚了。第一部快讀完,他才現身。我之前一直以為林平之會是小説主角,讀者對這個配角的情感理解、代入是先於令狐沖完成的。
小説可以這麼寫,特稿可不可以呢?我曾經做過一次嘗試,在寫《舌尖上的中國》幕後故事的特稿中,之前一直在寫陳曉卿,在寫到快2000字的時候才讓真正主角任長箴出場——這稿子總共不到萬字,而事實上,陳曉卿和她是屬於合作又鬥爭的雙方。
這篇可能有點特殊,一般而言,特稿不可能讓主角那麼晚出場,名字在開頭就要有了。我們可不可以從另一個人身上寫起,過渡到他這裏呢。注意,也不要硬選一個人,搞到最後讀者發現兩者關聯不大,我覺得要麼這兩人各自的故事線在稿子裏有多次交纏,要麼,就是第一個出現的人最近提供了一個由頭,讓我們從這裏開始討論主角。
比如我寫陳冠希的報道,從龍哥寫起。看似寫龍哥,其實這些段落也在完成對陳冠希的素描。
老闆在,龍哥就在。
在這家公司裏,龍哥沒有正式職位。老闆去北京,龍哥就去北京。老闆去上海,龍哥就去上海。只要是工作,老闆去哪兒,龍哥基本跟着。有些員工有話不敢對老闆直説,就先找龍哥。龍哥像個緩衝墊。
現在,他已經是個老人了。老闆12歲時,龍哥就做他的專職司機了。老闆有過很多女朋友,但龍哥有15年沒交過女朋友。這一點,老闆是有過問的:“你是不是gay 啊?”
“你神經病。”龍哥説。
“我從沒見過你同女朋友聊天。”老闆説。
2007年龍哥終於有了女朋友,後來他結婚,邀請同事去海邊燒烤。只有老闆不知道,他當時人在美國。後來老闆埋怨怎麼連結婚都不告訴他,龍哥説怕耽誤他的事情。
龍哥總是會成為老闆童心大發時那個被捉弄的對象。拍網絡鬼片《探靈檔案》的時候,老闆把龍哥推進一個“鬼屋”,在外面把門抵上,過了兩三分鐘才打開。龍哥生氣了,“有沒有搞錯啊。”
其實,老闆很喜歡龍哥。他曾對媒體説,龍哥就像他的父親一樣。龍哥對他説:“不要這樣説,你爸爸會把我幹掉的。”
他們之間早已超越了僱傭關係,但直到現在,龍哥還是喊他老闆,老闆則喊他阿龍。香港是個高速流動的都市,藝人更換門庭,公司職員在不同平台跳來跳去,職業經理人簽下新的合約。但龍哥一直在。只有一年例外。
那件事發生之後的那一年。龍哥是那個送老闆電腦去修理的人。
再比如另一篇寫馬東的報道。(對,一個月裏我寫了兩次,上篇是年度人物,這篇是封面特寫,素材還不能重樣,差點沒愁死我!)
在最終將馬東確立為批判標靶前,梁歡是有其他選擇的。他列了一個清單,寫下很多公眾人物的名字。作為一檔時事諷刺脱口秀,那期《惡毒梁歡秀》要談論的話題是,犬儒主義。
一些人有犬儒嫌疑,但沒有發表過犬儒主義宣言,於是,咪蒙、何炅這些名字被劃掉了。“他一定要明確的説過一句話,他看不上意義、價值、好壞這些東西。”梁歡認真地進行了篩選,最後縮減到3個備選:大張偉、李誕、馬東。大張偉總是玩世不恭、語出驚人;李誕的微博常有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他的簽名就是“人間不值得”;馬東則是因為他在《十三邀》中,對精英與大眾、高雅與粗鄙等問題上,與許知遠截然不同的看法,引發了爭議。
梁歡看了那期節目。他越看越生氣,當馬東説出那句——“看到那些特別積極地面對人生的人的時候,我就老想樂”,梁歡感到深深地冒犯了。坐在咖啡館裏,他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罵“三字經”。他承認選擇痛擊馬東,純粹出於一種個人感受上的受傷害。
從幾年前打擊假唱開始,到製作這個雄心勃勃但播放量平平的脱口秀,在很多人眼裏,梁歡是個姿態略顯笨拙的挑戰者。他的微博也多次被禁言。他抨擊的馬東站在天平的另一方,他是現象級綜藝《奇葩説》締造者、米未傳媒的創始人。《奇葩説》第四季的廣告招商總金額近4億,《惡毒梁歡秀》沒有找到任何贊助。
“最容易導致犬儒的兩件事兒,一個是強壓的管制,一個是海量的資本,這兩樣馬東是同時在經歷的。誰面對這種情況都不一定能守得住。《惡毒梁歡秀》也在妥協,在中國你只要在做內容,都在妥協。”梁歡對《人物》説,“我們為什麼絕不會説羅永浩是個犬儒主義者。他做了錘子手機以後他妥協太大了,當他做了這麼多妥協以後,你從來沒有見過一次羅永浩説自己當年那些堅持是傻逼的,現在還在堅持的人你們沒有意義,你們就甭堅持了,他從來沒有説過這樣的話。妥協一點都不可恥,嘲笑堅持的人是可恥的。”
《人物》問及馬東對那句看似欠妥的措辭的感受,他温和地笑了,表示並不後悔……
當時梁歡對他的犬儒主義批判還甚囂塵上,兩人看起來如此不同,又存在某種意義上的殊途同歸。我想把這個馬東的比照者一開始就放在那裏。
最後我想説,逼自己一下,你能寫出更好的開頭。我入行第一家媒體是《財經天下》,經常合作的編輯張厚是個很嚴肅的中年男人。(其實只比我大一歲,為什麼我要説中年男人?)記憶中,每次我交稿給他,他都會若有所思地説,這個開頭已經很不錯了,但我總感覺你能寫出更好的,再想想。我堅決地説不可能。“你能寫出來的。”“我真不行。”“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他總是不緊不慢地説。張厚真是一個噩夢一樣的存在。(後來他也會跟別人説我是他的噩夢,説我把他都整出抑鬱症了,這是改稿階段我們因各自堅持而發生的事,以後再表。)
至少我的記憶是這麼告訴我的,我和他爭辯,爭辯失敗,回去老老實實地改稿。那麼就拼命地壓榨自己,冷水衝臉,喝酒找靈感,在微博上喊打敗同題,站在樓頂向全世界喊我是最棒的——這我有點誇張了,最後我會交給他一個更好的開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