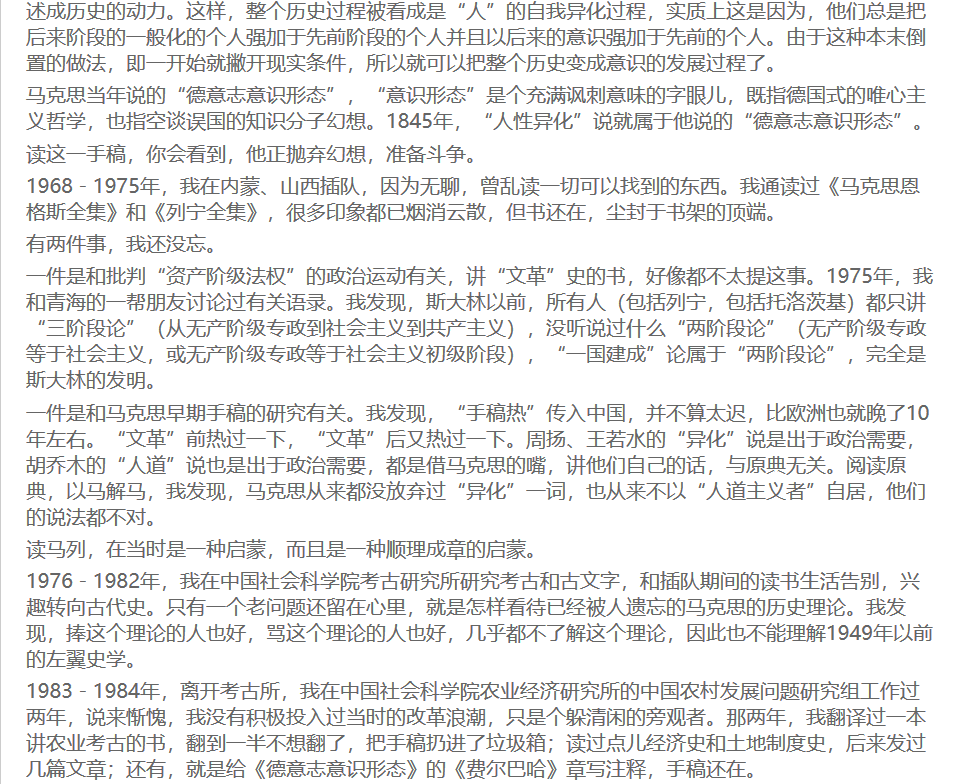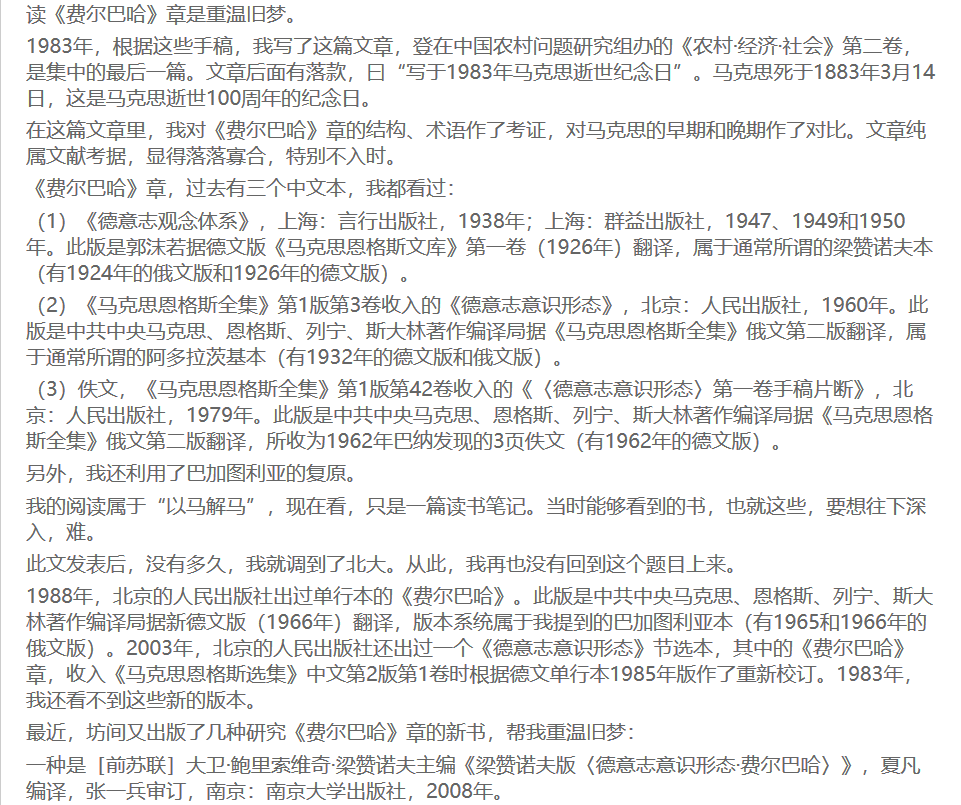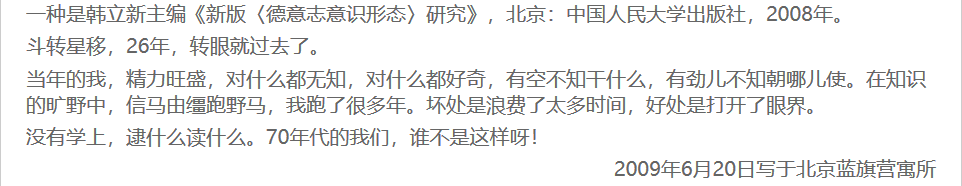李零 | 讀《費爾巴哈》章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8-12-04 08:23
保馬今日推送李零老師《讀
本文收錄於李零文集《何枝可依》(三聯書店,2009年版),感謝李零老師授權保馬發佈!
李零《何枝可依》書影
在西方的馬克思著作研究中,人們往往把“青年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或“哲學的馬克思”與“科學的馬克思”)對立起來,劃地自守,各執一端,陷入類似當年青年黑格爾派為瓜分黑格爾體系而展開的“狄亞多希”之爭。
對這一對立,僅僅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來反駁是不夠的,還應當指出其正確的階段劃分。在我們看來,馬克思的著作早期偏重方法論,晚期偏重實證研究,這種“由虛入實”的過程是科學思想進化的必然,中間並不存在所謂“思想斷裂”;其根本性的區分,即成熟與未成熟之分,是在早期著作本身當中,關鍵是要把真正的質變臨界點找到。在這一問題上,我們認為,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僅僅是起點,《德意志意識形態》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後總結和對唯物史觀的首次闡述,才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轉折。
基於上述考慮,我們決定選取《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費爾巴哈》為對象,從歷史考證的角度,對該章中的唯物史觀原始表述做一簡短討論。
《德意志意識形態》書影
一、版本原貌與敍述結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不止一次説過,他們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合寫的一部未能出版的著作中第一次對唯物史觀做了明確闡述。這部著作就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它的手稿在很長時間裏對人們一直是個迷。梅林在他的《馬克思傳》中就曾猜測它是被“老鼠的牙齒”消滅掉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的遺稿時,發現這一手稿仍然存在。他曾認真考慮過整理出版這一著作,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
《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在恩格斯逝世後,先後由馬克思的女兒艾琳娜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保存。它的各個重要版本都是列寧逝世後在蘇聯首先發表。這裏為了介紹《費爾巴哈》章的敍述結構,我們有必要先對有關版本情況稍加説明。
《費爾巴哈》章的版本可以大致區別為三類:
(1)單章舊本。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4年和1926年分別出版的俄文版和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卷所收。中文譯本有郭沫若譯《德意志意識形態》(言行出版社1938年11月版)。這一版本將手稿分為A、B、C三節,編排順序大致依據原稿,但將謄清稿Ⅴ中的第3—4張人為移入該章末尾,並且段落劃分不清,現在已經過時。
(2)全文本。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1932年出版的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國際版)第一部分第5卷和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所收。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所收譯文即屬此種。這一版本也分手稿為A、B、C三節,除A節為原標題外,其餘B、C兩節的大標題和A、B兩節的小標題皆系編者所加。它是誤據所謂手稿邊注的“提示”(編者把這些邊注當作作者為編定手稿而做的提示),打亂手稿原來的編排順序而重新編定,等於是個新編。
(3)單章新本。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於《哲學問題》雜誌1965年10
、11期重新發表的俄文譯本與1966年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單行本。這個版本是按手稿原來的順序編排,並增收進1962年新發現的兩個佚文片斷及手稿末尾所附的六條札記。兩個佚文片斷的中文譯本已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中。據編者巴加圖利亞考證,該章共包括按時間順序排列的五份手稿:未謄清稿Ⅰ(1—29頁)、Ⅱ(30—35頁)、Ⅲ(36—72頁,73頁未編碼)和謄清稿Ⅳ(無編碼)、Ⅴ(1—5張)。其中手稿Ⅰ寫於1845年11—12月,手稿Ⅱ、Ⅲ寫於1846年1—4月,手稿Ⅳ、Ⅴ寫於1846年6—7月。編者將謄清稿Ⅳ中的刪余文字插在Ⅴ當中編為第Ⅰ部分,未謄清稿Ⅰ、Ⅱ、Ⅲ分別編為第Ⅱ、Ⅲ、Ⅳ部分。每部分手稿下面再細分為若干片斷,每個片斷加有小標題。標題除原有的A節標題外,皆系編者新加。
上述三種版本只有第三種版本可以用作分析《費爾巴哈》章結構特點的依據。該版編者巴加圖利亞通過對手稿的整理,得出一個結論:《費爾巴哈》章的各手稿只有時間排列的意義,它們是作者對唯物史觀的三次闡述;這些闡述彼此重複,但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成熟,作者的總思路只能通過串連各手稿的同類敍述才能表現出來。因此,他從各手稿中抽出四條線索,並按這四條線索把該章細分為十二個方面,每一方面都是經歸併各手稿的相應段落而組成。
巴加圖利亞對手稿原貌的恢復之功固不可泯,但他對手稿結構的理解卻未能免於“新編”之譏,其説是有商榷餘地的。我們認為,誠然,《費爾巴哈》章的四部分手稿是寫於不同時間,但不一定就沒有結構聯繫,因為任何作品的寫作都會有這種時間先後,問題要看它們是不是代表了同一主題的不同側面。這四部分手稿,雖從表面上看,確有重複之感,但它們的討論角度並不相同,實際上仍然代表了作者討論的不同側面。更何況原稿的謄清部分與未謄清部分各有作者所加的統一編碼,也説明它們還是一個連貫在一起的整體。
下面讓我們來簡單分析一下《費爾巴哈》章的基本結構特點。
(一)第Ⅰ部分。手稿開頭是一個小序,在小序中,作者點出他們的批判對象是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然後有一個標題:“A.一般意識形態,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節是論一般社會意識形態和德國青年黑格爾派哲學與社會存在的關係。在標題下面的開頭部分裏,作者先對從施特勞斯到施蒂納的青年黑格爾派做了特徵描述和批判。然後接下去的整個中間部分,是針對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思想對唯物史觀的闡述,包括:(1)人類物質生活的自然基礎(人體、自然環境等);(2)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與交往形式;(3)生產力與分工;(4)分工發展的不同階段與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5)人們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6)意識形態。結尾,作者又回到開頭批判的對象,指出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上,他們與青年黑格爾派有着截然相反的理解;他們的歷史觀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而絕不提供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
這一部分在編排上和中文A節的開頭部分(小題“1.歷史”之前)大體一致,從中文版也可以看出它的基本結構。
(二)第Ⅱ部分。標題缺,從內容上看,主要是對費爾巴哈的批判。過去手稿缺開頭第1—7頁和結尾第29頁,結構不甚明朗。現在手稿開頭第1—2頁的殘稿和結尾第29頁都已找到,它有助於説明手稿這一部分的整體結構。根據手稿第1—2頁的殘稿及其邊注,我們可以判斷,這一部分是從討論“哲學的解放”和“真正的解放”的區別而開始的。接下去有若干缺頁,從第8—10頁,作者對費爾巴哈的感性原則和他對人的理解進行了批判,指出“正是在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看到改造工業和社會制度的必要性和條件的地方,他卻重新陷入唯心主義”。我們可以估計,手稿開頭的全部十頁是一個正面批判的部分。然後和謄清稿相似,手稿的中間部分也是關於唯物史觀的正面闡述,但這個闡述和謄清稿不同,主要不是側重於講歷史因素間的決定關係,而是側重於講歷史因素間的矛盾衝突。首先,作者把歷史因素概括為:(1)為滿足物質需要而進行的生產活動;(2)由物質需要引起的其他需要;(3)人類的增殖與家庭;(4)由勞動和生育兩種生產所決定的人們的自然關係與社會關係;(5)由上述因素所決定的意識。他們認為,由於分工的作用,上述因素或者説生產力、社會狀況和意識這三者間必然會發生一定的矛盾。這些矛盾導致:(1)私有制的產生;(2)與私人利益對立的公共利益採取國家這一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3)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表現為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然後接下去,作者從他們的共產主義觀點,論述了消滅上述後果(哲學家們稱之為“異化”)的歷史條件。手稿最後一部分和謄清稿相似,也對兩種歷史觀的對立進行了總結,但重點不再是圍繞着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一般關係,而是圍繞着國家、意識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它的結尾部分,包括新找到的第29頁,與開頭相呼應,主要是對費爾巴哈的批判,特別是批判他對共產主義的錯誤理解。
這一部分手稿中文版編排比較混亂:第一,是把夾在中間的作者對唯物史觀的闡述編入A節“1.歷史”下;第二,是把本來分處於手稿開頭和結尾的批判部分合並在一起,編入A節“2.關於意識的生產”下。
(三)第Ⅲ部分。標題缺,比較短,是個小插敍,只講了一個問題,即統治階級的思想如何在歷史上表現為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它與第Ⅱ部分所論“解放”的問題有關,並且其中有兩處對第Ⅱ部分的內容作了追述,與第Ⅱ部分關係比較密切。
中文版將這一部分編入A節“2.關於意識的生產”下。
(四)第Ⅳ部分。標題缺,主要是講資本主義社會、即“市民社會”的歷史以及共產主義的歷史條件問題。篇幅最長(將近全章的一半),採用正面論述。它包括:(1)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和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之間的差異以及私有制發展的兩種形式:地產與資本;(2)城市和鄉村的分離、資本和地產的分離、行會制度的產生,(3)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主要階段:商業資本的形成——工場手工業——世界市場的開闢——機器大工業;(4)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對立;(5)實現共產主義的條件: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矛盾衝突(這一衝突是形成歷史上交往形式演進序列的真實原因);(6)“市民社會”作為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有其一般意義,這種社會組織是構成國家和意識的上層建築的基礎;(7)國家和法與所有制的關係。未編碼的最後一頁附有六條札記。整個這一部分雖然是寫“市民社會史”,但包括了唯物史觀的敍述結構在內,也是關於作為唯物史觀一般範疇的“市民社會”概念的説明。
中文版這一部分也比較亂,分別編入B節“3.自然產生的和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與所有制形式”、B節“1.交往和生產力”、C節“共產主義。——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B節“2.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係”之下。
綜上所述,《費爾巴哈》章主要是由:(1)對青年黑格爾派的一般批判和對唯物史觀的相應闡述(謄清寫定);(2)對費爾巴哈的專門批判和對唯物史觀的相應闡述(未謄清寫定);(3)對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和共產主義歷史條件的論述(未謄清寫定)這三部分構成。前兩個部分都是針對該書第一卷的批判對象而寫成,第三部分則是對作者所持共產主義觀點的正面論述。它包括唯物史觀的各項基本內容,但有自身的結構特點。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
二、概 念 術 語
《費爾巴哈》章使用的概念術語主要有:
(1)生產力。這個概念在《費爾巴哈》章中沒有解釋,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作者當時對這一概念主要是從物質生產力、即廣義生產工具或生產資料的含義去理解,並相應地把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主要理解為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例如手稿第Ⅳ部分在結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講唯物史觀時,一上來就是講“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指耕地、河流等)和“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指人工製造的工具)。作者正是通過比較這兩種“生產工具”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來揭示地產和資本的對立以及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區別。同樣的理解,我們在《哲學的貧困》中也可碰到,如“產品的交換方式取決於生產力的交換方式”,“生產力”即指生產資料;又《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的《導言》中有這樣一句話:“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的辯證法”,“生產力”一詞後面括號內所注即“生產資料”一詞,可見生產力一詞原來的基本含義是指生產資料。
(2)交往。這個詞的德文原文(Verkehr)本義是交通和交際往來,但也可用為商業、貿易等義,作者把它當作英文“commerce”的對應詞彙,後者本義是商業、貿易,但也包含交際往來之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使用的“生產關係”一詞就是從這個詞演變而來。但在本書中,這個詞和後來的“生產關係”一詞還不完全一樣,除指一般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外,還特別指狹義的商品交換,是個雙重含義的詞。作者在本書《聖麥克斯》章中説:“資產者可以毫不費力地根據自己的語言證明重商主義的或個人的或者甚至全人類的關係是等同的,因為這種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因此像在現實中一樣,在語言中買賣關係也成了其他一切關係的基礎。例如……commerce,Verkehr〔商業,交往〕;……等等。所有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業關係,也意味着作為個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關係。在其他現代語言中,情況也完全一樣。”另外,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1846年12月18日)中也説:“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我在這裏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詞一樣。”在這段話中,兩次出現的commerce一詞,第一次是交換的意思,第二次就是指生產關係。
這個雙重含義的術語對我們很有啓發性。它對説明“生產關係”一詞的起源和演變是很重要的。
在《費爾巴哈》章中,“生產關係”一詞僅一見,原文是“這兩種所有制的結構都是由狹隘的生產關係——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業式的工業所決定的”,“生產關係”一詞的含義還不很明確,與生產方式的概念差不多。馬克思是在《哲學的貧困》及其他稍後的著作中開始像我們現在這樣使用“生產關係”一詞。但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馬克思並未立刻就因此而放棄“交往”一詞,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的《導言》中,馬克思仍然提到“交往關係”一詞,原文是:“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關係。”,其中“生產資料和生產關係”即相當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也就是“生產關係”一詞更具體一些的講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在許多地方提到“生產和交換的關係”或“生產和交換的方式”,這樣一些複合詞,當即來源於此。而生產和交換(或者再加上消費和分配),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説法,也就是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關於生產和交換兩者的關係,恩格斯做過這樣的説明:“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交往”這個雙重含義的術語,其較狹的含義與“交換”一詞相當,不像“生產關係”一詞是個純粹一般的術語,因此作者後來用“生產關係”或“生產和交換的關係”來代替它,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生產方式。這個術語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並無嚴格定義,有時似乎是指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生產活動方式,有時似乎僅指生產關係或者社會經濟形態。但是,在《費爾巴哈》章中,它在概念上主要是指前者,即“人們用以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作者認為“生產方式”的概念不僅應當從生產的目的,即“生產什麼”來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從這一活動的方式本身,即“怎樣生產”來了解,把它理解為人們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它主要用在像“農業勞動”、“工業勞動”、“商業勞動”或者像“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這樣一些概念上,與產業的概念比較接近。所以作者説“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把“生產方式”當作“一定的工業階段”的同義語。這裏的“工業階段”也可以理解為“產業階段”。
(4)分工。這一術語與生產方式的概念直接有關,但它表示的主要不是生產活動的具體方式,而是生產職能的分化,以及這些生產職能在人們中間的分配。“分工”一詞在《費爾巴哈》章中應用非常廣泛,歸納起來,主要有五個方面:1)“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發地或‘自然地產生的’分工”;2)工商業和農業的分離、城市和鄉村的分離;3)商業和工業的分離;4)各城市間的分工;5)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其他分工。
另外,我們還可注意到,作者常常是從兩個否定性的含義來理解“分工”的概念:第一,他們認為“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第二,他們認為分工導致了社會活動的固定化。所以他們主張“消滅分工”。
(5)所有制的形式。原文“所有制”一詞(Eigentum),本是法學術語,有時也譯為“財產”。但在《費爾巴哈》章中,作者借用這個術語表示的卻不是法學意義上的財產關係,而是作為總體含義的經濟關係。作者從幾個方面規定了這一術語的含義:1)它是由“個人與勞動的材料、工具和產品的關係”所決定的“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2)“所有制的形式”同時還是各種生產方式如“農業勞動、工業勞動和商業勞動的經營方式”;3)“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一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
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1846年12月28日)中曾對這樣使用的所有制一詞做過説明,他説:“最後,所有制形成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後一個範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魯東先生的所有其他範疇是總合起來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制的社會關係;在這些關係之外,資產階級所有制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另一時代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發展起來的。蒲魯東先生把所有制規定為獨立的關係,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沒有理解把資產階級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結合起來的聯繫,他不懂得一定時代中生產所具有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蒲魯東先生看不到現代種種體制是歷史的產物,既不懂得它們的起源,也不懂得它們的發展,所以只能對它們作教條式的批判”,又馬克思《論蒲魯東》:“蒲魯東實際上所談的是現存的現代資產階級財產。這是什麼財產?——對這一問題,只能通過批判地分析‘政治經濟學’來給予答覆,政治經濟學不是把財產關係的總和從它們的法律表現上即作為意志關係包括起來,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即作為生產關係包括起來。但是,由於蒲魯東把這些經濟關係的總和同‘財產’《lapropriété》這個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類似的著作中用同樣的話所作的回答:《La propriété cést la vol》〔財產就是盜竊〕”。可見他們在這一時期使用的“所有制”一詞,實際上相當於他們後來使用的“社會經濟形態”一詞。
在《費爾巴哈》章中,作者提到的“所有制的形式”,包括“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這三種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形態。可以作為對照的是,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也是用“所有制”一詞表示“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並把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形態分為“以部落體為基礎的所有制”(譯文原作“財產”,包括“亞細亞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三種)、“奴隸制”和“農奴制”,只是在經過整理而發表出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才第一次明確提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形式”,在《費爾巴哈》章中是與上述三種“所有制形式”分開專門闢為一節,馬克思也稱之為“市民社會”。作者曾以“父權制、奴隸制、等級、階級”這樣四個詞來提示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其中“父權制”即相當於“部落所有制”,“奴隸制”即相當於“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等級”即相當於“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而“階級”就是指資產階級社會。
(6)市民社會。這也是一個雙重含義的術語,既指資產階級社會,也指社會的“經濟基礎”。它是從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借用來的。這個詞本來是18世紀產生的(例如亞·弗格森寫過《市民社會史試論》),意思是“市民的社會”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但黑格爾卻把這個詞運用到該書中,把它當作一種介於家庭和國家之間的社會組織形式(見該書第三篇《倫理》第二章),用它表示物質生活和生產的領域以及為保護這一領域而設置的司法、警察、同業公會等機構。黑格爾指出物質生活和生產的領域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他對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卻作了顛倒和歪曲的描述。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對該書第三章《國家》做了專門批判。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把“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關係變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內部活動”,將二者“頭足倒置”,實際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這一點促使馬克思轉向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作者在《費爾巴哈》章中明確指出,“市民社會包括着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上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範圍,儘管另一方面它對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態出現,對內仍然需要組成國家的形式。‘市民社會’這一用語是在18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係已經擺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真正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這一名稱始終標誌着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這和馬克思後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説“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借用黑格爾所使用的“市民社會”一詞,用以表示他們所理解的社會經濟基礎的概念,和作者的這樣一種理解是分不開的: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社會是具有明顯經濟組織性質的社會,建立於這種經濟組織之上的社會上層建築已經失去獨立性的外觀,不像古代和中世紀社會那樣,被習慣上認為是政治或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
(7)國家和法。這也是《費爾巴哈》章中出現的唯物史觀範疇,但沒有太多複雜含義,討論從略。
(8)意識形態。這也是個雙重含義的詞,它既指作為社會上層建築的各種意識形式(如哲學、宗教等),也指唯心主義思想家特有的精神創作過程。1847年3月19日,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曾談到路·勃朗,説“他已經被‘一種妖術束縛住’——即意識形態”,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説:“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有意識地、但是以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行動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這些都是據後一含義而使用的。
以上九個術語,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晚期表述相比,(3)(4)(7)(8)基本相同,其他或者用詞不同,或者含義有別。
三、創 作 思 路
在《費爾巴哈》章中,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一點,即作者對唯物史觀的闡述,一上來就是講“現實的個人”,在敍述中也反覆穿插着許多關於“人”的討論。
為什麼作者要反覆討論“人”的問題?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對理解《費爾巴哈》章的唯物史觀思想是至關重要的。
撇開各種細節過程不談,我們可以試將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的形成過程看作是一種關於社會歷史現象發生原理的逆向追溯。
這一追溯是以青年黑格爾派運動為背景。
我們都知道,在馬克思以前,青年黑格爾派在宗教和哲學的領域中已經追溯過形成宗教或其他精神力量統治的原因。這一追溯過程,根據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一書中的概括總結,可簡示如下:
費爾巴哈超越了“實體”與“自我意識”的爭論,在黑格爾哲學中發現了“人”的秘密,把黑格爾哲學從宗教批判的角度還原為“人的本質的異化”形式,這是馬克思後來思想發展的重要起點。
馬克思本人的追溯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克羅茲納赫時期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是一個階段,可簡示如下:
巴黎時期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聖家族》是另一個階段,可簡示如下:
截止到《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前,馬克思所發掘到的最後一個層次是“勞動異化”。
“勞動異化”説在巴黎時期顯然是一個佔據中心位置的思想,它是馬克思同時進行的兩大批判的共同焦點。藉助這一學説,馬克思不僅批判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指出它用來表示資本主義財富源泉的“三位一體”公式是勞動異化的結果,從而給後來剩餘價值學説的產生提供了批判性的起點(同時也影響到馬克思對勞動價值學説的肯定和接受,參看《神聖家族》);而且也批判了黑格爾的哲學體系,指出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秘密實際是來源於勞動異化引起的社會現象的扭曲變形和層次倒接(顛因為果,反客為主)。與個人對立的一切社會關係所取得的非人化外貌統統是假象,必須恢復“人”的主體作用,這是馬克思在向唯物史觀跟蹤逼進的過程中首先邁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問題卻並未到此為止。馬克思的上述還原工作仍然受到費爾巴哈的強烈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已經開闢了全新的研究領域,提出了“勞動異化”這一重要思想,但他卻仍然以“實證的人本主義和自然主義”或“真正的人道主義”自命,把“勞動異化”説包容在費爾巴哈的那一套“人性異化”的術語之下。而這就暴露出一個矛盾,即如果一切社會關係都是由“人”派生而出,那麼就得事先假定有先於社會而存在的某種抽象“人”,也就是説,人們的社會關係可以從赤裸裸沒有任何社會關係的“人”推演而出。這當然是荒謬的。但反過來,如果説“人”不是這種起點性的東西,那麼至少從表面上看,問題像是轉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人”的主體作用又被取消掉了。
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是在布魯塞爾時期。這時施蒂納的書出版了。他以“個人”反對“人”這一形式而對費爾巴哈(也包括當時被認為屬於這一派的馬克思、恩格斯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挑戰非常適時。它從反面促使馬克思不得不作深刻反省,與費爾巴哈(以及“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思想上劃清界限。
答案是:必須用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費爾巴哈對抽象人的崇拜。在《費爾巴哈》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
(一)他們所理解的“人”是在確定物質前提下從事生產活動和其他活動的“現實的個人”。這些“前後相繼、彼此相聯的個人”(即處於一定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下的個人),並不是某種“從事自我產生這種神秘活動的唯一的個人”,因此不能認為“這些個人中有類或人在發展,或者是這些個人發展了人”,也不能把歷史上存在的各種等級和階級“理解為類的一些亞種,理解為人的一些發展階段”,從而設想出“某種奚落歷史科學的東西”。
(二)“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説”叫做“異化”的這個詞,現在應表達為生產力、社會狀況和意識等歷史因素間的矛盾衝突,人對分工和由分工產生的私有制、國家以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屈從。這種“異化”只有具備了“實際前提”之後才會被消滅。
(三)“哲學家們在已經不再屈從於分工的個人身上看見了他們名之為‘人’的那種理想”,因而將整個歷史過程“看成是‘人’的自我異化過程”,實際上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它用後來階段的普通人換置了過去階段的人,把整個歷史異化成了意識的過程。
(四)“個人力量(關係)由於分工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從頭腦裏拋開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並消滅分工來消滅”,共產主義所實現的個人對異己力量的重新支配,具有明確的經濟內容,而並不是什麼“類的自我產生”過程。
作者的認識在這裏走了一個之字形。從表面上看,肯定個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只能在具體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從事自我創造(參看《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使“主體”重新被取消。但實際卻並非如此,他是站在新的認識角度來看待“主體”和“主體”異化形式間的對立,通過引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概念,用歷史發展的觀點把二者統一了起來。
在《費爾巴哈》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闡述就體系來講,是第一次確立,但是它的某些範疇和範疇間的聯繫,像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國家和法與市民社會的關係等等,都是已經形成的東西。沒有形成的主要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交往)這一對範疇,以及社會經濟形態(所有制形式)演進序列的概念。正如巴加圖利亞所已經指出,這些範疇和概念是在《費爾巴哈》章中第一次被確立。
為什麼上述範疇和概念只是在《費爾巴哈》章中才突然出現?這個問題是比較令人費解的。我們認為它很可能是在馬克思於布魯塞爾時期寫成的另一著作《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已佚)中做了必要準備。該書在寫作時間上略早於《德意志意識形態》而相互又有交錯,在思想水準上應當同步相應,正像巴黎時期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聖家族》的關係一樣,是姊妹篇。其內容雖已無從瞭解,但我們可以估計,馬克思正是在該書寫作中對唯物史觀的框架結構和術語進行了提煉。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交往)這一對範疇的出現,對於上述“人”的討論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藉助了這對範疇,馬克思和恩格斯才為社會歷史現象的發生原理找到了終極性的原因説明。他們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一原生層次的矛盾去説明其他各種派生層次的矛盾。這樣,作為主體活動形式的“勞動”與“勞動”的異化形式(與“勞動”相對立的勞動產品、生產行為和社會關係)就不再處於非歷史性的僵死對立中,而是成為一種具有確定客觀內容和可以測度其變化的生動轉化過程。“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人與環境的任何一方都是歷史形成的結果。即使“異化”現象的否定作用,現在也可以通過由分工包含着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以及其他一切派生性質的矛盾得到確切説明,表達方式被整個地改造了。
在《費爾巴哈》章中,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直接有關,作者使用了“物質生活的自然基礎”這一概念。
馬克思恩格斯説:“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他們認為,雖然人類自身生理特性(包括種族差異)及各種自然條件的研究是自然科學(如生理學、體質人類學、地質學、氣象學等等)的對象,而不是社會歷史科學的對象。但歷史研究卻“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也就是説,社會與自然,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它們的中介聯繫對於社會歷史科學是不可缺少的前提。
與這一思想相應,作者還提出了“兩種生產”、“兩種關係”和“兩種工具”的理論。他們把“生活的生產”區分為“自己生活的生產(通過勞動)”和“他人生活的生產(通過生育)”;把人們的關係,區分為“一方面是自然關係,另一方面是社會關係”(案:“自然關係”指血緣組織)。關於生產力,他們也從廣義生產工具的概念(包括勞動對象),將它區分為“自然創造的生產工具和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兩種。
我們都知道,“兩種生產”和“兩種關係”説後來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曾經再度出現過。過去,蘇聯理論界出於膚淺的理解,曾錯批過這一理論。他們根本不懂這一理論是唯物史觀整個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費爾巴哈》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還不瞭解“家庭”這一概念的科學含義,仍然把家庭看作是歷史上唯一存在的人類血緣組織形式(這一錯誤也見於《資本論》),但他們用“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係”對早期人類社會中血緣組織所起作用的估計,卻是後來由《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用民族學材料驗證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劃分貫穿着一個共通思想,即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一個從“自在”到“自為”的過程。人對自然的依賴程度與生產力的發展成反比,生產力愈不發展,自然賦予社會的規定和制約就愈強,反之,則是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作者將這一矛盾現象稱之為“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這一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它使我們有可能對人類生產方式的進步、社會組織形式的進步以及生產工具的進步提出基本的趨勢性估計,從而揭示出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
最後,我們看到,在《費爾巴哈》章中,作者不僅提供了一種社會歷史現象發生原理的結構性説明,而且還引進了社會經濟形態演進序列(“所有制形式”)的概念。關於這一概念的含義,第二節已經做了必要説明,這裏應當指出的只是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和作用。我們認為,它並不是根據一般文化變遷或其他歷史事變而作出的歷史分期。這種分期(如矇昧、野蠻、文明;古代、中世紀、近代)在作者以前早已流行。他們並沒有提出新的分期,而只是對這些分期做了必要的經濟説明,指出這些不同的歷史時期是一定“所有制形式”即一定社會經濟組織形式發生變遷的結果。它類似於地質的形成過程,“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類型”。這種社會形態序列的“迭壓關係”也是一種有規律的發生過程。它是通過社會層次的“內部構造運動”而形成的。因此,在內容上是以上述發生原理作為背景和根據的。
社會經濟形態演進序列的概念,在《費爾巴哈》章中是以大量歷史實例經過概括總結而敍述出來的。除去前資本主義的三種“所有制形式”,作者重點對資本主義經濟史即“市民社會史”作了分階段的詳盡説明,從中探討了共產主義的實現條件問題。雖然,這些研究還僅僅是初步的,以晚期著作衡量還有不少缺點,但它已越出哲學—人類學範圍的追溯,向實證歷史科學的廣闊領域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歷史的生動場景終於在我們眼前揭開了它的帷幕。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1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四、與晚期表述的比較
《費爾巴哈》章是列寧逝世後才第一次公佈於世的馬克思恩格斯佚稿。在《費爾巴哈》章發現以前,人們一直都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晚期著作中的有關提示來了解唯物史觀。
這些提示敍述簡短明晰,似乎極易理解,但事實上人們卻往往對它存在不少誤解。例如有人懷疑,馬克思是否真正有過一個經過詳細制定的歷史理論,也有人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僅僅是以強調經濟作用為特點的某種普遍公式。
對這類誤解,恩格斯在其晚年書信中,列寧在其與民粹派論戰的著作中均做過澄清。他們指出:唯物史觀並非可以到處套用的公式而僅僅是用以指導實際研究的方法,這一方法最好地體現在馬克思的實際研究結果上。這些當然都很正確。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唯物史觀的產生時間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人們在完全不瞭解這一發現的原始內容和產生背景,僅憑上述提示,要想洞悉作者晚期研究結果中隱含着的研究方法,並不總是能夠如願以償。相反,正如以往的研究所表明,這類帶有方法性質的東西,正是馬克思晚期著作中最難把握的地方。
人們在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常常會得出與作者寫作初衷恰相反對的理解。他們在作者自認為最好體現了其方法的地方卻看不見方法,而在作者僅僅提示其方法的地方又忽略了實際研究本身。這種在以前幾乎是經常發生的錯覺,現在看來,在一定程度上與人們對馬克思晚期著作與早期著作的聯繫缺乏瞭解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先對這一聯繫作一概括説明:
首先,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區別於空想社會主義,就在於它並不是以某種理想社會的構想為內容,而是以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科學論證為內容。因此它本身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的一個獨立組成部分,而是以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説這兩大發現為基礎的理論體系本身。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説既是構成馬克思主義學説的組成部分,也是測量馬克思主義形成階段的兩個基本標誌。馬克思的第一個發現形成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第二個發現形成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這是劃分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基本時間界限。
馬克思早期著作,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起源地。過去,人們把馬克思與黑格爾哲學母體的聯繫,以及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內涵,看作是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謎”,這個“謎”的謎底其實就包含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在這一時期裏,馬克思雖然同時結合着與“三大來源”有關的多方面研究,但最大創穫是他首先發現了與德國古典哲學對立的唯物史觀,並同恩格斯合作詳細制訂了它。這一發現的意義在於:(1)它回答了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青年黑格爾派最終未能解決的問題,因而用間接的方式最終克服了黑格爾哲學本身;(2)它把黑格爾哲學從實證科學的領域、特別是歷史領域驅逐出去,從黑格爾哲學中拯救了“邏輯和辯證法”(是繼承而不是發現),給後者提供了一種新的起點。照恩格斯的説法,這兩點也就是“德國古典哲學終結”的含義。
在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為了“自己弄清問題”的哲學批判已經結束,整個研究轉向實證領域。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馬克思寫成的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是他的兩組經濟學作品:(1)《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與《政治經濟學批判》;(2)《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與《資本論》。通過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制訂剩餘價值學説,馬克思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奠立了第二塊基石。在這一時期裏,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史觀廣泛應用於各種實證性的研究課題,由這些研究的結果得到輝煌驗證。恩格斯曾舉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資本論》二書作為應用唯物史觀的範例。這兩本書,前書側重政治事變的分析,後書側重經濟現象的分析,代表了唯物史觀的最高成果。但是在這樣一些文獻中,被應用的唯物史觀方法已由“顯”而“隱”,方法本身已經滲透到細節當中,與研究結果難以區分。而作者在某些場合下就這一方法所做的提示,也由“詳”而“略”,變得濃縮起來,形成我們這裏所説的唯物史觀“晚期表述”。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與《資本論》書影
下面就讓我們來比較一下這些晚期表述與《費爾巴哈》章的異同。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晚期表述中,馬克思於1859年寫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是最早和最有代表性的一則。
在這一序言中,馬克思把唯物史觀的內容區分為兩個方面:
(1)靜態的或結構性的描述。作者對歷史現象作了高度概括,從中抽象出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這樣幾組範疇,並強調指出“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決定關係。其結構層次如下:
(2)動態的或歷時性的描述。作者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引起社會革命。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上層建築也會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變革的終極原因並不存在於意識之中,而存在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衝突,導致一種社會經濟形態被另一種社會經濟形態所代替,由此形成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序列(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以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消滅)。
我們若把這一表述與《費爾巴哈》章做比較,可以看出它們在內容上並無實質不同,但它們的論述角度和方式卻有許多差異:
第一,這一表述寫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中,是附屬於該書的研究對象,作為該書研究方法的提示而出現,而《費爾巴哈》章卻是把唯物史觀當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對立物而提出,不是結合着某一特定的研究對象,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外觀。
第二,這一表述異常簡短,語言凝鍊含蓄,只限一般方法,不涉及具體對象,而《費爾巴哈》章卻包含着許多結合歷史實例的發揮,並對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和共產主義的實現條件做了詳細討論,使篇幅拉得很長。
第三,這一表述具有條理明晰、形式整飭的特點,而《費爾巴哈》章卻是根據批判的需要從不同角度寫成,缺乏這種形式整齊的結構。許多針對施蒂納與費爾巴哈的爭論而對“人”所作的討論也是這一表述所沒有的。
第四,這一表述的術語含義比較確定,不像《費爾巴哈》章的術語往往具有雙關性。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表述形式和《費爾巴哈》章相比,術語變化很明顯。但我們在該書草稿《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當中仍然可以看到《費爾巴哈》章所使用的許多早期術語的痕跡。
《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是馬克思經濟學觀點形成的代表作。在該手稿的《導言》當中,作者對政治經濟學的廣義研究對象(生產、消費、分配、交換)和一般研究方法作了交待,後者包括了邏輯方法(從黑格爾那裏繼承來的)和歷史方法(馬克思發現的)兩個方面。《導言》第4題標題:“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關係。法的關係。家庭關係”,顯然是作者打算用來敍述他所採用的歷史方法即唯物史觀的一個寫作提綱。另外,作者在手稿《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一節中對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式進行了探討。它們仍保留了《費爾巴哈》章中的這樣一些概念和術語,如以“生產資料”為“生產力”,以“生產關係”與“交往關係”並列,用“所有制”表示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等等。可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表述只是在對上述手稿經過仔細加工之後才最後得以定形。這種加工只是屬於最後的形式加工。
自1859年以後,關於唯物史觀的闡釋基本上都是出自恩格斯之手。這類文獻主要有:
(1)《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8月3—15日);
(2)《卡爾·馬克思》(1869年7月28日);
(3)《德國農民戰爭》第二版序言(1870年2月11日左右);
(4)《卡爾·馬克思》(1877年6月中);
(5)《反杜林論》(引論:一;第一編:九至十一;第二編:二至四;第三編:一)(1876年9月—1878年6月);
(6)《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三)(1880年1—3月上半月);
(7)《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本初版序言(1882年9月21日);
(8)《卡爾·馬克思的葬儀》(1883年3月18日)〔《選集》改名為《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9)《共產黨宜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3年6月28日);
(10)《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1884年3月底—5月26日);
(11)《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德文第三版序言》(1885年);
(12)《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四)(1886年初);
(13)《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
(14)《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序言(1888年2月21日);
(15)《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16)《致約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17)《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18)《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1892年4月20日);
(19)《致弗蘭茨·梅林》(1892年9月28日);
(20)《致弗·雅·施穆伊洛夫》(1893年2月7日);
(21)《致弗蘭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
(22)《致瓦·博爾吉烏斯》(1894年1月25日);
(23)《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1895年3月6日);
它們可以大致區別為四類:(甲)書評、序言、導言類:(1)(3)(7)(9)(10)(11)(13)(14)(18)(23);(乙)傳記類:(2)(4)(8);(丙)插敍類:(5)(6)(12);(丁)書信類,(15)(16)(17)(19)(20)(21)(22)。其中除(丙)類篇幅略長外,其他多屬短篇或偶然涉筆。
上述四類文獻,除(乙)(丙)兩類純屬對馬克思學説的一般性介紹之外,其他大多都是針對特定的研究對象和問題而寫。它們雖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形式相仿,但仔細比較也有許多不同。例如《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就是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序言》就是從如何觀察政治事變的角度寫的,並不拘於一定的格式。
馬克思恩格斯的晚期表述經常是隨研究對象和針對問題的不同而變換其敍述角度與方式。它們往往都能溯源於《費爾巴哈》章,從中找到相似表述。因此,將二者加以對比和銜接,將有可能再現唯物史觀思想發展的生動過程,它是一般教科書所不能代替的。
在上面的敍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晚期著作中方法論與研究結果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正是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間關係的縮影。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這一點從唯物史觀本身的歷史可以得到最好的證明。
五、結語
《費爾巴哈》章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但是這部著作卻並不是一部一般的早期著作,而是具有承前啓後作用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它標誌着馬克思的第一個偉大發現(四十年代的代表性發現)的形成。
關於《費爾巴哈》章中唯物史觀思想的成熟程度,我們的基本估計是:
(一)它在內容上(各主要概念的形成和邏輯體系的建立)與晚期表述基本上是一致的。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説過,馬克思在1845年春已經把唯物史觀思想整理出來,“並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的敍述(案:指恩格斯本人的唯物史觀表述)中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説明了。”可見他們在1845年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已相當成熟。
(二)它與晚期表述在術語形式方面存在差距。但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仍大量保存早期術語,只是寫進“序言”,才換用了新的術語,變化完成的很容易,可見這一差距是非本質性的。
(三)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序言中曾經説過,
《費爾巴哈》章並“沒有寫完。已寫好的一部分是解釋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個解釋只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麼不夠。在舊稿裏面對於費爾巴哈的學説本身沒有批判;所以舊稿對幹我們現在這一目的是不適用的。”我們理解,恩格斯所説的後一方面,主要是指《費爾巴哈》章缺乏關於該章對象的正面批判(但並不是一點也“沒有批判”),因而對寫作該書説來不便取材(它實際更像全書導言)。這與當時作者唯物史觀思想的成熟與否無關,有關的實際上是前一個方面。《費爾巴哈》章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不夠(在歷史知識的其他方面也有許多不足,如關於史前社會和家庭的認識),這一點以晚期著作衡量是可以肯定的。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思想並不是一個僵死封閉的體系。它恰恰是在後期的應用中獲得充分發展,併為任何有益的開拓留下了足夠的“餘地”。
“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羣出眾”。 這也許就是導師給我們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誨了吧!
寫於1983年馬克思逝世紀念日
補記
我只屬於我生活過的時代,既不因出生太晚“前不見古人”而嚎啕大哭,也不因出生太早“後不見來者”而涕泗橫流。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書,簡稱“代書”。
馬克思的書,就是屬於“代書”。
這種書,當年印得很多,讀的人很多。很多人讀它是為了引它,引它是為了裝門面。其實,認真讀過他的書,人並不太多。
現在,情移勢轉,革命已成古董,馬克思主義已成古董,馬克思的書,已經沒人讀。對很多人來説,讀他的書,甚至是一件羞於啓齒的事,讓人覺得你怎麼這麼落伍。
但我讀過,認真讀過,一點兒都不慚愧,一點兒都不後悔。
因為馬克思主義畢竟是19世紀最有影響的一大思潮,波瀾壯闊,長達160年。我見證了它的高潮,也見證了它的退潮。這是我們那一代人不能忽視的讀物。
《共產黨宣言》寫得多好!
《資本論》的序跋和開頭寫得多好!
即使對現在也仍有啓發。
你想了解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嗎?一定要讀他的早期手稿。
你要讀他的早期手稿嗎?一定要讀《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
《費爾巴哈》章是唯物史觀的原始表述、經典表述,《共產黨宣言》之前,最重要。這一手稿,第二國際的領袖沒看過,第三國際的領袖也沒看過,[2]很多人都以為這個手稿早就不存在。只是到了1924年,它才終於露面,1932年才被少數學者注意。
論名氣,這部手稿沒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大。冷戰時期,後者因“異化”而出名,因解構馬克思主義而出名,影響比它大得多。
但1966年以來,事情越來越清楚,對馬克思本人來説,毫無疑問,它比《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重要得多。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的回憶是最好的證明。他多次提到這一手稿。他明確説,唯物史觀是成於1845年春,是成於這一手稿,卻從未提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馬克思講得多清楚呀:
哲學家們在不再屈從於分工的個人身上看到了他們名之為“人”的那種理想,他們把我們所闡述的整個發展過程看作是“人”的發展過程,從而把“人”強加於迄今每一歷史階段中所存在的個人,並把它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