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時代:我愛工作,加班使我快樂_風聞
夙兴夜寐刘沫沫-2018-12-17 09:06
來源:微信公眾號“鳳凰網讀書”
你,加班了嗎?
年末,所有人都忙得不要不要的。
睜開眼睛就工作、經常加班到凌晨、週末不休息是常態,“事情幹不完”、“老闆催得緊”、“為了年底績效”、“大家加班我也得加”是原因。前幾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佈的《時間都去哪兒了?中國時間利用調查研究報告》顯示:2017年我國勞動者超時工作(淨工作時間大於8小時)相當普遍,超時工作率高達42.2%。
年末,購物盛宴也安排着滿滿當當。
“雙十一”、“黑五”、近日的“雙十二”輪番上演,人們一邊高喊“搶錢啦”一邊心甘情願地消費着。雙十一”毫無懸念地再創記錄:“雙十一”期間全國網絡零售交易額超過3000億元,同比增長26.9%,遠超市場預期。在這樣的消費環境下,為了得到想要的東西,為了填補存款、貸款和花唄的大洞,也就只有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已經對超負荷工作有所察覺,但將其歸罪於企業和制度並不能使時代和個人免責,正如生產和消費就是現代社會上並蒂盛開的兩朵,沒人可以只取一端。
在日本森岡孝二教授的《過勞時代》裏,信息的無界化、被消費所改變的僱傭勞動均在這場被他稱為“社會性災難”的過勞現象中發揮作用。當我們從工作方式的角度重新審視以服務和方便為賣點的信息手段和消費理念時,會發現過勞不再是年末、或者上班族的專有現象。
— 過勞時代 —
是指高度競爭成為超越個體選擇的時代大背景,加班常態化的”過勞“成為一個時代的特徵,而過度加班成為導致職場年輕人過勞死的重要原因。
有資料顯示,中國每年的過勞死人數已達60萬人,已超越日本成為”過勞死“第一大國。
——《中國社會保障》2017年01期
1
-上世紀的預測全失敗了,工作依舊如影隨形-
在信息時代,特別是互聯網時代,按理説,電腦、手機等新型通信技術的應用和普及,理應會加快業務處理速度並縮短工作時間。
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曾經做出一個有名的預測:到2030年,人們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小時。1964年,美國《生活》雜誌分兩期探討美國社會所面臨的“真正威脅”,提出未來的趨勢,將是人們有過多時間用於休閒娛樂。在“有閒階層”的系列文章中,就連一些中立的預測者也認為,“自動化正在使我們的經濟向着每週工作30小時的方向發展。”
事情的發展背道而馳。不僅在首先提出“過勞死”(karoshi)的日本,在美國、英國、德國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過勞和過勞死都成為職場中的重大問題。此外,假期和週末也充斥着工作。螞蜂窩旅行網曾發佈《中國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報告2017》,指出88%的白領都需要在旅行過程中處理工作。
可見,當電腦、手機和電子郵件不僅作為社交工具,也作為工作手段時,它們帶來的未必都是方便。
自從有了通信工具,家裏家外都成了職場。步入工作的白領,很難説出很喜歡手機和電子郵件這樣的話。那裏等待她們的是吉爾·弗雷澤在《令人窒息的辦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國人》一書中描述的世界:
吉瑪是一名負責市場營銷的女性管理人員。她每天下午5點離開辦公室,卻並非為了享受5點後的下班時光。因為家裏有小孩,所以只能5點下班。但是,即使離開了辦公室,工作也還沒結束。
乘車的時候,她要往自己的辦公室打電話,還要用手機一個一個回電話。回到家,吃完晚飯,在孩子寫作業或者看電視的時候,要查看語音郵件,再回很多個電話,還要經常處理與工作有關的傳真。在投資銀行工作的丈夫也常常坐在家裏的電腦前,在睡覺前工作好幾個小時。
如今,在以電腦和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術不斷變革的背景中,以時間為核心的競爭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受益的只是工作效率,手機、電話、電子郵件等信息渠道模糊了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的界限,造成工作無孔不入的情形。
森岡孝二對此解釋道:
新型信息通信技術是減輕、省去工作量的強有力的工具,然而它同時也加速了業務運轉、加劇了時間競爭,商品和服務種類多樣化,經濟活動出現了無國界和24小時的趨勢,所以,不論從整體上還是就個人而言,工作量並未減少,反而是增加了。
2
-不是威逼,而是利誘,工作是為了買得起-
在生活水平高、媒體發達的大眾消費社會,人們為了滿足不斷膨脹的消費慾望,或以消費競爭來顯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必須得到更高的收入,或者找到工資更高的職位,因此便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加大勞動強度。
朱麗葉·斯格爾在《過度勞累的美國人》一書中,對美國長時間工作的實際情況和原因進行討論,指出“工作與消費循環”(work and spend cycle)也是過度勞累的重要原因。
從生產的對立面——消費,不難理解這一循環過程。隨着收入水平增加的,還有消費慾望的無限膨脹,掙了錢就花,為了消費而過勞,這就是斯格爾説的“工作與消費的惡性循環”。
最近,這樣的惡性循環直接表現為:購物已從實用性的家務瑣事,升級為全民性的狂熱。2018年,是“天貓雙十一購物狂歡節”的第十年,11月11日已經成為所有人一年裏約定俗成的重要節日,慶祝方式也整齊劃一:買買買。
某位女大學生:我吃了幾個月的泡麪,為了買多一些高級化妝品。
一位職場白領:雙十一,我把上半年工資花了。
一名購物癮者:我還透支了接下來幾個月的工資。
雖然這些案例略顯極端,不可否認的是,從五千萬到2135億元,交易額持續大幅攀升所凸顯出的巨大購買力。
同時,消費具有攀比性。凡勃倫在1899年的《有閒階級論》仍舊、適用於今天。相比他所生活的時代,不同之處在於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競爭消費的行列。
當今社會,人們進行社交和競爭的場所從狹隘的鄰里拓展至職場社會和健身房、美容院及各種為娛樂修建的商業設施:
特別是隨着大量女性進入勞務市場,攀比消費之風擴大到社區外部,消費競爭被觸發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多。不僅如此,與從前相比,模仿他人、與人攀比已成為一種交流方式,與名牌意識相仿,這些行為變成了集中顯示自我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手段。
森岡孝二 《過勞時代》
另外,在購物狂熱中,債務是密不可分的部分。在沒有立刻付現的限制下,購物變得更加容易,信用卡、分期付款和網貸的誘惑讓很多人入不敷出。在此消費環境下,即使不能立刻賺到足夠多的錢,也可以透支將來的收入。但這意味着,需要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去填補那些空缺。
3
-寫字樓、快遞、便利店……無人不深陷其中-
中國人加班歷來瘋狂。
在滴滴發佈的《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中,京東以平均23點16分的下班時間,奪得中國最“狠”公司稱號。在高德地圖發佈的《2016年度中國主要城市交通分析報告》中,華為以每日人均加班時間3.96小時的成績,成為中國企業中的“加班王”。
從信息無界化的思路出發,夜晚燈火通明的寫字樓裏,在逼仄的隔間中不斷敲擊着鍵盤的“寫字樓民工們”,理應是“過勞主力”。工作日晨會、下完以後開晚會、過年過節要排班、假期也需要和高層時刻保持聯繫。工作不全是鬥智鬥勇,拼的還有體力和耐力,只有耐得住寂寞、熬得了通宵的人,才會有更好的業績。
在“工作-消費”的循環模式下也如此,斯格爾直接指出:“隨消費而來的過勞是中產階級的痛苦。”為了追求和維持更高標準的生活方式,必須要加班或從事額外的工作。“如果有人沒有落入工作-消費的陷阱,那不是他們不會落入,而是因為他們無力落入。”因此,一位銀行家曾説:“知道有點兒錢了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貧窮。”
事實上,低收入羣體也參與其中。從工作方式的角度重新審視以服務和方便為賣點的消費理念會發現,講求即時和快速的服務型經濟與信息化共同發展,對過度便利性的追求催生了過度的服務競爭,從而妨礙了工時的縮短。
發展迅猛的網購背後仍是體力勞動,快遞則是其中的核心。隨着網絡購物競爭日趨激烈,更多滿足顧客個性化快遞需求的服務不斷產生,如精準預定時段至30分鐘的“京準達”、能夠下班之後順便去快遞的“夜間配”、專為高端配送需求退出的“京尊達”,最快就能幾分鐘送貨上門的“閃電送”……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對外發布的《2017年中國電商物流與快遞從業人員調查結果》顯示,62.2%的快遞員平均每天工作時長8~10小時,24.46%的人工作10~12小時,12小時以上的佔13.34%。為完成每日工作量,加班加點成為快遞員的工作常態。但計件工作的勞動報酬制度,意味着他們並不會得到加班費。
與網購相似,24小時便利店的經營優勢也在於方便。便利店,顧名思義,其特點就是便利性,全年無休、從白天到晚上、從晚上到早上,正是因為那些在不同時段倒班工作、為數眾多的小時工和兼職員工,這種營業模式才能得到保障。其實,不僅便利店實行“全年無休24小時營業”制度,近年來,超市、百貨店、快餐店、餐館以及其他零售業、飲食業和服務業也大幅度延長了營業時間。
森岡教授認為,便利店的深夜營業和越來越快的快遞服務象徵着消費者對便利性的過度追求:
整個社會都要求速度,殊不知,這種服務恰恰是和安全、放心的保障背道而馳的。
4
-過勞不好,時代不壞-
每隔一段時間,人們的危機意識都會被點燃,人人自危,生活搖搖欲墜,熱情在辦公桌前冷卻、墮落、失控,不斷詮釋着“喪“、”佛“等詞語的新義項。於是,下流社會、低慾望社會、過勞社會等聳動卻合乎道理的説法,成功戳中人們心中的痛點。
但能因此徹底丟棄那些令我們時刻工作的工具、唾棄那些需要超負荷勞動的職業嗎?誠然不是,因為那就等於拒絕了這個時代。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苦熬,哪個人不是在一邊泄氣一邊努力地工作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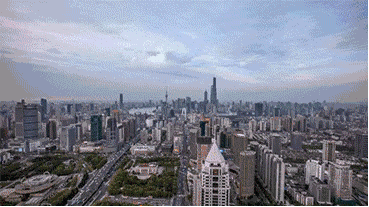
深夜十點,兩位程序猿在電梯裏相遇,一起到室外抽幾口煙,再一起回到工位;
零點,飯店經理在結算的同時,等待最後一桌顧客的離開;
兩點,外賣小哥還在給人送夜宵;
四點,出差的白領睡眼惺忪地收拾行李去趕飛機;
五點,準備回家補眠的記者和從出租車上下來的同事打了照面;
六點,鬧鈴準時響起,想到只睡了三個小時,銷售人員翻了個身;
七點,剛入職就遇到大項目、在公司睡了一宿的年輕人被酸脹的脖子叫醒;
八點,公交地鐵裏,擠滿了不敢遲到的上班一族;
……
也許有人亮出鋒芒,以“工作使我快樂”、“我從未加班”等體驗與過勞狀態劃清接線;也有人積極轉發,將一早的好心情轉為令人心悸的自嘲。
彆着急攻擊,也別懷疑自己,這也不是販賣焦慮。因為當我們與社會打成一片時,自然就會深陷其中。因此不需要着力批判勞動制度或約定俗成的規則——這些告誡是沒用的,就森岡教授自己都沒有遵守。恰恰相反,這是通過對制度和規則之外,其他原因的探討,試圖干擾我們每天在工作中的沉浸,宣泄早起晚歸的那一絲絲鬱結,然後再回到工作中。
因為在活力與疲憊並存的“過勞時代“,想要上升就要做出必要的讓渡。狄更斯幾近強辯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展現的是一種持續的歷史力量:高歌猛進的過程中必然要付出代價。只不過此時,那個代價是,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