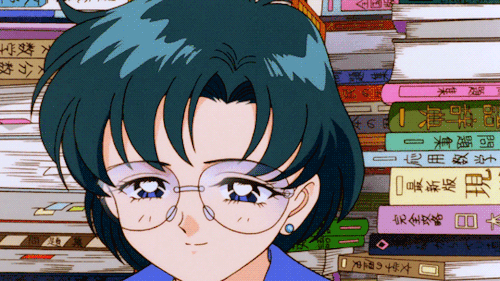男性認為性最能解決矛盾,女性則認為是情感溝通 | 2018年的10大心理學研究_風聞
KnowYourself-KnowYourself官方账号-泛心理科普与服务,美好生活从了解自我开始。2018-12-22 09:04
轉眼又到年底啦,今年我們照例為大家篩選和整理了2018年值得關注的10個心理學研究。我們在今年的最新研究中選擇了一些我們認為貼近生活的、有意義的研究來呈現,希望能對你們的生活有所啓示和幫助。

向他人展現自己的脆弱面意味着不確定、風險和真實情感的坦露,因此,暴露脆弱對大多數人來説都是一件困難的事。然而,Bruk等人通過多項實驗表明了他人對我們脆弱面的評價,可能要比我們自己的評價積極許多。他們將之稱為“美麗的混亂”效應(Beautiful Mess Effect)。
研究者們每項實驗都邀請了不同學校的大學生作為被試,被試的男女比例均接近1:1。
第一、第二項實驗從不同角度假設了若干場景(例:愛上好朋友,並對對方先説出“我愛你”),並説明了在這些情境中暴露脆弱所帶來的優劣勢。第三個實驗的情景中沒有告知被試暴露脆弱的優劣勢。
在第四個實驗中,研究者設置了一個真實場景,要求被試們在彼此面前即興創作一首歌曲。
前四個實驗中,被試們都被要求首先對“‘先説出愛’等行為意味着示弱”這個陳述進行1分(非常不同意)到7分(非常同意)評分,隨後針對“‘我’暴露脆弱時意味着展示無力”、“‘我’暴露脆弱時很勇敢”等8個陳述(正負面描述各4個)分別對自己和他人的暴露脆弱的行為進行1分-7分的打分。
實驗的結果表明,人們將暴露脆弱視為他人勇敢、有力量和令人欣賞的表現,而對自己的評價則是無力和令人討厭的——人們欣賞他人暴露脆弱的舉動,卻不願展露自己的脆弱。
第五項實驗的結果則表明了當人們評估自身脆弱性的時候,會對情景和自身做出更加具體性的分析,在評價他人時則更為抽象;而對事件越抽象的分析,就越能夠使得我們更加積極地看待事件本身。
另外,研究者發現了兩個影響對示弱行為評價的因素:空間距離的增加能夠幫助個體更加積極看待自己暴露脆弱的行為(如在離家更遠的公司犯錯);而事先處於負面情緒中(如先觀看葬禮的相關視頻引起悲傷的情緒,再暴露脆弱)則會使被試對自我暴露脆弱的評價更為消極。

這些年,一些研究者試圖尋求心理治療為患者帶來的變化與其神經系統之間的相關性。今年七月,《精神病學研究:神經影像學》刊出一篇論文,對此進行了系統性綜述,並做了相關的元分析,展現心理治療如何改變了抑鬱症患者的大腦。
研究表示,重性抑鬱的患者在接受認知行為療法(CBT)之後,從腦成像來看,他們大腦左側的中央前回活躍性降低。這一區域位於前額皮質, 與思考與反思過程相關。在情緒任務中,抑鬱症患者的這一區域更為活躍,對某些想法和擔憂有反芻傾向。所以,這一區域活躍性的降低預示着,治療的有效性體現在患者改變了這類消極的認知方式。
另一個發現是,在接受CBT或精神動力學療法之後,患者的左側前扣帶回皮質喙部顯示出更強的活躍度,這一片腦區與中心情緒處理區域緊密相連,對杏仁核的活躍程度有抑制作用。而身患重性抑鬱,人的前扣帶回與杏仁核的連接會更加脆弱,使得情緒更加強烈而難以控制。所以,心理治療的作用之一,就是讓被損傷的連接再次被建立。

以往的研究發現自尊水平較低的人,往往有着更不盡人意的人際關係。通常,低自尊者也會覺得伴侶在自己表達負面感受時給出的回應不令人滿意。有人指出,這是因為低自尊者消極的自我投射,但這項研究發現事實似乎並非如此。
Cortes等人邀請了122對本科伴侶(平均年齡22.28歲,親密關係平均2.66年)參與了在線調查。伴侶中的一方(被稱為Disclosurer)首先填寫了羅森伯格自尊量表(10-item RosenbergSelf-esteem Scale),接着回顧了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經歷的負面事件(排除了由伴侶導致的事件)、他們向伴侶透露壞消息的次數、傾訴負面情緒的方式、對方的回應情況,以及自己對對方回應和雙方互動的感受,並進行打分。
例如,伴侶面對自己的傾訴是否能做出“對的”回應、自己對回應是否感到滿意、“伴侶能多大程度上理解/尊重/專注/是個好聽眾/支持/有回應的”、“互動多大程度上強化了親密關係”等等(1分-7分表示從“一點也不”到“非常”)。伴侶中的另一方(被稱作Listener)也回答了相應的問題,例如“我能多大程度上對對方的負面情緒表示理解”等。
經過多元迴歸對比分析發現,與高自尊水平的人相比,低自尊的人整體上的確對“伴侶對他們感受的回應”更加不滿意。同時結果顯示,低自尊者及其伴侶自身對回應質量的感知高度一致——伴侶的自評也顯示,他們對低自尊伴侶的感受的回應的確不夠好,且也承認互動對雙方的關係沒有加強作用。
Cortes等人認為,這可能跟低自尊者表達負面情緒的方式有關:低自尊者更多使用間接的方式表達消極情緒;有時會淡化情緒,有時則誇大情緒;他們“並不説明到底怎麼回事,卻希望對方能夠領會自己的暗示”,這些都讓他們的伴侶更難給出他們期待的回應。
此外,相比自尊水平健康的人,低自尊者更有可能在一開始就抱有更低的擇偶標準——因為他們覺得自己“配不上”更好的。而這也讓他們想要從一開始就不夠好的伴侶身上獲得積極回應的期待落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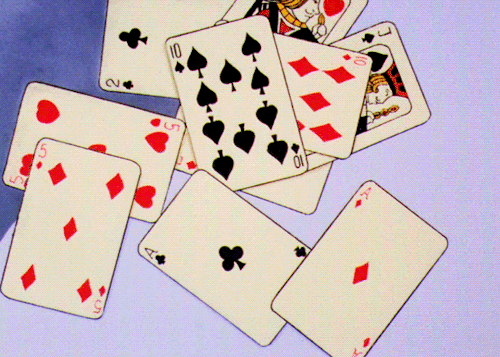

人們常常希望通過拍照來幫助自己更好地記得一件事,留下一段回憶。但實際上,拍下來會讓我們更難以記住所拍的事物。
Julia S. Soares和Benjamin C. Storm等人做了三組實驗。首先,他們在電腦上準備了一組圖像,讓第一組被試者使用Snapchat軟件對着這些圖像拍照(是一種“閲後即焚”的軟件,人們預先知道照片無法儲存),然後觀察電腦上的圖像15秒,第二組被試者拍攝照片後進行手動刪除,然後觀察預先準備在電腦上的圖像15秒,第三組則是沒有任何操作直接觀察圖像15秒。
研究者在十分鐘後對三組被試者進行對該圖像的記憶測試。結果發現,直接觀察的記憶最好,拍照和手動刪除的實驗者的記憶都更加模糊。這表明,即使人們已經知道拍下的照片無法儲存,拍照這個行為本身還是會對我們的記憶造成損傷。
研究者表示,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拍照這個行為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從而影響了我們對事物本身的觀察和記憶。此外,還有一種解釋則是認知幻覺——我們的大腦誤以為對焦,按下快門這些拍攝動作是在進行記憶,導致我們實際上並未動用真正的記憶能力,所以印象模糊。
你是否發現,伴侶爭吵之後,經常對對方道歉求和的方式感到不滿?覺得不夠真誠,或是不符合自己的心意。這可能是因為,男女之間對於和解方式本身就抱有十分不同的看法。
Joel Wade及其同事的一項研究發現,雖然男女一致認為感情衝突後,最有效的和解行為是溝通(e.g.真誠的談話)。但除此之外,男性更傾向於認為與性有關的行為(signal sexual accessibility)更有效,女性則認為與情感表達相關的行為(signal emotionalaccessibility)更有效。
研究者首先招募了74名志願者(38名女性和36名男性),讓他們根據自己以往經驗寫下5種在衝突後和解的行為方式。在男性的答案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有禮物,道歉,示好的行為(如主動做家務和恭維對方),女性的回答中則更多提到溝通和情感表達。
接下來,研究者重新招募了164名志願者(123名女性和41名男性),對第一個實驗中收集到了所有和解方法進行有效性打分。評分標準為1-7分(1分表示最沒有效果,7分表示最具和解效果)。結果發現, “溝通”、“道歉”、“原諒”、“花時間在一起”、“妥協”、“給一個親吻或擁抱”,是男性和女性都認為比較有效的幾種方式。
但,男女對道歉方式的看法也體現出了一些顯著的差異,比如男性認為性接觸是有效的和解方式,女性則認為伴侶道歉或哭泣更有效。
Joel Wade及其同事表示,這些研究差異與進化心理學的預測一致,即我們祖先過去形成的交配策略中,男性通常更關注性的機會,而女性則更多關心情感承諾。

日本立命館大學的Mario Liong和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的Grand HL Cheng通過一項新的研究指出,發送與性有關的短信(Sexting)並不一定是壞事,它還會通過促進性意識的解放使人們獲得更強的性掌控力(Sexual agency)。
有361名17~24歲來自香港的大學生志願參與了該項實驗,他們首先被詢問是否有過Sexting的經歷,這裏Sexting被定義為:通過手機或互聯網發送帶有性含義的自己露骨或裸照的行為。接着,實驗對他們自我身體監視(body surveillance)、身體羞恥感(body shame)、身體控制力(body control beliefs)和裸體舒適度(comfort with nudity)四項指標進行了評估。
結果顯示,不論男性還是女性,有過Sexting經歷的人表現出了更高水平的對自我身體的監視、身體羞恥感和裸體的舒適度。在此基礎上,Mario Liong和Grand HL Cheng還推導並論證了在發送性短信的過程中,人們會下意識地參照文化標準來監視自己的身體,從而產生相應的羞恥感,但同時也會對自己的裸體感到舒適,覺得不需要去管控自己的身材。
這意味着,Sexting能夠使人們在拍攝自己性照片的時候,進一步探索和理解自己的性特徵,從而形成主觀上性意識的解放,擺脱掉日常支配我們性慾的外部抑制力,尤其幫助年輕人培養自主的性行為的掌控力,並增強自身的性魅力。
不過,該研究沒有探討發送性短信的頻率因素,以及對不同性取向人羣的影響是否有差異。
日常生活中,幾乎每個人都有從別人的不幸中獲得快感的體驗,即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但每個人幸災樂禍時背後的心理動機卻存在差異。據此,美國埃默裏大學心理學家,提出了一個新的幸災樂禍分類:
**1.公平型,基於一種社會正義感,對社會分配不公平的厭惡。**尤其表現為集體對部分成功人士的隕落,表現出的不約而同地批判。
**2.競爭型,基於對自我評價的關注,源自惡意嫉妒(malicious envy)。**嫉妒和幸災樂禍都源於比較,前者源於向上的社會比較,與自卑有關,而後者源於向下的比較,與優越感相關聯。
**3.侵略型,基於不同羣體間的互動關係,受到組織內部身份認同感的驅動。**例如當自己喜歡的足球隊贏得了比賽,而對手球隊遭遇慘痛失利時,球迷們會因此感到格外愉悦。
研究還進一步揭示了更容易幸災樂禍的個體人羣:精神變態者(Psychopaths);具備黑暗人格特質者(包括自戀、馬基雅維利主義即唯利是圖、施虐狂);和低自尊者。
ShenshengWang等學者強調,在以上三種模式和人格特質中,一個激發幸災樂禍的核心情緒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即人們在一些特殊情境和性格變量的共同作用下,不能把遭遇不幸的人看作是人。
研究者指出,這種精神感知能力和情感共情能力的暫時喪失而產生幸災樂禍,就像一些特定的精神障礙的患者的狀態一樣。


滿意的性經歷通常讓人幸福,增強與伴侶的親密感,但是對一些人來説,性反而會讓他們悲傷和急躁,可能持續幾分鐘或幾小時,心理學家稱之為**“性交後心境惡劣”**(post-coital dysphoria,簡稱為PCD)。
之前,對此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女性羣體,JoelMaczkowiack和Robert
Schweitzer在今年6月發表了研究男性性交後心境惡劣的論文。他們在網上發起了一份匿名問卷,共有來自78個國家的1208名男性參與,年齡範圍為18至81歲,絕大部分人的親密關係持續了至少一年。
研究發現,有41%的參與者表示自己曾經歷過性交後心境惡劣,通常是間歇性地發生,20%的人表示在參加這一調查前的四周內就體驗過,且3-4%的參與者表示經常感到性交後心境惡劣,對此的描述包括:“我不想發生身體接觸,我想獨自一個人待着”“我感到不滿意,煩惱,坐立不安”“感到麻木和空虛”。
本研究沒有給出男性性交後心境障礙的確切成因,發現其與男性當時的心理壓力、童年時的性虐待及某些性功能障礙有關。考慮到發生的間歇性,研究者認為,性交後心境惡劣不像是某種性功能障礙,更接近人在性消退期的自然變化,所以他們認為這應該主要與性高潮後腦內啡及某些激素水平的降低有關。
人們常用“我倆好得跟一個人似的”來形容好朋友之間的親密,事實上,這句話可能是有一定科學依據的。
美國哈特福德大學的Sarah Ketay和她帶領的團隊研究發現,在視覺層面上,人們會把親密的朋友吸收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人們在視覺上會難以分辨自己和好朋友的臉。
他們做了兩個實驗。在第一個實驗中,24位女大學生被分為兩組後,被要求在電腦屏幕上觀看一組照片。第一組人觀看的是交替出現的、自己的和一位親密的女性朋友的單人照片,每一次屏幕上出現照片的時刻,她們需要在短短几秒內儘可能快地用按鍵作出“這是我的臉”或“這不是我的臉”的判斷。
第二組人觀看的則是交替出現的、自己的和一位女性名人的單人照片。同樣的,她們需要儘可能快地做出“這是我的臉”或“這不是我的臉”的判斷。
結果發現,比起分辨自己與名人的臉,被試們分辨自己與朋友的臉需要花費顯著更長的時間。這個結論建立在控制了長相相似程度、名人的知名度等變量之上。也就是説,人們需要更長的時間辨識自己和朋友的臉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長得更像,或是相比起名人,朋友的臉對他們而言更熟悉。
第二個實驗中增加了被試的數量。同時,這一次研究者並沒有讓被試和朋友/名人的臉交替出現,而是用修圖軟件將她們的臉與朋友或是名人結合成了同一張臉。同樣的,被試們需要做的是迅速判斷屏幕上出現的照片是否是自己的臉。結果顯示,比起自己和名人結合的臉,被試們同樣要花更長的時間去辨識自己和朋友結合的臉是否是自己。
不過,這個研究只使用了女性被試,並且樣本量很小,研究者承認這是該研究的一個較為明顯的侷限。
羞恥感讓人難堪,人們很難想到它的好處。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研究者Daniel Sznycer及其同事針對羞恥做了一項跨文化研究,來探尋羞恥感的來源及作用。
為了減少文化相似性的影響,研究者儘可能避免地理的可及性、語言和宗教的相似性,選擇了全球15個傳統的小型社會作為研究對象。他們從每個社會選出一組參與者,給出12個與羞恥相關的場景,比如“很懶惰”“長相醜陋”“不遵守承諾”等,令其假想如果一個同性別的人身處這些場景,他們覺得這個人會感到多大程度的羞愧,接着讓他們評定自己對這個人有多大程度的消極看法。之後,研究者會選出新的一組,讓參與者評定自己在這些場景中會感到多大程度的羞愧。
研究發現,參與者對這些場景的羞恥程度,與他們對身處其中的人的貶低程度非常接近。這一結果在單個社會內尤其正確,並在跨社會範圍上同樣成立。
研究者認為,在小型的、連接緊密的羣體中,人們需要彼此幫助才能更好生存。為了避免與羣體意願相違背,人們需要了解哪些行為和狀態會觸發其他成員的貶低,所以羞愧感的形成就是對此的適應性策略,減少人們只從個人想法和利益去考慮問題,以免被羣體拋棄。由於研究對象的跨文化特性,研究者認為,羞恥感來自於更普世的社會選擇,而不是文化接觸和融合的產物。